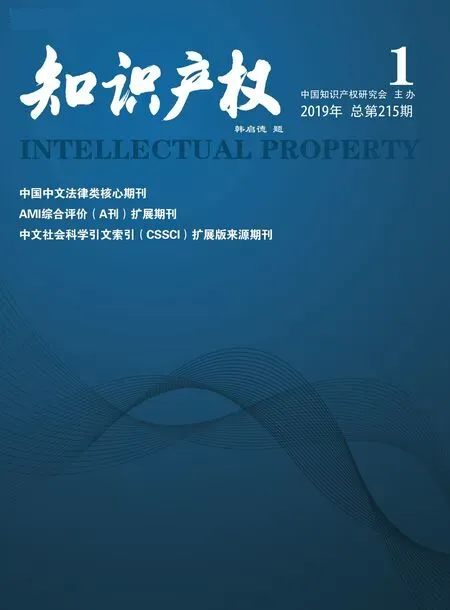“用戶生成內容”之版權保護考
倪朱亮
內容提要:“用戶生成內容”因涉及未經許可大量使用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而引起學界和實務界廣泛關注。從邏輯自洽來講,“用戶生成內容”概念界定、獨創性標準以及版權歸屬等問題是解決“用戶生成內容”版權問題的前提與基礎。傳統版權許可制度在以社會公眾為作品使用主體的“用戶生成內容”的適用上陷入困境。“用戶生成內容”作為社會公眾參與文化的方式具有主動性,不能完全依賴于抗辯性的合理使用制度解決作品事先許可的需求。版權法應當保證版權人退出使用的選擇,同時增設能區分對待“用戶生成內容”中業余者與專業者差異的法定許可制度內容,實現版權人與作品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促進文化繁榮發展。
“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Content,以下簡稱UGC)①User-Generated-Content有不同的中文翻譯,有學者將其譯成“用戶產生內容”,也有的譯為“用戶創造內容”。在代表性的文章中,前者翻譯可參見胡開忠:《論重混創作行為的法律規制》,載《法學》2014年第12期,第89頁;后者可參見熊琦:《“用戶創造內容”與作品轉換性使用認定》,載《法學評論》2017年第3期,第64頁。本文認為,User-Generated-Content翻譯成“用戶生成內容”更符合其概念與內涵,緣由將在本文第一部分予以闡述。是近幾年版權法學界較為關注的話題。之所以成為熱門話題,是因為“用戶創作內容”依托于新型技術而不斷影響作品的使用與傳播,進而引發版權法領域的諸多問題——這與始終繞不開的“技術發展與版權演進緊密相關”的規律相一致,②Maria Lilla Montagnani, A New Interface Between Copyright Law and Technology: How User-Generated Conten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Online Distribution, 26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719, 721 (2009).并且“用戶生成內容”已經成為人們交流思想、塑造文化、社會生活的主要方式,它使人們置身于“全民參與文化”的創作浪潮之中。③在我國“互聯網+”國家戰略催生了一大批新媒體平臺,如微博、快手、抖音等已成為當下主流的信息互動傳播媒介,并呈現“用戶生成內容”之趨勢。2018年,快手的月活躍用戶已超過2億、抖音與火山小視頻則分別超過1億,呈現“全民短視頻”現象。參見《億級新用戶紅利探秘:抖音&快手用戶研究報告》,載http://tech.ifeng.com/a/20180409/44942798_0.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5月16日。從現有“用戶生成內容”的學術文獻來看,絕大多數研究聚焦于“用戶生成內容”的性質④Mary W. S. Wang, “Transformative” User-Generated Content in Copyright Law: Infringing Derivative Works or Fair Use?, Vol.11:4 Vanderbilt J. & Tech. Law 1075, 1075 (2009);熊琦:《“用戶創造內容”與作品轉換性使用認定》,載《法學評論》2017年第3期,第64頁。、合法性分析⑤胡開忠:《論重混創作行為的法律規制》,載《法學》2014年第12期,第92頁。、理論基礎⑥朱劼:《共享經濟視域下重混創作版權法律制度的構建》,載《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第128頁。以及圍繞合理使用為中心的對策⑦Joanna E. Collins, User-Friendly Licensing for a User-Generated World: The Future of the Video-Content Market, Vol.15:2 Vanderbilt J. &Tech. Law 407, 407 (2013);梅術文:《從消費性使用視角看“微博轉發”中的著作權限制》,載《法學》2015年第12期,第101頁。等問題,但對“用戶生成內容”的內涵與版權歸屬,以及如何促進而不是規制“用戶生成內容”等問題少有涉及。鑒于概念界定是分析合法性、侵權判斷和合理使用等重要問題的前提與基礎,同時為避免出現大多數現有研究跳過“用戶生成內容”是否為作品這一基礎問題,直接默認“用戶生成內容”屬于版權法上的創作的做法,無法實現邏輯自洽。本文從“用戶生成內容”的概念界定入手,分析并非所有“用戶生成內容”都屬于版權法意義上的創作行為,進而展開版權法該如何保護并調整“用戶生成內容”這一社會現象。
一、“用戶生成內容”法律概念之界定
在立法上,各國版權法對UGC這一現象并未予以明確界定。在學理上,UGC概念界定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下定義式,認為UGC主要指互聯網用戶在線創作、傳播作品的行為,⑧Daniel Gervais, The Tangled Web of UGC: Making Copyright Sense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Vol.11:4 Vanderbilt J. & Tech. Law 841, 842(2009).或者,指由非專業從事作品創作的用戶生成、以網絡為主要傳播媒介的作品。⑨Vickery G. & Wunsch-Vincent S., Participative Web and User-Generated Content: Web 2.0, Wikis and Social Networking,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第二,列舉式定義則通常以UGC中最主要的重混(Remix)為例來闡述UGC。所謂重混乃指對已有的文字、音樂、美術等作品進行摘錄、合成而創作出新作品的行為。⑩Thomas W. Joo, Remix Without Romance, 44 Conn. L. Rev. 415, 416 (2011).同樣,盡管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教授在其書中并沒有界定重混,但其認為重混創作屬于版權法上的轉換性行為。11Lawrence Lessig, Remix: Making Art and Commerce Thrive in th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p255 (2008).那么,UGC究竟是版權法上的作品,還是創作作品的行為,亦或兩者都不是呢?本文認為,兩種界定方式并沒有完全反映UGC的全部內容,應當從UGC內部構造角度,逐一分析UGC的構成,進而得出UGC的整體含義。
在詞組上,UGC是由user、generated與content構成。首先,本文認為在UGC語境下的user具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利用數字與互聯網技術并具有一定程度網上成癮性的用戶;其二,是指不以此為職業謀生的業余者。有學者認為,將UGC中的user定性為業余者并不準確。人們習慣性地采用主體對比法,將UGC的參與者與專業制作流媒體的商業媒體或機構相比較,認為UGC中user在制作水平上應被定性為專業者的反面。但是實際上,UGC參與者與專業制作者之間并無明顯界限,應當以“正式與非正式因素”標準(formal and informal elements)來區分UGC中參與者身份性質。12Ramon Lobato, Julian Thomas & Dan Hunter, Histories of UGC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edia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draft),October 2010, electronic copy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749803.本文認為,UGC中user的界定應以是否以此為謀生手段為標準更為妥當。從媒體傳播學的角度,“業余”與否的標準在于作品分享是否限于周圍朋友和熟人的范疇,但是在UGC盛行的環境下,“業余”的典型標簽卻已消失,這些作品不再只是家庭范圍內的消遣,他們的目標對象已變成熟人圈以外的人群——社會公眾。13[美]亨利.詹金斯著:《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杜永明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28頁。更重要的是,UGC的參與者并不靠以小成本甚至零成本制作出商業品質或接近商業品質的內容來謀生、營利。因此,在這一點上,他們仍是業余的。UGC平臺為業余者提供了一個創新的場所,他們可以借此試水創作屬于他們的想法或者能夠完全表達出個人情感的內容,而傳統媒體的素材,包括已發表的音樂作品、電影作品和美術作品等,都成為他們靈感的來源。在這樣的環境中,UGC的內容已經不再被認為只是簡單地從傳統媒體衍生出來的產物,而是必須把它本身當作公開的、免費分享的結果并且能夠被公眾進行加工的對象。因此,UGC中的user乃是指借助互聯網與數字技術參與網絡活動且不以所制作內容為生的用戶。
其次,UGC語境下generated包含版權法意義上的創造行為與非創造行為。比如用戶在生成內容時摘錄了他人的作品,如果摘錄的數量在他所生成的內容中所占的比重小,而且不涉及所引作品最核心部分,那么該生成行為極有可能屬于合理使用范疇的創作行為。但是,如果將他人的作品予以大量摘抄,那么該行為可能不屬于合理使用,而是一種復制行為。因此,將generated翻譯成“創造”使之與created相對應并不妥當,縮小了generated的范圍,盡管有些情形下generated的最終內容屬于版權法所調整的創造性作品。14有些學者將“generated”翻譯成“創造”是基于將UGC界定為“在已有作品上增加新內容的方式在線創作和傳播的行為”,然而,“增加新內容”并不等于版權法意義上的創作,它還包括機械性添加與復制行為。本文認為將generated的翻譯為“生成”,除了體現具有版權法意義上的創造行為之外,還具有非創造行為與行為結果等含義。從生成行為本身而言,它不同于簡單的上傳或下載、也不同于一板一眼的復制行為,它是混合著復制、上傳、下載以及創造等多種行為動作;從行為結果而言,它所強調的內容也正好體現在content上。盡管content經常與版權法語境下“作品”一詞混用,但是content不同于“創造性作品或內容”(creative content)。如果將content等同于創造性作品,意味著用戶生成的content都屬于版權法上的作品,且滿足獨創性的要求。但這與實際情況不符,因為用戶生成的結果既可以是創造性的(creative)也可以是非作品(not copyrightable),比如網絡用戶只是簡單地將兩首歌曲剪切混在一起,沒有任何編排上的選擇,由此生產的內容并不具有創造性。因此,將content翻譯成內容而不是作品或者具有創造性的內容。綜上所述,UGC應翻譯為“用戶生成內容”更為合適,它是指網絡用戶在網絡平臺上通過創造性或非創造性的行為生成相應的內容。
二、“用戶生成內容”版權之歸屬
(一)“用戶生產內容”獨創性判定標準的審視
通過第一部分的闡述,用戶所生成的內容既可以是具有創造性的作品,也可以是非創造性內容。判斷是否構成作品,核心要件是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在獨創性判斷標準上,版權法體系對作品的獨創性要求不高,一般來講普遍低于著作權法體系。早期英美法系版權法中判斷“獨創性”的標準被形象地稱為“額頭流汗”標準(sweat of the brow),該標準強調的是內容之所以被視為作品并非因為它體現了作者的智力創造,而是它具有價值并凝聚了獨立和辛勤的勞動,哪怕是單純的體力勞動或者非常簡單的腦力勞動。15王遷著:《著作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但是,“額頭流汗標準”畢竟過于簡單,且被認為不符合《伯爾尼公約》有關“智力創造”的要求、違反該公約的實質精神而備受批評。美國在后來的案件中逐漸形成了比“額頭流汗標準”高,但依舊相對“低門檻”(low threshold)的判斷標準。在經典的費斯特出版公司訴郊區電話服務公司(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一案16See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499 U.S. 340, 363 (1991).中,法院認為盡管版權法未明確獨創性的含義,但該案中費斯特公司出版的電話號碼簿并不滿足版權法所要求的“少量”(modicum)創造性標準。盡管如此,美國其他法院在審理其他案件中還是逐漸采納了“最低限度標準”(minimis amount)。這與著作權法體系相似。按照德國著作權法上的學說與判例,作品必須具備一定的創造水準來超越那些人人可以制作的、普通的東西,甚至規定必須達到某種最低的創作水準——“小硬幣標準”。它強調獨創性不是指主觀方面,而是客觀方面(從外部看起來)的獨創性。17[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最低限度標準”或“小硬幣標準”,對于保護版權人免受來自競爭對手的剽竊之傷害來說已經足夠。但是,在提供長期的著作權保護以及在可能存在的文化上的資助措施方面,這種標準并沒有為那些更具有工業化生產性質之成果的作者帶來多少好處。18[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隨著數字與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公眾的網絡創作行為隨處可見且能輕易實現。人們開始思考“全民參與創作”的時代,獨創性標準是否需要重新調整。盡管獨創性判定標準從“額頭流汗標準”轉向“最低限度標準”或“小硬幣標準”,但是,這并不代表“額頭流汗標準”被完全摒棄,該標準甚至還在一些案件中發揮重要作用。19See Nash v. CBS, Inc., 899 F.2d 1537, 1542 (7th Cir. 1990).當網絡用戶在網絡留言評價而主張版權時,“額頭流汗標準”似乎比“最低限度”標準更適合適用于網絡版權糾紛的解決,因為新技術(包括UGC在內)使得創作本身比“額頭流汗”來得更加簡單、容易。
本文所持的觀點在北京互聯網法院成立以來的第一個案件中得到體現。在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訴百度在線網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案中,法院在判斷抖音上“我想對你說”的短視頻是否構成類電影作品時指出,“關于短視頻“獨創性”的認定標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始終與所處的社會環境、行業特點相聯系……自2016年起,大批移動短視頻應用密集問世,短視頻內容創業者呈爆發式增長,短視頻行業迎來快速發展期。短視頻融合了文字、圖片、語音和視頻等內容,直觀、立體地滿足用戶的多元化的表達和溝通需求。在此背景下,司法審判應持審慎積極的態度,妥善運用創作性裁量標準,以利于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因此,判斷短視頻是否符合創作性要求時,對于創作高度不宜苛求,只要能體現出制作者的個性化表達,即可認定其有創作性。”盡管法院對短視頻獨創性的判斷標準提出了指導意見,但終究還是困在何為“個性化表達”的哲學難題。
(二)“用戶生成內容”版權歸屬類型化分析
用戶所生成的內容要求構成作品時,便需要明確作品的版權歸屬,而版權的歸屬會因作品類型不同而不同。“版權屬于誰”是討論后續“用戶生成內容”是否構成侵權的前提條件,它有助于解決被使用作品的版權人向誰主張權利,以及涉及“用戶生成內容”屬于合理使用情形下作品的版權行使與流轉等問題。從行為模式上,“用戶生成內容”有兩種典型模式:一種是多人合作的“維基百科式”,主要行為特征是網絡用戶自發在某一內容上不斷地編輯生成新作品。“維基百科”作為“用戶生成內容”的典型例子,是由大量用戶持續不斷在原有基礎上添加、修改而成,這與“維基百科”所倡導的“自由內容、自由編輯”理念有關。另一種是“重混創作式”,它是指從大量作品中摘錄、合成而創作出的新作品。這兩種模式所創作的作品與版權法中的合作作品、匯編作品和演繹作品等之間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又無法完全落入其中一種作品類型。
其一,“用戶生成內容”不完全屬于合作作品。盡管我國《著作權法》第13條規定,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沒有參與創作的人,不能成為合作作者,但是對于“合作創作”的判定標準并無規定。《美國聯邦知識產權法典》(2015-2016)第17條規定,合作作品是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基于同一意圖貢獻各自創作從而形成不可分割、融為一體的作品。20See 17 U.S.C. §101, Fede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s (2015-2016), Jones McClure Publishing, p170.基于上述定義,合作作品必須滿足三個要件,即共同創作作品的意圖、貢獻各自獨立的內容、形成不可分割的作品。21See Janky v. Lake Cty.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 576 F. 3d 356, 362 (7th Cir. 2009).“共謀創作”強調的是合作建立在就共同的任務達成一致以及隸屬于某個共同思想指導的基礎之上。至于合作參與者之間是否完全知曉互相創作內容、彼此創作份額是否相同,在法律上并無要求。盡管版權法在判定版權歸屬時并不以任何法律行為方面的約定或意思表示為必要條件,但是,創作上的合作需要各方參與者達成一致才能進行。在“貢獻各自獨立的內容”上,要求合作者要真實提供具有獨創性的創作與實際表達形式的參與,而不是僅提供某種思想或者指明某種最初的思路。所貢獻的各自獨立內容也成為合作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對合作作品的分析,本文認為“用戶生成內容”并不完全符合合作作品之要求。以維基百科為例,盡管由用戶生成的“維基百科”在創作主體數量上滿足合作作品的要求,并且前后用戶均是為了完善百科內容而進行獨立創作,但是用戶之間并不存在合作作者之間的創作合意,后來用戶可以添加、更改或刪除前用戶所生成的內容。這意味著在前用戶在維基百科的創作并不是將來內容所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可見,維基百科式的“用戶生成內容”不屬于合作作品范疇。
其二,“用戶生成內容”不完全屬于匯編作品和演繹作品。我國《著作權法》第14條規定,匯編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構成作品的數據或者其他材料,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匯編作品,其著作權由匯編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基于該條內容,匯編作品涉及若干作品、片段或數據等素材,其獨創性體現在對這些素材的選擇或素材之間關聯性的編排上。以重混行為為例,重混行為是“用戶生成內容”的方式之一,它是指對已有文字、音樂、錄像和美術等作品進行截取、合成而生成的內容。重混行為不一定都屬于版權法上的創作,而在此所要討論的乃是構成創作的重混行為。由于重混創作中涉及已有作品或片段的選擇,并且圍繞某種旋律或主題再次編排而生成的內容,屬于匯編作品。比如抖音和快手等短視頻平臺上大量存在的“鬼畜”視頻,其創作方式便是從已有的影視作品中篩選片段并合成,形成區別于原作品內容所要表達的作品。在此層面,這種形式的重混創作又屬于演繹行為。而對于維基百科而言,并不屬于匯編作品或演繹作品。依上所述,維基百科秉持“自由內容、自由編輯”的理念,使用戶所生成的內容與版權作品相比較,不具有穩定性。維基百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斷更新與完善的內容,而不管是匯編作品還是演繹作品,從作品創作完成之日起,一個作品便已完成,后續的再編輯或演繹屬于版權法上的再次創作行為,形成的是一個新作品。因此,“用戶生成內容”又不完全屬于匯編作品或演繹作品。
三、“用戶生成內容”對版權許可制度的挑戰
版權制度的創設初衷并不是處理版權人與一般公眾之間的關系,而是主要用于處理版權人、出版者、生產者和發行者之間進行作品流轉與傳播等問題。22Daniel Gervais, The Role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in Web 2.0 Music Market, WIPO/Vanderbilt Law School Conference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2007), available at: http://works.bepress.com/daniel_gervais/11/,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12月31日。基于此邏輯,版權許可制度被視為可以解決所有版權授權問題,因為這些版權購買者有足夠的談判實力以及那些藝術家們也能輕而易舉地與版權人進行協商而取得版權許可。然而,傳統的版權許可制度在面對以公眾為版權作品使用主體的“用戶生成內容”行為時,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用戶生成內容”被視為公眾“參與文化”的方式
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具有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屬性,但不是公共產品。保羅·薩繆爾森在定義公共產品時,將公共產品與外部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公共產品是正外部性的極端情況,是將商品的效用擴展于他人的成本為零,并且無法排除他人參與共享。23[英]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經濟學》,蕭琛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公共產品的極強正外部性,必然伴隨著搭便車行為。由于搭便車效應的存在,公共產品不可能由私人企業或個人提供,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因為由私人提供產品勢必導致供應不足。為改變私人供應存在的弊端,需要改變針對私人供應的激勵措施,將正外部性的效應予以內化。“外部性的內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賦予財產權。正如德姆塞茨所言,新產權的出現是對互動的人們調整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性的愿望作出的反應。24Harold Densetz,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57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347 (1967).對于作品亦是如此,為減少作品公共產品屬性帶來的正外部性影響,對創作作品的人賦予一定程度的壟斷性權利,以激勵將來的持續創作。
因此,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社會若要獲得更多的作品,授予一定程度的版權是一種可行的手段。版權的經濟激勵通過版權的可執行與版權許可予以實現。在私法領域,許可是一種在不轉讓所有權的情況下讓渡財產中的權利,25[美]德雷特勒著:《知識產權許可》,王春燕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是財產交易的一種常見樣態。許可能夠涉及所有種類的財產交易,在知識產權領域亦是如此。版權許可又稱為“版權授權使用”,是指版權人采用合同形式授權他人以一定方式使用其作品并獲取報酬的一種法律制度。基于版權的私權屬性,版權人有權決定是否許可以及如何許可他人使用其作品。鑒于此,他人使用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之前應取得版權人許可。然而,在“用戶生成內容”中適用版權許可制度卻極為困難,其緣由包括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在客觀方面:其一,高昂的許可成本讓人卻步。在傳統環境下,通過版權人直接許可的成本是可預知或可控的,許可易于實現。但是在“用戶生成內容”情形下,傳統許可模式陷入難以實現的窘境。從版權人角度,要版權人執行與眾多個人所訂立的合同,其成本將非常高昂。26[美]威廉.M .蘭德斯、理查德.A .波斯納著:《知識產權法的經濟結構》,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頁。從用戶角度,他們上傳的大量內容處于作者與版權歸屬不明確之情形,這導致作品的使用者與傳播者處于不確定的法律狀態下。27吳偉光著:《數字技術環境下的版權法危機秘對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頁。即便想要取得許可,也沒有充分的資料顯示所利用作品的權利歸屬,并且也無法辨識所使用作品是否屬于原始作品。強行要求用戶遵循事先許可模式,極易出現為找尋版權人達成協議而支付的費用超過想方設法獲得作品的價值。其二,用戶處于弱勢的談判地位。即便是用戶有機會與版權人協商許可事宜,除非有足夠的經濟對價,否則通常情況下不易獲得許可。因為對于版權人而言,除了關注許可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外,他們還要關注作品的長期收益與影響力。在主觀方面:一方面,社會公眾認為“文化再利用”(recycling of old culture)是根深蒂固的傳統。人們習慣性地認為,作者在其作品公開發表并供大眾消費后,默許他人“合理且習慣性地”使用其版權作品,而數字與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僅使用戶利用已有文化作品進行再創作變得方便和低成本而已。另一方面,用戶無版權激勵的意識與需求。對于絕大多數用戶而言,創作的首要目的不是獲取版權,而是一種表達的方式與獲得自身滿足感的路徑。版權與表達之間的沖突是歷史性的,它貫穿于版權發展的整個過程。人類渴望言說、創作、簡述,有時不期望獲得經濟上的回報,而只是為了表達而表達,這一點并不新鮮。在沒有免費下載的前網絡時代,由于同樣的表達愿望、與他人交流的愿望促使了廣播的產生,但從沒有人聽說要獲得回報的話。28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s Parad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0.數字與互聯網技術為社會公眾提供的全新表達渠道,沖擊著版權的控制領域。如果說,在傳統環境下,版權與表達之爭因復制與傳播技術自身的物理局限而主要發生在版權人之間的話,那么,數字與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則急劇地改變了作品普通消費者與作品文本以及版權人之間的原初權利關系,從而使得作品普通消費者試圖通過強調信息與文化產品的公共資源性質來維護其表達的主張,與版權人試圖通過擴張及強化版權體系來維護其作者身份與表達私有化的努力所形成的沖突,成為可能影響社會公眾文化實踐的重要議題。29尤杰著:《在私有與共享之間:對版權與表達權之爭的哲學反思》,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但并非在歷史上每個時期表達都可以私有化。相反,表達能否進入私權領域取決于一定的社會和法律習慣,取決于各方力量的對比與當時的社會結構。30李雨峰著:《著作權的憲法之維》,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頁。縱觀眼下,“用戶生成內容”的表達儼然成為一種新的生活習慣。即使在傳統環境下,創作也可以超脫經濟激勵,僅關注于自身的滿足感。以亞當·斯密創作《國富論》為例,在創作《國富論》期間,他自稱“孤獨的哲學家”,盡管他看起來是一個容易交往的人。他從自己的事業中獲得樂趣,并能夠在無需外部激勵的情況下獨自出色地創作。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過去的兩百年中,經濟學僅僅是做了些“梳理工作”,在此期間,經濟學家們只是對《國富論》的分析工作進行一些補充、更正和提煉而已。31[美]羅納德.H.科斯著:《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羅君麗、茹玉驄譯,上海三聯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頁。
(二)網絡平臺的版權責任分析
版權許可制度在網絡用戶中遭遇困境時,版權人常用的辦法是尋找與網絡用戶使用版權作品不是獲取版權有關的網站或平臺,要求他們對發生在他們所控制的平臺上未經許可使用作品的行為予以賠償。那么,這樣做是否合理?網絡平臺是否應當替代用戶承擔相應的版權侵權責任?在用戶所生成內容構成作品且未將有關版權轉讓給網絡平臺時,兩者之間又是什么關系?
用戶能夠生成相應內容并在平臺上分享的渠道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在網站上注冊登記,并以所注冊的賬號生成并分享;另一種是通過下載網絡平臺的應用軟件(APP),通過移動客戶端注冊相應賬號并生成、分享內容。無論何種方式,用戶在注冊時均會遇到包含知識產權格式條款的“用戶注冊協議”對話框。該對話框要求用戶必須點擊“同意”選項以表示滿足條件且接受協議;否則無法繼續安裝軟件。這種“要么接受,要么離開”(all-or-nothing choice)的情形,在數字網絡時代極為普遍。本文以“快手”為例:
“快手”用戶注冊協議中涉及著作權條款的內容:您在使用快手公司相關服務時發表/上傳的文字、圖片、視頻、音頻以及直播表演等屬于您原創的信息或已獲合法授權的內容,您在快手平臺上傳、發布的任何內容的知識產權歸屬用戶或原始著作權人所有;基于部分產品功能的特性,您通過快手公司上傳的音頻可供用戶發布快手短視頻時使用。
即言之,任何用戶應當保證在快手上上傳的內容版權歸屬于用戶所有或原始版權人已授權,否則不得上傳或應被刪除。同時,要求通過平臺上傳的內容還可以被其他用戶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絕大多數用戶在注冊時并不會注意到版權轉讓有關條款的情況下,平臺并未在“用戶注冊協議”中要求以準許用戶進入、使用平臺以換取用戶所生成內容的版權或者要求用戶許可平臺使用作品,而是直接要求用戶授權平臺其他用戶將來的使用。從版權許可主體身份而言,平臺并不屬于任何一方。那么,平臺為何不直接從用戶那里直接受讓版權?本文認為有兩方面原因:第一,從保護版權角度,用戶注冊協議與傳統作品許可使用一致,有利于保護版權人的利益。同時,軟件服務提供者(即平臺)基于用戶注冊協議上的知識產權聲明,極易受到“避風港規則”的保護。第二,平臺服務商與作品版權人簽訂的協議免責模式要求平臺建立一個侵權作品過濾機制,以達到事先預防侵權的效果。如果平臺受讓用戶可能涉及侵權作品的版權,那么對于平臺主觀免責便極為不利。32劉志剛:《博客作品適用版權授權方式的可行性分析》,載《知識產權》2006年第4期,第44頁。因此,在有合理理由規避因用戶利用作品導致的侵權風險,同時可憑借平臺技術準入要求間接換取對用戶作品的再利用的情況下,網絡平臺自然不愿意分擔用戶的版權責任。
四、替代性方案
(一)被動性的合理使用
既然傳統版權許可制度無法適應“用戶生成內容”對版權作品的需求,那么將“用戶生成內容”有條件地歸入合理使用范疇從而避免因版權許可帶來的弊端,是學界所普遍支持的路徑。縱觀世界立法,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四要素判定法”;另一種是以《伯爾尼公約》為代表的“三步檢驗法”,該模式通過詳細列舉合理使用情形,意圖使人們更加容易、準確地預測某種使用行為的性質與結果。我國著作權法及司法解釋中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便是源自以《伯爾尼公約》為藍本的《TRIPS協議》中有關“三步檢驗法”之規定,但適用過程中由于尚未形成司法共識,判決結果甚至大相徑庭,影響了司法的權威。33在立法與司法對新媒體平臺用戶二次創作行為的合法性還存在爭議的情況下,2018年7月16日,國家版權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四部委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啟動“劍網2018”專項行動,針對以合理使用為名對他人作品進行刪減、改編制作短視頻并通過網絡傳播的版權問題進行重點整治。這既不利于行業的長期發展,也不利于保護用戶參與文化創作的權利。對此,多數學者建議我國借鑒美國合理使用制度,或者在修改美國制度中具體某些要素下予以借鑒。那么,美國的合理使用制度能否滿足“用戶生成內容”對受版權法保護作品的需求呢?
根據《美國版權法》第107條的規定,在判斷使用受版權保護作品的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時應當考慮以下因素:(1)該使用的目的與性質,包括該使用是否具有商業性質,或者為了非營利性的教學目的;(2)受版權法保護作品的性質;(3)所使用作品的整體數量與所使用部分的質與量相比較情況;(4)該使用對版權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所產生的影響。盡管《美國版權法》列舉了四要素,但是對于合理使用條款的整體適用性并沒有直接給出所謂的明線規則(bright-line rules),而是把權力交給法院,允許法院在個案中裁定某一特殊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范疇。34賀炯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40頁。面對這種情形,美國學者認為合理使用“具有極強的迷惑性”,并且基于合理使用條款來尋求版權許可是相當冒險和不確定的。35Joanna E. Collins, User-Friendly Licensing for a User-Generated World: The Future of the Video-Content Market, Vol.15:2 Vanderbilt J. &Tech. Law 407, 417 (2013).美國漢德法官甚至將合理使用制度描述為整個版權法中“最難使用的”“最麻煩的問題”。36Dellar v. Samuel Goldwyn, Inc., 104 F. 2d 661, 662 (2d Cir. 1939).對于“用戶生成內容”的參與者而言,合理使用制度本身也在“為難”他們。首先,從性質上,合理使用是版權侵權抗辯的手段,而不是一種積極權利。根據《美國參議院報告》,起草者頂住來自特殊利益群體的壓力制定合理使用制度,但是卻把該條設計成一個要求個案分析的抗辯權利。37No. 83, 90th. Cong., 1st Sess., 37 (1967); Patry 477, n.4.版權人主張用戶侵權時,用戶通常以合理使用為由主張不侵權抗辯。然而,該主張的舉證責任由用戶承擔,這對于學法律的專業人士來說都極為困難的問題,一般民眾自然無法承受合理使用釋明之重。其次,從適用性上,合理使用因概念與適用因素的不確定性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可期待性,用戶無法基于有關具體條款預判行為的合法性或可苛責性。根據《美國眾議院報告》所述,盡管法官們一直在反復思考著合理使用,也經常據其作出判決,但是對這一概念的真正定義卻始終沒有出現過。每一個涉及這個問題的案件的裁決,都必須在基于個案本身的事實上才能作出。38(H.R.Rep.) No. 94-1476, 94th Cong, 2d Sess. 65 (1976).對于用戶來說,究竟是合理使用還是侵權行為,最為直觀的標準是所使用作品的數量與質量。但是,根據“所使用作品的整體數量與所使用部分的質與量相比較情況”要素,用戶其實無法準確掌握這個度,即在未經許可情況下究竟使用多少數量的文字或段落能構成合理使用。與此同時,他們又不能因為所使用的內容僅構成版權作品中的非實質性部分,就因此而免責。正如漢德法官所言,剽竊者不能通過證明其作品中有哪些部分是非剽竊內容而獲得免責。39Sheldon v. Metro-Goldwyn Pictures Corp., 81 F.2d 49, 56, cert. denied, 298 U.S. 669 (1936).第三,非營利性并非“用戶生成內容”免責的“尚方寶劍”。根據合理使用判定要素“使用的性質與目的”的要求,公眾經常習慣性地認知“所有教育性的和非商業性的使用”都屬于合理使用的范疇。鑒于“用戶生成內容”是受社會公眾喜愛的作品創作方式,鼓勵此種創作有利于促進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有學者提出以“用戶生成內容”營利與否為標準的方案:將符合合理使用判斷標準的滑稽模仿行為及業余作者非營利性創作重混作品而使用在先作品的行為納入合理使用情形中;對于職業作者為創作重混作品而使用在先作品的行為,應通過法定許可使用等方式予以規制。40胡開忠:《論重混創作行為的法律規制》,載《法學》2014年第12期,第96頁。然而,該方案本質上并未解決“用戶生成內容”與合理使用之間的關系,而是從行為人是否營利的角度予以劃分,這與美國版權法的合理使用中“作品使用的性質與目的”的含義相差甚遠。營利性與否只是考察使用性質與目的的一個方面,并且營利與否主要區分的不是使用者是否完全以賺錢為動機,而是使用者是否能不支付常規價格而從版權作品的利用中獲利。41Roy Export Co. Establishment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503 F. Supp., 1137, 1144 (1980).為解決合理使用制度過于模糊的問題,美國法院引入“轉換性使用”概念。轉換性使用在于判斷新作品是否只是以取代原作品為創作目的,還是通過使用新的表達、含義或信息而改變了最初的表達、增加了新東西,42Pierre N. Leval, 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 103 Harv. L. Rev. 1105, 1110 (1990).從而試圖避免判斷合理使用時拘泥于判斷使用原作品的質與量,以及不再以“非商業性”作為使用行為的合法前提。針對轉換性使用的優勢,我國學者認為,轉換性使用使得“用戶生成內容”行為的合法性得以通過合理使用認定,作為著作權例外,既因無需事先許可協議而避免全民眾創面臨的交易成本困境,也擺脫商業/非商業性判定標準的束縛而釋放了“用戶生成內容”傳播效率。43熊琦:《“用戶創造內容”與作品轉換性使用認定》,載《法學評論》2017年第3期,第69頁。然而,與合理使用制度一樣,轉換性使用的判定同樣存在不穩定性,對于是否具有轉換性以及轉換性程度大小存在不確定性。更為重要的是,轉換性使用標準僅解決“用戶生成內容”中創造性行為使用作品的合法性問題,那些非創造性的生成行為又該如何解決作品許可的困境?
(二)綜合性的方案
鑒于“用戶生成內容”遭遇的傳統許可制度困境與合理使用制度的被動狀態,在物與物互換實現資源共享理念的影響下,知識共享模式因其簡單的許可程序與靈活的授權方式,被視為解決“用戶生成內容”中作品使用事前許可困境的路徑之一。知識共享模式依賴于知識共享許可協議,是作者放棄版權的一種聲明。因此,知識共享模式能否適用于“用戶生成內容”取決于作品版權人是否愿意將作品放入“共享池”,并且要求后來者以相同方式處分自己的版權。這種要求對于“用戶生成內容”參與者而言并不是問題,因為他們絕大多數并非以此營利、謀生,自然愿意將所生成內容貢獻于大眾。但是,對于以內容創新為業的傳統版權人而言,共享版權作品不僅是處分作品本身,還意味著舍棄基于作品衍生出來的作品市場利益。通常情況下,基于作品產生的市場利益是可預期的,但是基于作品衍生出來的市場不具有可預期性。對于諸多類型的作品而言,其經濟價值并非一次創造即可完成實現,而是建立在原作品基礎上的衍生利益。44Paul Goldstein, Derivative Rights and Derivative Works in Copyright, 30 J. Copyright Socy, USA 209, 227 (1983).因此,要求全部版權人,尤其是要求傳統內容版權產業采納知識共享協議并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本文認為,在本質上知識共享模式是事前放棄版權的做法,屬于“選擇加入”(opt-in)機制,45與“要么同意,要么離開”(all-or-nothing choice)一樣,著作權法意義上的“選擇加入”是指利用他人作品都必須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除非符合著作權法關于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特別規定,否則為侵權行為。是權利人正面地積極處分自己權利的表現。為了與“用戶生成內容”對版權作品的需求相適應,且減少事前授權許可成本。與其正面地積極行使版權,不如從反面角度積極調整作品許可模式,會更加適合當下版權制度的生態環境,而版權“選擇退出”(opt-out)機制便是有效的途徑。“選擇退出”機制是指在作品使用過程中,如果版權人選擇退出使用,則使用者未經授權不能再予利用。46梁志文:《版權法上的“選擇退出”制度及其合法性問題》,載《法學》2010年第6期,第91頁。通過“選擇退出”機制可以規避“用戶生成內容”參與者事前尋求版權許可的高成本,又不損害版權人自主決定權。值得注意的是,從功能上“選擇退出”機制并未完全解決未選擇退出的版權人的利益如何實現的問題。就利益而言,版權人的整體利益包括作品許可費與潛在的作品衍生市場利益。作為理性經濟人,在整體利益有保障的情況下,版權人極有可能釋放作品的傳播效率。同時,在面對社會大趨勢——數字與技術環境下,保持作品完整性的利益(如果曾經有的話)不復存在了。因為,作者必須忍受他人對其作品進行修改和重構。保持作品完整性的利益要遠遠小于符號民主的價值——使得消費者大眾能夠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文化環境的建設中來。47[美]威廉·W.費舍爾著:《說話算數:技術、法律以及娛樂的未來》,李旭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20頁。所以,法律必須要進行調和。為此,音樂產業最為發達的美國國會采納了強制許可制度,意圖防止音樂版權的壟斷行為,降低音樂版權許可的交易成本。48Howard B. Abrams, Copyrights First Compulsory License, 26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 J. 215, 220 (2010).強制許可制度是指版權人默許他人不經許可使用其作品,使用者只需按相關部門(如哈里·福克斯代理公司HFA)的規定支付相應的費用即可。同時,根據《美國版權法》第115條規定,允許被許可人對音樂作品進行重新編排,但是不能改變音樂作品最基本的旋律或特征,以及不能進入衍生作品市場。49See 17 U.S.C. §1115 (2006).在判斷“用戶生成內容”是否影響版權作品的衍生市場時,可采用經濟學分析中的需求交叉價格彈性標準。如果一種商品的價格上漲,導致另一種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表明這兩種商品有市場替代關系;反之,則兩種商品之間沒有替代關系。50朱劼:《共享經濟視閾下重混創作版權法律制度的構建》,載《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第130頁。因此,基于音樂作品強制許可制度的架構,版權人的許可費依法定許可費收取,不包含作品衍生市場利益。當前,強制許可制度適用于音樂作品,其如何適用于“用戶生成內容”中的影視作品還存在爭議。支持者認為,強制許可適用于影視作品與適用于音樂作品的理由是相同的,只是需要修改三項具體內容即可。第一項,釋放影視作品衍生市場利益,對作品使用方式不加限制。相比于音樂內容,視頻內容的“用戶生成內容”具有不可預期性。第二項,按照作品使用者性質區分許可費率。由于“用戶生成內容”參與者中有大量業余創作者,他們不以此營利、謀生,作品強制許可制度區分對待業余使用者與專業使用者更具合理性。第三項,放棄以分鐘作為作品利用長度計算單位的方式。相比于傳統作品利用方式,“用戶生成內容”存在大量僅有幾秒種的作品混輯,如果以單位作品每分鐘作為計算單位,許可費將是巨額數字。因此,需要在傳統強制許可制度基礎上,增設針對“用戶生成內容”的低標準的許可費參考標準。51Joanna E. Collins, User-Friendly Licensing for a User-Generated World: The Future of the Video-Content Market, Vol.15:2 Vanderbilt J. &Tech. Law 407, 434 (2013).
考慮到我國并無強制許可制度,但同時“用戶生成內容”已成為社會公眾獲取信息、利用作品、表達自我的重要方式的情形下,可以將強制許可所體現的理念轉移到法定許可制度中。與我國已有法定許可制度不同的是,關于“用戶生成內容”作品利用中涉及的作品許可費區分計算標準和作品衍生市場的判斷,立法上僅給予指導性原則。同時,應配合以版權“選擇退出”機制,從整體上既要保障版權人利益,又能解決“用戶生成內容”版權許可的困境。
結 語
隨著數字技術與流媒體的發展,已有文化作品被不斷地利用與翻新,“用戶生成內容”成為公眾表達觀點與想法、相互交流的主要方式。盡管受版權保護的作品被大量免費使用,但并不意味著這些行為具有版權法意義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用戶生成內容”在促進社會文化繁榮上意義重大,但保障版權人合法利益同樣至關重要,版權法無法偏廢其一。除了從合理使用制度中尋求消極的抗辯之外,版權法應積極回應“用戶生成內容”中社會公眾對作品的需求以及版權人對實現收益的渴望。在版權法已有制度的基礎上,增設版權人的“選擇退出”機制,區分對待“用戶生成內容”中業余者與專業者在法定許可費上的差異,最終才能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