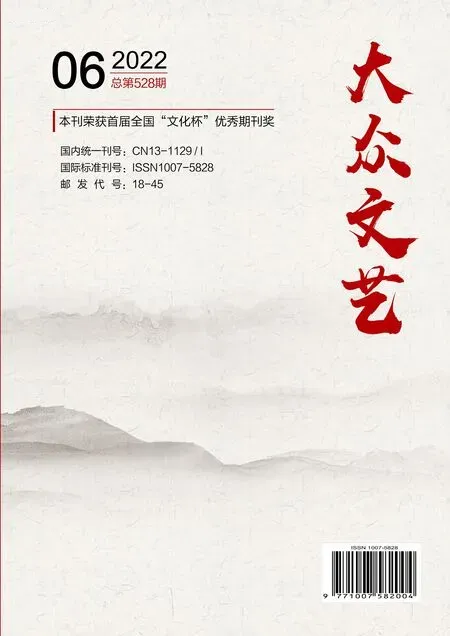以德里達解構主義視角探析《呼嘯山莊》主題
(北京交通大學 100044)
一、德里達解構主義觀點概述
德里達(1930-2004)是解構主義界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學術生涯的早期曾一度將結構主義奉為圭臬。然而,他不久便發現結構主義在解決主流文化問題上表現得過于屈從和軟弱,無法有效推動社會進步,也無法有效擺脫官方話語的控制。因此他把矛頭指向結構本身,試圖拆解結構中存在的二元對立。德里達認為,“二元對立”是根植于傳統西方哲學的核心要素之一,要達到解構的目的,就要從結構的源頭,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入手。他借此提出“延異”等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了解構主義的思想內涵。時至今日,“解構”作為一種不拘一格的批評方法和研究手段,在諸如美學、政治、符號學、語言學以及文學等領域都得到了充分實踐,并提供打破陳規的創新思路和超前于時代主流的獨特視角。
然而,“解構”作為概念本身卻很難被定義。因為作為一種消解概念的手段,一旦它具有明確的定義,便會消解自身。也正因為這種特性,解構便如同幽靈一般始終游離于有形之外,亦不具有一套系統的方法論去指導實踐,它的全部價值都處于流動之中。對“解構”下定義,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行為。在此基礎上,評析德里達解構主義的具體思想比直接討論“解構”更加實在。
(一)延異(Différance)
“延異”是德里達在研究解構主義時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詞匯,該詞本身也是解構主義不拘一格的最好寫照。從詞語本身來看,它結合了“延宕”(defer)和“相異”(differ)的概念,具體來說,則至少包含了三層含義:區分、散播和延展。德里達通過解構柏拉圖的思想來解構整個西方哲學體系,首先拆解的是“說”與“寫”的二元對立。他認為,把說放在首位而把寫放在次要地位的做法是沒有道理的。在《散播》(1972)中,他用“藥”這一概念闡述其具體觀點:古埃及傳說中的特烏斯古神向國王泰莫斯推崇自己發明的文字,表示文字能夠增強埃及人民的智慧和記憶力,是豐富其精神的“藥”。然而,德里達指出,“藥”本身兼具“良藥”和“毒藥”的雙重屬性,它沒有辦法獲得準確的定義。這一例子不僅表現了西方形而上學推崇“說”的原因,也揭示了“說”與“寫”之間潛在的優劣關系。只要寫下的文字離開了語境,它便成為了無主之物,意義也變得含混不清。德里達利用了“父”與“子”的比喻來說明這種關系:“說”就像父親,而寫下的文字就像被父親遺棄的孩子。孩子原本需要依賴父親而存在,一旦被遺棄,則喪失了原有的社會關系,正如同文字喪失了它本來的含義,可以被隨意解讀。然而,正因為這一點,文字也在意義上獲得了更加自由的延展空間。這種改變既是對原本含義的“褻瀆”,也是對原本含義的“再創造”。柏拉圖認為“寫”不可避免地摻雜了多余的要素,玷污了“說”原本的純潔性,所以“寫”的地位始終不及“說”。德里達正是在這一點上做文章,借此發現文字中蘊含的反叛和創新精神。這種精神重新定義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使文字擁有了超越話語并且延展話語原本含義的功能。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也是永恒的,文字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形成新的含義。德里達將其看作“子”對“父”的反叛和超越,在這一恒久的過程中,“說”的地位不斷降低,“寫”的地位不斷提高,兩者間的優劣關系不復存在,它們融為一體,原本的二元對立也隨之被消解。
(二)簽名(signature)與反簽名(countersignature)
德里達認為,文學離不開重復,即通過“簽名”這一過程體現其背后的普適性。“簽名”本身具有合法性和可重復性,文學作品的表達也具有這一規律。文學作品多有表達某種東西的意圖,而這種東西則是對其背后某種母題的演繹,否則它就沒有意義。若是將“母題”比作簽名者,將作品比作簽名,那不難發現許多作品中蘊含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和同一個人在不同文件上簽下相同的名字道理相同。然而,簽名作為一種“寫”,其自身的含義也會在歷時和共時的維度上發生延異,由此便形成德里達的“反簽名”概念。盡管簽名者始終是同一人,在不同文件上簽下的也是同一個名字,但人不是機器,每一次簽名在筆觸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某些情況下,簽名者也可能用不同的字體進行簽名。對同一個簽名的不同形態進行分析,不同的人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簽名”與“反簽名”是始終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的,每一次簽名的本身,既是簽名者的確認,同時也是對于上一次簽名的反簽名。
二、《呼嘯山莊》主題思想探析
《呼嘯山莊》在當代文學界收到了空前的贊譽,這和它細膩的角色刻畫和獨到的敘事手段不無關聯,但最重要的是它所表達的主題思想。誠然,愛與恨、苦難與復仇都是構成這部名著的一些精神要素,它們還不足以構成這部偉大作品的主題和內涵。尼古拉斯·馬爾什在《文學分析》一書中,利用洛克伍德的夢為切入點,將全書的主題思想分為“表層”和“深層”兩部分。表層是通過作品的字里行間可以直接為讀者所感的思想,例如上文提及的精神要素;而深層則是《呼嘯山莊》的精神內核,馬爾什將其定義為“絕對”(absolute)和“限制”(limitation)。從解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是表層的愛與恨還是深層的絕對與限制,都是嚴格的二元對立概念,正是這種概念構成了《呼嘯山莊》主題思想的現有結構。馬爾什在《主題》一篇中,提出“絕對”和“限制”在某些情況之下可以互相轉化,部分體現了解構主義的思想,但沒有對此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愛與恨作為貫穿全文的兩條主要線索,可以通過一種延異關系來消解彼此的二元對立。從一開始凱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愛,伊莎貝拉對希斯克利夫的愛,再到最后小凱茜和哈里頓和解之后萌生出的愛,無一不發生在“復仇”的大背景之下。愛生于復仇、興于復仇,最后反過來推翻了復仇的主導地位,即希斯克利夫最終選擇了和凱瑟琳永遠地沉睡在一起,而不是持續自己對兩個家族無休止的報復行為。從這一點來看,“愛”與“復仇”的關系正如德里達所描述的“寫”與“說”之間的關系——當愛從復仇的源頭之中脫離出來,它便能夠自發地實現延異,其內涵也隨著敘事的進行而變得愈加豐富。對于復仇來說,愛既是產物,也是它的反叛者。因此,表層主題結構上的二元對立被拆解,愛與恨在《呼嘯山莊》不再那么涇渭分明。
對于《呼嘯山莊》深層次的主題結構,我們可以沿用馬爾什的“絕對”與“限制”思想進行分析,而在整部作品中最能體現這一層次的是小凱茜與哈里頓之間的關系。哈里頓被希斯克利夫刻意培養成了一個目不識丁、粗魯不堪的人,然而他對小凱茜的愛可以說是“絕對”的。但如果沒有契機,他們之間巨大的文化與性格差距使這一感情變成了不可能。小凱茜在一開始也是處處嘲諷、侮辱哈里頓,使這一感情被“限制”在單相思的范圍內。這種“絕對”與“限制”的關系也是文學與影視作品中人物沖突的來源,從簽名的概念來看,它具有較強的普適性。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兒子與情人》中莫雷爾夫人與保羅之間畸形的關系、《白鯨》中亞哈船長力圖殺死白鯨卻終將不敵的宿命等,均體現了“絕對”與“限制”的鮮明對比。可是當這種對比在《呼嘯山莊》里演繹的時候,卻又表現出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即兩者的互相融合。小凱茜對哈里頓的一吻不僅打破了限制,也成為《呼嘯山莊》相比于其他作品在安排兩者關系時作出的創新。這一對母題的“反簽名”從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這部作品的成功,它深化原有主題,再主動將其進行解構,使這部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作品同時擁有豐富的思辨色彩。
三、結語
《呼嘯山莊》的成功絕非偶然,其主題思想之豐富遠遠超過情感的范疇。從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思想出發,這部作品的一切表面的對立沖突均可被消解,轉而形成對人類終極哲學命題的詰問與思考。更重要的是,作品并不止步于此,一次絕妙的反簽名過程成功揚棄了先前的絕對概念,使整部作品的理念不再固定僵化,而是流動起來,為主題思想的延展提供了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