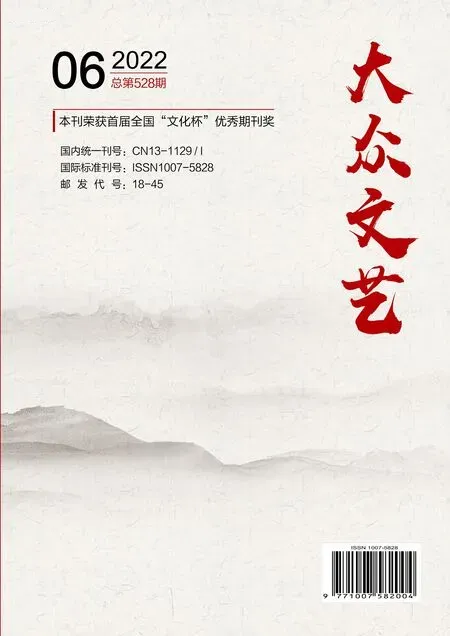從社會認同心理角度分析《欲望號街車》中布蘭奇的悲劇命運
(三峽大學 外國語學院 443002)
《欲望號街車》是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姆斯的一部戲劇。故事講述的是女主人公蘭芝這一典型的南方女子,在家庭破裂后,不愿放棄舊生活方式,生活腐化后,她迫不得已求助于斯特拉。但是蘭芝的生活方式與妹夫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繼而遭到妹夫強奸,最后送進瘋人院的故事。目前評論界廣泛從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及象征手法等方面入手進行分析,而鮮少有從社會認同理論方面進行解析,本文著重從布蘭奇社會認同矛盾的心理過程,以及所采取的策略等方面入手,全面的分析布蘭奇悲劇命運的根源。
社會認同理論強調了社會認同對群體行為的解釋作用,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群體心理學研究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它認為社會認同的心里過程有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和積極區分。社會分類,又稱社會范疇化,個體為了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識別對象,就會把對象進行分類。對人的分類也會運用類似的辦法,這在人類適應環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分類區分了多種刺激,使個體更容易管理它們,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增強效應,即個體傾向于加強同一分類之間的相似性,和不同分類之間刺激的差異性。泰費爾(Tajfel)和威爾克斯(Wilkes)的經典實驗證更是明了增強效應的存在。一旦個體認同某個群體,他們就傾向于將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進行比較。社會比較使社會分類變得更有意義,個體為了獲得和維持自尊,在群體比較時傾向于在特定維度上夸大群體間的差異,給群體內部的成員更加積極的評價,而努力在團體比較的維度上表現得比外部群體更加優秀,這就是積極區分原則。
一、布蘭奇尋找社會認同的“真誠”心理
在作品中,威廉斯不僅對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進行了描寫,還著重介紹了布蘭奇年幼時的成長環境,為她日后的悲劇命運作了鋪墊。布蘭奇本出自貝爾立夫莊園的顯赫家庭,是一位典型的南方淑女,她感知到自身所屬的社會團體中,男人們應該都是富有教養和內涵的紳士,而女人們則應該是高雅,美麗,氣質出眾而又滿腹詩書的矜持淑女。雖然后來家道中落,丈夫早亡,事業上慘遭辭退,生活上無依無靠又人老珠黃,迫不得已投靠妹妹妹夫,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中,布蘭奇嫣然早已經淪為和妹妹妹夫一樣貧苦,甚至更加不堪的生活窘境。但布蘭奇卻從未因此而放棄南方大家閨秀的自我形象,對美貌打扮,優雅舉止,眾星捧月般地追逐以及象征著高尚與智慧的華麗辭藻等等的追求以及由此帶來的情感和價值體驗。在對他人進行分類的過程中,布蘭奇很難不受自己情緒的影響,因為對他人的分類也會影響到他自己的價值。人們往往會根據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相似點和不同點來對他人進行分類,這樣他們就可以將對象分類為同一個內部組的成員或者不同分類的外部組的成員。
從布蘭奇初到伊利恩地段,無論是言行舉止還是思維方式與周遭的一切都顯得那么地格格不入。如第一場剛開始對布蘭奇的描寫中提到,她首先是不敢相信妹妹居然住在這樣一種魚龍混雜,烏煙瘴氣的環境里面,其次是她自己的衣著打扮與周圍的人群及環境顯得格格不入。而她之所以如此在意自己的形象,除了她丈夫早逝,還未再嫁之外,就是希望獲得男人們眾心捧月般的追逐,討好,服侍,亦或是獻殷勤。因為如此,她就可以像個淑女一樣端起自己的架子,在男人們的恭維聲中獲得更多的體面與虛榮。而這些也正是布蘭奇所認同的社會團體中,女人該有的驕傲與尊嚴。在一次布蘭奇與史蒂拉的對話中,布蘭奇坦白說自己喜歡被人服侍,而被人服侍正是她所認同的這個團體中女人該享有的待遇,同時也是她周圍的婦女們所屬的團體中不可能享有的特權與待遇。布蘭奇在與其他團體進行比較并夸大差異的過程中獲得自尊與積極的評價,同時獲得社會認同。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容貌打扮上,在言語表達上更是如此,不論何種情況,對象是誰,她總是喜歡刻意用優雅的語言來表達她的才華與博學,當她在氣憤的情緒中指責斯坦利的粗俗暴力之時,她形容斯坦利的舉動像個動物,有著動物的習性,甚至比喻他為猿人;當她在浪漫曖昧的氛圍里挑逗勾引密奇時,刻意賣弄自己的博學,假裝無意中發現密奇煙盒上寫著的是一首布朗寧夫人十四行詩中的一句。布蘭奇不僅用高雅的語言標榜自己受過高等教育,區分自己與周圍人群所屬的不同團體,也通過對斯坦利的鄙視與指責提升自己的自尊及所處團體的優越性。
二、布蘭奇尋找社會認同的“矛盾”心理
表面上看來,布蘭奇的行為之所以不合常理,是因為她認不清現實,在現實與理想的漩渦之中迷失了自我,從而導致了自己最后悲劇的命運,而實際上,筆者認為布蘭奇雖然企圖通過種種故作高雅的行為,刻意優雅的舉止和賣弄文采的言辭等等舉動來劃清自己與低地位群體成員的界限,但在她內心的深處,她仍然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實際情況是處于一種低地位的社會群體。其實布蘭奇對自己的年老色衰的容顏有一個清晰準確的認識,不然她也不會說自己在太陽底下看簡直就是一塌糊涂,也不會形容自己是已經摘下好幾天的雛菊,更不會總是藏匿在黑暗角落與密奇戀愛約會。除了容貌之外,布蘭奇對自己的經濟狀況,個人名聲,以及社會地位都有一個很清晰的認識。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父母丈夫孩子都相繼離世,莊園也沒有了,只剩下了一大堆文件,更糟糕的是連工作也丟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來投靠自己的妹妹,而且在當得知妹妹家不僅沒有仆人,還只有兩間房,更糟糕的是還有一個粗野無禮的妹夫,就算是妹夫時常和一群毫無前途的人打牌到深夜,時常出言不遜,打砸東西,她也依然要和妹妹妹夫擠一起,種種跡象足以表明,布蘭奇對自己的經濟情況非常清楚;在個人名聲方面,布蘭奇也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之所以來投奔妹妹,除了經濟窘迫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早已聲名狼藉,在家鄉早已無立足之地。當斯坦利質問她是否認識一個姓肖的人之時,白蘭奇一邊曉得前仰后合,一邊用撒了香水的手絹揩太陽穴,當斯坦利說可以查對一下,澄清錯誤之時,白蘭琪做出閉上眼睛像要昏厥的樣子,拿起手絹揩額的手也在發抖。從這種種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布蘭奇面對有人盤問她的過去,她是心知肚明的,同時也是心虛的,她清醒的認識到自己的實際行為和她所標榜自詡的淑女形象是大相徑庭的。雖然白蘭琪舉止高雅,妙語連珠,時刻注意著自己的容貌形象,竭盡全力的將自己與周圍的群體區分開來,處處表現出優越與高傲,但是從她選擇與密奇談戀愛,并一心想和他結婚的行為來看,她其實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和境況是非常清楚的。
那為什么一個對自己現實情況了解如此清晰,做事絕不含糊的知識女性會在言行舉止上與現實和周圍環境如此得格格不入?事實上,布蘭奇之所以表現出種種不和適宜的行為,是試圖通過模仿高地位群體成員的行為,努力改變外界負面評價的表現,從而融入高地位群體之中。她不僅通過種種故作高雅的行為和賣弄文采的言辭等等舉動來劃清自己與低地位群體成員的界限,更通過貶損排斥周圍她所痛訴為粗俗暴力野蠻的人,向理想中的多金紳士形象靠攏以及模仿高地位群體成員的行為來努力改變外界諸多的負面評價,產生積極的差異比較,帶來更高的威望,以加強自己身份的認同。布蘭奇正是企圖通過美麗的外表,優雅的舉止以及華麗的辭藻等等不屬于她所處于的低地位群體的行為,試圖拋棄現實中低地位群體中現有的社會認同行為,轉而融入理想中紳士淑女們所處的高地位群體。
三、布蘭奇尋找社會認同的失敗悲劇
布蘭奇通過運用個體/行為策略中的個體流動和同化方式,模仿高地位群體成員的行為和拋棄現有社會認同的行為來達到提升個體地位,維護個人尊嚴的目的。而追求高地位群體的社會認同心理就是布蘭奇一系列不合理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而可悲的是,她所有意圖提升個人地位的行為都被認定為虛偽的謊言,被人們無情的揭露與批判,直到最后,布蘭奇所有的追求都一層層慘遭剝離與碾壓之時,布蘭奇也最終在尋找社會認同這條路上走進了人生的死胡同。
布蘭奇努力在眾人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端莊淑女的美好形象,她深知作為一個淑女,應該是品行端正、潔身自好的,然而她卻處處招蜂引蝶、名聲在外。布蘭奇自己也深深的意識到這一點,為了維護僅存的尊嚴和驕傲,她一邊痛恨著自己的放蕩無度,一邊又渴望著貴族小姐的虛榮光環,所以她離開家鄉,轉而投奔生在他鄉的妹妹,為的就是擺脫早已坍塌的個人名聲,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拾貴族小姐的光環,然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妹妹居然住在魚龍混雜破敗不堪的地方,盡管如此,她依然從未放棄過任何一個可以表現自己高貴身份與良好教養的機會,從行為方式到語言修辭,無不刻意營造著高人一等的姿態與驕傲。然而,當布蘭奇的風塵往事被斯坦利查明并告知密奇之后,密奇找到布蘭奇,憤怒地指控了布蘭奇青春不再以及“不規矩”的現實,這一舉動使布蘭奇企圖通過努力模仿和塑造一個高地位群體形象,從而改變外界負面評價的想法瞬間化為泡影。在悲涼與失望的同時,遭斯坦利還落井下石,戳穿布蘭奇的廉價服飾以及虛構富商追求她的現實,最后甚至強奸了她。這一切的一切徹底地擊垮了布蘭奇所營造的一切可以提升其個人地位的謊言,而提升個人社會身份的徹底失敗使布蘭奇最終走向崩潰與瘋狂。對于布蘭奇,放蕩是對命運的反擊,是向南方道德標準的宣戰,同時也是與自己人生的博弈。只是她在反抗中日漸迷失自我、難辨方向,與噩運的距離一步步拉近。
三、結語
布蘭奇本應是南方貴族家庭中受到眾人追捧與膜拜的窈窕淑女,命運的捉弄使她失去了財富與地位,然而在生活的壓力下,她不僅沒有腳踏實地、面對現實,反而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放蕩自我、逃避自我,企圖通過模仿高地位群體成員的行為和拋棄現有社會認同的行為來達到提升個體地位,以達到維護個人尊嚴的目的。布蘭奇最終在希望逐步破滅,現實步步緊逼的過程中,走向了悲劇與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