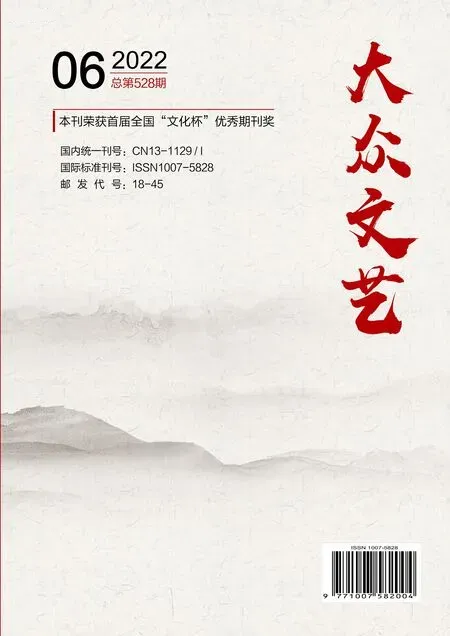論紀錄片《我的詩篇》的詩意再現
(浙江師范大學 321000)
一、畫面再現
在《我的詩篇》中,詩歌文本與影像文本相互作用,影像畫面再現詩歌內容。例如詩歌《吊帶裙》:“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聚集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吊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多么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親赴一種安靜的愛情/ 然后把裙裾展開/我要把每個褶皺的寬度熨得都相等/讓你在湖邊,或者草坪上/等待風吹//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濕的廠服/吊帶裙,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走向某個時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愛你。”從詩學意義上,這是一首現實主義詩歌,詩人通過細膩的內心,由手中認真對待的物品聯想它可能發生的境況,連衣裙代指“姑娘”,渴望享用愛,也代指詩人本身,則更有給予愛的雙層意蘊;“等待風吹”的美好與“唯一的你”的珍視,組成詩人生命與愛情的價值意象,與讀者達成移情。
在鏡頭下,詩歌語言轉化為視聽語言,畫面再現是紀錄片詩歌再現的第一步,也是最直觀的一步。在《吊帶裙》詩歌作為畫外音出現之前,鏡頭是一輪明月,交代時間,聯系前后影片,這個鏡頭奠定了空間基調。當鏡頭轉至鄔霞,我們可知,在車間的夜晚,鄔霞仍在加班工作,而月光靜謐又溫柔。鄔霞在車間做著熨衣的本職工作,鏡頭跟隨著她溫柔的動作,從“肩帶”熨到“腰身”熨到“裙裾”,鏡頭 沒有任何技巧修飾,卻因其質樸而顯出生命的活力與本真的靈動。鏡頭切到大場景,是封閉雜亂的車間,詩的甜蜜與現實的貧瘠對比出主人公靈魂的自由,以及無法忽視的現實困境。
畫面再現的手法平實質樸,鏡頭跟隨詩歌的字眼,實拍詩人生存環境,展現詩人的創作背景。介紹性陳述的旁白說到:“鄔霞的父親患有嚴重的抑郁癥,又不愿再拖累家人,不久前曾有過兩次輕生之舉。”面對父親,鄔霞于是創作了《家》,寫到:“爸,生活有多艱難,就有多珍貴/我們的小屋就是暴風雨中寧靜的鳥巢“;面對自己,鄔霞創作了《爬山虎》“我一定會昂起我的腦袋,向著陽光生長,/像工廠灰墻上地爬山虎。“同時,她的心聲與創作動力,在紀錄片中以采訪自白交代,“我覺得我要像那個石縫里面的草啊花啊什么的,就算是有一塊石頭壓著我,我也一定要倔強地推開那塊石頭。要昂起我的腦袋,向著陽光生長”;“我寫小說、寫散文、寫詩歌,我覺得詩歌最能抵達人的靈魂。我希望別人看到我的詩歌,能感受到美好。”
二、情節再現
《我的詩篇》以紀錄2015年年初的工人詩歌朗誦會為敘事主線,每朗誦一篇,鏡頭則引以詩歌聲詩歌、作詩人及其群體。據采訪,秦曉宇導演在編排《跪著的討薪者》這篇詩時,朝陽門附近地下通道有100多名農民工討薪不成夜宿于此,他們的神情就如詩中所寫“我們失意的得意的疲憊的幸福的/散亂的無助的孤獨的……表情/我們來自村屯坳組我們聰明的/笨拙的我們膽怯的懦弱的……”一個名詞一張面孔,詞與臉剪輯步調一直,節奏沉緩、平和、有力,更顯人數眾多與民眾憤懣張力。導演請工人們讀詩,工人們齊齊跪在地上,用各地的方言大聲念出“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與詩句“我們跪在地下通道舉著一塊硬紙牌/上面笨拙地寫著’給我們血汗錢’/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如出一轍。導演在這一段落中記錄工人們集體發聲的歷史一刻,用詩歌朗誦穿插期間,以情景安排再現詩歌,討薪工人們與討薪詩的契合令人震撼;詩之精神真實與紀錄片之形式真實巧妙結合,得以使文本呈現精神,而影像給予精神實體。
三、寫意再現
《我的詩篇》在以影像闡釋詩歌時,其空鏡頭表達缺少前奏鋪墊,詩句意象剪輯刻意,缺少潛在邏輯與意韻的連貫,從而在寫意層面缺少與詩本體的意境共鳴。例如,爆破工陳年喜《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巖層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組合”,“打發”與“借此”用力輕巧,卻在“五千米深處”、厚厚“巖層”下思考責任重大的“中年”,一種張力被拉開了,壓抑之深之沉,忍耐,憋著渴望沖破一切的強烈意念;讀完整詩回看,“炸裂”是詩眼,“我”“炸裂”的不僅是巖層,更是人生,一個人到中年,依然被束縛無掌控的人生。而紀錄片怎么處理的呢?畫面僅僅是工人和礦洞,于是“炸裂”一詞出現時,畫面轉為忽然的爆破場面與爆破同期聲,非常刻板生硬,折損詩義。私以為,詩歌讀到”炸裂”一詞時,所配畫面如果是一群工人從黑暗的礦洞洞,忽然間,蜂擁而出,見一片光明藍天,是否更見詩之蘊涵與影像魅力呢?相比之下,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中拍攝余秀華去看雪,因患有腦癱疾病而身體狀況不佳,她走路時的模樣一瘸一拐。鏡頭下,搖搖晃晃的人影走遠,是人文關懷的注視;鏡頭轉至空鏡,雪紛紛落下,曠白、潔凈、緩慢,觀者則思緒停留,悲天憫人的詩意心境頓生,詩人詩情的寫意再現得以淋漓,甚至烘托出了觀者詩情,產生移情效果。
在文字藝術轉化為影像藝術的過程中,詩歌的詩藝結構,文學文本間通過詞語間、上下句之間的,以意象的勾連與沖突所營造的詩意想像,藝術再創造為影像文本的結構時,體現為一種二次解讀、一種再闡釋,其中詩意想像的詩藝內蘊流失與否、表達精準與否,則考驗導演與剪輯導演的影像藝術表達力度。誠然,《我的詩篇》由于寫意再現與情節再現的處理較為平敘樸直,對于其中詩歌詩藝的表達是欠缺的,而作為一部對社會階層底層工人的生活境況、心靈狀態的直接呈現,畫面紀實記錄,直面當代現實,為一群生活貧困而才華橫溢的打工詩人發聲,一股清流,涓涓而粼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