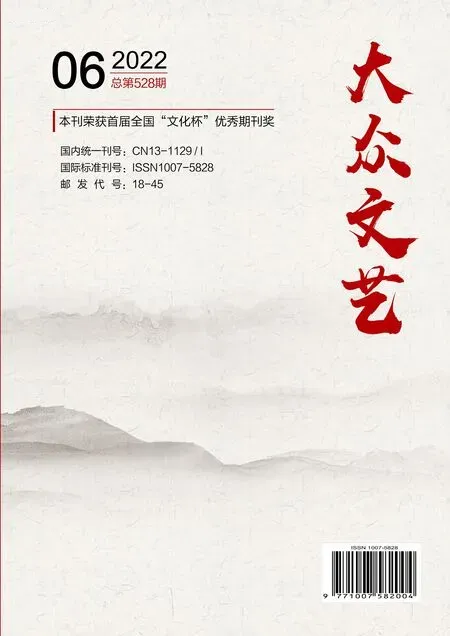淺析中國新、舊導演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以費穆、田壯壯《小城之春》中的周玉雯為例
(西北大學 文學院 710000)
一、人物語言的留與舍
在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開頭,出現了周玉雯的內心獨白。她帶著一種全知型視角,第一和第三人稱的不斷切換,向觀眾介紹人物。在中國早期的電影發展中,電影與戲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很長一段時間內,電影被稱為“影戲”。
在戲曲中,因為舞臺空間單一性的限制,因此人物出現通常都會自報家門,講述生存狀態。如果不通過語言講述觀眾是無法通過視覺理解戲份。使用說明性的對白和獨白都是為了彌補無法呈現的東西,演員必須依靠語言的力量。但是電影是一門非線性的視聽藝術,可以任意的表現時間和空間。如果畫面已經交代清楚,不需要通過聲音的元素再次傳遞相同的信息。戲曲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樣式,將戲曲舞臺上的某些方法帶入到電影中會顯得不合時宜。但是戲曲美學對費穆的影響很深,在《小城之春》開頭,周玉雯的獨白緩慢冗長,未免有畫蛇添足之嫌。而在田壯壯的《小城之春》中,充分利用電影語言的獨特優勢,創新性地將這一段獨白去掉。兩部電影時隔五十多年,不可否認電影技術的進步為電影語言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自古以來,隱忍成為中國女性形象的代名詞。在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中,周玉雯通過獨白將內心的苦悶憂郁與對丈夫戴禮言的不滿通過私人化的口吻展現給觀眾,與中國傳統女性的性格相矛盾。而在田壯壯的電影中,開頭周玉雯只是提個菜籃子緩慢地走在城墻上,沒有任何語言,通過行動表達內心,完全符合電影藝術的獨特呈現方式。
二、性格設定的收與放
在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中,周玉雯是孤獨的、古典的。而在田壯壯的《小城之春》中,周玉雯沒有沉下來,年輕氣盛、浮躁、諂媚,小城的沉悶體現不出來。演員每個動作、臺詞、眼神都體現角色性格與內心。在費穆的影片中,周玉雯的一顰一笑都透漏著濃郁的中國美,平靜而驚艷,很符合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女性形象。但是在田壯壯的《小城之春》中,周玉雯的表演隨性而做作,更像是解放后的女性形象。例如,當章志忱來到家里敲門時,周玉雯在房間內大喊:“老黃,老黃,有人敲門”!表演聲音和動作都很大,充滿了裝腔作勢的居高臨下和世俗的諂媚。
費穆以悲觀抑郁的筆觸,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充滿責任感和克制力的女性。在戴秀生日那場戲中,周玉雯和章志忱借酒生情,兩人喝得大醉與昔日的舊情人鬧起酒來。費穆處理的手法是收斂而非放縱。在她進入章志忱的房間后,章志忱理智地趕他走,緊接著在情欲邊緣掙扎,猛地一下將她抱起。在這個過程中,周玉雯幾乎沒有說話,也什么都沒有做。而在田壯壯導演的《小城之春》中,處理手法更加放縱。周玉雯進入章志忱的房間后,先是坐在床上將自己的頭倚靠在章志忱身上,他受理性的控制站起來逃離之后,周玉雯又緊接著跟了過去。這樣的手法給觀眾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叛逆、缺少含蓄和責任的女性形象,有悖于電影的主題。
在《小城之春》中,周玉雯是一個隱忍、順從與無奈的女性形象的時代代表。如果任其發揮,太過放縱,反而適得其反。費穆導演的電影中能感覺到人物的壓抑,不敢面對最真實的自己以及他們內心的掙扎,引起共鳴,更讓人震撼。
三、表演形式的增與減
道具是表演的最基本元素之一。在章志忱和戴秀出去當天,周玉雯進入章志忱的房間,在兩人對話中,周玉雯一直舞動著手里的紗巾。費穆是一個極具中國化的導演,紗巾像是戲曲舞臺上花旦的水袖,周玉雯和戴禮言已經分居多年,有夫妻之名卻無夫妻之實。她是一個充滿責任感和克制力的妻子,但她也有多年來壓抑的欲望,她不斷舞動紗巾,可以看出害羞內心的外露以及她的欲言又止。周玉雯的表演拿捏自如,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而在田壯壯的影片中,將紗巾的橋段去掉,不免顯得有幾分失色。
除上述之外,田壯壯導演在影片中特意加了一個情節。在章志忱還未與周玉雯見面前,玉雯對著鏡子梳妝打扮,讓觀眾感覺周玉雯原本就是一個很愛美的女人。而費穆的影片中,在二人沒有相遇之前,周玉雯對生活充滿了絕望,只有她要見章志忱的時候,才會特意梳妝打扮,體現出花為悅己者容的態勢以及她的心旌蕩漾。
當周玉雯擊破玻璃,手上的鮮血流出。他們二人才真正看清自己,意識到自我和責任之間的取舍。兩人的曖昧也就此結束,就像夜里的蠟燭一樣太亮了。周玉雯和丈夫之間雖相敬如賓,但彼此又為對方著想,她對丈夫也不是毫無眷戀,為影片的結局做鋪墊。
四、結語
在《小城之春》中,從表面上看,章志忱的到來使得周玉雯充滿生機和希望。實際上,章志忱的到來更象征著早春的乍暖還寒,當他離開,小城的春天才真正來臨。離別并不是憂傷和無奈,而是人物的真正覺醒。周玉雯和戴禮言夫妻之間才意識到對彼此的眷戀。1948年,國家動蕩不安,人人在從艱苦中尋求生活。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一切百廢待興,國家和小城才迎來了春天。過去是灰色的,未來是彩色的。
兩個不同的時代,兩位風格迥異的導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塑造著不同的女性形象,詮釋著《小城之春》的獨特魅力。兩部電影各有千秋,沒有標準,都充滿著獨特的活力。后者在某些方面依舊保留了前者的精華,不僅是對電影和表演藝術的豐富,更是對前輩導演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