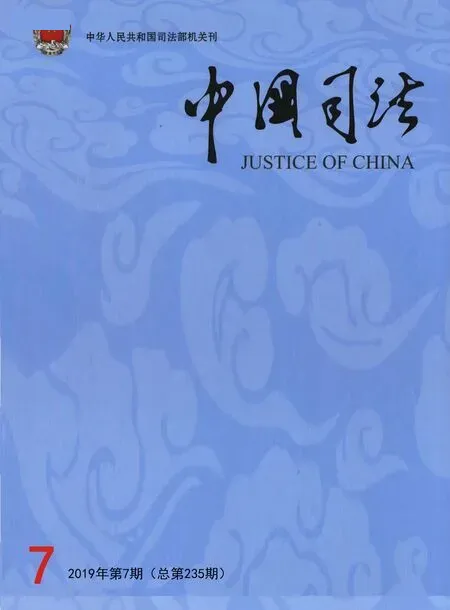全面依法治國(guó)是天下歸心的事業(yè)
韓春暉[中共中央黨校(國(guó)家行政學(xué)院)教授]
一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中指出,要堅(jiān)持全面依法治國(guó),深化依法治國(guó)實(shí)踐。并且強(qiáng)調(diào),必須把黨的領(lǐng)導(dǎo)貫徹落實(shí)到依法治國(guó)全過(guò)程和各方面,堅(jiān)定不移走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治道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律體系,建設(shè)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治體系,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guó)家。習(xí)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非常清晰地表明,我們已經(jīng)成功地探索出了法治的中國(guó)道路,并且基于法治實(shí)踐逐步發(fā)展出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治理論。
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并且充滿自豪地說(shuō):在一個(gè)有著14億人口、960萬(wàn)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guó)堅(jiān)定地追求、奉行和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這是世所罕見(jiàn)、前所未有的光榮事業(yè),也是實(shí)現(xiàn)強(qiáng)國(guó)富民、國(guó)泰民安的崇高事業(yè),更是實(shí)現(xiàn)眾志成城、天下歸心的偉大事業(yè)。它既展現(xiàn)了我黨為促進(jìn)國(guó)家崛起、民族復(fù)興、人民幸福,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夢(mèng)”過(guò)程中的使命、勇氣和和執(zhí)著,也標(biāo)志著我黨治國(guó)理念、策略和技術(shù)更加理性、智慧和成熟。
古人云:“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如果一個(gè)國(guó)家法度明晰,那么百姓就有了共同的追求,國(guó)家體系就能夠運(yùn)轉(zhuǎn)順暢有序,社會(huì)各界也就能夠維持安定和諧。歷朝歷代,天下歸心都是國(guó)家治理者最高的政治追求,而法治正是一種天下歸心的事業(yè)。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指出,當(dāng)今中國(guó)社會(huì)矛盾和問(wèn)題交織疊加,全面依法治國(guó)任務(wù)依然繁重,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qiáng)。我們此時(shí)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更加凸顯了法治事業(yè)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同時(shí)也賦予了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治道路更加獨(dú)特、明確和具體的時(shí)代內(nèi)涵。
所謂“天下”,是指國(guó)家、社會(huì)和個(gè)人三個(gè)層面的綜合體,包括生活在中國(guó)這一地理國(guó)度上的各種階層、各種類別、各種族群的主體。它既包括政府官員,也包括普通百姓;它既包括工人、農(nóng)民、知識(shí)份子,也包括商人和民營(yíng)企業(yè)主;它既包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也包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以外的民主黨派、無(wú)黨派和所有擁護(hù)黨的方針和政策的其他組織;它既包括漢族,也包括和諧生活在960萬(wàn)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少數(shù)民族;它既包括中國(guó)公民,也包括長(zhǎng)期居住在我國(guó)的外籍友人。
所謂“歸心”,是指所有人對(duì)基本國(guó)情、所處階段、發(fā)展道路和民族未來(lái)具有類似的判斷、持有相同的理解,堅(jiān)持正確的方向,抱有共同的追求,達(dá)致了較高的共識(shí),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價(jià)值取向。具體來(lái)看,它包括“主體歸心”“道路歸心”和“價(jià)值歸心”三個(gè)方面。“主體歸心”是指黨和政府具有高度公信力,人民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對(duì)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給予充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相信黨和政府是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崛起、民族復(fù)興、人民幸福的原動(dòng)力。“道路歸心”是指所有成員普遍贊同并且堅(jiān)定不移地走中國(guó)特色的法治道路,對(duì)以法治強(qiáng)國(guó)的歷史規(guī)律具有高度的共識(shí),對(duì)法治安邦的未來(lái)發(fā)展具有堅(jiān)定的信仰。“價(jià)值歸心”是指法治將所有人的價(jià)值取向引導(dǎo)并統(tǒng)一到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上來(lái),讓這些價(jià)值成為政府、社會(huì)和個(gè)人的前進(jìn)方向、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和行動(dòng)指南。
“歸心”的最終目標(biāo)是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崛起、民族復(fù)興、人民幸福的“中國(guó)夢(mèng)”。中國(guó)的法治道路是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夢(mèng)”的應(yīng)有之義、重要內(nèi)容和必由之路,它服務(wù)于國(guó)家崛起、民族復(fù)興的總體大局。“中國(guó)夢(mèng)”既是國(guó)家的夢(mèng),也是人民的夢(mèng)。同理,“法治中國(guó)”既是我黨對(duì)民族騰飛的追求,也是人民對(duì)美好未來(lái)的向往。
二
民無(wú)定志必亂,國(guó)無(wú)法度則衰。兩千多年前,法家思想就倡行一種服務(wù)于國(guó)家發(fā)展大局的國(guó)家主義法治觀。當(dāng)今中國(guó),黨的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與依法治國(guó)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有機(jī)統(tǒng)一,法治已經(jīng)成為黨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對(duì)國(guó)家、社會(huì)和公民進(jìn)行有效治理的治國(guó)方略。它必須全面服務(wù)于我黨所面臨的戰(zhàn)略發(fā)展大局。
第一,深化改革需要天下歸心。改革的特點(diǎn)是“變”,它意味著可能突破和逾越既定的規(guī)則和秩序;法律的特點(diǎn)是“定”,它意味著必須維護(hù)和保障現(xiàn)行的制度和秩序。改革始終是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也只能在社會(huì)主義法治體系的框架和規(guī)范下進(jìn)行。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處理改革與法律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關(guān)系,在改革的“變”與法治的“定”之間保持正確的“度”。既不能因?yàn)閺?qiáng)調(diào)依法治國(guó)而影響改革的進(jìn)度和力度,更不能由于推進(jìn)改革而損害法律的權(quán)威和尊嚴(yán)。
第二,科學(xué)發(fā)展需要天下歸心。在實(shí)踐中,有些地方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把依法治國(guó)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立起來(lái),認(rèn)為依法治國(guó)束縛手腳,妨礙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通過(guò)片面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速度來(lái)追求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導(dǎo)致?tīng)奚嗣袢罕娎娴膯?wèn)題比較突出。我們必須認(rèn)識(shí)到,法治也是生產(chǎn)力,是最持久、最穩(wěn)定、最富效率的生產(chǎn)力。
第三,保持穩(wěn)定需要天下歸心。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中國(guó)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時(shí)間創(chuàng)造了西方幾百年才實(shí)現(xiàn)的經(jīng)濟(jì)奇跡,完成了社會(huì)的多次跨越式發(fā)展。這種超常規(guī)的發(fā)展速度在激發(fā)了超常社會(huì)活力的同時(shí),也更快地激發(fā)了人民內(nèi)部的矛盾,使得原本在西方幾百年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中逐步展現(xiàn)的各類社會(huì)矛盾,卻在當(dāng)今中國(guó)這一“壓縮時(shí)空”涌現(xiàn)。所以,我們必須以法治方式來(lái)消除導(dǎo)致矛盾產(chǎn)生的深層次因素。一方面,我們需要引導(dǎo)百姓正確認(rèn)識(shí)自身的合法、合理利益,糾正一些不當(dāng)、無(wú)端的利益訴求,鼓勵(lì)百姓采取合法正當(dāng)?shù)闹贫然緩饺ソ鉀Q問(wèn)題,避免采取非法手段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增強(qiáng)百姓對(duì)黨和政府的信任,避免形成“塔西佗陷阱”。
三
“法者,治之正也。”法治是治國(guó)之正道,是一國(guó)之內(nèi)各方主體能夠?qū)崿F(xiàn)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機(jī)制。它對(duì)于國(guó)家建設(shè)是如此,對(duì)于社會(huì)治理也是如此,對(duì)于個(gè)體發(fā)展更是如此。
從國(guó)家建設(shè)層面來(lái)看,法治是構(gòu)建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強(qiáng)國(guó)之路、富國(guó)之策和定國(guó)之方。縱觀中國(guó)歷史,“大變法”往往是“大發(fā)展”的揭幕曲。因“抱法處勢(shì)”而為的“商鞅變法”,不僅使得秦國(guó)強(qiáng)大并一統(tǒng)天下,而且確立了封建集權(quán)制的基本體制,自此往后“百代皆行秦政治”;明朝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不僅使得政府歲入顯著增加,而且促進(jìn)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宋代的“王安石變法”盡管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客觀上仍穩(wěn)定了宋朝的統(tǒng)治基礎(chǔ),為總體上已顯頹勢(shì)的王朝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風(fēng)。
從社會(huì)治理層面來(lái)看,法治是治理天下的理性之道、公平之道和長(zhǎng)久之道。其一,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文明,它是公共精神的載體,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其二,法律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器,核心是調(diào)整權(quán)利義務(wù)等利益關(guān)系。奉行法治就是通過(guò)整體、全面、合理的制度安排,從制度上理順各種利益關(guān)系,平衡不同利益訴求,是治理天下的公平之道。其三,法律是明確的、穩(wěn)定的、可預(yù)期的、符合民心所向的規(guī)范體系。反之,其他個(gè)體化、權(quán)宜性和應(yīng)對(duì)性治理方式要么難以持久、要么標(biāo)準(zhǔn)不明、要么矯枉過(guò)正,帶來(lái)的問(wèn)題甚至比解決的問(wèn)題更多。惟有法治,是實(shí)現(xiàn)天下長(zhǎng)治久安的長(zhǎng)久之道。
從個(gè)體發(fā)展層面來(lái)看,法治是現(xiàn)代社會(huì)成本最低、機(jī)會(huì)最均等、和諧度最高的生活方式。在專制體制下,個(gè)體的生活成本較高,而且機(jī)會(huì)不均等,和諧度也不足。在禮治秩序中,個(gè)體的生活成本較低,和諧度也較高,但機(jī)會(huì)嚴(yán)重不均等。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中,規(guī)則的確定性降低了公民之間的交易成本,制度的公平性賦予了公民平等的發(fā)展機(jī)會(huì),救濟(jì)的有效性防范了人民內(nèi)部矛盾激化。對(duì)于公民而言,學(xué)法、尊法、守法、用法就是一種最優(yōu)良的生活方式。
四
中國(guó)特色的法治道路,其本質(zhì)就是“天下歸心”之路。這一發(fā)展過(guò)程應(yīng)當(dāng)遵循“先規(guī)范個(gè)體,再統(tǒng)一社會(huì),繼而歸于國(guó)家”自下而上不斷升華的邏輯步驟。具體為三個(gè)方面。
第一,以法律規(guī)范“立規(guī)”,重在劃定行為底線。也就是說(shuō),以法律規(guī)范規(guī)定、倡導(dǎo)或確認(rèn)某些行為標(biāo)準(zhǔn)和行動(dòng)模式,以調(diào)整社會(huì)成員的行為方式,起到為天下“立規(guī)”的作用,進(jìn)而對(duì)個(gè)人“歸行”。法治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為所有社會(huì)成員劃清行為底線,它構(gòu)成了社會(huì)和諧的基礎(chǔ)。對(duì)于官員而言,最基本的底線是法治思維;對(duì)于百姓而言,最基本的底線是公民責(zé)任。
第二,以法治精神“立公”,重在倡導(dǎo)公共精神。法律是公共利益的載體,法治是公共精神的源泉。社會(huì)主義法治精神可以引導(dǎo)、認(rèn)可或強(qiáng)化某種價(jià)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社會(huì)共同體確立正確的價(jià)值取向,起到為天下“立公”的作用,進(jìn)而對(duì)社會(huì)“歸德”。最為重要的是,必須以法治來(lái)呵護(hù)公共精神。同時(shí),對(duì)損害公共精神的行為按名責(zé)實(shí),將其法律責(zé)任落在實(shí)處。
第三,以法治建設(shè)“立信”,重在樹(shù)立政府權(quán)威。 “法者國(guó)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本身就是一個(gè)政府向所有社會(huì)成員發(fā)出的有國(guó)家強(qiáng)制力保障執(zhí)行的公開(kāi)承諾。“行必信,信必果。”政府的公信力也最終來(lái)源于政府積極、主動(dòng)、堅(jiān)定而忠實(shí)地奉行法治,兌現(xiàn)它向社會(huì)成員的公開(kāi)承諾,起到為天下“立信”的作用,最終實(shí)現(xiàn)整個(gè)社會(huì)“歸心”。
- 中國(guó)司法的其它文章
- “公調(diào)對(duì)接”的開(kāi)展現(xiàn)狀、存在問(wèn)題及對(duì)策分析
——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qū)司法局為例 - “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法律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SWOT分析與對(duì)策
——以浙江省杭州市為例 - 全面依法治國(guó)背景下縣級(jí)司法行政機(jī)關(guān)職能履行存在的問(wèn)題及優(yōu)化路徑
——基于浙江省寧波市的實(shí)證調(diào)查 - 關(guān)于完善強(qiáng)制隔離戒毒工作頂層設(shè)計(jì)的思考
- 公共法律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框架下的司法鑒定制度改革*
- 更高質(zhì)量推進(jìn)上海律師行業(yè)黨的建設(shè)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實(shí)踐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