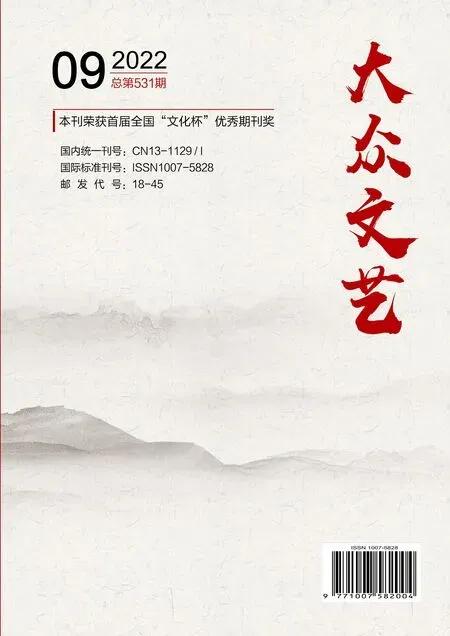孟子、荀子和董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究
(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12000)
一、引言
在人類原始時期,多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由“天”、“神”統治,所以禮本是祭祀神靈的行為、儀式,其價值在于獲得神靈的佑護。由于人類原始時期智識除開,神事與人事不分,且人事包裹于神事之中,所以作為祭祀規則的禮,同時也是指導人事的原則。也就是說,禮不僅僅是神人交通的準則,也演化為了人人關系的范式。禮,不僅僅是宗教性的神圣存在,同時也是社會性的世俗存在。直至階級產生,這種“祭神祀天”轉化為“少數人”的特權,神人溝通的這種宗教儀式代表著世俗的權力和等級名分,禮引申為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基本原則和政治制度。
春秋后期是禮崩樂壞的時期,也是“諸子之學(禮學)”興起的時期。當“禮”被視為神圣的存在,因其神圣的光環,禮治被視為是理所當然;而當“禮”的神學依據、神性的一面被剝奪,道德的審判與謾罵無法阻擋上下僭越的違反“禮”的行為的時候,“禮”存在合理性則需要理性的審視與智慧的觀照,禮的價值才進入人們的視野。要恢復或重塑“禮”的神圣性,其非從“天”這一范疇出發探討天人關系而不能成。所以,概而言之,中國文化核心之學問就是“天人之學”,即不僅僅以天道為對象,也不僅僅著眼于人道,而是著重研究二者的關系。它包括的問題主要有:天人能否和一?天人如何合一?天人合一的途徑是什么?
二、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孟子生活的年代比孔子大約晚200年,是一個列國兼并、戰事頻發的時代,也是具有社會政治抱負的士人施展其才華和實踐其社會抱負的時代。孟子認為,“士”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尚志”。而“尚志”的具體涵義就是“居仁由義”,士要以仁與義為目的。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這里,孟子將人心稱之為“仁”,將人路稱之為“義”,這實際上是說“仁”必須實現為“義”。所以,“仁”是道德主體,“義”則是其表現。亦或可以說,“仁”是體,“義”是用,任何道德行為都是由體和用兩個方面的。所以,仁義就成為了對個人行為與社會行為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任何的道德行為都是道德意識與道德規范合一的。
對于具體的道德行為,孟子又提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孟子·離婁下》)。所謂“由仁義行”,指的是自覺自愿地按照道德的自由意志去做合乎道德規范的事情;“行仁義”則是指做符合社會道德與社會規范的事情。顯然,前者強調道德的自覺自律,后者著眼于行為的后果。孟子主張“由仁義行”,將道德的自由意志作為判斷行為是否道德的根據,所以孟子是典型的動機論者。孟子之所以提倡道德的自由意志、宣揚動機論,那是因為在孟子看來道德的產生不是源自社會的需要,而是出于普遍人性,他將這種普遍人性稱之為“良知良能”。他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進而又對“良知良能”進行了具體討論。他提出,這種“良知良能”包含“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的此種基本道德“仁義禮智”就是由這四端派生而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只要經過后天的努力,使得“四端”彰顯出來,自然地就具備仁義禮智的道德品德。所以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但是人為什么會有這種“良知良能”呢?孟子訴諸于一種宗教意識,即天命。他繼承了孔子關于“天”的見解。在孔子那里,宇宙間萬物都是由“天”的意志或命令在起作用,但是對于天的內容,孔子沒有明確的概念進行表達。到孟子這里,明確的宣稱天命或天道為“誠”。因為在孟子看來,天是真實無妄的。天雖然是“誠”,是真實無妄的客觀存在,但天道之“誠”卻必須要體現和展現為人道,通過人來實現它。所以,孟子關于天道和人道的關系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下》)天道必須有待于人去“誠之”。天道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人的道德意識以及道德行為產生的依據,同時 ,這種天道之誠只有通過人的道德行為才能表現出來。這代表了孟子以及中國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的運思方式。
孟子解釋道德意識產生的依據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的:一是源于天道之誠,而是源于普遍人性。所以天道之誠與普遍人性之間的關系是他必須說明的。對這個問題,孟子通過“心”這一概念的引進來解決這個問題,他造性的提出“性與天道”相統一的問題。在他看來,性即是天道,天道也彰顯為性。天道是誠,而人是“思誠”。性與天道在心這里實現了統一,而在孟子眼里,“思”是人心所特有的功能,“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所以人要獲得關于天道之誠的知識,只需要“思誠”、“反求諸己”、“求其放心”,切身體會良心本心之發用,一切按照良心本心去做,人的行為就自然復合天道,人道也就實現了與天道合一。
在孟子的思想體系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貫穿在他思想體系方方面面。他提出的“盡心知天”說,有主張人們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的韻味,這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三、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
荀子,生活在戰國時期,長期以來被視為儒家的異端。他首先對傳統的“天命決定人事”、“君權神授”的唯心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首先應該區別自然界的規律和社會人事的變化,即“明于天人之分”。他指出,星墜、木鳴、日食、月食等只是自然現象,反對唯心主義者用來宣揚天命、上天譴告。他說:“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天論》)
荀子也強調,不應該把人世社會的變化和天命、自然規律相掛鉤。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而輟廣。”人們生活的吉兇和社會的之亂,與自然界本身沒有直接關系,更多的取決于統治者治理措施是否恰當。所以他說:“上明而平允,則是雖并是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致者,無益也。”(《荀子·天論》)
荀子對有意志、不可知的天進行批判之后,將自然看作是物質的,其變化只是自身的規律,并沒有任何神秘色彩。他說:“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圣人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
荀子雖然將“明于天人之分”,但是他堅決反對人在自然面前消極無為,所以他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認為,人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去掌握和利用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規律,造福人類。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同上)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
四、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
董仲舒是漢代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子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
“天人感應”源出于董子向漢武帝獻的“天人三策”,確立于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觀會議上,以《白虎通義》為標志。董子繼承了孟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也發展了“天人感應”理論主要包括“人副天數”、天人同類、天人相應構成。首先,他說:“天地之符,一陰一陽一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一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春秋繁露·卷十三》)人的形體和天道之運行是相符、相副的。其次,他舉例說:“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春秋繁露·卷十三》)這就是同類相動。最后,他認為人的喜怒哀樂與春夏秋冬四時相應,這也充分地說明了天人感應。他說:“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郁滯一也,天終歲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春秋繁露·卷十三》)
五、總結
孟、荀、董三子都有著不同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思想,但其理論旨趣都體現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諧共生。而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極大地豐富了人的物質生活,但只是豐富了人的物質生活。其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的物質家園,而且使人喪失了精神家園。要改善我們的物質家園,重建精神家園,需要我們發覺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發揮文化的“文治教化”作用,為我們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思想資源、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從根本上,是封建社會生產方式下的產物,而且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論證封建社會秩序的合理性。對此,我們應當持批判的態度,使之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建立時代的、大眾的文化提供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