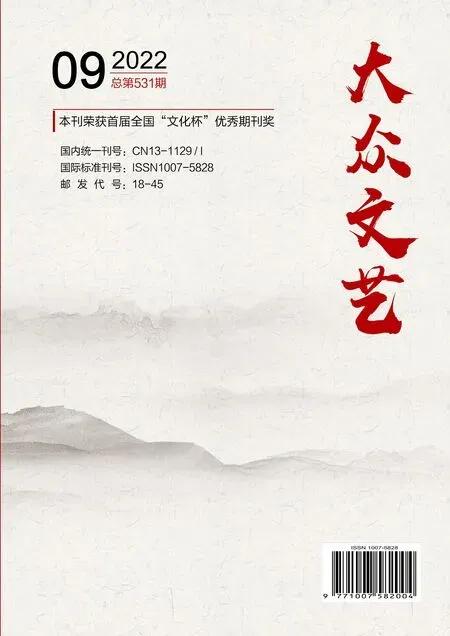以石濤“心識一畫”分析其賦予筆墨皴法的意義
(浙江師范大學 321004)
一、石濤對皴法的建立
石濤在其《畫語錄》皴法一章中指出皴法的 運用是為了表現山川的獨特形式美,表現山川的本身具有的造型特性,較前人的實踐和理論更加全面和具體,他強調皴法的運用要表現出山川不同的特征,體態和造型,謂:“筆之于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山的形態萬千,則皴法需要符合山川自具的形貌,要表現出山川不同的肌理關系和塊面關系,他反對“非山川自具之皴”,認為皴法應該配合山川的特質即“峰之體異,峰之面生”,才能描繪出形態各異的山峰,追求“峰與皴合,皴自峰生”山石效果。石濤本人皴法從真山中來,并且能因山而異,他強調不拘于古,法自我立,正如他的題跋“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心期萬類中,黃峰無不有”,在自然觀的映射下,與山水建立情感交流,達到一種融渾的狀態,形成從而自然而然達到山水我所有的境界。
二、“一畫”與“一畫之理”對于筆墨的意義
1.筆墨表現與悟“道”
石濤的“一畫之理”具有道學上的意義,在道家哲學中,道“先天地而生”、“自本自根”,道構成了萬物存在的終極依據,老子所說的“道生一”,到落實到宇宙混沌未分的狀態,即是“一”,道家哲學中,“一”是道生萬物的中介,是最初的“有”。道”先天地而生”、“自本自根”,“道生一”,道落實到混沌狀態即為“一”。石濤在《自書畫語錄》中分析到,“一畫生道,道外無畫,畫外無道。畫全則道全。雖千能萬變,未有不始于畫而終于畫也。”在本根意上,“一畫”即“道”,即“一畫之道”。石濤在《畫語錄》中提出,“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周易》中“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乾旋坤轉”即宇宙的運化,萬物資始資生,因而就是“一畫”。王夫之在論述“實有”論時說“資始資生之本體也,故謂之道。”因而可以發現,“一畫之道”具有承載萬物“資始資生”的周流運動的特點,其本質在于表現萬物的生生之氣,“一畫”合理運用可以表現出山水的靈動和生命。筆墨為“一畫”所統攝,同時“一畫”也通過筆墨得到落實。因此,筆墨與“道”的精神表現也有體用關系。石濤首先強調筆墨的渾然一體,石濤認為“筆與墨會,是為氤氳,氤氳不分,是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用氤氳說明筆與墨交融無間的神韻,同時突出了筆墨對山川內在肌理和氣勢的作用:“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筆墨意義不僅僅在于機械性地描繪一丘一壑,還在于表現天地萬物流動的氤氳氣勢,說明了筆墨承載的生命意味。唐岱在《繪事發微》中說“氣韻從筆墨而生,或取圓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肯定了筆墨造化傳神的功能,石濤通過反對“形式不變”、“畫法不變”進一步說明筆墨的意味:“且也形式不變,徒知鞹皴之皮毛,畫法不備,徒知形式之拘泥。”之后,他又進一步要求畫家練習腕力來“化”解筆墨成法,他說“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通過練習使筆墨脫離成法和“習氣”,才能達到“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的境界。筆墨為我用,非我為筆墨用,書畫乃我作之書畫也。1石濤繼續說“懸腕既成,無論沉著空靈,欹斜操縱,始有措手處”,“至落筆時,勿促迫,勿怠緩,勿陡峭,勿散神,勿太舒。”畫家心使腕運,“脫塵而生活”自能達到“無法而法”的境界。在題畫中,他總結道:“出筆混沌開,入拙聰明死。理盡法無盡,法盡理生矣。”石濤明確提出畫家需要將自己的真心情感投入、對于宇宙內在之理即“一畫”的領悟,破除法的束縛,才能將“氣”通過筆墨表達在畫面中,在畫面中體現“一畫“的精神,這符合他分析的“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后廣其用。”
2.畫家的學識氣質
在《大滌子題詩畫跋》中,石濤提出“山水真趣,皆是入野看山時,見他或真或幻,皆是我筆頭靈氣。”這里的靈氣,生氣,來自于畫家的學識、品格,“人品不高,用墨無法”,畫家品格之高,則筆下自然生動,所謂“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筆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石濤受理學重視“格物致知”和強調大自然之中有流轉不息的生命之“理”的影響,認為筆墨的生氣離不開畫家的書卷氣,即士氣,他說:“每圖畫一幅,忘坐亦忘眠”,石濤崇尚士人精神氣概,表現為畫家作畫時慘淡經營的嚴肅態度,致力于說明修養學識的重要性,注重在繪畫中“以畫載道”,因此石濤將“載道”作為筆墨的根本目的,而他所說的畫家的“盤礴睥睨之氣”,需要不斷獲得學識修養,而石濤將修身養性歸結于“智”,他說“得筆墨之會,解氤氳之分,作辟混沌手,自成一家,傳諸古今,是皆智得之也”,畫家重視“積學”即“智”,才能充分在筆墨之中融入真摯的情感,將自身的性情之“氣”通過筆墨呈現于繪畫。“氣”是畫家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本源,曹丕說:“文以氣為主”,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藝術家的藝術創造活動的展開,即“氣”的運化,石濤明確將“氣”和作為創造主體的“我”相連——“皆是我筆頭靈氣”,突出“我”是學力深厚,能夠感通天地之人,我之所以能破除“法障”,正因為“了”明“乾旋坤轉”之理和萬物周流之氣,“我”是具備通天地一氣而表現神韻能力的人,于是他總結道“筆墨乃性情之事,于依稀仿佛中,有非筆墨所能傳者”。
通過石濤的筆墨理論將筆墨皴法提升到了與宇宙萬物自然之”理”與生生之“氣”相同的高度,同時突出了“我”具有通天地、使筆墨的權威性,這就從筆墨生發的角度將天、地、“我”三者連接起來,為后世重視畫家重視人格修養、“以筆墨寄吾神”提供了依據。
三、石濤筆墨理論對后世的影響
1.對黃賓虹“五筆七墨”和“渾厚華滋”的影響
首先,黃賓虹受石濤“筆與墨會,是為氤氳”的影響,同樣重視筆墨的氤氳統一,他作畫先勾勒,后干筆皴擦,層層積染,達到“渾厚華滋”的效果,他研究破墨積墨法,追求墨中見黑,黑中見亮的“亮墨”效果,并繼承了石濤“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的精神,在藝術實踐中總結出了自己的“五筆”、“七墨”法,認為用筆要去除釘頭、鼠尾、蜂腰、鶴膝四病,追求“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的效果。2創造出了縱橫恣肆而疏密有致的畫風,其“黑、密、厚、重”的藝術風格,黑而不重,密而不悶,正是石濤所說“黑團團中墨團團,黑墨團中天地寬”的體現。同時,他還提出了作畫落筆的具體方式,“作畫落筆,起要有鋒,轉要有波,放要留得住,收要提的起。”這是對石濤提出的“懸腕”的進一步闡發,黃賓虹進一步說明運腕的重要性,他認為欲求畫學之實,“必專練習腕力,終身不可有一日之間斷耳”,說明了刻苦練習、修身養性的重要性。總結筆墨經驗的同時,黃賓虹并不拘泥于古法或者成法,在《黃賓虹畫語錄》中,他指出“畫家欲自成一家,非超出古人理法之外不可,作畫當以不似之似為真似”,是對石濤“變幻神奇懵懂間,不似之似當下拜”的思想延續,規矩可以為人所認識,但對理法的認識和變通要由心得,是故繪畫“本于天而全之于人也。”
2.對于潘天壽“師造化”的影響
石濤認為筆墨的根本目的是表現“道”,畫面不僅僅在于抒發感情,同時在于表現出“人“天道”、“畫道”,即“一畫之道”,潘天壽認為筆墨“取于物,發于心,為物之像,心之跡”,石濤認為“蒙養”是筆墨的依據,潘天壽在此基礎上強調人心的作用,體現石濤所說的“隨筆一落,隨意一發,自成天蒙。”
石濤的“蒙養”,既包括畫家對自然先天的感受性也包括后天的學識修養,而潘天壽提出“畫格,即人格之投影”、“畫事,須有天資、功力、學養、品德四者兼備”,修身的同時又拋棄物欲干擾,正是石濤“先思其蒙,復審其養”而的真諦,如此筆墨才能達到“開蒙而全古、盡變而無法”的自由化的境界。潘天壽不僅繼承了石濤“載道”的精神,同時注重通過“學”和“受”領悟筆墨運行之道。他說“不學,無以悟常,不受,無以悟變,然此中關鈕,還在心胸耳”,筆墨之道既要注重自然內在統一的生機,同時又要通過學識的積累以達變通,以心胸之性情運筆墨,在尊重自然之理的基礎上達到“化境頓生”的境界,是對石濤借古開今的進一步概括。
可以說,石濤的筆墨理論中強調脫俗、獲于“智”以追求筆墨清高的思想,豐富了筆墨之道的重要內涵,對山水近代化具有極大的影響。
注釋:
1.俞劍華.《中國歷代畫論大觀》[J].美術觀察,2018.5.38.
2.蘇薈敏.《石濤畫語錄美學思想研究》[D].復旦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