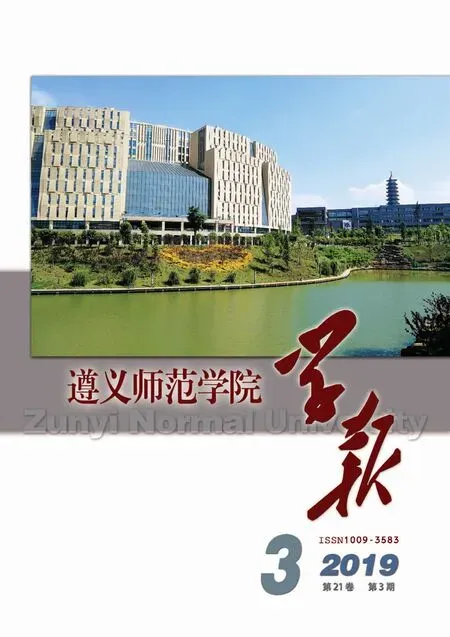莫迪亞諾小說尋找主題生成模式探微
郭昆侖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西安710119)
法國作家莫迪亞諾自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至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國內外關于莫迪亞諾的研究成果已不計其數,研究范圍覆蓋了其二戰時期的猶太記憶及后現代下的敘事策略的展現等多個方面,充分說明了莫迪亞諾小說中所蘊藏的生命力。莫迪亞諾創作初期的“占領三部曲”傾向于對自身處地定位的形而上思考,并將這種對個人的思考置身于宏大的歷史背景中,使之能更好地凸顯個人生命的本質。由于莫迪亞諾自身很特殊的猶太身份,猶太身份的書寫時不時地要帶進文本之中,這在其最初創作的《星形廣場》(1968)、《夜巡》(1969)、《環城大道》(1972)三篇小說中都有所體現。猶太身份進入文本的途徑比較細微和隱秘,比如在《夜巡》中同時受雇于總督和中尉兩個互相對立的團體的“我”想從兩方同時得到利益,“我”在兩方的壓力下識破了他們的詭計,“這些人雖分裂成了兩個對立派別,但早已秘密結盟要毀掉我。總督和中尉不過是一個人。我自己不過是一只驚慌失措的飛蛾,從這個燈火飛向那個燈火。每次都燒焦點翅膀。”[1]P51因此,將來世界的命運與“我”無甚關聯,只求能夠無煩惱也無憂愁地隨波逐流。[1]P79于是,當“我”在兩方的偽裝身份被揭開的那一刻,“我”毫不猶豫地予以承認,中間充斥著無奈的感傷和命定的悲劇感,身份的無所歸依在這里展露無遺。莫迪亞諾在后來的文本創作中雖然極力抹去其特殊的猶太身份,文本中卻仍然充斥著無根感和漂泊感,反而更進入到了一種人生普遍意義上的身份或歸屬感的質詢。這種對普遍意義上身份的質詢在莫迪亞諾的小說,尤其是關乎小說的尋找主題有著最深切的體現。
一、尋找的契機:三種關系模式
莫迪亞諾小說主人公在尋找的初始階段始終處于某種“關系網”之中,這里要么是關乎個人,要么是與個人有直接關系,要么凸顯的就是時代的群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會像磁鐵一樣吸附在周圍,相識、相戀、相愛和相知,但終究有一天,“每個人都在一條不同的時間走廊里”“如同兩個人被魚缸玻璃隔開那樣”互相聽不到對方的聲音[2]P116,然后關系開始破裂、分離,但分離恰好又是尋找的開始。《暗店街》(又名《尋我記》)是主人公尋找自我經歷的代表作:主人公“我”十年前突然得了遺忘癥,忘卻了自身先前的記憶,偵探于特幫助“我”辦理了一份假戶籍(附帶身份證和護照)——居伊·布朗。借用于特保留的年鑒、電話簿等探尋自身歷史的種種,“我”的面孔在各色人物面前轉換變色,“我”完全需要外人來確定“我”個人本身,自我注定不能脫離于他人對“我”的“海灘人”印象中;“我”個人的經歷仍需要本人加以拼貼、組合和推演,這種選擇性或間歇性記憶的方式,既有著現代主義思潮下的人無法找到自身歸屬的失落感,也有著個人對過去沉痛回憶的不堪回首。
而尋找與主人公有直接關系的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親人的尋找,另一類是對戀人、朋友的尋找。《環城大道》中,主人公“我”由一張照片想追尋父親的身影或足跡,生活之父的缺失造成“我”精神之父的不在場。莫迪亞諾小說中把父母并置在一起并非是想尋求父母之間的一種絕對的對立態勢,他們全然處在同一層級的地位上,在生活中的缺席致使兒女缺失家庭的溫暖而走向逃逸的邊緣,伴隨著兒女的長大成人,這種對親人的尋找帶有自我尋根的意味。毫無疑問的是,莫迪亞諾小說主人公都很年輕、流浪和無職業,縱然有著看似牢不可破的三人家庭關系的組合,仍然暗示了家庭關系的松散。《地平線》中的主人公博斯曼斯和《青春咖啡館》中的主人公雅克琳娜都有對母親或親情的逃離,家庭中的親子關系永遠處于不確定、漠然和對立的邊緣。《一度青春》中開頭有一段詩意生活的描繪:“她和路易坐在木屋的涼棚下,遠遠觀賞他們一對兒女:他們正同維特爾多的三個孩子在草坪上奔跑。兒子才五歲,左胳膊打了石膏,但似乎并不妨礙玩耍。”[3]路易和奧迪兒十五年前的生活是“驚心”,現在卻比較“安逸”,這段安逸的場景可以說是莫迪亞諾作品中鮮有的一個亮點。可以說莫迪亞諾小說中“精神之父”的缺席讓主人公像一株無根的浮萍,表面看似光鮮艷麗,內心實則已經千瘡百孔。“我關注這些被社會遺棄的人、生活在世外之人,正是要通過他們確認我父親的不可捉摸的形象。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但我要編造出來。”[4]P50通過那么一種“編造”的技巧,“我”確定了自己的“精神之父”的地位,這樣也才能為當下的生活找到更為堅實的基礎。對朋友和戀人的尋找,既是向青春美好歲月的致敬,又是向階段性青春的告別,個人的記憶的書寫依托于對他人的記憶之上,通過對他人或與他人相交叉關聯的歷史來激活對自身經歷的回憶,以此來確認自身生存的意義。《凄涼別墅》《多拉·布呂代》《夜半撞車》和《地平線》等即是此類代表作。《夜半撞車》在“我”即將步入成年的一天深夜,一輛轎車撞向了“我”,“我”被送往診所,出診所后,“我”一直追索轎車主人雅克琳娜的路程,并在尋找的過程中回憶起了事故前生活的點滴。看似這場車禍是致使“我”失卻了一段時間記憶的“罪魁禍首”,但卻毫無疑問地扭轉了“我”車禍前萎靡頹敗的生活,由此“我”開始了規劃往后生活的企圖,這便是這場車禍的意義。主人公通過與自己有直接關系之人的尋找,其實更大程度上在他人身上尋得了自己,重新賦予個人生活以意義,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激活個人的生命體驗。
最后,這種關系模式還有對時代群像的展示。《星形廣場》《夜巡》《環城大道》《一度青春》和《地平線》等都是這方面的題材,尤其是以莫迪亞諾的“占領三部曲”為代表。莫迪亞諾的“占領三部曲”從個人與歷史的關系入手來把握時代的群像,通過一種情境的書寫展現歷史大環境下的個人生活。《星形廣場》序章說是寫的“猶太人故事”,文中鋪開展現二戰時猶太人的歷史,莫迪亞諾這里對二戰存留的記憶與普魯斯特的記憶有著絕大的不同,莫迪亞諾本人也認為,普魯斯特展現給我們的是本有穩定的社會,“普魯斯特的回憶讓過去在最些微的細節中重現,就像一幅活生生的畫”,現在正是由于對記憶的失憶和忘卻,“我們只能捕捉到一些過去的碎片、斷裂的痕跡,飛逝的、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5]P67李玉民先生認為,“莫迪亞諾和普魯斯特的文學創作,雖然都以記憶為內動力,但是一個是記憶的夢游,一個是記憶的追尋,一個呈現虛幻,一個體現真切,兩者有本質的差異。”[6]這樣來看,莫迪亞諾筆下不論是關乎個人經歷的尋找,還是與個人有直接關系之人的尋求,都有一種展現宏闊的歷史和凸顯時代群像的沖動。其實,三種關系模式有時又可相互交叉和聯系的,不論以何種關系模式開始主人公的尋找,都有對時代背景的展現和歷史集體群像的揭示,這樣才有利于主人公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堅定生存下去的勇氣和信心。對各種人及各種形式的追索,其實緊追不舍的只有我們自己。[4]P106主人公在尋找的過程中當然也充滿了艱難險阻,這些阻礙正是莫迪亞諾筆下“點石成金”的時刻,其本身早已形成了一道迷霧中的風景。
二、尋找的途中:霧中的風景
主人公始終處在尋求自身生存意義的三種關系模式之中,中途往往充滿著神秘和恐怖的氛圍,這當然與莫迪亞諾偏愛偵探小說不無關系,但同時也反映出對先前記憶的每一步探尋可能真如在迷霧中前行并觀賞的兩邊風景。
(一)光線、電話鈴和人名
《青春咖啡館》中偵探受雅克琳娜的丈夫讓-皮埃爾·舒羅的委托尋找妻子的蹤跡,兩人交流完有關雅克琳娜的信息后定時開關的照明燈突然熄滅了,這時偵探式的想象發揮出余地來。[7]P42偵探在追查雅克琳娜的過程中也有遭逢到燈光的想象,“更確切地說,我感覺到她就在這條燈火如閃爍的信號燈一樣輝煌的林蔭大道上,我分辨不出這些信號燈,也不知道它們是從哪個遠古年代發給我的。而這些燈火在土臺的黑暗中顯得更加璀璨奪目。既璀璨奪目又飄渺悠遠。”[7]P54其實,唯有在暗處才能觀察光影中的一切,思考也才能更豐富,“我是屬于那種黃昏時分在池塘邊停住腳步的人,是在觀看死水所有的動靜前,讓自己的眼睛適應昏暗光線的人。”[8]P85電話在互相分離的人們成了互相聯系和交流的紐帶,這時不論是《夜半撞車》中神秘的“帕藍”旅館電話鈴,還是《地平線》中博斯曼斯夢見之前辦公室響了許久的鈴聲都成為久已失聯的人與人溝通的一種媒介。人名(含戶籍和護照)在莫迪亞諾早期小說中只是作為作者處理的一個難題,之后人名只是作為一個代號,作者不會對人名有任何懷疑和疑慮,敘述者讓讀者也信以為真,人名的追索在這里失去了先前所賦予的光輝。
(二)宗教、集會等集體性的催眠
《夜半撞車》中博維埃爾“博士”聚會,《青春咖啡館》中羅蘭和雅克琳娜參加神秘學。“暗物質”才是這里想要追尋的,“在確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著所有已變成暗物質的東西:短暫的相遇,沒有赴約的約會,丟失的信件,記在以前一本通訊錄里但你已忘記的人名和電話號碼,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卻不知道有過這回事”[2]P2,而其顯現的只能是冰山一角。乙醚在《夜半撞車》中既是致使主人公發生車禍事故并失憶的一個因子,當然也成為回憶的一個出發點和引起回憶的一條線索,即想要對之前模糊記憶的尋根溯源。《青春咖啡館》中雅克琳娜偏頭痛的時候有買維佳寧和乙醚,并和亞娜特吸叫“雪”的白色粉末,“過了片刻,那東西就讓我產生一種神清氣爽和輕松自如的感覺。我堅信在大街上侵襲我的恐懼和迷茫的感覺可能永遠也不會在我身上再現。”[7]P79
正如譚立德在《夜半撞車》譯者前言認為,“莫迪亞諾的小說并沒有什么情節,其真正的魅力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在故事所傳遞和調動的氛圍……故事中常常設置懸念,提出疑問,套用偵探小說的手法,緊扣讀者心弦,并通過氛圍的渲染,來表現作者的寓意。”伴著神秘的氣息,并從中建構著莫迪亞諾個人的態度,即在一種對似是而非事實的把握中抵達回憶的終點。莫迪亞諾想在平凡的東西中,在背景材料中尋找到一種超現實的東西,認為事物的真實性反而就隱藏在這種超現實當中,“有一種磷光現象,它并非必然地來自于我,而是來自于這件事情本身。”[9]其實,莫迪亞諾認為“消失、身份、時間都和大城市的變遷密切相關”,顯然,現在的城市不同于巴爾扎克筆下的巴黎、狄更斯筆下的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圣彼得堡等作家筆下城市的書寫,而是充滿了各種神秘的可能性。[5]P66毫無疑問的是,莫迪亞諾通過對種種氛圍的神秘描寫既成就了莫迪亞諾創作的文學特質,同時又發現了小說的存在和書寫何以可能性的問題,這種尋找途中的可能性直接伴隨著所要追尋的結果。
三、尋找的結果:或此或彼的模糊書寫
(一)浮動的敘述者
莫迪亞諾小說筆下敘述者常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視角出現,敘述者基本上等同于作品中主人公的視角,“敘述者和人物知道得同樣多,在人物對于事件沒有找到解釋以前,敘述者也就不能向我們提供解釋。”[10]首先是主人公家庭關系的歸屬問題。主人公在小說文本中大都沒有確定的名字,有關家庭的線索只隱晦穿插在文本中,主人公像“海灘人”一樣是不確定的、無所歸依的個體,這種浮萍似的主人公帶來的只能是整個尋找過程的茫然無頭緒和與之相伴隨的一種無所憑依的狀態,這樣使得“小人物”的書寫成為莫迪亞諾筆下一道亮麗的風景,雖則能增加讀者的認同感,但同樣展現了主人公缺乏一定固定社會關系的根基。余中先先生認為,莫迪亞諾在《暗店街》中把尋找自我的主題發展到了極致,主人公喪失了姓名、履歷、職業、社會關系等全部外部特征,真正成了一個飄忽的影子。[11]這樣,以一個“不健全”的人的視角看待世界其實是不很確切的,處處是充滿懷疑和不完滿的。其次是主人公的限知視角。限知視角的使用一方面增加了尋找過程的神秘性和難度,另一方面同樣也使得所追尋到的事實呈現出模糊不清的狀態。《環城大道》中父親想拋棄“我”獨自生活,忍心把“我”推下火車道,幸好有人拉住了“我”,在警察審問的過程中,“我應當承認明顯的事實:有人要把我推下火車道,讓列車把我碾成肉餅。推我的人,正是坐在我身邊這個南美人模樣的先生。證據:當時我感到他的戒指觸到我的肩胛骨。”[4]P69他們是真正的父子關系嗎?是敘述者固有的策略或者是在玩什么伎倆欺騙讀者嗎?……這些問題沒有答案而且也不可能會有答案,讀者只能進行無盡答案追索的循環。《青春咖啡館》從學生視角、偵探視角、羅蘭視角展開對雅克琳娜的點點追憶,雅克琳娜在這里就像是一個被觀察者,那么雅克琳娜個人的視角又作何解釋呢?《青春咖啡館》有四個同級的敘述者,其中雅克琳娜的視角在其中處于主導作用,另外三個視角對雅克琳娜的視角所展現的內容形成輻射或佐證的作用,雅克琳娜到底是何種真身仍然值得探究。敘述者和主人公的感覺是否可靠,真實到底掌握在誰的手里?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莫迪亞諾像艾麗絲·門羅一樣“……較多采用的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她通過直接敘述或其他人物間接介紹等現實主義方式將人物的外貌、背景、職業、性格及個人經歷等一一呈現,使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在我們生活的周圍隨處可見。”[12]莫迪亞諾看似是一種對現實人物的真實呈現,我們仍然把握不住人物的真實形象。也許,這也就是莫迪亞諾想引領我們思考的寓意所在,而這也恰是莫迪亞諾所要引導讀者注意分析的關鍵。
(二)模糊與精確的時空觀
莫迪亞諾小說的時間觀可以說是對現在時間的延續,現在時間并非是循環輪回的時間觀,“我”之所處的現在是流動的現在,“我”由現在回溯至歷史的記憶,過去的時間和現在時間發生重合;當“我”在追索屬于過去的時間時,現在的時間又和未來的時間重合。現在便成了過去和未來進行交流的場域,回憶在這三重時間里能自由轉換,記憶在這三重時間的重合中全然沒有了與過去和未來的分界。因此,過去由于時間分界的消失與現在難分難解,“我”雖然能隨時跨越這三重時間的記憶,但對過去的專門記憶卻變得模糊而不可追尋,逝去的時間便無理由地逃遁而去。莫迪亞諾小說充滿著地理空間的互文性,其空間詩學架構在對巴黎全景的整體構思上,并運用空間分割、切換主人公的經歷和記憶的方式使得主人公在這種被切割空間中的逃逸變為可能,巴黎的星形廣場、環城大道、香榭麗舍大街、咖啡館等完全成了莫迪亞諾自由馳騁想象的園地,巴黎的瑣細而又繁復的街道、歷史與現在交匯的遺跡、光與影的變幻在莫迪亞諾的筆下展露得巨細無遺。各色人物在巴黎的時空里穿梭而相互不識,“時間走廊”和“固定點”的時空錯位全然找不到一個在靜處可觀察的一點,充滿著變化和各種存在的可能性,這與現代社會節奏的加快密切相關。莫迪亞諾想通過尋找逝去的回憶抵制時代過快發展的現實,莫迪亞諾對十九世紀的小說充滿著一種“懷舊的意緒”,認為十九世紀的時間過得要比今天要緩慢,十九世紀時間的那種緩慢和小說家的寫作恰好是合拍的,那時的作家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和注意力搞好創作。[5]P61結合第一部分對關系模式的論述,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理解:莫迪亞諾所盼望建構的是一個不用識辨他人的歷史就能和睦相處,大家雖互相存有防備心但馬上就能互相融入對方的真實理想的社會,每個人的背景關系雖則復雜,但卻能相處融洽,各取所需的現實。尋找的過程既有對自己、他人等的尋找,同時又把這種尋找嵌入到有關巴黎的時空觀中進行具體的展現,從而使得尋找的過程變得既具體又模糊,小說中的人物是否都尋得了自己的回憶,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并且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義?不僅主人公在追索,我們也在尋找的邊緣,我們與主人公之間好像也在發生著某種時空的錯位和置換,以此為我們指明繼續生活的方向。
四、結語
莫迪亞諾在創作觀念上是少有的幾十年如一日的題材形式堅持如一的作家,其筆下的主人公始終處于尋找的漫漫長途中。無論是對自我的尋找,親朋的尋找,還是對時代群像的考察,都是想定位自己的位置,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途中經歷的像是在欣賞著迷霧中的風景,并極力向我們展現了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吳岳添先生認為,莫迪亞諾小說中虛實相間的創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小說吸取現代小說的結果,“他的小說以雖然虛構卻真實可信的故事來表現生活的不安和危險,由此形成了一個既確實存在又變幻不定的世界。”[13]但莫迪亞諾筆下展現的難道真正是所想要展現給我們的真實?昆德拉在對海明威進行分析時發現了“現在”,認為人只在過去的時間才能認識現實(記憶中的現實),回憶并非是遺忘的對立面,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14]“現在”具體的情境由于時間的退場或缺席轉變成為過去被講述的抽象,尋找失去的時間在莫迪亞諾的小說中變成了對抗遺忘的方式,這種碎片化的敘事很難讓人想到是具體的現實回憶,這就像“莫里森的小說充滿著分裂的故事片斷,她的敘事者從不連貫地講述故事,而是偶爾進行插話,隨后便消失在小說的進程中,讀者所要做的是積極參與到小說的碎片敘事中,與作者一起建構。”[15]
《夜半撞車》中披露主人公追尋的原因:盡管“我”出身卑微,但追尋或許能讓“我”發現“并不了解的自己生命中的整整一個部分,一個在流沙下面的堅實的基礎”[8]P104,認為生活要比想得要簡單的多。個人通過回憶發現了未來,意味著尋找的并不僅僅在于結果的撲朔迷離和這個不確實的世界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重新激活個人的生命體驗,然后能讓人們恢復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