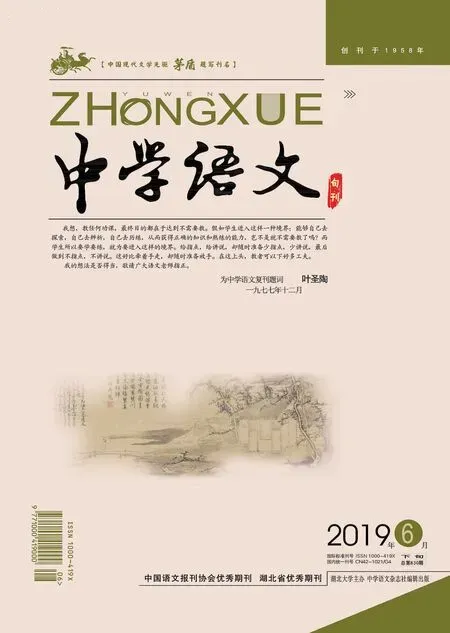俞平伯語文教育思想初探
金傳勝
俞平伯先生素以詩人、散文家和紅學家聞名遐邇,然與許多現代文人相似,他亦長期投身教學教育事業。1920年秋, 剛從北大畢業不久的俞平伯赴杭州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國文教員,其教書生涯由此開始。 1922年暑期受浙江省教育廳委派, 俞平伯以視學的名義前往美國考察西方現代教育近四個月, 以期運用到中國的教育實踐中。 嗣后,俞平伯主要執教于高等學府,歷任上海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國文系講師、教授,一邊講授古典文學課程,一邊從事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可謂三管齊下。 緣于上述這些經歷,俞平伯對教育問題不乏個人的獨特認識,并時而通過撰文、講演的方式予以表達。 1929年3月,俞平伯曾作《教育論》,以雜文的筆調表達了對于教育與人性關系的思考,提出教育上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觀”。 1948年9月,俞平伯曾在北平電臺作題為《孔門的教學法》的廣播演講, 對孔孟施行的問答教學法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講解與闡釋。 具體到語文教育方面, 俞平伯曾寫過《中學語文教學和古典文學》等專題論文,亦在隨感等其他文字中就語文教育的某些問題表述了自己的見解。 同時他還與朱自清、 葉圣陶等語文教育家過從甚歡,是《中學生》《國文月刊》的長期撰稿人。 本文擬梳理、介紹俞平伯對語文教學提出的一些主張,并簡要評述其對當前語文教學的啟示。
一、關于語文教學的任務
1945年底, 北平廣播電臺邀請俞平伯向聽眾講演《讀書的意義》,講稿發表于次年1月。 文中揭明“讀書的真意義,于擴充知識以外兼可涵泳性情,修持道德,原不僅為功名富貴做敲門磚”。 這雖然是就讀書的意義而發,實則也適用于國文教育。 緊接著,作者談到二三十年以來國民國文程度低落的問題,指出這“不僅象征著讀書階級的崩潰,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民族的前途,國家的生長”。 國文程度低落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別字廣泛地流行著”,即文字教育的成效不大。 俞平伯對此表示擔憂,因為“方塊字的完整,艱深,固定,雖似妨礙文化知識的普及, 亦正于無形之中維護國家的統一與永久”。 也就是說,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屢受侵擾而團結一致, 華夏先民的典籍智慧之所以能歷經千年而流播不輟,方塊文字(漢字)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假如當初使用的是音標文字,中國的國運定然更加坎坷。所以在作者看來, 文字教育的失敗表面上只是一般國文水準的低落,其實已損害到民族國家的前途。 俞平伯的講演時間距離抗日戰爭的勝利僅三個多月, 聯系到日本軍國主義曾在中國推行日語奴化教育的慘痛史實, 他的上述論調實非聳人聽聞, 而是具有深長的意味。 隨后,作者對學校教育中“聽講的時間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課業, 有如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幾人” 的現狀提出了批評, 并提議解決社會生計問題,改革教育考試銓敘各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如何在中小學各門課程中開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是教育界十分關切的論題。 1951年3月22日《人民日報》于第三版刊出江山野的《加強語文課的愛國主義內容——對中學語文課本的一些意見》,批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語文課本缺少愛國主義內容。 4月21日,葉圣陶、宋云彬等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義發表 《語文課本里的愛國主義內容——答江山野先生》予以回應。 1952年1月,《語文教學》雜志發表俞平伯的《語言文學教學與愛國思想》。 在“附記”中他解釋因“語文”二字指語言文字還是語言文學,有時會發生混淆,所以本文不用簡稱。 這表明作者眼中所理解的“語文”主要是指“語言文學”。 此文旨在討論如何通過語言文學的教學, 啟發青年學子們的愛國思想, 即視愛國教育為語言文學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希望在語文教育中滲透愛國主義思想。 文章認為,語文教育中若想真正落實愛國教育, 不能僅僅依賴口號宣傳,進行空洞的說教,而應該聯系實際,恰當選取與運用相關語言材料。 作者指出以下三種材料均可選用:一是“凡說中國有什么偉大的,可愛的,可敬的”;二是“凡高揚中國人民大眾的歡樂的,申訴以往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痛苦哀愁的, 即是能表現人民的生活實況的”;三是“凡今日正確地在思想上作領導的文字”。 不過由于特殊的時代氛圍與寫作背景, 文中標舉的愛國主義思想是有所限定的,即與“國際主義”與階級立場緊密結合。 本文的一些看法有其時代的局限性, 難脫“應時應景”之嫌疑,但其探討的語文教學中如何實施愛國主義教育這一話題始終未曾過時。
二、關于中學語文課本的編選
1947年,葉圣陶在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組織了一期“中學生與文藝”筆談會,就“語文教育與文藝教學的關系”等話題邀請有關人士執筆。 俞平伯應約撰寫《談“中學生與文藝”》一文。 文章寫道:“中學的國文課本我看得極少,似乎太深太雜,有些我簡直沒有讀過。選錄的標準,應該偏重思想的清楚正確,而文字的淺顯次之。 文藝的涵養在中學的階段里亦應該有,似可選錄詩歌。 ”可見在俞氏看來,中學國文課本中選文的選錄標準,應首先注意思想的清晰正確,旨在進行思想的訓練,文字的淺顯則次之。 選錄詩歌則裨益于中學生文藝涵養的提高。 在談到 “古典作品與現代新寫實主義作品,就今日中學生說,哪一種尤其切要? 還是兩者不能偏廢”這一問題時,他說:“古典作品與新寫實作品自不能偏廢。 老實說,古典的分量重些,只是時代已差得太多,教學多感困難。 ”并且強調:“古典作品宜分別觀之,雖合于我們現代的標準很少,但亦不能因噎廢食,故選材第一,教法第二。 ”即認為雖然合于現代標準的古典作品不多,但不能劍走偏鋒,忽視古典文學的價值;在語文教學中要關注古典作品的選材問題, 選材如欠考慮,教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在選材精當的條件下,教師還應當“洞知選家之意”,在洞察編者意圖的基礎上再鉆研教法。
在《中學語文教學和古典文學》(1953)一文中,俞平伯從“發揚愛國主義的教育”和“創造人民的新文化”兩個角度出發, 認為古典文學在當時的中學語文教學中應得到相當的重視。 他首先批評現行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古典文學部分的編選在質上、量上、系統上都很不夠。 隨后他重點論述了中學語文課本中古典文學的選材問題。 他建議中學語文教材在選用古典文學時不宜太狹、不宜過短和不宜太少。 所謂不宜太狹,指應適度地放寬編選的標準,有人民性、革命性的當然要選,其他具有現實主義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類作品也可選入, 表現祖國山河壯美的篇什亦可酌選。 所謂不宜過短, 乃作者以為當前語文課本中所選文言作品篇幅太短,既不利于表現我國古典文學偉大的形象,又不利于教學的開展。 他提議教材中應選一些篇幅適中的,稍長一些的,讓長、短互相配合。 對于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而言,這樣的安排要比只選短文來得經濟、有效。 俞平伯的第三個看法是語文教材中的古典文學作品不宜太少。 首先,古典文學歷史悠久,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需要我們去繼承弘揚。 其次,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白話與文言不是彼此孤立的關系。 作者強調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并非憑空產生,實際上是數千年古典文學傳統的賡續。 不過編選教材時古典文學部分不能簡單地附在現代文學的后面, 而應盡量體現古今文章的流變、文學的發展,有助于新文學的拓進與創造。 從《談“中學生與文藝”》到《中學語文教學和古典文學》,我們發現俞平伯建國后對古典文學的語文教學價值愈加重視, 這既與他的治學道路緊密相關, 也因古典文學編選問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語文學界一度研討的議題之一。 俞文發表三天后,《人民日報》即刊載北京市若干中學語文教師共同討論,向錦江執筆的 《中學語文課本必須適當地編選古典文學作品》,縷陳現行中學語文課本古典文學作品編選上的缺點,提出了針對性的意見,可與俞文相互參讀。
三、關于文藝作品的教學
正如前文所引述,俞平伯《談“中學生與文藝”》一文談到語文教學中古典作品“選材第一,教法第二”,隨即探討了詩文的教授法:“詩文的講授法正不必一致。文章既在注重思想的訓練,自必須講解得很清楚才對。詩則除訓詁名物詮表大意以外,或無需多講,以令學生背誦為主。 背誦原是很重要的,耳朵的學習有時較眼睛的學習更為得力,所謂‘聲入心通’。 背詩要比背文容易,且更有趣。 ”作者根據詩、文這兩種體裁的不同特征與教學價值,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講授方法。 對于文章,教師必須注重講解,講解得清楚,學生才能得到“思想的訓練”。 大部分詩歌無需多講,應提倡學生多多背誦,不但用眼睛學習,也要調動耳朵參與進來,此所謂“聲入心通”。 早在1940年代初,俞平伯就有作《文章四論》的打算,曰文無定法,曰文成法立,曰聲入心通,曰得心應手,試圖將寫文章的經驗與道理概括無遺。 這既是他久事寫作的心得,也是其總結出來的“研讀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 據目前文獻,他最終并未完成《文章四論》的寫作,但卻曾在數篇文章中有所論及。 《文章自修說讀》(1943)集中闡說“四論”之一——“聲入心通”的讀書方法,文中寫道:“讀,聲入心通之謂,有二焉,曰朗,曰熟,不朗,聲何由人,不熟,不通于心矣。 ”該文核心關鍵詞即是“讀”,并將“讀”與“聲入心通”畫上等號。 “讀”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曰“朗”,一曰“熟”。 “朗”指朗讀,即讀之出聲,耳目并用;“熟”指熟讀,即反復閱讀,直至成誦。 只有大聲朗讀,熟讀成誦,才能最終達到“聲入心通”。 如果能對名著典籍背誦如流,則可左右逢源,收事半功倍之效。 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作家對誦讀多有論述,俞平伯的好友葉圣陶、朱自清等對此均有頗為深入細致的探討和研究。 而以“聲入心通”來解說誦讀的,還有顧隨、黎錦熙等人。 顧隨曾說:“根據‘聲入心通’的道理,‘耳治’實不失為語文教學的有效方法。 ”黎氏有“口與耳關系密切(自讀熟,自聽慣),文言文若能貫徹‘口到’,自然‘聲入心通’,既得于‘心’,而應于‘手’,故亦足促進其寫作”的闡述,與俞平伯的“聲入心通”“得心應手”八字可謂所見略同。
與《談“中學生與文藝”》所述遙相呼應,晚年俞平伯在談論古典文學的多篇文章中重申 “聲入心通”之法。 在《略談詩詞的欣賞》(1979)中,俞平伯就詩詞的欣賞與學習有如下闡發:“閱覽分精讀、 略讀, 吟誦分朗誦、吟哦。 目治與耳治,不可偏廢;泛覽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謂‘聲入心通也’。 ”《關于治學問和做文章》(1985)一文重提“文章四論”,并表明“聲入心通”與“得心應手”兩句更重要。 為什么要反復誦讀才能實現對古代詩文的深入理解,并進而掌握創作的門徑呢? 兩文均有表述相近的闡析。 前文講道:“作者當日由情思而聲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傳,已成陳跡。 今之讀者去古已遙, 欲據此跡進而窺其所以跡, 恐亦只有遵循原來軌道,逆溯上去之一法。 當時之感慨托在聲音,今日憑借吟哦背誦,同聲相應,還使感情再現。 雖其生也至微,虛無縹緲,淡若輕煙,閱水成川,已非前水,讀者此日之領會與作者當日之興會不必盡同,甚或差異,而沿流討源終歸一本,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幾近之。 反復吟誦,則真意自見,箋注疏證亦可廣見聞,備參考。 ‘鍥而不舍’‘真積力久’,即是捷徑也。 ”作家創作的情形被描述為——從情思到聲音再到文字, 因此今之讀者要逆流而求,追根溯源,憑借反復吟誦,體察作者當時之感興。 后文首先指明“自學之法,當明作意”,就是說我們讀文章要“從創作的情形倒回來看”,盡力窺探古人的用心,感知作家的情旨。 作者特意現身說法,以自己幼時的讀書經驗為例,說明記誦之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好文章可以背,好詩則一定要背。 僅僅念詩是不夠的,念出的詩是平面化的;翻來覆去地背誦,反反復復地吟哦, 詩就變得立體化, 詩中的味道與境界就全部出來了。 文章接著闡明:“誦讀,了解,創作,再誦讀,詩與聲音的關系, 比散文更為密切。 杜甫說,‘新詩改罷自長吟’, 又說,‘續兒誦文選’, 可見他自己作詩要反復吟哦,課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讀。 俗語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雖然俚淺,也是切合實情的。 ”作者注意到詩與聲音的緊密聯系,比散文更甚。 古人作詩一般都會經過反復吟詠, 在誦讀中推敲改定, 終成佳句,故閱讀學習古詩必須要熟讀成誦。 此外,俞平伯還建議研究詩詞的人最好自己也動手寫一寫, 這樣才能體會到其中的甘苦,有了創作體驗后,對于揣摩與研讀古人的文學作品會有較大幫助。
從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 我們發現俞平伯對于語文教育的論述略顯零散, 尚未形成周密完整的理論體系,個別觀點不免存在局限或不足。 然而俞平伯擁有講授國文的長期經歷和精深的文學造詣, 故他對語言文學的學習常有獨到的判斷, 對一些問題不乏敏銳的觀察與洞悉。 針對民國時期國文程度的普遍低落的現狀,他體認到方塊漢字之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貢獻,從而將國文教育納入民族復興國運重光大業之一支。 到了建國之初, 他再度申說中學語文教學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迫切性。 同時,他也簡略論及語文教育在“思想的訓練”“文藝的涵養”等方面的目標。 由此觀之,俞平伯似更看重語文的“實質訓練”,而疏于“形式訓練”的討究。 著眼于愛國教育,他對中學語文教材中古典作品的選材甚為關注, 建議古典文學的編選不宜過狹、過短和過少,且需將其與現代作品彼此配合,得體編排,反映古今文學的文章流變與歷史脈絡。 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俞平伯認為詩文的講授之法不同,文要多講,詩要諷誦,著重揭示了詩詞教學中誦讀或曰“聲入心通”的重要性,對于今天的語文教學依然大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