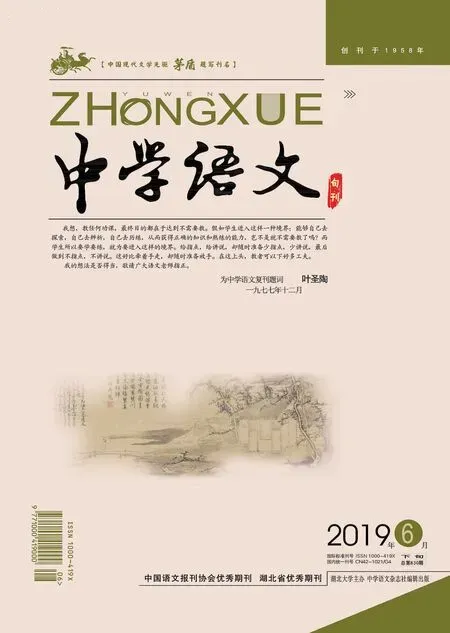巧用“變式理解” 提高語文能力
葉麗丹
理解,是認識事物的一種重要的思維活動。 在中學語文教學活動中,引導學生對文本概念的把握,揭示語文現象的本質特征、相互聯系和規律,都離不開理解。 本來,語文教學中,無論是聽說,還是讀寫,其中心任務都是指導學生對語文知識的理解。 但教學,又不是一種純知識的教授過程, 而是要讓學生把知識轉化為一種能力,一種高級的思維能力,語文課堂,應該成為培養學生語文思維能力的場所,提高語文思維能力的主戰場。
既然如此,那么靠什么來完成此重任,達到教學目的呢?
我認為,“變式理解” 是把知識精化為語文思維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教學中巧妙地運用它,能大大地提高學生的語文思維能力。
潘菽在他主編的《教育心理學》中指出:“變式就是使提供給學生的各種直觀材料或事例不斷變換呈現的形式,以便其中的本質屬性保持恒在,而非本質屬性則不常出現(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
縱觀近幾年的高考語文試題, 提供給考生的各種被試材料或事例,就是利用了變式原則,改變了命題的表現形式,來測試考生的理解水平和語文思維能力。
可見,我們要認真研究在教學中如何運用“變式理解”,去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提高他們的語文能力。
教學中,運用“變式理解”,就是讓學生抓住學習對象的本質特征,把它和非本質特征區別開來,從而形成正確的概念,對知識理解既深刻又全面。
比如,洪鎮濤老師在教學《雷雨》時,對“不規矩”“不清白”“不守本分”做了如下處理:
師:對了,為了拆穿謊言,也是披露事實,所以說“不規矩”“不清白”“不守本分”。那為什么要拆穿他的謊言呢?周樸園美化侍萍其實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也是美化自己。那么把侍萍的話做些改變,侍萍這樣說行不行:“她不是小姐,是個作風敗壞的丫頭。她跟周家少爺鬼混,不明不白地生下兩個孩子。”這樣說不是更有力量些嗎?哦,有同學擺頭了。請你(指一舉手的學生)說一說。
生:她本來就很痛苦,如果她那樣說的話,她會更加痛苦,就不可能掩飾下去了。
師:她沒有必要把自己罵一頓,這也無益于揭露周樸園的罪行,還有,如果她這樣說,她們的談話還能不能繼續下去呀?
生:當時她說得太清楚的話,周樸園可能就會反應過來,知道她就是當年的梅侍萍。
師:不一定馬上知道,但他會懷疑,是吧?如果主觀感情色彩太濃的話,好像她就是當事人,至少和當事人關系很密切,這“閑談”就難以繼續下去了。
師:“不大規矩”是從侍萍的角度說的。其實罪責在周樸園身上。為什么不采用更有力的揭露周樸園的話呢?“她不是什么小姐,而是一個單純、善良的丫頭。她太年輕,太幼稚了,不知道周家少爺是個狼心狗肺的東西,她讓周家少爺給騙了,給他生了兩個孩子后被他拋棄了。”行不行?
生:她那樣說無疑戳到了周樸園的痛處,談話就無法進行了。
師:對,戳到了周樸園的痛處,談話就無法進行了。主觀感情色彩太濃,會引起周樸園的懷疑。
洪老師在教學中采用“變式理解”,即“改一改”,目的在于讓學生比較、推敲、品味語言使用的妙處,形成語感。 將原來的臺詞作兩種不同的改動:一改為作風敗壞的丫頭與少爺鬼混; 一改為單純善良的丫頭被狼心狗肺的少爺所騙。 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原作語言的分寸感便凸現出來了, 學生對文本的探究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再如,《祝福》 里有兩次描寫祭祀時四嬸不讓祥林嫂沾手的情節:
第一次:
“祥林嫂,你放著罷! 我來擺。 ”四嬸慌忙地說。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著罷! 我來拿。 ”四嬸又慌忙地說。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于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地走開。
第二次:
“你放著罷,祥林嫂! ”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再也不敢去取燭臺,只是失神地站著。
(四嬸前后兩次不讓祥林嫂動祭具,祥林嫂兩次反應大不相同,為什么?比較一下“祥林嫂,你放著罷!”和“你放著罷,祥林嫂! ”在表達上有什么不同? )
祥林嫂的這兩次反應,作者運用變式手法,語序顛倒,考查學生的變式思維能力。 第一問:第一次,祥林嫂并不明白自己的“罪過”,她不明白四嬸為什么不讓她沾手,所以只是感到“疑惑”。 而第二次,她已經從柳媽口中明白了四嬸不讓她動祭具的原因, 但她捐了 “門檻”,認為自己已經“贖罪”了,可以被“寬恕”了。 可是四嬸的斷喝讓她明白自己永遠不能被這個冷漠的社會“接受”。因此,她的精神徹底崩潰了。第二問:“祥林嫂,你放著罷! ”“你放著罷,祥林嫂! ”兩句話的語氣是很不一樣的,后者是一個倒裝句,命令的意味更強烈,態度也更嚴厲。
考試中,運用“變式理解”,可以考查學生的變式思維能力和辯證思維能力。 請看下面一道模擬試題:
2019年2月湖北省 “八校聯考”:(活著的儀式·王溱)8.請從不同角度賞析小說結尾的畫線句子。(6分)
這道考題有意思的是,它測試的材料是多角度的、各方面的,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也就是說材料具有“變式”性,它與一般考查句子含義材料比較起來,形式顯然改變了,這就要求考生必須運用“變式理解”,抓住被試材料的本質特點,準確地作出選擇。 1.作品以“我”在瑣碎的家務中手忙腳亂,卻“迸出了一句詩”而結束,給人留下想象空間,“童子尿”與“詩”的巨大反差,形成了戲劇效果,語言含蓄詼諧;2.結構上,“我”的生活狀態與前文“他置若罔聞,緩緩開了口說:‘生活,不易’”照應,寫出了人們在詩意和生活中選擇務實生活的現實狀態;3.情感上,前面“我”因為追求務實的生活而逃避詩人,現在生活的現實讓她吟出詩句,從中可以看出“我”的轉變,含有對“詩人”詩意生活態度的默認,讓故事情節產生起伏;4. 動作描寫,“手忙腳亂地解開二娃的尿褲”“被一泡溫潤的童子尿噴得滿臉都是”,再現了“我”生活的忙碌瑣碎,而“我嘴里迸出了一句詩”,表達出渴望在枯燥的生活中尋覓詩意的愿望, 暗示出小說的主旨:面對生活,要用積極的態度去尋求精神的詩意和遠方,讓生命富有儀式感。
再如, 廣東省惠州市2019屆高三第三次調研考試試題:6.對于這篇小說的標題,有人說取“爭水”,有人說用“妙招”,還有人說用“冤家”更好,你認為呢? 請說明理由。 (6分)
該題考查標題,命題人從不同角度設置問題,考查學生變式理解的思維能力。 考生可結合小說人物、情節、主題、藝術效果等角度闡明,理由符合情理即可。 比如,用“冤家”更好。 “冤家”一詞本身就具戲劇性,牽引讀者的獵奇心和閱讀興趣。 文章前半部分寫村人都在猜疑老門媳婦的“冤家”,又遲遲不露,才推動情節的步步前進,牽引著村人和讀者好奇探知。 后文的演戲一說,讓人恍然大悟,柳暗花明,所謂“冤家”子虛烏有,抑或說歷史舊冤,最后變“歡喜冤家”,雙贏收尾,彰顯主題。
因此看來,我們教師在教學或試卷講評時,充分運用好了“變式理解”,對學生形成正確的概念,幫助他們克服日常概念的消極作用,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特別是在新高考背景下,更能培養學生發散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