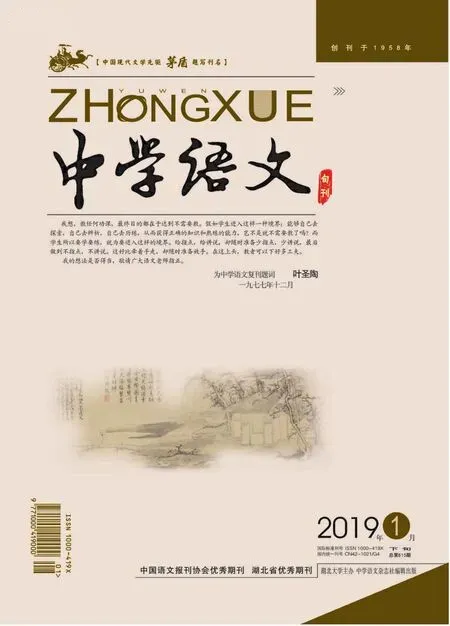隔絕與生成:語文言說的扃與作為
成旭梅
當我開始這個話題的時候,立刻陷入一個深淵——
我表達的你也懂,可是我的表達你沒有,這就是語言最妙不可言的可愛之處,也是語言最居心叵測的陽謀——作為表達實體的內容在宇宙時空的存在,由語言來承擔的部分確乎存在巴別塔效應;也由此,人類難以集結自身的正能量從而企及天堂。然而,一個人的角色,總是首先由他的語言(詞語性符號與非詞語性符號即身體語言)呈現,并最終由他的語言完成建構。無可否認,語言就是一個精神王國。
人的豐富,來自語言;人的間隔,也來自語言。語言在表達實在的同時,也遮蔽它。或者說,現實只有通過語言來呈現,但一旦經過了語言的覆蓋,我們也就再也無法接觸到那個現實了。這便是語言生發與破壞的兩面。
不,這也正是語言的作為——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認識到語言的本質。
一、語言的作為:意義世界的建構與傳達
從歷史存在主義的角度說,沒有一個朝代的立敗興廢能夠繞過語言。這樣說決非夸大其辭。統治者對于語言所能達及的影響十分清楚并深為敬畏,因而總不放過在語言上動些手腳。制度的刷新是一著,宣傳控制是一著,再加上以統一語言來統一思想,以焚毀語言來禁絕自由等等。所以今天語文人自言對語言的成就,還真有些小天下的狂妄。語言的本質,并非來自教育,當然,語言的作為,也并非必須倚賴教育的成全。
1.世界在語言性的理解中存在
重新認識語言的職任與豐富,20世紀上半葉形成了語言哲學運動。語言哲學不是一項單一的哲學運動,它不僅是對20世紀上半葉整個西方哲學“語言”轉向運動的整體描述,而且還是對所有與語言有關的哲學思想的總括。其中既有嚴格科學意義上的語言分析哲學,也有現象學意義上的解釋學語言哲學,同時還是有語言學意義上的結構主義語言哲學。
在語言哲學的視野里,語言是人之為人的最重要的符號系統。伽達默爾更是建構了以語言本體論為核心的哲學體系:“理解不是主體諸行為方式中的一種方式,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西方哲學傳統把人定義為理性動物,力圖通過理性、觀念來把握人的特征,但伽達默爾認為,與其他一切相比,語言才是最基礎的東西,唯在語言中才有所謂的思想、觀念等等。因此,伽達默爾把人定義為具有語言的存在。基于這樣的語言學邏輯,我們可以進一步推理,也正是由于作為具有語言的存在,人才能夠被理解。一切理解都是發生在語言之中,因為只有進入了語言的世界,理解者才與被理解的東西形成某種關系。
2.對話實現理解
語言(Sprache)的原形動詞為言說(sprechen)。 “言說”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聽者“你”的。 因而,“在語言中理解”表現為“你”和“我”的對話結構。如此,我理解的對象便不是“你”,而是你向我所述說的內容,是你的語言的指涉;而在這個語言發生的情境中所衍射的 “你”,便因為語言而多了許多屬性——它實際上涵蓋著包括文獻、藝術品、歷史,文化傳統、乃至整個世界等等一切與理解者發生關系的對象。這是對一元論、“絕對真理”(黑格爾)的宇宙主體論的顛覆,因為只有在對話中,真理才是真實存在的,真理不是被發現的,而是發生的過程;而在對話之外,真理不能在語言之外獨立存在。
而由于語言的個體先驗性和體驗性,在承認他人的意見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合法存在的同時,也帶來語言理解的隔閡。也即,我們必須把他人的語言納入自己的生活語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說,要把他人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語言。
3.私言說與避言套:被遮蔽的整體與被放大的個體
2012年接近尾聲的時候,“避言套”搶鏡成為網絡最紅一詞,這誠然是眼球經濟下的語言創意,某個層面上也是對私言說安全性的一種憂慮。
語言具有私性特征,這種私性特征是語言活性的必要保證。這種語言活性在自由社會中被最大程度地許可,也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甚而至于有時表現為即被遮蔽的整體與被放大的個體。比如倫敦海德公園中的演說角,更是因其開放、自由的言說氛圍舉世聞名。
原始形態的廣場或者現代成熟形態的公園,都作為一個外在于國家政治權力的公民自治的領域存在,民眾獨立性與主體性在此得到充分張揚;同時,輿論交鋒、信息融匯又催生著公共精神的內核——獨立個體所具有的整體意識、普遍性的共識和共同的價值。此時,語言的私性因為在整體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表現出相對惰性特性。比如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所所呈現的群體性語言的不安全性與錯誤性特征。這種不安全性是“避言套”之所以創生的社會深層因由。
總之,語言作為意義世界的建構與傳達的重要依憑,我們須要依靠語言來生存。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夠發現一個事實:語言的作為遠在教育之外,語文,只是路過語言——這種并非一體而是間隔的關系,我稱之為語文教育的“扃鐍”;至此,語文言說自以為能的自信轟然倒塌。
然而,正如“扃鐍”所涵蓋的雙面意義,隔絕之處必然啟示著再生的機能,所有問題都能給予我們間離和超脫的機智。
二、語文言說的扃鐍:指向終極關懷的本體性言說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跨越宇宙本體論而至生存本體言說的時代,這是人的歷史必然的軌跡,是教育行為須要面對的信仰與意義。提出“語文言說”,意在基于語言的立場反思語文的指向,反思語言(寫作)教學與教學語言在人“生存”意義上的效應,即在終極意義上追問語文言說可能的質地與品相。
1.絕對的價值差異性
世界在語言性的理解中存在,任何一種語言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任何一種語言現象都是世界存在方式的一種理解與表達。這樣,言說的本質就不是指向一元,而是多元;言說的基本姿態不是話語霸權,而是對差異的尊重:這樣的言說可稱之為生存本體言說。
20世紀中國文化主潮,就是一個從宇宙本體言說到生存本體言說的過程。語文言說,應該了解并跟進這個過程。
從新文化運動到30年代,中國文學發出的最響亮聲音是關于啟蒙的吶喊。周作人“人的文學”的吶喊;魯迅的“拯救國民性”的吶喊;郭沫若的讓中華民族來個涅槃的吶喊;曹禺的讓電閃雷鳴把封建老屋子搗個稀爛的吶喊……驚心動魄,震撼人心。它們的力量,來自于先覺者對著昏睡的人群發出的急切而近乎凄厲的疾呼。所以,啟蒙吶喊可視為一種曠野藝術。
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國文學的主潮,走上了救亡政治與階級政治的宣傳之路。文學作為政治宣傳,其形態是面對著群情激奮的人們,發出那種超強度的、夸飾的甚或是偏執的鼓號。因此,作為政治宣傳的文學,可稱之為一種廣場藝術。
80年代,文學開始從政治一統化的不安全感中掙脫出來,走向一種消解宏大價值和政治意識形態的獨語和私言說。這是一場“反意義”的逃亡,或者說,這是一場卓有成效的祛魅的運動,改變了文學政治功利的工具性質,唱響了自我主體,因此可稱為露臺藝術。
從曠野藝術到廣場藝術再到露臺藝術,文以載道責任的放下是一個方面,對言說的自由化和價值差異性絕對存在的認同是另一個方面。從人的角度來說,一元化的突破,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它意味著對于非人性桎梏的反諷與棄絕,和對終極性意義的追求。
理析這個文學言說的過程,再反觀我們的語文言說,不得不感慨于教育隔絕之巨、教育視野之狹隘,感慨于語文人之無力。我們的語文言說距離我們時代太遠。尤其是,當我們自以為在追尋經典的時候,我們忘了瞻顧正在發生和形成的歷史,忘了用新經典精神來追尋我們當下的生活。
2.終級關懷:理解和對話的語文意義
今天,我們對新課程名詞耳熟能詳,卻難能避免踐行時的困惑。什么是學生主體?什么是教學對話與寫作對話?語言的理解與寫作生成是否必要經由對話?什么是對話生成?——對話生成結果的品質高低用什么來衡量?成績還是生活?或是人的終極意義?
如前述伽達默爾的闡釋,“理解……是通過對話——諸如傳統與現實,過去與現在,自我與它者等等之間的對話——通向效果歷史的運動”,“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那么,達成理解的對話的意義是指向終極關懷的,其形式是靈活多變的,層次也是豐富多樣的。
不同的對話決定了不同的語文生活和精神特質。
“主體——客體”的存在論方式是我國現代乃至當代語文教育的基本存在論方式。在它看來,語文教學(學習)的過程就是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通過學習語言文字認識外部客觀世界的過程。語文教育中一切神秘難解、精微古奧都被嚴謹而執著的科學認知與分析精神所俘獲和修正。語文言說成為一種可以被科學地加以控制與調節的模式化的公共程序,語言也在這種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壓力下漸漸失去了詩意創造的生命活力,蛻變為口號式的、標簽化的符號。
“在場——不在場”存在論立場是對主客二分立場的一種超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語文教育的認識論功能,也不完全否定邏輯在構造知識世界時的決定性力量,而是要努力把這種關于世界的對象性認識植入人與世界的對話關系之中來把握,把被知識的客觀性所排擠到哲學邊緣的人的主觀創造精神召喚回來,把存在者從片面的知識鏡像中帶入到人的整體意識的能動的顯現之中,帶入到語言的無限敞開之中,從而構建了“交往——實踐”的語文言說關系。在這種關系下,語文的知識世界不只是靜止的命題陳述,而是人的情感與意志的生動表達;語文的想像世界不只是預設好的可能性,更是被實踐不斷創造并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它不只是個人思想內部的超越,而且還是主體間的共同超越。
傳統教學觀以為,教師一言的課堂形式必然會帶來廣布性和單向性的形態性、方法性特征。所謂廣布性,是指教學的基本形態,它是居高而往下流布的,從中心向四周擴散的;所謂單向性,是指不重視接受方面的回流、反饋,主要的興趣只在于以某種特別的姿態引起在場眾人的驚異,以及這種驚異的效果。但是這樣的觀點并不能解釋所有的教學方式。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否認中國古代私塾教學嚴苛之下的教學成效,不能忘懷民國時期學人們的精彩絕倫、鴉雀無聲的學術講座,也不能無視西方重視課外實踐與實驗的非對話教學的實際價值,不能排拒與文本靜默對話中生成的深刻感動。對話的本質意義在哪里?功利主義者以為是眼見為實的效果,而語言哲學以為:對話因其精神實質從而表現為生存本體言說,實現人的終極關懷。這是在說,思想的成熟與精神的塑立才是對話應該關注的方向。
3.思與美的靈動性與涌流性
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而莊子卻一個學生也沒有,以經濟社會的眼光來觀照,似乎是一個言說的社會效應問題,好像孔子雖然是政治上的落敗者,但他在民間的明星效應更好一些。這其實矛盾又荒誕,至少今天看起來是這樣。另一個諷刺性意義的荒誕是:其時的門前冷落并未妨礙莊子在歷史流轉2500年以后成為今天的熱點焦點。這個比況提出的問題是:言說的受眾數量是否可以作為衡量言說成敗的標準?
我在勒龐的《烏合之眾》找到這個問題的解答:“政治和語言的墮落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有這些避免分析與批判的觀念(表達),才能在群體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讓群體肅然起敬、俯首而立……”勒龐所指出的,正是一個語言的詭計:政治演說者要達到他一呼百應的目的,一定會選擇一套取媚于公眾的世俗化言說系統,以便于最大程度地激起最大數量的群體的政治熱情。
但語文言說的目的當然不在一呼百應,所以語文言說并不需要迎合之態、降格以求。相反,因為“就終極意義而言,語言正就是人類的本質和寓所”,所以教育言說恰恰應是尊嚴、高尚、嚴謹、深度、優美、感動的;因為“世界體現在語言中”,所以教育言說還應是充滿變化,富于靈動性和涌流性的。這種思與美的靈動性與涌流性所表現出來的言說風范,正是一種樸素、自然、和諧的胸襟與氣度。
在“語用學轉向”的背景中,法國思想家福柯對作為行動與事件的語言即話語是非常看重的,他不無深刻地指出:“人類主體被置于生產關系和意義關系中的同時,他同時也被置入極為復雜的權力關系中。”當然,福柯話語理論中的權力主要是指體制性權力,但我們不妨借用他語話權力理論中的“關系性的概念”來反觀我們的語文言說。既然對話存在“關系性”,必然要通過具體的控制和反控制來實現。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課堂呈現方式應該是言說者與言說回應者之間的雙向性控制。從這個意義上反思,聽得懂的語文言說能否作為言說品質的唯一前提就成為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前述言及,“聽懂”是廣場藝術的追求,最為淺易,甚至連淺易也談不上,僅有口號性的簡單僵硬的符號而已。比如希特勒,他可以影響一個民族的整體意識,確立一個時代的整體信仰。我們今天教育言說的影響力,遠不及他,你說他是不是優秀的言說者?當然不是。所以,我以為思與美的靈動性與涌流性可以作為語文言說呈現的形態和本質性規定之一種。
的確,語文言說的難度的層級不是那么確定,這許是困境,但我以為更是活境,這就給了語文人更大更自由的言說空間。聽不懂,可以意會,可以默會,可以追思,可以潛行,這是中國文字的妙處。但當下浮躁的對話態度總把對話窄化,以為對話只在于聲音的對流;而在“聽”里習慣了的奴性心態并不去審視與重視自己的反控制力量。聽的難度某種程度上是來自于隔絕,來自于對話雙方話語系統的不同。所以,聽的陌生化,也有聽的一方自己未曾進入言說者的話語系統的責任。因此,如果簡單地把陌生化稱作難度,這并不合理。“我們首先要向經典表明自己的價值”,赫爾曼·黑塞啟示我們:聽者首先要向言說者表明自己的價值。對話場域之內,聽者與言說者的思與美的涌動是相互控制的,因而也應該是相互尊重的,絕不能因為聽者本身的無知而否定言說的價值。這是生存本體性的另外一個維度的詮釋。
不是所有的開啟都有圓滿的回應,這樣識認,語文言說才能獲得一種心平氣和的氣度和冷靜思考的可能。
當然,課堂言說應有回應,只是如何回應,以何種方式回應。實際教學中,言說者多以為課堂的完成就是教學內容與任務的傳達。其實這并不是課堂的全部。海德格爾說“語言本身在說話”,這實際上指出了教師資源的重要性。教師有問題,學生如何優秀?伽達默爾說世界體現在語言中,這是指出在語言中蘊含人類的各種世界觀念和文化建構。因此,我們在語言中存在的含義是否可以理解為:其一,語言使我們獲得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共同性和理解的可能性;其二,語言不是一種把意識和世界聯結起來、用來消除謬誤和獲得知識的手段與技術;其三,就終極意義而言,語言作為人類的本質和寓所,它是科學、歷史、文明之母,是一切理解的基礎,無論引領或是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