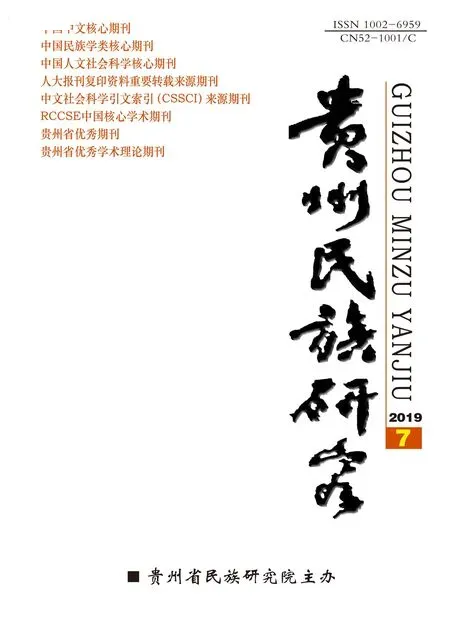論明代科舉制度在貴州民族地區的開展及人才分布
廖榮謙 常海星
(1.貴州師范大學,貴州·貴陽 550025;2.貴州師范學院,貴州·貴陽 550018)
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作為封建王朝文武官吏及后備人員的選拔制度,自隋唐以來,歷代封建王朝除了將科舉考試作為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以外,還非常看重科舉在確保社會精英的有序流動以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一統,加強民族的凝聚力,促進政權的鞏固,加速儒學的傳播等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尤其是中央政權在經營開發邊疆地區時,往往將科舉作為一種國家利器來籠絡人才、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以及拉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地區文化的差距,最終達到夷漢一體的目的。因此,要探究明代貴州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必須關注明代科舉制度在貴州的發展變化。
一、獨立開科以前貴州的科舉考試
今貴州地區早在北宋年間即有人參加科舉考試并取得進士,但歷經南宋、元代近三百年的歲月里,貴州參加科舉的人數寥寥無幾。其中原因,雖然與歷代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統治策略、重視程度及貴州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狀況有很大的關系,但也與這段時期內文化教育發展緩慢不無關系。明朝建立以后,明確規定“科舉必由學校”,[1](P1675)將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捆綁在一起,試圖把科舉考試作為統一全國思想和貫徹以儒術治國的執政理念的重要工具,這一舉措,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文化教育發展和學術思想進步的作用。明代貴州建省以前,沒有單獨行政的權力,經濟文化的發展一直萎靡不振,學校教育尚處于起步階段,參加科舉的人數很少,直到永樂九年才由永寧人劉宏首開明代貴州科舉之門,此后一段時間內發展仍然極為緩慢。建省后,貴州成為單獨的行省,但一直沒有獨立開科的權力,貴州士子參加科考得遠赴云南,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成為了擺在全體士子面前的最大障礙。
貴州在明初及建省后的一百三十年里沒有獨立開科取士的權力,士子要參加科考,只得到外省考試。據明代吳維岳所作《貢院記略》載:“洪武甲子(十七年),天下開科取士,貴州附云南試焉。”[2]說貴州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起即可附試云南,但據嵇璜《續文獻通考》:“云南鄉試始于(永樂)六年(1408年),貴州亦附試焉。”[3]云南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尚未具備獨立開科的資格,貴州如何附試云南呢?此說肯定有誤。據道光《遵義府志》載:“洪武時,未詳科分,趙仕祿,《桐梓草志》‘進士’列此人,川、貴《通志》皆無。”[4]按照常理,如果趙仕祿真為洪武時進士,四川、貴州兩省省志不當失載,不知《桐梓草志》所據為何,故民國《桐梓縣志·選舉志》卷三十二說:“郡志此后桐梓尚有元代恩進士楊朝祿、明進士趙仕祿,皆不確。”[5]此說當可信。在永樂六年的云南鄉試中,貴州沒有士子中舉。
真正開明代貴州士子科舉入仕之先河的,當屬永樂九年(1414年)永寧人劉宏中辛卯科舉人。民國《貴州通志·選舉志一》記載:“永樂辛卯,貴州未開科,永寧衛屬四川,附與云南,故系之云南鄉試。是科中式者僅劉宏一人。”[6]貴州建省后,永樂十二年,播州宣慰司人廖沉在四川鄉試中中舉,成為明代貴州的第二位舉人。十四年(1419年),明廷仍令貴州士子附試云南,《明會要》載:“(永樂)十四年(1419年),命貴州士子附試云南。”[7]次年丁酉科,永寧人魏真中舉。二十一年(1423年)癸卯科,永寧人胡友諒中舉。
綜觀永樂年間貴州科舉,四名舉人中有三名為永寧人,一名為播州人,而宋元時期文化教育基礎相對較好的思南府和貴陽府卻無人中舉。究其原因,我們認為與明朝對貴州的開發與明代初年西南地區的政局有關。洪武年間,朝廷對西南邊疆地區的開發,完全是出于統一云南、穩定邊疆政局的戰略考慮,使貴州成為鞏固云南的后方基地。即使建立了少量的官學學校,也是為了使各土司子弟“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8]而廣大普通民眾及子弟是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的。在建省以前,明朝承襲元朝舊制,將思州、思南二宣慰司隸屬湖廣,播州、貴州二宣慰司及烏撒、普定等土府與金筑、都云等安撫司隸屬四川,今貴州境內大部分地區處于三省交界之地,實際政權仍掌控在各大土司手中。各大土司之間為了爭權奪利而連年發生戰亂,根本沒有心思發展教育,所以永樂前期思南府和貴陽府很少有人遠赴云南參加科舉考試。而永寧衛則長期深受四川和播州的文化熏陶,又有赤水河的交通便利條件,“故居人頗稱富庶,往往有登科第榮顯者”。[9]永樂十一年(1416年),貴州雖然獨立建省,但整個永樂朝期間,一直處于經濟恢復階段,政治局勢還沒有完全得到穩固,教育基礎依然相當薄弱,只有零星幾所官學得以興建,“文教浸明如啟牗”,[2]還沒有形成全民興學和讀書向學的風氣,文化的積淀和人才的培養尚需時日,所以參加科舉的人數寥寥無幾。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命“貴州應舉者就試湖廣”。[7]由于距離湖廣武昌路途遙遠,有近四十余驛的路程,又要橫渡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應試異常辛苦和艱險,令大部分士子望途生畏,且這一政策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兩年后就發生了變化,期間只舉行過一次會試,即宣德元年(1426年)丙午科鄉試,所以現存文獻中找不到士子赴湖廣參加鄉試和中舉的記錄。宣德二年(1427年),布政司以“貴州去湖廣四十余驛,去云南止八驛,乞以近相附。”[8]請求附試云南,朝廷同意了這一請求,“前奉禮部文書,本司所轄州郡生徒堪應舉者,許于湖廣布政司就試,緣去湖廣路遠,于云南為近,宜就近為便。”[8]從此貴州生員附云南鄉試成為定制。宣德年間,共考取十三名舉人。
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會試采用“三色卷”。貴州因附試云南而被劃為中卷,在國家保護弱勢省份的政策下,鄉試錄取名額也相應地逐年增加。從正統年間開始,科舉中式人數在不斷增長,正統三年(1438年)取中三名舉人,六年(1441年)取中七名,九年(1444年)取中九名,十二年取中十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赤水衛張諫在正統四年(1439年)己未科會試中,以三甲第十三名考中進士,成為明代貴州首位進士。此外,七年(1442年)壬戌科,貴州前衛秦顒以三甲第二名,十年(1445年)乙丑科思南府申祐以三甲第四十七名、永寧衛王敞以三甲第六十四名,十三年(1448年)戊辰科平越衛黃紱以三甲第七十二名分別考中進士,四科會試中五人得中進士,這種喜人的成績對于廣大士子而言確實是個極大的鼓舞。
由于正統年間實行的分地而取原則損害了文化強勢區域部分士子的利益,故招致了南方有些省份的強烈反對。景泰帝登位后,下令廢除“分地而取”的做法,重新恢復洪武、永樂年間的不分地成規,錄取不限額數,景泰元年(1452年)庚子科鄉試云貴共中三十六名,其中貴州十四名。次年會試時,雖然給事中李侃堅決反對不分地的做法,但景泰帝卻不予采納。景泰四年(1453年),給事中徐廷章又強烈要求恢復分地而取原則,這一次景泰帝只好同意仍然按照正統年間的錄取原則和錄取名額執行,五年(1454年)會試時,試卷仍分三色。從此以后,“遂著為令”,這一制度一直沿續至整個明清時期。整個景泰年間,共考取四十一名舉人和兩名進士。
從永樂六年士子參加鄉試,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獨立開闈前的130年 (1408年)里,貴州共考中舉人561名,進士42名。
從永樂建省以來,政治局勢逐漸穩定,經濟狀況得到不斷恢復和發展,在國家興學政策的鼓舞和地方官員與士紳的倡導下,尤其是王陽明等知名人士的大力興學和書院講學的激勵,全省上下興起一股興建官學和書院的熱潮,科舉中式人數逐年增多,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越來越高,至弘治十八年(1505年),僅貴州宣慰司“在城儒學弟子員凡一百七十人,武弁、幼官、應襲官生讀書習禮者近百人,社學二十四處,習學童生僅七百人,選入書院肄業者僅二百人。近廓社學有仲家、蔡家、仡佬、苗子、羅羅幼生僅百人”。[10]讀書士子人數的增多,直接導致了鄉試和會試進第人數的成倍增長,自成化朝以后,每年鄉試中舉人數一直保持在百名以上。按照錢茂偉的統計,“明代鄉試錄取率大體在4%左右”,[11](P99)而明朝政府在貴州設科取士只是“聊寓用夏變夷之意”[9],歷來不予重視,令貴州長期附試云南,其鄉試錄取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如嘉靖九年(1530年),思南人給事中田秋在《開科取士疏》中稱“貴州合省士子不下三千余人,每科鄉試五經皆全,上春官登膴仕者先后弗絕,則于人才未有不充也”[2],此“不下三千人”當為全省秀才總數,明代秀才要通過初選和二選兩次考試篩選,成績優秀者方有資格參加鄉試,實際參加鄉試人數為“應試七百人之中,取原定解額二十一人”,[12]三千多名秀才經過兩次篩選以后剩下七百人,這七百人參加鄉試后錄取二十一人,初選和二選的淘汰率為77%,鄉試錄取率僅為3%,其競爭的慘烈程度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甚至文化發達的江浙地區。
從獨立開闈以前人才的地域分布來看,在561名舉人、42名進士中,府、州、縣所占舉人為93名、進士7名,分別占總數的16.7%、16.6%,絕大部分舉人和進士出自各衛所,人才分布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驛道沿線,其他地方尤其是邊緣山區則非常少。從以上舉人和進士的籍貫來考察,若以貴陽為中心將全省分為東、西兩部分,在貴陽以西者(含貴陽)有進士31名、舉人444名,其中出身于衛所者,進士22名,舉人333名,出身府州縣者,進士9名,舉人111名。在貴陽以東者則僅有進士10名、舉人117名,其中出身衛所者,進士6 名,舉人74名,出身府州縣者,進士4名,舉人43 名。
以上統計顯示,開科前貴州科舉人才的分布呈現出明顯的東西分化、西強東弱的現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諸如政治的原因,明代前中期,朝廷為了平定云南和防范貴州少數民族叛亂,在貴州西部設立眾多的衛所,并從中原遷移大量人口至貴州屯田,應衛所軍人及其家屬與移民及其子弟積極向學的要求,政府官員在西部創建大量官學及其書院,教育的發展帶動了科舉的興盛。另外,貴州土司多集中在西部,明廷為了逐漸改變西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為下一步的改土歸流作準備,采取了一系列優惠措施來鼓勵土司及土民子弟學習中原文化和禮儀,學習優異者可以通過優先參加科舉考試而入朝為官。其次,如經濟的原因,明初對元代開通的湘黔、滇黔、川黔滇、川黔、黔桂五條驛道重新加以修整,增設驛站,并派重兵保護,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交通孔道。此外,水西彝族安氏土司首領奢香開設了“龍場九驛”,打通了黔西畢節與省會貴陽的交通屏障。上述六條驛道中,除湘黔驛道與黔桂驛道位于貴陽東部以外,其他四條驛道均位于貴陽西部。陸路交通以外,西北的赤水河連通了貴州與四川、牛欄江連通了黔西與云南、南盤江和紅水河連通了黔西南與兩廣。交通的便利促進了西部礦產的開發、商業的繁盛以及人口的急劇增長。貴陽西部礦產資源極其豐富,如宣慰司、烏撒衛、普安州等地盛產鉛鋅礦,普安州、安南衛、新興所等地盛產煤礦,這些礦產由于明代驛道的開通而得以大量開采,對于發展當地經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明代貴陽以西各衛及府、州的商業比東部發達,其中尤以普定、普安為最。普定衛居民多從事貿易活動,在衛城內有十字街市和局前街市,在城外有馬場市和牛場市,大宗牲畜貿易非常發達。徐霞客曾記錄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闊。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13]可見其商業貿易之發達。普定衛以西的安南衛、普安州等,也是當地的商業中心。黔西北的赤水衛、永寧衛、烏撒衛和畢節衛等地,地處川滇要道,因置驛設衛,外來人口漸多,商業也日漸發展,形成了一些城市。商業的發達為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造成上述東、西部科舉人才分布差異的原因,除以上政治、經濟因素對科舉成績起著決定性作用以外,與鄉試考場距離的遠近也是制約科舉成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貴州獨立開科以前長期附試云南,雖較湖廣為近,但也有不短的距離,正如田秋所言:“且以貴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寧等衛,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為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14]時任巡撫的鄧廷瓚也在向朝廷的上疏中說:“惟科場一事,仍附搭云南,應試中途,間有被賊觸瘴,死于非命者,累世遂以讀書為戒。”[9]由于貴陽以西地區距離云南相對較近,所以應試和中舉人數遠比東部地區要多,而東部地區中舉者主要集中在文教基礎較好的思南和清平兩地,其他地方則極少,甚至有許多地方一直未破科舉之荒,分布極不均衡。應試地點的路途遙遠和交通不便,嚴重束縛了本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于貴州整體發展格局和西南地區政局穩定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自弘治年間起,執政貴州的地方官員及本地一些開明紳士,著眼于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維護西南邊疆地區的政治安定,屢次奏請朝廷,請求在貴州獨立開闈鄉試。
二、明代獨立開科以后貴州的科舉考試
貴州建省后的124年里,雖然在外籍官員和地方鄉紳的勵精圖治與極力推動下,儒學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發展,但貴州士子在科舉舞臺上的表現與中原地區相比,仍然有著很大的差距。為此,歷任地方官員與開明紳士不斷地向朝廷呼吁,請求貴州單獨開闈鄉試,歷經三朝、40多年的接力棒式的不懈努力,朝廷終于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同意貴州獨立開科取士。從此,貴州的文化教育走上了騰飛之路,儒學的發展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峰。
早在弘治七年(1494年),時任巡撫右都御史的鄧廷瓚即向朝廷上奏,請求開設科場并量增解額,但明廷以貴州人才未盛,舊制不可輕改為由未能允準,只令貴州量助錢糧以備云南供給,準予云貴鄉試解額增加五名,其中云南準添二名,貴州準添三名。弘治十二年(1499年),巡按監察御使張淳向朝廷上疏:“竊見貴州校至二十四處,生徒至四千余人,前科赴云南鄉試者逾四百之上,具每科中經魁并前例者往往有之。科場之費,則鎮遠、永寧二處商稅銀,歲至一千三百余兩,贓罰等項又可二千五百余兩,用之有余。況本城內舊有公館一座,地勢軒敞,少加葺補,堪作試院,請各自開科為便。”[8]次年,巡撫都御史錢鉞等奏請開科取士,并請求欽定解額,禮部以擔心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布政司一概比例為由拒絕。正德九年(1514年)、嘉靖元年(1522年)、嘉靖六年(1527年),巡撫都御史陳天祥、湯沐等先后會同鎮巡衙門上疏,禮部又以貴州錢糧之少,不敢輒議開科為由不予允行。
嘉靖九年(1530年),時任給事中的思南人田秋,為了改變家鄉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毅然以臺諫的身份向世宗呈上《請開賢科以宏文教疏》,為貴州獨立開闈鄉試據理力爭。田秋作為跋山涉水遠赴云南應試的親身經歷者,深知其中的艱難困苦,因此其奏疏言辭懇切,有力駁斥了禮部以貴州人才未盛、錢糧不足等理由,痛訴了貴州士子遠赴云南應試之艱辛,“且以貴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寧等衛,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為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親見其苦,親歷其勞,今幸叨列侍從,乃得為陛下陳之。”并援引“國初兩廣亦共一科場,其后各設鄉試,解額漸增,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14]的先例,請求朝廷允許貴州獨立開科鄉試以風勵遠人。因田秋的奏疏理由充足,引起了朝廷的重視,經禮部復議后下貴州撫按勘議。嘉靖十三年,王杏任巡按御史,負責勘議開闈鄉試一事。王杏到任后,大力支持貴州開闈鄉試,積極與當地有識之士籌資選址建立貢院號舍,并上書朝廷,奏請允許貴州開科取士。經禮部復議后上奏皇帝:“照貴州文教漸洽,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臺諫之選者,往往文章氣節與中原江南才俊齊驅。今既查省城南隅有空閑分司堪立貢院,即動支前項官銀于議定基址建立貢院,依期開設鄉試,以備一省賓興之制。”[9]明廷終于同意了田秋和王杏的請求,嘉靖十四年(1535年)八月十二日下旨,允許貴州自十六年辛酉科始開闈鄉試,并同意將鄉試解額增加到二十五名。歷經四十二年的努力爭取,士子們盼望已久的開闈鄉試終于得以實現。
獨立開科取士免除了士子們遠赴鄰省應試的長途跋涉之苦,讀書應舉日益成為士子的價值追求,科舉取士逐漸為貴州各族人民所接受,好學之風逐步濃厚,對貴州社會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嘉靖十六年(1537年)至明朝末年的110年之間,共考取進士130名(含武進士34名),舉人1232名(含武舉人21名)。
從時間分布上來看,開闈前的130年里,只考中了42名進士,561名舉人,而開闈后至明末的110年里,就考取了130名文武進士,1232名文武舉人。舉人進士數量的成倍增長,反映了獨立開科取士對貴州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意義。如以嘉靖朝為例,開闈前僅有5名進士、106名舉人,開闈后進士達20名,舉人達291名。隆慶朝雖僅開兩科,仍取中3名進士、62名舉人。萬歷朝更是以43名進士、532名舉人的驚人數量達到明代貴州科舉的巔峰。
此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與朝廷逐年增多解額有關。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撫王學益應提學副使徐樾的請求,向朝廷上《廣解額疏》。在疏文中,王學益說:自開闈以來“凡在寒微,皆知興起,蓋自丁酉以迄于今,歷歲無幾,而圣意所示,振奮類殊,人文之盛,弗啻倍昔,若果解額未足以盡之者。”[9]況且此時原屬湖廣的五邊衛學已經朝廷允許就試貴州而占去部分名額,希望朝廷以貴州地處邊徼,人才易棄難成為念,將貴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鄉試解額酌量加增。明廷同意了王學益的請求,是科增加解額五名,連前共為三十名。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貴州生員應試人數大幅度增加,已達“七千有余”,科舉名額的有限增加顯然已經跟不上應試人數劇增的步伐,所以巡撫林喬相、巡按薛繼茂聯名上疏要求增加解額,疏文中說:“貴州節年會試與云南互相上下,而館選臺省常不乏人,是云貴人才本不相遠,云南四十五名,貴州連外學三十名,多寡懸絕。學校漸增,解額仍舊,每至鄉場,棄璞遺珠,落卷強半,主司長嘆而不忍釋手。貴州壤地偏小,稱為一省,解額三十名,曾不抵一郡之數。”[9]此科貴州增加解額五名,共前為三十五名。此后,明廷又多次增加解額,至崇禎年間已達到四十名,比開闈前的最高額數(嘉靖十三年(1534年)甲午科為二十一名),增加了近一倍。但即便如此,明代中后期貴州的鄉試錄取率仍然非常低。
嘉靖十六年(1537年),應試825人,錄取25人,錄取率為3.0%[11](P289);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試之士凡千一百有奇,則副使(徐)樾所遴擇者也。遵新命,取士三十人”[15],錄取率為2.7%;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遂進提學副使所簡士一千二百有奇而三試之,得俊三十人”[16],錄取率為2.4%;嘉靖四十年(1561年),“先乃合提學副使況叔奇所選士二千有奇,既三試得三十人”[17],錄取率為1.5%;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參試人數“七千余人”,僅錄取35人,錄取率為0.5%;崇禎九年,“進提學臣龍文光所取士一千四百有奇,鎖院三試之得士三十七人”[18],錄取率為2.6%。從以上六次鄉試錄取率來看,貴州開科后錄取率平均僅為2%左右,而開科前卻有3.0%。雖然錄取名額不斷增多,錄取率卻不但沒有相應增加,反而逐科降低。由于科舉制度公開招考、公平競爭的取士原則,以及及第后的光宗耀祖和功名利祿,對貴州各族人民產生了強大的誘惑力,極大地刺激了各階層人民讀書求學的積極性,正如田秋所言:“茲幸圣人在御,百度惟新,鴻化博洽。邇者以臺諫進言,禮官上請,準于貴州設科取士。遠方士子,無不感戴天恩;垂白父老,拭目以面文教之興;椎髻夷酋,皆有遣子入學之志。”[19]科舉已然深入貴州各族人民心中,讀書、應舉、入仕已經成為貴州士子的普遍價值追求。
另一方面,科舉促進了貴州文化教育的大力發展,不僅有效地刺激了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積極性,而且調動了地方官吏、社會賢達辦學的熱情。同時,教育的發展也為科舉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保證。至嘉靖、萬歷兩朝止,官學和衛學已經遍布各大府州縣衛,連邊遠山區也布設有啟蒙性質的社學,各種教學活動已經步入了正軌。在明代貴州共有的47所書院中,嘉靖朝15所,占總數的31.91%,萬歷朝16所,占總數的34.04%,兩朝所建書院之和占總數的65%以上。正是因為官學和書院的蓬勃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才帶來了明代嘉靖、萬歷兩朝在貴州科舉歷史上的鼎盛。開科后,進士、舉人數占整個明代總數的比例分別為75.6%、68.7%。
從開科后人才的地域分布來看,與開科前最大的不同是,開科前人才的分布呈現向衛所一邊倒的態勢,而開科后府州縣所考取的進士、舉人數分別為54名、681名,分別占總數的41.5%、55.3%,所占比例與衛所大體持平,與開科前的17.1%、16.6%相比,府州縣的人才增長實現了一個大的飛躍。說明自萬歷改土歸流以來,大部分土司領地相繼歸流,府、州、縣所轄范圍逐步擴大,在流官們的積極倡導下,貴州的儒學文化教育施及的范圍不斷擴展。同時,因明后期朝政腐敗,朝廷對衛所的控制力逐漸減弱,衛所控制的范圍也在不斷地縮小,教育規模逐步萎縮,導致府、州、縣與衛所的人才分布趨于平衡。如貴陽府的前身為程番府,系分貴州宣慰司地而置。成化十二年(1476年),以元代八番地置程番府,設治于小程番,撥貴州宣慰司所屬的十三長官司及金竹長官司與木瓜、麻響、大華三長官司來屬。至隆慶三年(1569年),貴陽府領新貴、貴定二縣及定番、開州、廣順三州,統轄范圍不斷擴大。嘉靖十六年(1537年)獨立鄉闈后,將貢院設于省會貴陽,作為全省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貴陽在教育方面迅速崛起,共考取4名進士、192名舉人,舉人數約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位居全省之首。同時,以貴陽為中心輻射至鄰近地區,如安順府、都勻府、平越府以及新添衛、清平衛等地,開科后文化教育迅速發展起來。思南府自宋元以來因交通便利、礦產豐富而一直經濟實力雄厚,文化教育基礎較好,開科貴陽后,思南府憑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教育基礎,在科舉考試中爆發出了強勁的實力,共考取進士11名,舉人107名,人才總數躍居全省第二。普安州與普安衛同城,位于貴陽與昆明的中心,鄉試地點的東移對其影響不大,開科貴陽后仍然沿續其強勁勢頭而位居全省第三。
貴州獨立鄉闈以后,在人才分布上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東、西兩部趨于平衡。開科前因長期附試云南,導致科舉人才絕大部分聚集在距離云南較近的西部地區。貴州自設科場后,將鄉試地點設于貴州的中心城市,對于東、西兩部的士子來說機會均等,使許多無力遠涉外省參加鄉試的貧寒子弟得以就近參試。據統計,就文科進第人數而言,開科后,西部共考取進士40名、舉人594名,東部共考取進士56名、舉人617名,略勝于西部。由此可知,應試地點的改變對一個地區科舉考試成績的決定性作用,也證明了獨立開科對于一省文化教育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終明之世,貴州共考取進士172名(其中武進士34 名),舉人1793名(其中武舉人21名)。
三、明代貴州的人才分布
綜觀明代貴州科舉考試中人才的分布,與明以前相比,有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出現了以點帶面,多個中心并存的局面。兩宋時期,貴州的人才大多分布于烏江以北的遵義和思南一帶,元代才逐漸往黔中的貴陽一帶滲透。明代則除了貴陽異軍突起成為主要人才分布中心外,還帶動了周邊地區教育的發展,出現了思南、安順、普安、清平四個中心,形成了以貴陽為主,思南、安順、普安、清平為次的人才分布態勢。人才分布的范圍比明代以前更為廣泛,這一現象有力地說明了明代貴州的儒學教育已經遍及各衛所及各大府、州、縣等主要城市。
第二,人才分布雖然還很不平衡,但地區差距在不斷縮小。獨立開科前,人才主要集中于衛所和距離鄉試考場云南較近的西部地區,呈現西強東弱的局面,開科后由于鄉試地點的東移,使東部地區迅速趕上甚至略微超過西部地區,同時,扭轉了以往人才往衛所一邊倒的局勢,府、州、縣的人才數量與衛所大體持平。明后期,鎮遠府、黎平府、銅仁府、平越府、思州府等地的儒學教育迅速發展,鎮遠、清浪、偏橋、平溪、五開、銅鼓等六衛由隸屬湖廣轉而改屬貴州。從嘉靖至明末,鎮遠府有進士4名、舉人56名,黎平府有進士2 名、舉人69名,銅仁府有進士7名,舉人76名,平越府有進士3名、舉人41名,思州府有舉人76名。以上五府的人才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趕上了思南、安順、普安和清平。盡管如此,但明代的人才還是主要分布于交通干線周邊,其他邊緣山區則很少,尤其是位于黔東南的管外苗族地區則仍然處于少數民族聚居的化外之地,沒有納入到中央的統一規劃中來,更不用說對其實施儒學教育了。
第三,作為明代以前的文化重鎮和人才分布主要地區的遵義,兩宋時期出現了貴州僅有的8名進士,元代出了1名進士,但到了明代卻默默無聞,僅僅有3名進士、6名舉人記錄在案,相比于其他府來說,處于墊底的狀態。其原因與遵義歷代的政局有關。遵義原稱播州,唐乾符三年,太原人楊端領兵擊敗南詔而獨領播州,其后楊氏子孫世代相襲,據有播州七百多年。兩宋時期,楊端后裔楊選、楊軾、楊粲、楊價、楊文等重視文教建設,崇儒尊孔,播州的文化教育迅速發展起來。但自洪武五年楊鏗歸順明朝起,楊氏土司內部開始驕奢淫逸,肆意妄為,“漢英以后,恩寵益隆,統制益闊,迄于鏗、升,日以驕恣。”[4]正統十四年,楊鏗之孫楊綱死,其子輝襲職,此后,土司內部發生重大矛盾,長期內訌。先是楊輝之子楊友、楊愛為爭襲互相攻殺,到了楊愛之孫楊相,其子楊烈與庶弟楊煦又為爭襲仇殺多年。隆慶五年(1571年),楊烈之子楊應龍襲職宣慰使,倒行逆施,“殘害多命,縱欲欺罔,賄賂公行,禁錮文字,寇仇儒生,坑儒焚書……”萬歷十八年(1590年),“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論應龍兇惡諸事,巡按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1]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楊應龍公然舉兵反叛,至二十八年(1600年)才將叛亂平息。隨后,明廷對播州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土歸流,廢除了播州宣慰司及其所屬的安撫司和長官司,將播州一分為二,遵義府屬四川,平越府屬貴州。所以幾乎大半個明代,播州都處于內訌和戰亂之中,根本無心興辦教育,人才培養更是無從談起,故郭子章曾感嘆道:“貴州宣慰司有學,故士多匯征,夷亦向化。播州宣慰司無學,故酋既狂狺,民亦頑悖。”[2]遵義府教育和科舉人才的重振,要等到清代康熙朝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