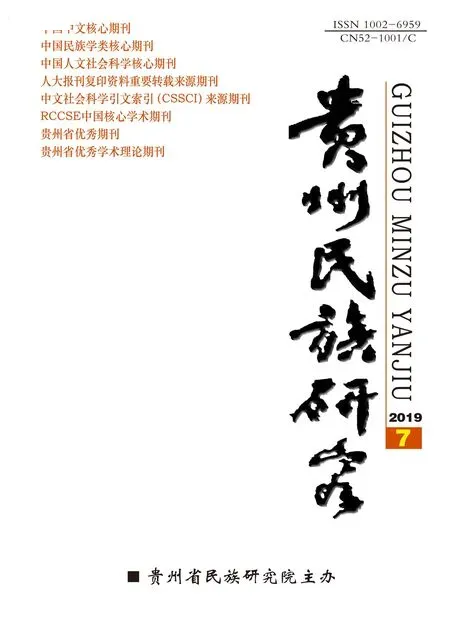民族教育史的梳理邏輯
江 濤 蘇 德 阿木古楞
(中央民族大學 教育學院,北京 100081)
民族教育史的梳理邏輯,是民族教育史學回眸的思維范式和價值倫理,是指研究者在史海鉤沉中所基于的立場、秉持的原則、傾向的價值和聚焦的內容。它不僅關涉著研究主體最終呈現“歷史”的客觀性程度,也關涉著研究者能否發掘出客觀歷史背后的“所以然”,更關涉著研究者能否得出相關教育規律和借鑒啟示。
一、民族教育史梳理的研究立場
所謂立場,即是指行為主體在社會實踐中所處的位置及所秉持的態度。民族教育史的梳理立場,則體現為研究者以何種方式、何種視角來看待民族教育史。立場不同,所呈現的史學結果必然有所差異、甚至大相徑庭。研究立場的出發點和終極旨歸,均為價值利益的全面體現,是基于場域內部相關主體利害關系的博弈后,對特定主體利益的特殊性觀照。因此,民族教育史的梳理立場,就是在反思立足何種場域、基于何種視角、秉持何種傾向來看待民族教育史。
(一)堅持“主客性”與“主體間性”相統整的立場
首先,要以國家的立場審視少數民族教育史。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任何一個少數民族都不是絕對孤立的,而是與主體民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任何一種“絕對獨立”的民族存在論,都是機械片面、形而上學的。在梳理民族教育史的過程中,就必須基于整個國家的立場,以國家維度的廣域視角,來審視不同民族的教育脈絡。即是說,要以一種“主客性”的研究立場,以整個國家全體民族(主體)的宏大史觀,來考量不同少數民族(客體)的教育發展史,進而發掘不同少數民族教育在與整個國家教育的交流融合中,所表現出的獨特個性及對整個國家教育發展的歷史助推,并為整個國家教育的現代化發展,提供更多的文化養分和路徑選擇。
其次,要以少數民族的立場審視國家教育的反作用。如同物理學場域中“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內涵相似,不同民族間的教育影響亦是相交互的。少數民族教育在融入(作用)整個國家教育的過程中,更深受整個國家教育的反作用。在開展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基于少數民族的立場,以少數民族教育為主體,以整個國家教育為客體,著重審視“外源”教育因子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影響和助推。系統發掘少數民族教育的嬗變進程中,受整個國家教育的影響而發生的與自身“原發性”民族教育特色不同的變化,進而得出民族教育改造和民族教育超越的歷史借鑒。
再次,要以少數民族的立場審視自身教育的嬗變發展。民族教育與國家教育之間不僅是“主客性”關系,更是一種“主體間性”關系。雙方在互為客體、互受對方影響的同時,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本我的姿態發展邁進。這就需要我們基于少數民族自身的立場,去梳理少數民族自身的教育發展脈絡,并對“民族教育何以成為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何以促成本民族的發展超越、民族教育何以能更好地傳承并鑄就民族個性”等問題進行系統反思,以此來促進民族教育個性的恒久彌香,實現不同民族教育“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發展盛景。
最后,必須實現上述三種立場的有機統整。單一立場的研究旨趣,只能代表個別群體的利益價值。唯有將各維立場的有機整合,方能彌補單一立場的研究缺陷,更可規避民族主體間的矛盾沖突,實現整個國家各民族教育的價值最優與利益均衡。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要著重處理好不同民族主體之間的關系,以多維視角、多條主線的形式,達成民族教育史學研究的最佳效益。
(二)堅持“教育性”與“社會性”相統整的立場
首先,要以“教育性”的視角審視民族教育史。“教育性”是民族教育的首要屬性,它專指少數民族系統內部的獨特教育形態,是以“教育”的形式來兌現民族教育的多維價值。這就要求我們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基于教育的場域,以教育的立場來審視民族教育,以教育的學科范式來思考民族教育的歷史事件及發展沿革,并從中得出個性化的民族教育規律,進而為“民族教育學”的自身建設提供歷史借鑒,更為廣義教育的理論提升和實踐發展提供“民族”范疇的個性佐證。
其次,要以“社會性”的視角審視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相似,民族教育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區域社會對民族教育具有影響制約作用,民族教育也同樣對民族區域社會產生能動的教育功能。進一步講,“民族教育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的共性外,其自身還具有顯著的特殊性與復雜性。”[1]譬如,少數民族與所在國家各民族之間的政治協統、文化交融、經濟互助等等,這些問題都有賴于民族教育進行教育維度的協調消解。因此,民族教育史的梳理,就要打破教育的藩籬,以更高遠的視角,更廣闊的場域,從全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來考量民族教育史的運動嬗變。把民族教育史融合到多民族國家發展史的宏大圖景之中,全面系統地思考民族教育之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大貢獻。
最后,必須兌現上述兩種立場的有機統整。“社會性”的研究視角雖有助于從宏觀上把握民族教育史的來龍去脈,并可系統闡述民族教育問題背后的“所以然”,但過于規范性、程式化的理論預設,也容易湮沒鮮活的民族群體知覺,進而導致理論研究的呆板和空泛。“教育性”的研究視角雖縮小研究范疇,直接聚焦教育問題,但亦因“根基”的淺薄而難以演繹出民族教育深層次的歷史規律,并可能陷入“就教育論教育”的傳統泥潭。因此,必須將“社會性”和“教育性”兩種立場有機整合,既凸顯宏觀社會背景對民族教育史延伸的支撐承載,也凸顯個體系統場域對民族教育史拓展的帶動引擎。
二、民族教育史梳理的基本原則
原則是人們在對客體本質特點和內在規律充分體認的基礎上,而采取的實踐行為準則,是行為主體“見之于客觀”的主觀價值導向。探究民族教育史梳理的基本原則,就必須立足于民族教育的本質屬性,從民族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兩個維度,反思民族教育自身系統內部運轉的本我個性,反思民族教育與上級系統之間的內在本質聯系(規律),以此來保障民族教育史梳理的客觀、精括。
(一)堅持從屬性原則
首先,民族教育史要從屬于國家史。“民族”總是處于一定的國家之中,帶有鮮明國家烙印的民族性。即便相同的民族群體,其教育文化底色,也將因其所處不同國家政治文化和主體民族教育的熏染而呈現不同的個性魅力。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將民族教育史與國家發展史相聯系,不僅要重點考察國家文明之于少數民族教育的各維影響,還要考察國家內部不同民族教育文化的博弈與同化,更要開展不同國家中相同民族的教育發展邏輯對比。同時,在民族教育史的主要階段劃分、關鍵教育矛盾呈現、核心教育思想生成等方面,都要與國家整體歷史相聯系,并以國家史為參照坐標,衡量和審視民族教育的運動邏輯。
其次,民族教育史要從屬于少數民族史。教育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其肇端源起和嬗變發展都要受制于社會要素的多維制約。鑒于歷史的原因,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形態、社會文明積累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譬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的少數民社會就同時存在封建地主所有制、封建領主制、奴隸制和殘余原始公社制四種社會形態。”[2]相應地,其社會形態所轄的教育系統,必然因其民族的發展程度而形態各異。因此,對民族教育史的梳理,就必須將其與少數民族發展史相聯系。要緊密結合少數民族的發展沿革來審視民族教育的邁進軌跡,結合民族社會的發展形勢來反思和評價民族教育,以此來呼應民族教育與民族社會發展的契合性。
再次,民族教育史要從屬于中華民族教育史。歷史地看,無論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還是窩闊臺時期的崇儒興學,各民族間思想和教育的融合都是積極且頻繁的。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樹立整體史觀,要看到長期的各民族教育是凝聚各民族力量并最終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及中華民族一體觀念的重要力量。”[3]要堅決避免將民族教育史和中華民族教育史的人為割裂,避免在零散性、碎片化的教育史料中,錯失呈現整體性和必然性民族教育規律的良機。同時,還要密切觀照民族教育與中華民族教育的共有屬性,借鑒廣義教育的史學研究范式,以廣義教育的宏大視角來把握民族教育的史料梳理。此外,有關國家整體教育之于少數民族教育的影響方式、影響內容、影響結果等等,亦是民族教育史學梳理中需要予以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堅持個體性原則
民族并不會憑空誕生,她總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4]。特定的地理生態,造就了獨特的生產方式(如漁獵、農耕、游牧等等),生產方式又造就了獨特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又進一步塑造了獨特的民族心理。而所有的這些要素,又孕育了個性鮮明的民族教育體系。即是說,民族教育是與少數民族社會存在相適契的,它們共同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民族社會系統,并按照本我的個性邏輯和諧地運轉著。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堅持“個體性”原則。
首先,要凸顯個體性的民族教育底色。教育是“以文化人”的實踐,而民族教育則是以民族文化“化”民族人的實踐活動。因此,精準把握民族文化的精髓,是科學溯源民族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的重要前提。而這種核心靈魂的實質,就是民族教育的傳統底色。譬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群體價值觀等等,這些要素在通過民族教育途徑予以傳承的同時,也在改變著民族教育的內容和形態。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對傳統民族教育基因進行解碼和詮釋。
其次,要凸顯個體性的民族教育歷史分期。階段劃分是史學歸集的重要焦點,是從整體上把握民族教育階段化個性的重要手段。而對民族教育的歷史分期,則不能完全照搬主體民族發展的歷史劃分。鑒于少數民族獨特的民族歷史、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等要素,就必須“從各民族不同的歷史發展形態的實際出發,制定合乎本民族或整個民族發展的歷史分期。”[5]要堅決避免生搬硬套或削足適履的歷史分期,避免因強調“大一統性”而人為地泯滅少數民族教育的獨特個性。
再次,要凸顯個體性的民族教育歷史矛盾。矛盾是推動民族教育發展的原動力。不同的歷史階段,面臨內外場域的多維利益沖突,少數民族教育會形成不同的實然矛盾,這些矛盾又引導著民族教育朝向個性化的軌跡延伸。因此,梳理民族教育史,事實上就是要梳理民族教育矛盾史,通過呈現矛盾的發展演變,呈現消解矛盾的路徑演變,最終勾勒出民族教育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
最后,要凸顯個體性的民族教育“關節點”。史學的梳理并非是對如煙前塵的全然羅列,而是在浩瀚史海中甄選出具有一般性、典型性乃至“非主流性”的關節點,通過“點對點”的架構支撐,對茫茫史學予以扼要的提示。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將少數民族教育發展中出現的關鍵人物、關鍵思想、關鍵事件、關鍵政策、重大轉折等等,重點放置于民族教育的歷史坐標中,并通過這些個性化的關節點,勾勒出民族教育的嬗變曲線。
三、民族教育史梳理的價值取向
價值取向是主體對外在事物的主觀評判,表現為一定的主觀傾向和情感喜好,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主體的實踐行為。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研究者的主觀價值必然影響“歷史還原”的客觀性。為此,我們有必要從史料搜集的場域、史料采擷的方式、史料甄選的標準以及對史料的歷史評判和價值分析等各個環節,來對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予以應然性的價值預設。
(一)教育場域與非教育場域的雙向觀照
“教育場域”與“非教育場域”指向的是民族教育史料的搜集場域。教育的現象與內涵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教育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今天教育現象的豐富多元,是前代社會教育所遠不能及的。從前代社會追尋現代教育表象,則無異于問道于盲、緣木求魚。但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實踐,民族教育必然與民族社會的繁衍發展緊密相隨。那些并非以“教育”為指稱的教育行為,卻著實地零散于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實踐之中。因此,在對民族教育歷史的搜集中,就不能局限于教育場域,在非教育場域,亦會散存豐沛的民族教育思想。譬如,“反映民族內部支系關系的譜牒、族譜,有意義的節慶聚會,不成文的契約法規,民族地區的文獻和出土文物,壁畫、雕塑、服飾、建筑反映出的民族傳統等。”[6]凡是涉及民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可獲得民族教育的相關信息。也只有將收集場域予以延伸拓展,方能獲取更加全面、系統和深入的民族教育史料。
(二)“主流”與“非主流”的雙向觀照
“主流”與“非主流”指向的是民族教育史料的采擷方式。傳統史學的素材搜集,多傾向正規典籍中的文字記載,并通過文獻之間的相互佐證,輔以研究者的反思、推理,最終呈現歷史的基本樣態。但對于民族教育史而言,此種“主流”史料搜集方式則頗顯欠妥。首先,囿于部分少數民族沒有文字,難以找到專門記錄其教育乃至民族發展的文字典籍,無法在資料中獲得其教育史學素材。其次,零散于漢文典籍中對民族教育的記載,多以“主—客”姿態對民族教育傲視睨睥,難以從主體的立場細微地感知少數民族教育的內在機理。再次,鑒于部分少數民族與國家主體民族間的封閉隔離,加之其特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研究者既難以從國家主流典籍中獲取有關其教育歷史的記載,也難以在其民族歷史中發掘相關文獻資料。故此,在民族教育史的素材采擷中,既需要以“主流”的方式向文字典籍中索取教育史實,更需要以“非主流”的方式向民族群眾的“口頭敘述”中索取歷史回憶。確保在史料豐沛充足的前提下,開展對民族教育史的批判性承襲。
(三)“精英”與“大眾”的雙向觀照
“精英”與“大眾”指向的是民族教育思想的甄選標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創性,但絕不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關鍵期的重要助推作用。作為群眾思想的集大成者,英雄人物總是在特殊的歷史關鍵期,以奮力一擊的形式助推著歷史的超越邁進。長期以來,在民族教育發展史中,涌現出了大量的“精英人物”,他們“既包括少數民族精英人物,也包括主體民族精英人物;既包括著名政治人物及行政官員,也包括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等知名人士、社會賢達。”[7]這些精英人物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崇論閎議,構成民族教育中的“思想史篇”,為民族教育的進步和民族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在民族教育史的梳理中,就必須要考慮民族精英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在關鍵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說精英人物是民族教育史梳理的關鍵“點”,那么,社會大眾意識則是民族教育史梳理的重要“面”。“從廣闊的視野看,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教育運轉和變化發生影響的思想來源是復雜多樣的,精英人物及其思想至多只是其中的一個來源。”[8]那些習慣成俗的民間信仰、民間文化,以及特定時期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都是影響民族教育形塑和嬗變的思想源泉。因此,社會大眾的群體價值和文化心理,同樣應作為民族教育史的梳理素材,以此來為民族教育史學提供更加深厚的思想積淀,以便更加系統地把握民族教育思想的生成背景及縱橫關系。
(四)“歷史”與“現實”的雙向觀照
“歷史”與“現實”指向的是對民族教育史料的客觀研判。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社會問題及不同的教育矛盾。為了“問題”和“矛盾”的消解,不同時代的人們看待教育的視角和立場亦是千差萬別。在民族教育領域,這一現象顯得尤為明顯和復雜。因此,在對民族教育史實的研判時,首先就必須堅持“時空還原”的歷史感。要把具體問題、具體思想放置到民族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中去系統考量,以期全面反思這一思想或理論產生的客觀條件及對當時教育和社會發展的時代貢獻。反之,如不能將其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整合審視,無法呈現教育思想的肇端語境和生長基壤,便會造成民族教育史實的形單影孤、晦澀抽象、懸浮無根。其次,對民族教育史實的研判還必須堅持“時空穿越”的現實感。要將歷史中出現的民族教育矛盾、民族教育思想放到現代民族社會場域中,對標古今之間的歷史相似性,并基于古代的經驗啟示,反思現代問題的消解理路,進而嘗試性預測民族教育的發展趨勢,豐富對民族教育規律的把握積累。
(五)“教育”與“教化”的雙向觀照
“教育”與“教化”指向的是民族教育史料的價值分析。史學回眸的價值不僅在于客觀呈現,更在于歷史還原之后的“以史為鑒”,即對史實資料的價值分析。而民族教育不僅具有狹義的“教育”屬性,更具有宏觀的“教化”特質。作為生產于我國古代的本土專有名詞,“教化”的內涵和價值遠非“教育”所能及。在傳統社會里,“教育”除了具有個體功能外,更被統治階層賦予了“化民成俗、建國君民”的重要使命,不僅突出了培養人的“教育性”,更體現了社會治理的“社會性” (即教化)。而民族教育更是如此,“它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治革新、文化傳承、民族交流、民族凝聚力創生、大一統民族觀念的形成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9]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多族一體”國家的形成。因此,對民族教育史料的價值分析,就必須跳出“教育”的段位,要將“教育”上升至“教化”的高度,系統審視民族社會場域中,助推民族教育發展的生產方式、政治決策、民間信仰、文化習俗等要素,并進一步反思民族教育史實所帶來的人才培養、社會助推等實踐功效,以此來兌現對民族教育史實評價的客觀公允和系統全面。
四、民族教育史梳理的聚焦內容
研究立場、原則和價值取向,只能為民族教育史的梳理提供前提性思考,而具體內容的聚焦,才是史學研究最終的落腳點。如果沒有具體的民族教育史實,縱然有再好的方法論導向,也終究是“有炊無米”。
(一)宏觀層面的民族教育史學內容
宏觀層面是從整體性視角來把握民族教育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重在凸顯對民族教育史的整體性界說和特色性概括。這一維度的民族教育史學內容主要包括:一是民族教育的肇端源起。重點呈現研究主體對少數民族教育發端時間及形式的體認,為民族教育史學研究劃定精準的邏輯起點,從源頭上系統把握民族教育與少數民族和民族社會發展的縱橫關系。二是民族教育的階段劃分。主要呈現民族教育發展的躍升層級和重大轉折,在探究民族教育升騰邁進的征途中,不同階段民族教育的主要特點、造成這一特點的內外致因、以及該階段民族教育的共時性成就和歷時性啟示。三是民族教育的底色概要。主要基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之于民族教育的影響干預,探究民族教育個性化的教育思想、內容形式、價值傾向等要素,解碼民族教育的傳統基因,概括凝練民族教育的文化底色。并通過這一系列的史學梳理,探究民族教育之間的個性差異,以及民族教育個性的“所以然”。
(二)中觀層面的民族教育史學內容
中觀層面是從價值目的、發展導向維度來審視民族教育的發展軌跡,重在凸顯對民族教育具有指導性、影響性乃至決定性要素的呈現。主要包括:一是民族教育史中的關鍵人物及其思想流派。呈現民族教育史中出現的重要教育人物及非教育人物,系統梳理這些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反思這些思想背后的成因及時代價值。對相關教育思想聯結而成的教育流派予以歷史追蹤,勾勒民族教育流派思潮的豐富、壯大乃至革新、覆滅的圖景。二是民族教育史中的關鍵教育事件。重點呈現教育場域及非教育場域中出現的對民族教育具有或助力推進、或重創阻滯的關鍵事件,反思民族教育之于民族社會及國家整體發展之間的正相關系。三是民族教育目的的發展嬗變。呈現不同階段民族教育目的的價值傾向,反思民族個體、民族社會及民族教育之間的博弈與協同關系。四是民族教育類型的發展嬗變。重點呈現少數民族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各自的價值和形式變遷;呈現少數民族非形式化教育、形式化教育和制度化教育之間的交融牽絆及其各自的演變過程、邁進邏輯。
(三)微觀層面的民族教育史學內容
微觀層面是從民族教育具體運行的視角來審視其自身嬗變,重在從民族教育各要素的維度來把握其內部的相互作用規律。主要包括:一是民族教育的教育者。重點呈現民族教育史中,承擔教育者角色的主體類型及主體轉向。即歷史中哪些人物扮演了民族教師的角色,隨著社會的發展,民族教師又逐漸轉向為哪類特殊人群。二是民族教育的受教育者。主要呈現歷史中少數民族受教對象的人群類型、主體轉向及受教人群覆蓋面,呈現歷史中培養出的少數民族思想鴻儒、專業翹楚、能工巧匠等各行各業的卓越人才。并通過培養人才類型的嬗變推理民族教育價值取向的發展軌跡。三是民族教育的教育方法、教育途徑和教育語言,尤其要重點呈現民族教育中使用的教育語言,探究教育語言由“單語”到“雙語”或“多語”的轉變歷程,進而發掘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之間的認同和融合,發掘少數民族和國家之間教育文化的博弈與趨近。四是民族教育的教育內容。主要呈現包括民族團結教育、民族認同教育、民族文化自信教育、國家認同教育等在內的思想維度的教育內容,呈現包括民族生活知識教育、民族學科專業知識教育、民族特色產業技能教育等在內的知識及技能維度的教育內容,呈現包括民族民間藝術傳承、民族特色體育運動教育、民族傳統音樂、美術、詩歌、游戲、服飾、飲食、建筑、手工教育等在內的體育及審美維度的教育,并通過對教育內容的遞增程度、教育內容的轉型傾向來反思民族教育的發展速度。五是民族教育的教育場域。主要呈現民族教育發生地點的變化及交錯,如生產勞動場域、家庭場域、寺廟場域、學校場域、社會活動場域等等,并通過教育場域的轉移及協同來反思民族教育在民族社會中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