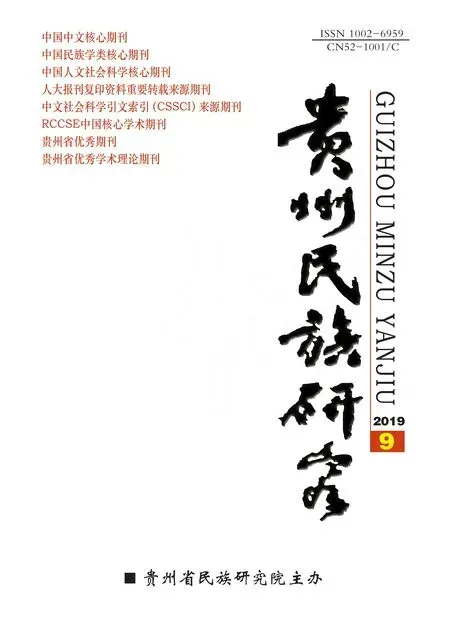多模態(tài)視閾下傣族敘事詩《召樹屯》英譯與民族文化認(rèn)同研究
郝會肖 任佳佳
(1.西南林業(yè)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云南·昆明 650224;2.昆明理工大學(xué) 外國語言文化學(xué)院,云南·昆明 650550)
《召樹屯》源于傣族佛教典籍《貝葉經(jīng)》,是一部流傳極廣且深受傣族人民喜愛的敘事長詩。它通過歌頌王子召樹屯和孔雀公主喃婼娜之間純潔和忠貞的愛情,表達(dá)了傣族人民崇高的美學(xué)理想和包容開放的道德原則。這部長詩不僅繼承了傣族神話傳說和口頭敘事程式的文體風(fēng)格,更承載了傣族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地理景觀,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之一。1956年,這部敘事長詩經(jīng)陳貴培、劉綺、王松等整理和翻譯后首次發(fā)表在《邊疆文藝》第1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相繼出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譯為漢文本的首部傣族文學(xué)作品。然而直到20世紀(jì)90年代,這部典籍的多元民族色彩及其所蘊(yùn)涵的文學(xué)、文化和教育價值才開始受到西方學(xué)者的關(guān)注。Felicity Lufkin認(rèn)為《召樹屯》凝聚了中國多元文化的民族精神。[1]Michael Edward Brown和Sumit Ganguly在《亞洲語言政策與民族關(guān)系》一書中評價認(rèn)為《召樹屯》傣文版和漢文版的出版有助于推動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資源的保護(hù)和開發(fā),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學(xué)寶庫增添了一顆瑰麗的明珠。美國學(xué)者Yuan Haiwang和Timothy L.Gall分別在其著作《孔雀公主:中國少數(shù)民族民間故事》和《世界文化與生活百科全書:亞太卷》中譯介了傣族歷史和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概況,對《召樹屯》的淵源和故事梗概作了詳細(xì)評述,為世界了解我國多元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形態(tài)提供了重要參考。《召樹屯》以豐富的民族文化承載量、少數(shù)民族女性形象建構(gòu)和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等,儼然成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美學(xué)思想最集中的體現(xiàn)[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召樹屯》在國內(nèi)歷經(jīng)“口頭傳唱、翻譯出版和影視藝術(shù)改編”等多模態(tài)的跨文化傳播,為民族典籍走向世界,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力開辟了廣闊的闡釋空間。1961年,《召樹屯》(連環(huán)畫改編本)的英、法、德和世界語譯本出版,以重彩畫的視覺呈現(xiàn)形式,為西方讀者了解傣族絢麗多姿的文化打開了窗口。20世紀(jì)80年代,我國開啟了少數(shù)民族典籍整理和研究的新時期,西南等多民族地區(qū)在少數(shù)民族文字翻譯和整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云南人民出版社對《召樹屯》做了重新修訂,突顯了作品的文學(xué)性。無論是藝術(shù)形式還是思想內(nèi)容,修訂后的《召樹屯》都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是了解傣族發(fā)展史和民族風(fēng)情的一面鏡子[3]。2008年,《召樹屯》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名錄”,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也將其列為“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動態(tài)數(shù)據(jù)庫項目”中的主要典籍樣本,為研究傣族典籍的國際傳播和接受情況提供了數(shù)據(jù)支撐。2018年,由李昌銀主編的《云南少數(shù)民族經(jīng)典作品英譯文庫》出版,文庫對《召樹屯》等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神話和民間故事典籍進(jìn)行了英譯,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和擴(kuò)大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在世界文學(xué)舞臺上的影響力譜寫了新的篇章。總體來說,《召樹屯》歷經(jīng)多模態(tài)的改編和翻譯,說明它的流傳不僅涉及民間文學(xué)的傳承問題,更與時代和文學(xué)傳播媒介的變化息息相關(guān)。
一、新媒介語境下民族典籍翻譯的多模態(tài)
多模態(tài)是一種“來自不同符號系統(tǒng)的意義集合”[4],本質(zhì)上指在給定語境中兩種及兩種以上不同模態(tài)的并存現(xiàn)象,這些模態(tài)包括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圖像和聲音等。傣族敘事長詩《召樹屯》在跨文化傳播中,歷經(jīng)敘事上的重構(gòu)和文化隱喻上的變異,從口頭傳承、印刷傳播和多維度的媒介嬗變,再到域外的文學(xué)改編和重寫,經(jīng)典文本在多元語境中形成了共生互補(bǔ)的不同文化,是多模態(tài)話語相互交織、共同參與意義構(gòu)建的結(jié)果[5]。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研究先后經(jīng)歷了從重視語言技能到重視文化功能的轉(zhuǎn)向。上世紀(jì)90年代末,多模態(tài)話語分析理論進(jìn)一步打破了語言學(xué)的認(rèn)知藩籬,開始融合現(xiàn)代多媒體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最新成果,強(qiáng)調(diào)非語言因素對翻譯的制約作用,并倡導(dǎo)文化及翻譯的多維性理念。
翻譯是文化之間互動交往的橋梁。譯介非遺文化典籍過程中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讓中華文化的民族瑰寶以鮮活的形態(tài)與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斷加深,愈來愈多的國外學(xué)者感受到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異域風(fēng)情,與漢文化相比更具有樸素的生態(tài)智慧和異彩紛呈的審美情趣。此外,民族典籍也不再只是學(xué)者或海外漢學(xué)家的專業(yè)領(lǐng)域,較之學(xué)術(shù)界相對深入和系統(tǒng)的線性研究,普通讀者則更多地呈現(xiàn)出“碎片化、視覺化和信息索取性”的閱讀傾向。翻譯包含著多種符號系統(tǒng)的轉(zhuǎn)換與信息傳遞[6],因而在傳達(dá)原文本語言文字信息的同時,再現(xiàn)其附帶的多模態(tài)內(nèi)容,以適應(yīng)新時代受眾的認(rèn)知心理,成為民族典籍翻譯領(lǐng)域的研究者深入探究的重要問題。多模態(tài)翻譯作為新媒介語境下翻譯研究的一個新方向,改變了人們對翻譯活動和翻譯質(zhì)量評估標(biāo)準(zhǔn)的傳統(tǒng)認(rèn)知[7]。
二、《召樹屯》的多模態(tài)翻譯模式建構(gòu)
(一)視覺模態(tài):文體與思想視界上的契合
讀者已有的閱讀經(jīng)驗和思維結(jié)構(gòu)會使他們對譯作的顯現(xiàn)方式產(chǎn)生一種定向性期待。每次面對一個新文本,讀者就會在經(jīng)驗視野中重新組織以往的知識積累,綜合各種“經(jīng)驗、趣味、素養(yǎng)、理想”等要素,在閱讀過程中產(chǎn)生審美接受。這種期待視野能夠喚醒讀者的文化記憶,把他們帶進(jìn)一定的情感狀態(tài)。翻譯同樣是一個雙重和互動的文本閱讀過程,譯者首先要以原語讀者的身份對原文本進(jìn)行閱讀,然后還要依據(jù)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制定適當(dāng)?shù)姆g策略,縮短讀者與原文本之間的審美距離,使二者在視界上達(dá)到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文本的意義是由原語文本所富含的意義和譯者的能動性共同造就的。因而,譯者的首要任務(wù)就是考量民族典籍譯文的文體風(fēng)格。例如,對于彝族撒尼民間敘事詩《阿詩瑪》和傣族敘事長詩《朗鯨布》的翻譯,Gladys Yang和Rewi Alley 都采用了歌謠體(Ballad)形式,把我國優(yōu)秀的少數(shù)民族詩歌典籍介紹給了西方世界,這種文體的轉(zhuǎn)譯方式也得到了國內(nèi)外學(xué)界的肯定,收到了理想的傳播效果[8]。吳相如的《召樹屯》英譯本在文體風(fēng)格上亦選擇了歌謠體,以詩譯詩,直觀地再現(xiàn)了原語詩歌簡潔的語言特點,揭示傣族文化的精神內(nèi)涵。在第三章“勐董板有七個姑娘”中,敘事者以詩人的口吻向隱含讀者描述了傣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環(huán)境——勐董板是個好地方/ 遍地開鮮花/ 滿山是牛羊/ 來往的人都騎著大象。對應(yīng)的譯文如下:
Mengdongban was a nice place,
With so many blooming flowers.
Cattles and sheep were all over the mountains and plains,
People rode on elephants to and fro.[9]
從表現(xiàn)方式和反映生活的廣度來看,歌謠也屬于敘事詩的一種。譯者嘗試采用歌謠體這一呈現(xiàn)方式,既與原詩“四行為一個詩節(jié)”的基本文體結(jié)構(gòu)一致,又呼應(yīng)了歌謠傳達(dá)的“英雄、愛情、正義、冒險和悲劇”主題,讀者更能從類型的先在理解上對譯文產(chǎn)生期待,感受到原語語言與敘事藝術(shù)的美感。
插圖不僅對原語詩歌文字作了補(bǔ)充說明,而且?guī)椭D(zhuǎn)換和保存文化元素,映射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期的社會習(xí)俗,起到了視覺信息的傳播作用。196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首部《召樹屯》(連環(huán)畫版)英譯本收錄了畫家程十發(fā)繪的40幅插圖,畫稿色彩絢麗、色度鮮艷,不僅真實地反映了傣族地區(qū)的自然地理風(fēng)貌,對傣族女性柔美而又剛毅的氣質(zhì)形象和艷麗的服飾格調(diào)等均刻畫得生動而浪漫,具有極強(qiáng)的敘述性。“召樹屯之俊朗勇武,喃婼娜之秀美善良,皆神情活現(xiàn)呼之欲出;傣家之服飾器用,其村寨民俗,異域情調(diào),都出之有據(jù),刻畫入微”[10]。197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召樹屯》漢文本收錄了劉紹薈作的4幅插圖,流動的線條勾勒出了傣族人民對人性的自由和理想愛情的追求,渲染了傣族敘事詩的原生態(tài)形式和美感,體現(xiàn)了傣族文化典籍文學(xué)性和藝術(shù)性的有機(jī)結(jié)合。
在多模態(tài)翻譯中,視覺元素用于傳遞語言信息。圖文符號同時呈現(xiàn),圖像以不同的模態(tài)完成對文本的翻譯[11]。《召樹屯》中蘊(yùn)涵的具有顯著的傣族文化特色的“服飾、裝飾、身姿和色彩”等多模態(tài)的視覺符號,在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中彰顯了民族審美文化的亮點。讀者在閱讀語言文本和圖畫信息的過程中會建立多重的和互為補(bǔ)充的心理表征,插圖的融入能拓展譯者對文本內(nèi)容的闡釋,強(qiáng)化讀者對文本主題和文化信息的接受,減少民族典籍在翻譯中的文化損失。《召樹屯》2018年版的吳譯本雖在語言和文本結(jié)構(gòu)上做到了對原作的忠實,但因舍棄了民族重彩畫的敘述元素,閱讀的趣味性、生動性和藝術(shù)的感染力無疑在跨文化傳播中產(chǎn)生了“文化折扣”。
譯文加注是跨越文化鴻溝,補(bǔ)充傣族詩歌典籍民族志信息的一種有效手段。只有以多元文化觀察者的身份來審視傣族獨特的風(fēng)俗禮節(jié),對《召樹屯》中的方言土語、典章制度和民俗風(fēng)情等提供相應(yīng)的知識性注釋,譯者才能在保留民族性的前提下闡釋異文化事象,填補(bǔ)目的語讀者的想象空白。《召樹屯》(吳相如譯)中共有30多條英文注釋,對傣族的宗教信仰、神話典故和崇水習(xí)俗等一一作了釋義。為確保譯文的流暢性和文化意境傳遞的準(zhǔn)確性,直譯和添加注釋的翻譯策略最大限度地還原了傣族詩歌的文學(xué)性和思想性特征。例如,對于傣族諺語、宗教信仰、傳說中的金鹿和神鳥“錦那麗、錦那暖”以及傣族婚俗“拴線禮”等,譯者都增添了詳細(xì)注解,充分展現(xiàn)了原語詩歌的精神風(fēng)貌及其深層文化內(nèi)涵,使譯文真正地達(dá)到了形神兼?zhèn)洹?/p>
(二)聽覺模態(tài):傣族詩歌的韻律美與意境美
源于貝葉經(jīng)的《召樹屯》在傣族民間主要以口述故事和韻文體的“贊哈唱本”兩種形式流傳開來,后經(jīng)民族學(xué)家發(fā)掘、整理和翻譯成漢文出版后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書面文學(xué)媒介的傣文手抄本和漢譯本不但改變了口述文學(xué)的傳播方式,使其原有的語言文字樣式和聽覺符號得以保存下來,更促進(jìn)了傣族文學(xué)的跨文化傳播和發(fā)展。音樂性作為傣族詩歌的一個自然屬性,在《召樹屯》翻譯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語贊哈調(diào)的韻律美和意境美,使目的語讀者對原典的格律特征有所認(rèn)識,也是譯者應(yīng)盡力遵循的一個翻譯原則。
贊哈調(diào)在集傣族古歌謠、頌歌等唱腔韻式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由三、四個音節(jié)的短句和十幾個音節(jié)的長句交替組成,韻律上有內(nèi)押韻和句末押韻等主要形式[12]。《召樹屯》中出現(xiàn)的“铓鑼、玎琴、蘆笙、象腳鼓”等都是贊哈伴唱的主要樂器,這些傣族樂器的共同特點是曲調(diào)與詠唱密切結(jié)合,樂段變化反復(fù),與傣族敘事詩“反復(fù)鋪敘、反復(fù)詠唱”,以及“比喻、夸張、重疊、渲染”等多重修辭手法相契合。英國歌謠體詩歌同樣具有很強(qiáng)的韻律感,通常在詩節(jié)中大量運用疊句遞增和重復(fù)來渲染氣氛和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因而,在英譯中通過歌謠體這一聽覺化的呈現(xiàn)形式,能夠最大程度地再現(xiàn)傣族詩歌的音樂特征。例如,在第二章“王子召樹屯”中,占卜師摩古拉為王子召樹屯卜卦祈福時說道:“天空中最能飛的是老鷹/地上跑得最快的是金鹿/ 孩子的名字啊/ 應(yīng)該叫做召樹屯”。譯者可借助歌謠體形式,來做出切合原詩歌語篇的形式特征和藝術(shù)內(nèi)涵的翻譯:
The noblest eagles flies at sky’s height,
Speed gives the golden deer fame.
Be a warrior and win the fight,
Zhaoshutun mathes his name.
詩化的語言能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和情感共鳴,譯文采用抑揚(yáng)格四音步和三音步交替的歌謠體詩行形式,第二行與第四行押尾韻,整體工整,有張有弛,曲折多變,再現(xiàn)了傣族詩歌的節(jié)奏性和音韻感,更能讓讀者在心理上找到一種能共鳴的文化和情感結(jié)構(gòu)。
此外,譯名作為民族典籍進(jìn)入西方文化概念系統(tǒng)并持續(xù)不斷地生成意義的第一個文化符號,其重要性在翻譯過程中也不言而喻。 《召樹屯》目前存在六種英譯名,勾勒出了傣族典籍在國外的演化與接受史。1961年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譯名為“Chaoshutun and Nannona”,采用音譯的方式保留了其聽覺上的聲音效果,為傣族典籍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開辟了道路。通過WordCat數(shù)據(jù)庫進(jìn)一步檢索發(fā)現(xiàn),這版譯本在英、法、美、新西蘭等多個國家的大學(xué)圖書館都有館藏。這些圖書館在著錄時,對《召樹屯》的載體形態(tài)和文類特征還作了以下附注:“Chaoshutun and Nannona.Adapted from a Folk Narrative Poem of the Tai People in Yunnan Province,China.Illustrated by Cheng Shih-fa.”,提高了讀者索取信息的針對性和準(zhǔn)確性。在西方學(xué)者的研究文章和學(xué)術(shù)專著中,《召樹屯》還有“Zhaoshutun: Dai Folk Narrative Poems” “ Zhaoshutun: Legend of a Dai Prince”“ Zhao Shutun Epic” “ Peacock Princess” 和“Zhaoshutun: Peacock Princess Story”等變體形式,可見這部長詩的譯名經(jīng)歷了從“音譯”到“意譯”再到“音譯、意譯和描述相混合”的變化,以及“敘事詩”“傳奇”“史詩”和“故事”等的類別探微。
過于歸化的舊譯和音譯會掩蓋原典的文化意義,而過于雜亂的譯名也容易給人帶來困擾,在數(shù)據(jù)檢索上不具唯一性和一致性。因而,規(guī)范民族典籍的譯名十分必要。為保持原語的文化特征和聽覺屬性,對《召樹屯》這一書名的翻譯可借鑒 《郎鯨布》(Not a Dog: An Ancient Tai Ballad)的譯法,將其譯為“Prince Zhao Shutun:An Ancient Dai Ballad”,首先沿用部分舊譯以便目的語讀者對其歷時傳播中形成的規(guī)范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滿足譯名的指稱性和專屬性的認(rèn)知條件。其次,再對譯名進(jìn)行符合時代語境的少許變異。依據(jù)國家頒布的各民族名稱的羅馬字母拼寫法和代碼,將民族名稱“傣”規(guī)范為“Dai”。最后,再采取補(bǔ)充人物身份和文本體裁等背景信息的“文化互滲”譯法,實現(xiàn)文本的“交際—語用”功能,讓目的語讀者深入了解譯作的文化屬性。
(三)傳播模態(tài):民族文化基因的再生
《召樹屯》在跨文化和跨媒介的流變中,衍生出了繪本、木偶片、歌舞劇和電影等多模態(tài)的符碼形式,共同塑造了以“孔雀形象”為象征的傣族文化和價值觀念體系,促進(jìn)傣族詩歌典籍在不同文化交融中獲得新的生命力。文化的生產(chǎn)、傳播和消費其實就是符號的生產(chǎn)、傳播和消費。對受眾來說,當(dāng)一種民族文化以動畫、舞劇等藝術(shù)形式進(jìn)入衍生產(chǎn)品市場后,消費者更愿意為之投入熱情[13]。
動畫藝術(shù)是傳承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載體之一。1963年上海美術(shù)電影廠攝制的木偶動畫《孔雀公主》在場景、人物和道具設(shè)計中,從不同角度還原了傣族人民的文化傳統(tǒng),生產(chǎn)生活場景,而且對寄托傣族人文精神的“孔雀舞”進(jìn)行了唯美的呈現(xiàn)。這部動畫以極具意象性的民族文化刻畫,受到了國內(nèi)外觀眾的喜愛,客觀上推動了《召樹屯》這部敘事詩走向世界[14]。20世紀(jì)70年代末,傣族神話舞劇《孔雀公主》更是多次在國外演出,受到日本及泰國、緬甸、印度、老撾等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歡迎,成為中國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舞劇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為《召樹屯》的域外傳播開辟了一條生機(jī)勃勃的新途徑。白樺改編的電影劇本《孔雀公主》進(jìn)一步吸收了貝葉文學(xué)中的浪漫主義元素,借鑒了《召樹屯》的“天鵝處女型”故事母題和敘事結(jié)構(gòu),講述了一個美妙動人、具有濃郁傣族風(fēng)情的愛情故事,在國際影壇上獨樹一幟,獲得多個獎項。英國兒童文學(xué)作家、插畫師Suzanna Leigh游歷云南后,依據(jù)《召樹屯》的故事原型創(chuàng)作出了繪本《孔雀公主的傳奇故事》(Peacock Princess: A Self-Rescuing Princess),對充滿“藝術(shù)之美”和“舞蹈之美”的傣族女性形象進(jìn)行了贊譽(yù),這表明傣族文化已經(jīng)跨越國別,邁向了世界文學(xué)會通的舞臺。Sean Macdonald和Emily Wilcox 分別在《中國動畫:歷史、美學(xué)與媒介》和《中國社會主義早期的舞蹈發(fā)展史》中梳理了《召樹屯》的動畫和舞蹈的改編史和世界影響力,及其作為敘事文本的符號意義。總體來說,《召樹屯》的舞劇、動畫、電影和文學(xué)等改編實踐與探索實現(xiàn)了傣族貝葉文化資源的現(xiàn)代化之路,把少數(shù)民族文化交流推向了一個更縱深的層次。
開放出版可以方便讀者在第一時間共享人類文明成果,這一模式的興起可以說是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典籍找到了一個新的傳播方式。青海土族學(xué)者李得春與Gerald Roche合譯的《土族敘事長詩》是“Open Book Publishers”平臺第一部關(guān)于我國少數(shù)民族詩歌典籍的譯作。它采用“土族語-漢語-英語”三語對照方式,向西方讀者譯介了流傳于青藏高原東北部土族的七部長詩。它不單是土族活態(tài)口頭文學(xué)的經(jīng)典集成,更融匯了藏族、土族和漢族的民間智慧和文學(xué)成就,堪稱是中國少數(shù)民族絢麗多姿的藝術(shù)寶庫的一個縮影[15]。
《土族敘事長詩》的翻譯和傳播模式,對進(jìn)一步探討《召樹屯》的翻譯和國際傳播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一方面,“傣-漢-英”三語對照方式能真實反映我國民族聚集地多元的語言文化景觀,能為讀者引介諸如“婚姻制度、僧侶文化、民間音樂”等文化理念,保留傣族語言文字這一獨特的風(fēng)姿和情調(diào)。另一方面,集體合作的翻譯方式和在線出版的傳播模式,符合新媒體文學(xué)的認(rèn)知和接受特征,能為譯作贏得更多的受眾,讓少數(shù)民族詩歌經(jīng)典在與讀者互動中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和發(fā)展。
翻譯是對原語言文字的再闡釋和再創(chuàng)造,在與文本形態(tài)、媒介載體和目的語讀者的不斷對話過程中,發(fā)揮民族典籍的審美張力和文化功用。隨著大數(shù)據(jù)時代和新媒體文學(xué)的推進(jìn),《召樹屯》的對外傳播應(yīng)充分調(diào)動先進(jìn)的科技手段和學(xué)術(shù)觀念,探索出一條符合新受眾認(rèn)知的翻譯和傳播路徑。例如,傣文輸入法的研發(fā)實現(xiàn)了傣族典籍的數(shù)字化,學(xué)術(shù)交流的國際化更是擴(kuò)大《召樹屯》影響力的一個催化劑,“阿詩瑪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將彝族文化傳播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就是最好的佐證。此外,從比較文學(xué)視角探尋《召樹屯》與西方敘事詩的共識,以及采取“節(jié)譯”的方式,在國外權(quán)威的詩歌雜志上對《召樹屯》進(jìn)行譯介等,都能加深其在國際傳播中的文化印象。
三、民族典籍翻譯與民族文化認(rèn)同
翻譯并非是簡單地把一個文化的能指轉(zhuǎn)化為另一文化的所指過程,更是一種文化行為,一項建構(gòu)社會和民族價值觀的社會活動。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語言學(xué)家James Martin開始關(guān)注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關(guān)系,提出了從語言的每一個層面到意識形態(tài)都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的觀點[16],并從宏觀的語篇結(jié)構(gòu)角度探討了適用于翻譯理論和實踐的語境模型。美國學(xué)者John Gullory則提出詩歌等文學(xué)作品具有媒介性,能夠構(gòu)筑和連結(jié)一個社會的關(guān)系和現(xiàn)實。他建構(gòu)了如下的“文學(xué)傳介功能”模型:
單一作品 ]生平著作 ]文類 ]論述 ]媒介]社會脈絡(luò) ]社會整體[17]
根據(jù)這個模型,傣族敘事長詩《召樹屯》的民族文化認(rèn)同功能可以如此敘述:
《召樹屯》]傣族 ]敘事詩 ]民族文學(xué) ]口述、印刷、媒介融合]傣族歷史和文化遺產(chǎn) ]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與民族文化認(rèn)同[18]
翻譯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傳介的關(guān)鍵途徑,具有讓民族典籍走出文本語境和促進(jìn)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重要功能。一方面,翻譯在民族形象塑造和文化傳承過程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例如《召樹屯》中關(guān)于傣族女性服飾和穿戴習(xí)俗的描述無處不在,譬如公主喃婼娜身穿和佩戴的“孔雀衣”(peacock gown)“金簪” (gold hairpin)“金手鐲”(gold bracelet)以及“玉石戒指”(jade ring)等,都折射出了傣族女性熱愛生活、精致典雅的審美情趣。另一方面,翻譯在對傣族詩歌語言層面信息進(jìn)行還原的同時,在語境層面對其所在的社會文化也做出了較為充分的補(bǔ)充。傣族詩歌《召樹屯》的譯介,不僅傳承了傣族的傳統(tǒng)文化,更加深了傣族人民對自身優(yōu)秀民族文化的認(rèn)知,提升了傣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認(rèn)同和民族自信力。
四、結(jié)語
在全球互聯(lián)互通的新媒介語境下,推動少數(shù)民族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時代精神,應(yīng)是民族學(xué)家和翻譯家共同肩負(fù)起的一項重任。傣族人民居住在云南邊疆地區(qū),處在與周圍國家交流的橋頭堡,在“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位置上起著“連接云南,輻射東盟”的重要作用。傣族詩歌典籍《召樹屯》的多模態(tài)翻譯和傳播不僅能讓世界共享民族文化遺產(chǎn),更有助于維護(hù)民族團(tuán)結(jié),增強(qiáng)民族文化認(rèn)同。《召樹屯》的多模態(tài)翻譯和研究視角,為構(gòu)建和闡釋傣族人民“親仁善鄰、樂群愛寨、民族和睦、和諧共生”的民族形象和傳統(tǒng)道德內(nèi)涵,以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民族典籍翻譯應(yīng)力圖跨越文化距離,以適應(yīng)新受眾認(rèn)知和開放獲取的新媒體文學(xué)形式,拓展譯作的接受空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以積極的姿態(tài)來參與世界文學(xué)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