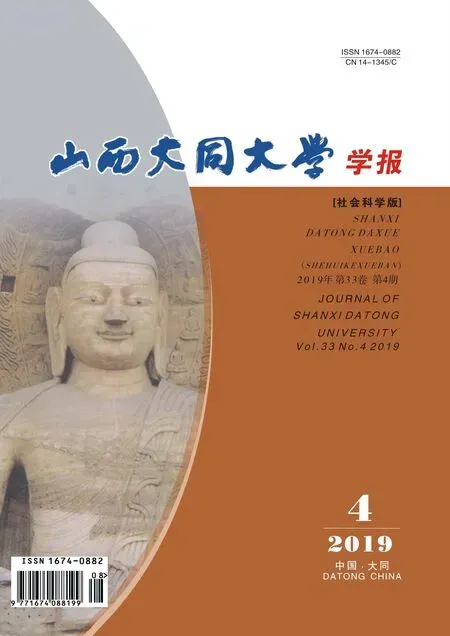晉北大同遼金墓葬文化特征探析
張 玲
(山西大同大學云岡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大同 037009)
大同是北方遼金漢人墓葬分布的重要地區(qū),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同遼金墓葬考古成果不斷出現(xiàn)。墓葬不僅能夠展現(xiàn)遼金喪葬制度及喪葬文化的面貌,而且其所蘊涵豐富的歷史社會信息亦有助于揭示歷史與地域文化內(nèi)涵。
一、墓葬形制
迄今大同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遼金墓葬可分為磚室墓、土坑墓、土洞墓三大類。
磚室墓是大同遼金墓葬中最為常見的墓葬形制。其墓向大都坐北朝南,體現(xiàn)了古代“負陰抱陽”的風水觀念。墓室均為單室墓,皆由墓道、甬道、墓室構(gòu)成。遼代磚室墓墓室平面為圓形,不少墓道或為長方形斜坡式,或為長方形階梯式;墓室頂部以疊澀砌筑的穹窿狀居多,亦有如十里鋪M15 的圓形券頂式。金代磚室墓墓室平面多為方形,而1960年7月在大同市西南發(fā)掘的金墓平面則為八角形;墓頂多為疊澀穹隆頂,亦有四角攢尖圓錐頂,如閻德源墓。磚室墓中多建有棺床,以磚砌于墓室后部。遼代棺床于墓室后部傍靠北壁砌建而成半圓形,占墓室面積的1/4-1/2 不等;金代棺床則于墓室后部砌建成長方形。墓室的甬道、周壁、墓頂、地面所砌青磚為長方形或正方形,磚有素面、溝紋、直紋。其中以單面溝紋磚最具代表,遼墓磚的溝紋以7 條見多,金墓磚溝紋有5 條、6 條、8 條、11條不等。墓室砌磚采用錯縫平砌或丁順砌法,有的砌磚之間還會以膠凝材料勾縫,所用有黃泥、紅褐色粘泥、白灰等。
大同遼金磚室墓多有壁畫,遼代早期磚室墓中業(yè)已出現(xiàn),如十里鋪遼墓M27、許 從 赟夫婦墓、2004年大同機車廠遼墓,至晚期磚室壁畫墓已相當普遍,在大同金代早期、中期墓葬中壁畫依然流行。遼、金墓葬壁畫制作方法相同,皆以磚壁作為支撐體,其上涂抹草拌泥(個別遼墓涂抹褐色粘泥)與白灰膏作為地仗層,于其上繪作壁畫。墓室內(nèi)部為影作木結(jié)構(gòu),在墓壁繪仿木建筑構(gòu)件,如角柱、斗拱、櫨頭、闌額、普柏枋等;有的墓葬中還施以磚雕仿木,如 許從赟 夫婦墓砌筑的墓門門樓上的各色斗拱、閻德源墓墓壁上的單抄四鋪作斗拱。興起于晚唐五代墓葬中的仿木結(jié)構(gòu)建筑式樣,至遼金盛行于北方墓葬中,地上世界人們生活居所的風格被模仿于地下世界的墓室中,體現(xiàn)著“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理念。
大同公開發(fā)掘資料的5 座遼金土坑墓均為豎穴土坑墓。所不同的是,南關(guān)遼墓M3 的平面近方形,而十里鋪4 座金代呂氏墓的平面為圓形。在十里鋪4 座土洞墓中,遼墓M9、M10 為豎穴土洞墓,均為坐北朝南,先向地下開挖長方形豎穴,然后在豎穴北壁開鑿洞口朝南的洞室。其墓葬形制與大同南關(guān)唐墓的豎穴土洞墓形制相似。另外龍新花園遼墓與西環(huán)路金墓M6 為斜坡墓道土洞墓。此種形制的墓葬在大同北魏時一度流行,唐墓中亦有發(fā)掘。兩座墓葬均為坐北朝南,墓道皆為長方形斜坡式,但龍新花園遼墓墓室平面為長方形,西環(huán)路金墓M6 墓室平面為方形。
二、火葬習俗
“云中故俗,人亡則聚薪而焚之”,[“1]云中故俗”所指時期即為遼代。大同火葬始現(xiàn)于遼代,盛行于金元。其火葬墓多將骨灰放置于小型石棺內(nèi),或為長方形盒狀,或為前寬后窄狀,稍講究的石棺棺身會雕刻紋飾。而如許從 赟這樣較高等級的官員墓,其石棺外則有木棺罩,這與遼地一些契丹墓中木構(gòu)小帳內(nèi)放棺的習俗頗為相似。還有置于石棺中的木匣之內(nèi),如十里鋪金墓M11、M12、M14。亦有用木棺,或置于石棺內(nèi)套的木棺中,如云大金墓M2。石棺內(nèi)置木匣或木棺,是金代流行的葬具使用方式。另有盛放于釉陶棺中,如馬家堡遼墓M1;又有以瓷罐存放骨灰,如十里鋪遼墓M27 將骨灰置于黃白釉刻花瓷罐、臥虎灣遼墓M5 與M6 均將骨灰置于黑釉瓷罐。
自佛教傳入中國, 槃受其涅 思想及荼毗之禮的影響,火葬一度成為僧尼群體推崇的喪葬方式。但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時期土葬始終在漢地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迄至宋代,火葬風行。與此同時,遼、金亦出現(xiàn)火葬習俗,佛教被視為主要的影響因素。佛教之于遼金葬俗,正如遼道宗時期的塔墳記中所言:“及佛教來,又變其飭終歸全之道,皆從火化,使中國送往,一類燒羌。至收余燼為浮屠,令人瞻仰,不復(fù)顧歸土及泉之義”。[2](P413)
需考慮的是,北魏崇奉佛教,作為帝都的平城(大同)佛教氛圍濃厚,但從大同北魏墓葬考古發(fā)掘看,并未見有火葬,直至與宋朝并行的遼金方見火葬。火葬的盛行,更是因于佛教在此時期發(fā)展的社會化與普世化。大同保留至今的許多遼金佛教文化遺存反映了佛教在當時民間社會的傳播與發(fā)展,如寺廟、經(jīng)幢、題刻、壁畫、佛典等,而墓葬中更是蘊含著豐富的佛教內(nèi)容。如仿效佛塔特征的器物,1957年機車廠遼墓出土的塔形棺、許 從 赟墓與龍新花園遼墓出土的長頸梟首壺塔式陶器及彩繪堆塑塔式陶器;東風里遼墓出土的至今唯一的石質(zhì)真容偶像,亦與佛教喪葬觀念相關(guān);劉承遂墓志中記述了其生前信奉佛教,在 擔任僧職維那期間 粧印《大藏經(jīng)》,并繪畫毗盧佛像、大悲壇、彌勒佛像、觀音菩薩像等以供瞻仰禮拜,更為當時的民眾佛教信仰提供了佐證;受密教擬人獸圖像影響的十二生肖像,在1974 紙箱廠遼墓墓頂壁畫與許從 赟墓棺蓋 盝頂刻圖中皆有出現(xiàn);作為佛教吉花的蓮花是較為多見的墓葬裝飾題材,如十里鋪遼墓M27 的磚砌棺床上朱繪蓮花毯,其骨灰罐上刻有蓮瓣紋,供奉所用長方磚與小方磚均繪有朱色蓮花圖案。大同遼金墓葬中所蘊含的佛教因素映射出佛教在民眾中的流行,體現(xiàn)著佛教信仰的社會普及化。
遼金佛教在大同民間的廣泛傳播以及對民眾信仰的陶染,與其佛教政策及良好的佛教發(fā)展氛圍密不可分。遼代統(tǒng)治者崇信保護佛教,推動了佛教對遼地社會的滲透與影響,自圣宗始逐步走向鼎盛。金代佛教政策相較遼朝謹慎,但隨著女真的漢化,佛教得以快速發(fā)展,至金世宗大定時期亦走向繁榮。從考古發(fā)掘來看,大同遼代自圣宗始出現(xiàn)火葬墓,金代火葬墓則主要為正隆、大定時期,“遼代火葬墓盛行于遼圣宗以后,金代的火葬墓盛行于海陵王和金世宗以后,都不是偶然的,正是同佛教由傳入到盛行的過程相一致的。”[3](P108)
三、密教信仰
密教諸佛與菩薩皆有所屬自己的陀羅尼密咒,認為密咒具有相應(yīng)的神力。陀羅尼咒是大同遼墓密教因素的代表,其載體為棺蓋、碑志,或以梵文刻寫,如十里鋪遼墓M9、M10、M15;亦有用漢文者,臥虎灣遼墓M3 便是漢文陀羅尼密咒的典型。
臥虎灣遼墓M3 葬具為長方形小石棺,棺蓋內(nèi)豎寫墨書:“唵,耶耶文質(zhì),孃孃焦氏,灰襯樞張。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一字法舍利塔記。唵(引)步嚕唵(三合)。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乾統(tǒng)柒年拾月捌日再建,孫僧懷謙、公孝、公義寫記。虧壬,唵齒臨。重孫箂哥、慶哥、僧德拱記。”[4](P432)此中,“唵”為凈法界咒,可消除罪障,令身業(yè)、口業(yè)、意業(yè)清潔純凈;“唵步嚕唵”為大輪一字咒,可驅(qū)散惡鬼神魔,驅(qū)除傷害及障惱,獲得無量壽福。“唵齒臨”為護身咒,即“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可驅(qū)災(zāi)避難、修善向善,消除五逆四重十惡之業(yè)障,現(xiàn)世來世獲得安穩(wěn)。另,墓室北壁石棺西側(cè)石碑正面刻寫:“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曰,曩謨,阿灑吒(二合)悉底喃,三摩也三母馱,故致喃,唵,艮嚙(二合)曩嚩婆悉,蹄哩提哩,吽。”[4](P433)智炬如來心破地獄咒,可使信眾免受地獄之苦而往生極樂,而如將此咒書寫在鐘鼓、鈴鐸等上面,聽聞鐘鼓、鈴鐸之聲者若有十惡、五逆之罪亦可盡行消除,免墮惡道。碑背面刻寫:“凈法界真言曰唵,次誦護身真言唵齒臨,次誦六字大明陀羅尼真言曰唵麼抳缽訥銘(二合)吽。”[4](P433)六字大明咒,又稱觀音菩薩心咒,漢文通常音譯為“唵嘛呢叭咪吽”,是最為人所熟知的流傳最廣的密咒,可驅(qū)災(zāi)避難、免劫益壽、清除煩惱,免受六道輪回之苦。
密教信眾通過持誦陀羅尼實現(xiàn)與諸佛、菩薩的感應(yīng),從而獲得無上的加持力量,以增加自身功德,實現(xiàn)自己的祈愿。對死者而言,陀羅尼可以消除其生前業(yè)障,度化其脫離三惡道之苦,寄托著對死者脫離生前業(yè)力苦海、往生佛國凈土的祝愿。
唐代,密教建立起完備的理論體系。為推動傳播,密教積極與皇權(quán)靠攏,獲得統(tǒng)治者的扶持與推崇。五臺山密教化的文殊信仰的推廣即為此作了有力的注腳。唐代是文殊信仰發(fā)展的重要轉(zhuǎn)折期。相傳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佛陀波利至五臺山遇到化現(xiàn)的文殊菩薩,受其點化前往印度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取回中國。而五臺山又系屬李唐龍興之地。由此五臺山成為唐王朝、文殊信仰、密教相聯(lián)的重要紐帶。密教正是借助文殊信仰以五臺山為道場的影響力及其信仰的密教化與普及化來弘揚自身的教義及修持方法。并且,其又吸納借鑒了其他佛教諸派、儒、道、民間信仰中適合自身發(fā)展的成分,逐漸實現(xiàn)了密教的中國化與社會化。遼代大同密教成為與華嚴相比肩的主流教派,并且在民間甚為盛行,與唐以來以五臺山為中心的密教發(fā)展的波及影響不無關(guān)系。
另者,大同密教的盛行亦源于其自北魏以來所積淀的佛教文化底蘊及逐漸形成的地域佛教差異。湯用彤先生認為由于文化環(huán)境的差異,南北佛教自魏晉南北朝漸趨分化,“北方佛教重行為,修行、坐禪、造像。北方因為重行為信仰,所以北方佛教的中心勢力在平民。……南方佛教則不如此,著重它的玄理,表現(xiàn)在清談上,中心勢力在士大夫中”。[5]大同自北魏以來,開鑿石窟、修建寺廟、建塔造像、立幢刻經(jīng)等無不體現(xiàn)著北方佛教崇尚實踐、注重行為的特點。而密教修法講求語密、身密、意密三者結(jié)合,無疑又與此特點相契合。可見,大同具有孕育密教生長的歷史文化土壤。
而遼代推重佛教的政策及濃厚的崇佛氛圍,使得密教空前發(fā)展。遼密的特色之一就是顯密兼修、顯密圓通,這也反映出其在當時佛教諸派中的重要影響力,而此主張的倡導(dǎo)者道辰殳便是遼道宗時云中(大同)人。遼密另一特色就是陀羅尼經(jīng)咒在民間的流行,除修持念誦,還書寫鐫刻,除墓葬陀羅尼外,大同目前所保留的不少遼代塔碑、經(jīng)幢、造像等上面都曾發(fā)現(xiàn)陀羅尼咒。
四、胡風濡染
遼太宗天顯十三年(938年)燕云十六州歸屬遼朝,為適應(yīng)境內(nèi)蕃漢統(tǒng)治的實際情況,遼實行一國兩制、南北因俗而治的統(tǒng)治之策。由此,燕云漢人原有的風俗得以延續(xù),然而隨著民族文化的交流,燕云地區(qū)日益受到契丹民風的陶染。
衣飾裝扮常常被看作彰顯民族習俗的重要內(nèi)容。在大同遼墓壁畫人物中,如2004年機車廠遼墓墓室東北壁的侍從望奴身穿圓領(lǐng)窄袖長袍,剃除頭頂與腦后頭發(fā),只于兩鬢留一綹頭發(fā)垂及耳前處;西環(huán)路遼墓M1 東壁的書童衣服為圓領(lǐng)窄袖,頭頂髡發(fā),前額保留頭發(fā),兩鬢留少量頭發(fā)垂及耳側(cè),顱后頭發(fā)梳成圓髻;東風里遼墓墓室北壁壁畫右側(cè)前起第一、二個侍從皆身穿圓領(lǐng)窄袖長袍,頭頂除保留一綹頭發(fā)梳成小辮,其余處髡發(fā),前額及兩鬢保留少量頭發(fā)。髡發(fā)、圓領(lǐng)窄袖長袍正是契丹男子的發(fā)式服飾特征。
金代初期,一方面沿用遼代的南北分治制度,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法制手段強化本民族習俗,進而同化燕云漢人。如金太宗天會年間曾禁止百姓穿漢服,下令歸屬漢人依女真發(fā)式削發(fā)、衣服左衽,如若違犯,則將獲刑乃至處死。至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金統(tǒng)治下的汴京漢人的生活習俗、觀念喜好已呈現(xiàn)胡化,更毋說至此已熏染胡俗230 多年的大同漢民。
同為女真民族典型發(fā)式的髡發(fā)亦出現(xiàn)在大同金墓壁畫中。如云大M1 北壁東側(cè)和M2 南壁西側(cè)兩侍童的發(fā)式,頭頂及兩耳上方保留三撮頭發(fā),以白布包裹、以線捆扎成三個根部較細的近橢圓形的“包”(為發(fā)髻式樣),頭部其余部分頭發(fā)則剃光。另者,云大M1 北壁西側(cè)和M2 北壁東側(cè)兩侍童發(fā)髻梳扎方式、形狀與之相同,只是前額保留少量短發(fā),耳后垂發(fā)及肩。有學者認為云大M1 北壁東側(cè)和M2 南壁西側(cè)兩侍童的發(fā)式應(yīng)屬宋金兒童三搭頭式發(fā)型。[6]但筆者認為其與三搭頭式是有區(qū)別的,反而與故宮博物院所藏“金代玉童子”的發(fā)式[7](P136)較為相似,玉童亦為髡發(fā),僅于頭頂與兩耳上部留發(fā)梳成三個小髻,即三丫髻發(fā)式。但是云大兩墓壁畫中侍童頭頂發(fā)髻的梳扎稍顯特別,其樣式與南宋范成大所描述的中原漢人胡化后的發(fā)式頗為相似,“男子髡頂,月輒三四髡,不然亦間養(yǎng)余發(fā),作椎髻于頂上,包以羅巾,名曰蹋鴟,可支數(shù)月或數(shù)年”。[8](P13)另者,壁畫中還出現(xiàn)了具有女真族服飾特征的左衽、頭飾,如徐龜墓墓室北壁壁畫東側(cè)侍女、東壁下部北側(cè)侍女、西壁箏臺后撫箏女及其身后從左至右第一、三、六侍女皆身著左衽交領(lǐng)襦;西壁壁畫中的侍女多戴頭巾,云大M1 東壁亦有發(fā)髻裹巾侍女,這是金代女子的典型頭飾,“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9](P298)
陶瓷是大同遼金墓葬中的重要隨葬品,除漢地陶瓷特征外,其又呈現(xiàn)出遼金民族文化的風格特色及其工藝特點。
最具遼金民族特征的瓷器類型雞腿瓶多有出土,如遼劉承遂墓中的2 件黑釉雞腿瓶;金閻德源墓中的2 件醬釉雞腿瓶,云大金墓M1 的3 件缸胎雞腿瓶,西環(huán)路金墓M6 的1 件茶葉末釉雞腿瓶。這種適用于馬上民族日常盛水裝酒的器皿,盛行于契丹民族,亦為女真族沿用。再如遼代瓷盤中的特殊器形方盤,本源于契丹民族歷史上使用的木制方盤,遼劉承遂墓與臥虎灣遼墓M2 曾各出土1 件砂陶長方形印紋盤。
具有遼代鮮明陶瓷工藝特點的“缸胎瓷”,胎質(zhì)粗糙厚重,器體施釉不徹底,金代亦有生產(chǎn)。如馬家堡遼墓M1 的2 件瓷碟,其中一件施釉厚重,碟身外壁下半部至足部露胎不上釉,另一件胎質(zhì)較粗,碟口沿處、口沿以下外壁大部及圈足皆不施釉;西環(huán)路遼墓M1 的2 件黃釉瓷碗,胎體皆施敷化妝土,碗外壁皆施半釉。遼三彩是遼代陶瓷的重要品類,其以黃、綠、白為主色,褐色或黃褐色亦為常用顏色。所謂“三彩”并非專指三種顏色,有單彩、雙彩、多彩者。馬家堡遼墓M1 出土的釉陶棺是為代表。其以高嶺土為原料低溫燒成,棺蓋頂部所刻海棠花及菊花紋飾、堆貼于棺身側(cè)面與后面的纏枝牡丹以及棺壁周邊的卷草紋等皆是遼瓷的代表性紋飾,其棺身外部釉色為黃、綠,色彩鮮明卻不失莊重古樸之感。金代山西是燒制孔雀藍釉瓷器的主要地區(qū)之一,閻德源墓的2 件長頸瓷瓶可謂獨具特色。瓶胎表面施敷白色化妝土,于其上繪以黑彩花紋,然后再施孔雀藍釉燒制。器身翠藍與墨黑輝映,明麗中又透露幾分幽靜雅致,紋飾隨意自然,頗具水墨寫意之韻,反映了早期孔雀藍釉黑花的燒制技藝。
綜上所述,遼金時期,北方民族的融合是雙向的,不僅包含著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漢化,作為遼金境域內(nèi)重要漢人聚居區(qū)的西京大同,又呈現(xiàn)出民族融合的另一面,即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化對漢地的熏染,而這一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大同漢人墓葬內(nèi)容中得以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