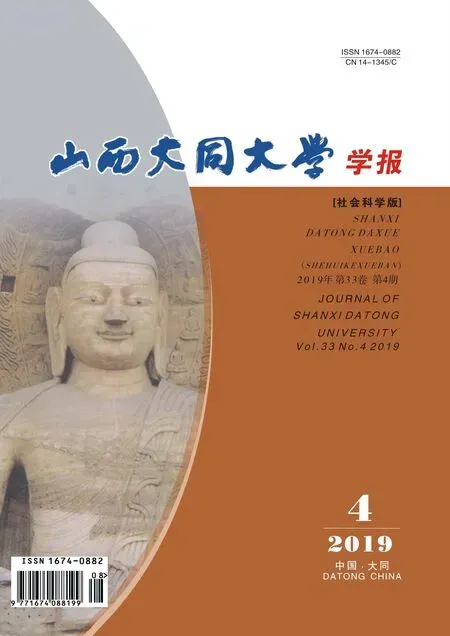宗教表象下的民族敘事
——論《深河》中人物的隱喻性
祁雁蓉,秦 琰
(山西大學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遠藤周作(Shusaku Endo,1923-1996)是日本戰后“第三代新人”作家,代表作有《海與毒藥》(1957)、《沉默》(1966)、《武士》(1980)、《深河》(1993)等。他生于東京巢鴨的一個天主教家庭,少年時代在家人的影響下開始信仰基督教,其作品“滲透著關于文化、社會、歷史、宗教的濃厚思考,以及對于現代人生存困境、信仰危機的深切關懷”[1](P31)。創作于1993年的《深河》是遠藤最后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包含有他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回顧和本人宗教思想的總結。小說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 至80年代的日本,以磯邊此人悼念亡妻開始,為了尋找亡妻可能轉世的地點,他與幾個原本互不相識的人組成了一個印度旅行團。旅行團中的每個人都懷有各自不同的訴求而遠赴印度,包括為了看犀鳥和鷯哥的故鄉的童話故事作家沼田,想要吊唁二戰戰友的木口,新婚的三條夫婦以及結婚不久就離婚、不知愛為何物的虛無主義者成瀨美津子。小說共十三個章節,印度之行前的每一章以一位人物為中心著重講述其過往經歷,章節名稱如“磯邊物語”、“美津子物語”、“沼田物語”等。旅行開始后旅游團的成員在每章中都出現,在導游江波的帶領下參觀印度的代表性景點。此外,美津子的大學同學大津是整部小說的核心人物,他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為了探索適合東方人的基督教,只身前往印度。美津子也正是為了追尋大津的蹤跡而踏上了印度之旅。與其他人物不同的是,關于大津的獨立章節“大津物語”出現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第十章),之前對于大津的敘述多來自于美津子的回憶,顯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作為日本基督教文學的先驅,遠藤通過小說文本來表達本人的宗教觀,這也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具體到《深河》而言,國內學者如路邈、史軍等指出遠藤在小說中探討了一神教與多神教融合的問題,間接表達了宗教信仰的核心在于宗教包容性,并希望以此來消解各宗教之間的沖突,其視野進而擴展至對整個東洋文明以及人類生命本質的探索。[2]本文承接以上研究者的觀點,通過大津的經歷探討宗教之間沖突與融合,進而透過美津子的“元視角”敘事進一步探討戰后日本的“文化定位”和民族道路發展。
一、大津:來自“東方”的基督徒
同遠藤周作一樣,大津也出生在日本的一個天主教家庭,自小就虔誠地信奉天主教,但他又受到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中泛神論思想的影響,不能完全理解和認同一神論的基督教。大學畢業后,大津遠赴歐洲留學,第一次接觸到了日本之外“正統”的基督教思想,卻發現自己與西方基督教在“一神”還是“多神”這一根本性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法國里昂修道院的神甫們告訴大津,神只存在于基督教世界里,可是帶有泛神論思想的大津卻越來越認為“神擁有各種臉”,認為“神不只是在歐洲的教會、小禮堂中,神也在猶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中”,[3](P152)“洋蔥(指神)是愛的作用的集合”。[3](P75)大津的泛神論思想被歐洲教會斥責為異端邪說,大津最終也被修道院判定為不適合成為一名神甫。但大津并未就此放棄追隨神的腳步,他只身前往印度,和成千上萬的“棄民”們一起經受苦難的過程,不斷思考適合日本人、適合東方人心靈的基督教。
需要關注的是,生長在日本的大津從未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即使面對強烈排斥基督教文化的美津子的誘惑和詰問也始終堅定,但如此虔誠的基督徒在赴西方學習時卻被認定不適合成為一名神職人員。面對來自東方的泛神論思想,法國里昂修道院的神甫和學生們態度高傲而輕蔑。大津多次與他們交流后卻陷入更深的困惑,西方的思考模式“對于東方人來說,太沉重了,我無法與他們打成一片”[3](P148),可大津的苦惱卻被認為是他“神經衰弱或自卑感的關系”[3](P148)。代表著正統和權威的歐洲基督教會極度排斥大津“非正統的”、“邪惡的”泛神論思想,而大津在其面前缺乏表述自我的能力,始終無法擁有與之平等對話的權利,最后只能黯然離開法國。大津與里昂修道院的沖突表面上看是泛神論和一神論之間的沖突,也即兩種不同宗教觀之間的沖突,這是大多數學者都認同的觀點。但筆者認為,掩蓋在宗教矛盾之下的是長久以來被置于二元對立位置的“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隔閡和排斥。
薩義德(Eaward Waefie Said,1935-2003)指出所謂的“東方”與“西方”并不只是地理上的劃定,更是人為建構起來的權利等級的劃分,東方作為“歐洲最強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歐洲文明和語言之源,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4](P2)而在以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為主導的文化霸權(hegemony)之下,東方代表著一系列“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從而由此凸顯歐洲“是理性的、貞潔的、成熟的、正常的”。[4](P49)薩義德指出,將東方視為“他者”的目的是鞏固和強化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并將除歐洲(主要是兩個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和法國)以外的東方(主要是亞洲和非洲)納入到這一意識形態之中。所以,東方主義并不是只停留在話語表層,隱藏其后的是西方殖民體系下的操控機制,這種操控在二戰后逐漸從顯性的政治、軍事控制不斷轉向文化、宗教等更加隱性的領域。而先將大津納入后又將其排斥的正是作為現代東方主義變體(或者稱之為替代品)的基督教,它并非為了彌合“信教人與野蠻人之間深不見底的鴻溝”,[4](P157)相反是為了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操控,所以“正統的”基督教勢必會固守其宗教思想,進而導致了東西方更加鮮明的二元對立。基于此,宗教的包容性也就無從談起。至此,便可以充分解釋里昂修道院為何對大津從規勸到排斥,在多次訓誡大津擯棄“邪惡思想”、皈依“正統”基督教無果后便將他逐出了教會等一系列行徑的原因和動機了。在某種程度上,大津的困惑、思考和理想追求也正是遠藤本人的心聲和訴求,而遠藤本人的宗教觀也主要是依托大津這一人物形象來表征的。
二、美津子:作為戰后日本的能指
《深河》中似乎不只是大津所代表的日本被歐洲“他者化”了,在日本與中國、印度等亞洲其他國家的接觸之中也充滿著東方主義色彩。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歐美立憲式”的現代化國家,在思想統治上明治政府給本國人灌輸一種“‘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觀念,在血統上是與天皇一脈相承的、均質的優等‘大和民族’意識”,[5](P323)日本學者網野善彥指出,“基于這種意識,他們無視阿伊努和琉球人的‘民族’特性,進而蔑視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人民”,[5](P323)這種意識長久以來在日本民眾的腦海中深深扎下了根。雖然二戰失敗使得日本經濟幾近崩潰,但日本人面對亞洲其他國家時思想上的優越感卻并未消除。用這一眼光觀照《深河》這部小說,可以發現其中有許多“東方主義”的直接書寫:沼田的幼年在中國大連度過,作者通過少年沼田的視角描繪了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那里住著帶有暴發戶心理、低俗而又蠻橫的日本人,他們輕視那里的中國人”。[3](P85)再如新婚的三條夫婦,作為新聞記者的三條先生一門心思想拍到些神秘古老的異域照片以滿足國人的獵奇心理,而原本想去歐洲旅行的三條夫人不斷抱怨印度的骯臟和混亂,認為印度各種神明的雕像是骯臟的雕刻,將印度的母親河恒河稱為“那么臟的東西”,[3](P256)絲毫不掩蓋對印度的輕蔑和鄙視。上述幾位主人公的經歷作為當時日本社會的幾個橫截面,從中可以發現,中國、印度所代表的古老亞洲之于日本顯然已不僅僅是異質文明間的隔閡與誤讀,而是潛藏在無意識中一種以他者為參照來凸顯和鞏固自己中心地位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天皇統治在將亞洲其他國家視為“他者”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實現和鞏固。這種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勢必導致自我(日本)與他者(亞洲)無法和諧共生,薩義德稱之為“一種幾乎是恒在的沖突感”。[4](P257)
所以,一方面作為戰敗國被美國操縱,一方面又是優等的“大和民族”,戰后的日本處在一個尷尬的歷史境地中。正如學者孫歌所言:“這樣一個復雜的結構,我們很難給它一個準確的說法,它似乎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很快擁有了自己的合法政權,但它同時又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6](P5)日本將自己置于東西方二元對立的夾縫之中,進而導致本民族的位置和發展道路無法得以確認。
遠藤在《深河》中展現了當時日本社會混亂無序的狀態:一方面主張抵觸西方文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另一方面主張西化、鄙棄東方文明。而作為小說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美津子,她既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但同時又非常排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她說“西洋的基督教借傳教之名奪取廣闊的土地,還殺了人”,[3](P48)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基督教的東方主義本質。因為信仰的失落,印度之行前的美津子是一個善惡并存的矛盾體,她無法確認自身價值和人生意義,總是在行善和作惡的兩端游移徘徊,時常感到“一股有如冷得透骨的空虛感襲來”,[3](P44)也在不斷思考“我究竟需要什么?”[3](P81)。美津子在不斷追隨和觀察大津的過程中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如果說大津的經歷代表著遠藤對宗教信仰之間沖突與融合深沉思索,那么文本中總有一個不斷追隨和觀察大津的“元視角”,這個“元視角”便是美津子。宗教信仰堅定而明確的大津對美津子有難言的吸引力,她總會不自覺地追尋大津的蹤跡以至于遠赴印度,在參觀查達姆女神像、恒河等景點的過程中,尤其是看到衣衫襤褸的大津堅持背著尸體來往于恒河邊時,內心不斷受到觸動,逐漸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可以說,美津子的迷茫是戰后大多數日本人的迷茫,或者說是戰后作為國家的日本的迷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在其著作《激蕩的百年史》中說:“今天,對于日本最重要的是:懷有理想,將自己置身于世界舞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7](P1)而美津子作為迷茫空虛、處于東西二元對立夾縫中的日本的能指,蘊含著遠藤周作在宗教敘事表象之下對民族文化定位問題的深沉思索。戰后的日本如何再次體認自我并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作為一個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國家責任感的作家,作為一個生長在東方的基督教信徒,這正是遠藤周作通過《深河》想要言說的深層問題。
三、“深河”即第三空間
除了大津和美津子之外,《深河》中還有其他多個人物。將這些人物歸納整合后可以發現,雖然他們均為日本人,但除三條夫婦外,其他主人公都有在國外生活或暫時居住的經歷。這些人物的共同特點是都有著跨越單一國界、單一種族的雙重或多重文化視野。而與旅行團中其他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條夫婦,一直想去歐洲旅行的三條夫人被三條先生帶到了印度,可三條先生并非向往印度文化,而是想要違反禁令、偷拍到印度教徒送葬的照片以獲得報紙頭條和獎金。三條夫婦的形象很具有典型性,他們代表著現代日本社會中部分精神空虛、信仰失落、自私淺薄、極端功利主義且一副西式做派的年輕人群體。旅游團的各個成員都是具有自主意識的獨立個體,承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性格的差異性也非常明顯。遠藤周作將自己隱匿在文本背后,讓“書中人物根據各自的階層、宗教、職業、性別等說著與自己身份相符的語言”,[8](P141)從小熱愛動植物的沼田被印度的自然風光所吸引,旅行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眾生平等,他“不知道該怎么說明自己希望和所有有生命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愿望”;[3](P94)美津子被印度的查達姆女神像所吸引,在雕塑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三條夫人一路上都在抱怨印度的混亂和骯臟,認為“這個國家(印度)真是太離譜了”,[3](P131)疾呼“我不想看那么臟的東西(指恒河)”;[3](P142)江波非常熱愛印度文化,雖然身為導游始終和顏悅色地為日本游客介紹景點,但他內心對豪無信仰的日本人嗤之以鼻……旅行團成員們以不同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小說之中形成“對話”,構成人間之河中的一幅百態眾生像,也是遠藤在創作方式上體現其“包容”的思想。
“包容性”不僅體現在小說的多聲部上,也是遠藤在探討宗教問題甚至是異質文明的碰撞時反復強調的核心。書名“深河”可以理解為包容著普羅眾生的“人間之河”,同時也指向被印度人譽為母親河與生命之河的恒河。恒河位于印度瓦拉納西城(Varanasi)——印度教教徒巡禮的圣城,它是印度的圣河,“在印度教徒的眼里,恒河是凈化女神恒迦的化身,而恒河里的水就是地球上最為圣潔的水,只要經過它的洗浴,人的靈魂就能重生,身染重病的人也可以重獲健康生命。每年都有眾多的朝圣者虔誠而來,在恒河水里舉行自己的重大宗教儀式”,[9]許多印度教徒在河中沐浴、洗漱、拋灑骨灰,甚至將尸體浸泡其中,相信恒河能洗滌罪孽、凈化靈魂。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曾提出“第三空間”(Third Space)這一概念,認為處于后殖民時代的國家、民族的文化,既不是定位在后殖民宗主國的文化的普遍性意義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異的所謂多元話語的問題上,而是定位在“處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10]在第三空間中一元中心論被打破,多元文化能夠相互交融、平等對話。雖然并不能完全將《深河》定義為一部后殖民小說,但“第三空間”的涵義與遠藤本人的思想在某種維度上相契合,《深河》中的印度恒河便可以看作是“第三空間”的象征,都以包容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為顯著特征。
和美津子一樣,旅行團的其他成員承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訴求踏上印度之行,最終都在包容一切、接納一切的恒河之濱(或者說印度教中)找到了各自一直追尋的問題的答案,內心重獲平靜。旅行團成員們(除三條夫婦外)之所以能在印度教中汲取精神力量,一方面得益于自己開闊的文化視野,他們在印度之行的過程中對于印度的文化和宗教的接受和認同程度頗高,更懂得在保持差異的基礎上尊重和理解異質文明;另一方面因為印度教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其本身是一個“清凈與污穢、神圣與猥褻,慈悲與殘酷混合共存的世界”。[3](P192)當美津子將全身浸在包含有垃圾、尸體和骨灰的渾濁的恒河水中時,她仍聲稱自己并無信仰,可此時她的內心顯然已經發生了某種深刻的轉變。她被一種“巨大永恒的東西”所感化并產生了向其祈禱的沖動,這種“東西”可以是基督教、印度教或是任何宗教。透過美津子,我們可以理解遠藤宗教思想的旨歸,比起外在的名字和刻板的形式,所謂信仰更重要的是發自內心的對“神”的追隨和信奉;換句話說,比起因隔閡與排他而導致的流血與沖突,異質文明之間更重要的是理解與包容。
階級、種族、宗教或許是當今我們談民族文化定位時無法回避的三個問題。遠藤在創作中也始終把對宗教問題的思考和對民族發展的思考緊密相連。《深河》是從宗教書寫到民族書寫的雙重復合結構。大津始終作為美津子的引導者,不斷身體力行引領著美津子踏上自我救贖之路。在遠藤看來,日本在確定民族位置之前,必須要解決宗教問題。如何解決日本的宗教問題?遠藤給出的答案是:多元的宗教派別和宗教觀念應該在保持差異性的基礎上共生共存于日本,甚至于全世界。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大津身上,大津可以說是遠藤周作精神的化身。小說的最后,大津像背負十字架一般背負著尸體來往于恒河邊,他衣衫襤褸、遍體鱗傷、貧窮而病弱,在世人嫌惡的眼光下卻依然淡然處之,堅持與“棄民”們共同分擔痛苦:
他無佳形美容,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
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以上是《圣經·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描繪耶穌的一段話,在《深河》中完整出現過三次,“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和“他無佳形美容”分別作為第十一、十三章的章節名,作者反復強調的用意在于暗示耶穌和大津之間的關聯性。經歷了困惑、失語并被驅逐的大津對自己的信仰有了更加明晰的認識,此時的他儼然已是遠藤周作理想中耶穌的化身。再反觀小說前半部分,如此虔誠信仰耶穌的大津卻被里昂修道院判定為不適合成為一名神甫,致使大津“背叛”了基督教而對印度教產生認同。但正如日本學者三浦朱門指出的那樣:“這種‘背叛’卻恰恰表明了主人公對神的強烈信仰”[11](P198)。而這一反諷意味頗濃的情節也曲折表達了遠藤對于歐洲基督教所包含的東方主義色彩的抵制和批判,同時也再次重申了他本人倡導的宗教思想。遠藤借大津之口說:“各種各樣的宗教,它們從不同的道路聚集到同一地點,只要能達到同樣的目的地,即使我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也無妨。”[3](P245)更進一步來說,對于戰后身處東西方夾縫中的日本社會,遠藤希望能打破異質文明之間的對立與偏見,像美津子、磯邊、沼田、木口等人在包容一切的恒河之濱得到靈魂的洗滌一樣,多元的文化應該以平等對話的方式進行雜糅與融合,共生共存于處于流動狀態的人間之河。
雖然遠藤用積極的態度看待和描述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但他仍在小說中流露出隱憂。20世紀后期是民族、宗教問題備受矚目的時期,書中一筆帶過的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英迪拉·甘地遇刺、黎巴嫩戰爭、恐怖分子襲擊等事件使讀者窺探到當時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之一角。遠藤在小說結尾借美津子之口不無悲觀地說到:“在這樣的世界里,大津所信仰的洋蔥的愛既無力又卑微。”[3](P268)晚年的遠藤或許意識到,人類社會離真正拋卻對立與偏見,到達愛與和平的理想國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結語
《深河》所講的故事并非宏大敘事,但卻有著復雜而深刻的主題。小說中多個人物形象有著豐富的隱喻性,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具有復合結構的政治寓言,即遠藤周作透過對宗教問題的思考進而探討戰后日本的“文化定位”和民族道路發展問題。他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同時也貶斥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希望能在平等對話中打破一元中心論,構建出處于流動狀態的不確定世界,也即“第三空間”。這一文化策略可見于許多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印度裔英國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在長篇小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中同樣探討獨立后的印度其國家建設和民族道路發展的問題。與遠藤不同的是,拉什迪作為一個加入英國國籍多年的離散作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為了迎合西方主流話語而對母國進行想象性的回溯,筆觸間多少帶有優越感和審視意味,所以有些研究者將拉什迪及其作品稱之為“新東方主義”。[12]相較于《午夜之子》,《深河》更多了一份悲憫與人文關懷,就像日本作家安岡章太郎評價的那樣:“遠藤周作不是憑借文字取勝,他的作品整體擁有讓人感動的力量。”[3](P1)這或許與遠藤本人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