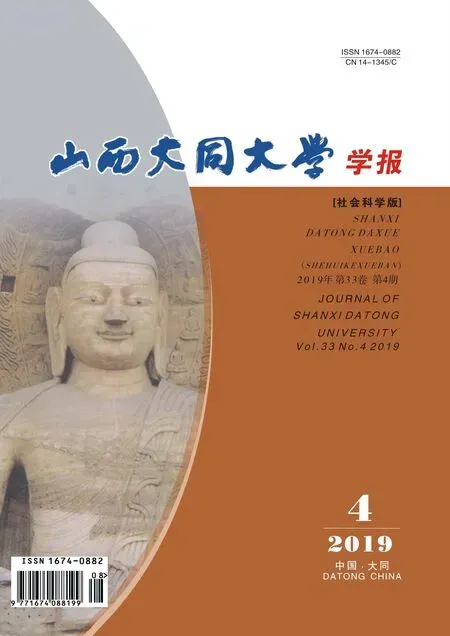許淵沖創造性翻譯中意義的建構
楊艷蓉 ,劉鴻慶
(1.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2.許淵沖翻譯與比較文化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許淵沖先生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享譽國內外,在英語讀者當中有非常高的接受度。以前的研究者們主要通過其他譯文的橫向對比,分析其韻體詩譯文中傳達的美,存在的局限性。[1]通過縱向對比,探究許先生詩詞改譯過程中的心路歷程,[2]探討許淵沖如何不斷修改譯文,追求“三美”。[3]王振平認為許淵沖的翻譯并沒有超過一定的限度,屬于創造性翻譯而非叛逆。[4]筆者以許先生同一詩歌不同時期的譯文為研究對象,以認知語言學識解觀的四個要素為框架,旨在研究許先生在詩歌改譯中,重新建構的意義與傳達原作者表達意圖之間的關系,探析譯者的認知變化過程,從而為中國古詩文創造性翻譯帶來啟示。
一、認知語言學識解觀與譯者的創造性
認知語言學基于體驗哲學,[5]認為人類對世界的共同體驗感知是人類進行交流的前提。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知語言學強調意義的動態性、開放性,語言使用者的參與性及其選擇性;否認語言系統是封閉的,意義是固定不變的。因此,認知語言學家Langacker 提出意義就是“概念化”。[6](P194)語言的形成有賴于認知主體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加工。Langacker 把認知的過程定義為“識解”,即“人們具有用不同方式來理解同一場景的能力”。[6](P138)Langacker 的學生D.Lee 從視角、前景化、隱喻、框架與概念合成等維度來解釋識解以及意義的形成。[7]由于認知個體的知識經驗具有獨立性,因此,經過不同個體的認知加工,“概念化”的結果不同,意義也就不同,對“現實”的語言表達也不盡相同。[8](P70)因此意義不能直接等同于現實。我國教授王寅認為Langacker 的“概念化”過分強調語義的主觀性,識解性,忽視了體驗性和互動性,因而把概念化修補為“體驗性概念化”。[9](P211)這樣的修補告訴我們,意義的識解需要主觀參與,但主觀性的發揮受到“體驗性”的制約。
認知語言學識解觀對意義的闡釋決定了翻譯無法直接傳遞意義,而是要建構意義。因此,譯者建構出來的意義是經過其識解后的概念化意義。王寅提出過翻譯的“兩個世界”。“我們所談論的一切無非是關于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它們是語篇生成的基礎”。[10](P18)既然任何文字都是在描寫現實世界以及認知主體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即認知世界,那么譯者就要深刻體驗原文作者描述的這兩個世界及其表達意圖,盡其所能讓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有著最大相似度的體驗。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譯者要把識解后的意義重新概念化,建構意義。由于兩種語言認知語境的差異,在概念化的過程中,譯者必然要發揮創造性。許淵沖教授提出“譯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繪畫,所以譯作不能只臨摹原作,還要臨摹原作所臨摹的模特”。[11](P411)許先生用生動形象的比喻告訴我們,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并非亦步亦趨地遵循原作的字面意義,而是要發揮創造性,重新建構意義,讓譯文讀者通過對原文作者描述內容最大相似度的體驗,來識解出原作者的表達意圖。
二、改譯文中意義的建構
譯者思想和經歷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因此對原作者情景描述的體驗不同,概念化方式有所不同,同一譯者不同時期的譯作就有差異。譯者通過改譯,更好地表達原作者的意圖,使得譯文讀者和原文讀者的體驗具有同一性。許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和原文競賽,也同時和自己競賽,對同一詩歌的譯文多次修改,精益求精。本文以許先生1988年和2012年的譯本作對比,分別從視角、前景化、隱喻、框架四個方面分析許先生如何創造性地重新建構意義,使譯文更符合原詩表達意圖。
(一)轉換識解視角 面對同一客觀情景,認知主體選擇不同的角度觀察,其結果就有差異。視角的選擇與認知主體的生活經驗、視覺經驗息息相關。認知主體在觀察事物時,總會受到個人經驗的影響。[12]譯者作為認知主體,結合個人與譯文讀者的生活體驗,選擇適當的識解視角解讀原文作者所描述的現實世界及認知世界。翻譯時選擇的視角不同,則會建構出不同的意義。在下面的例子中,許先生大膽地轉換了識解視角,改譯后譯文與原詩作者的意圖更加貼近。
李商隱《無題·颯颯東風細雨來》是一首“相思”主題的情詩。“隱晦”是李詩的特點,這就需要譯者對原作者所描述的現實世界、認知世界進行深入的體驗。兩個時期譯本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譯者采用了不同的識解視角來建構意義。中國古詩多為無主句,翻譯成英語時要把主語明示化。譯者根據其對原文的識解結果及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選擇主語進行描述。原詩頷聯“金蟾嚙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的“香”“絲”與“相”“思”諧音,暗示出了詩歌描寫愛情的主題。頷聯的原譯文為,“Incense can drift through golden toad on lock and chain.The tiger winch of jade can draw up water under.”[13](P346)許先生把意義建構為香氣從金蟾狀的香爐中散發出來,轆轤把水從井里打了出來。識解視角鎖定為“香氣”,“轆轤”。原譯文反映出詩人描述的現實世界,但由于譯文讀者缺乏相關的背景知識,“香氣”和“轆轤”無法激起他們有關愛情的聯想,傳達原詩的意圖也就無從談起。在中國古代,熏爐多用于晚上,而轆轤則在早晨用于打水。改譯文中,譯者把“夜晚”“早上”這些暗含在原文中的信息明示出來。When doors were locked and incense burned,I came at night.And went at dawn when windlass pulled up water cool.[14](P181)回譯過去就是,晚上燒香,用金蟬鎖門的時候我來了;拂曉,人們用轆轤打水的時候,我離開了。這樣的譯文既包含了“香氣”“轆轤”這樣的意象,同時,為了能夠讓譯文讀者體驗原詩人關于愛情的主題,許先生大膽發揮創造性,把“我”作為主語,以“我”為敘述視角,把現實世界描述為“我”與戀人的約會。詩文改譯后,字面意義與原文不對等,但是譯文讀者對原作表達意圖的體驗更為接近,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忠實。
(二)改變前景化內容 前景化內容是認知主體想要突顯的。通常來說,句子的主語,文章中反復出現的內容,都是認知主體想要突出的重點,因此在敘述過程中被前景化。譯者通過調整前景化的內容,則會建構不同的意義,形成不同的表達效果。
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一首寫給妻子的抒情詩,表達了對妻子的相思之苦以及期待與妻子重聚的殷殷之情。“巴山夜雨”在原詩中出現了兩次,不同的時間,同樣的地點卻反復出現在作者的心中,不但讀起來朗朗上口,更構成了意境之美。巴山夜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妻子詢問何時能回家,詩人無法給予準確的答案,心中郁悶。他盼望重聚之時,和妻子一起回味這“巴山夜雨”。詩人想象未來重聚時的歡樂和當下思念妻子的煩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巴山夜雨”的反復出現也成為了這首詩的特色。顯然,“巴山夜雨”在原詩行文中形成了前景化。
對比兩個時期不同的譯文,第二句與第四句譯文的意義建構有較大差異。“巴山”是指“巴蜀之地”,巴蜀位于中國西部,因此,作者把它譯為“western hills”,即“西面的山”。在原譯文的第二句當中,譯者僅僅描述了池塘里漲滿了雨水,略去了“下雨”這一動態的情景,即“The pools in western hills with autumn rain o'erflow”,[13](P344)而第四句譯文又僅談“雨”而不提“山”,“And talk about this endless,dreary night of rain?”。[13](P344)在改譯文當中,譯者為了能再現原詩中回環往復的意境之美,在第二句譯文中詳述了“夜雨”,“It rains in western hills and autumn pool o'erflow”,[14](P176)同時第四句增譯了“ 巴 山 ”,And talk about the western hills in rainy night?[14](P176)兩句形成呼應。改譯之后,譯文讀者更能體驗到原詩作者那種由于歸家遙遙無期而產生的低落情緒。同時,第四句略去了原譯文中修飾雨夜的形容詞。“endless,dreary”這兩個詞表面上是修飾雨夜綿綿無期,枯燥沉悶,實則是譯者想用這兩個詞表達原作者的情感,也就是認知世界。譯者在改譯文中,通過對第二句、第四句相關信息的詳略描述的調整,使“巴山夜雨”這一情景和原詩一樣在譯語行文中形成前景化,讓譯文讀者和原文讀者對原詩作者所建構出的現實世界,認知世界有了更為相似的體驗,從而更好地領悟原作者的表達意圖。
(三)重新建構隱喻 在認知語言學的范疇里,隱喻不是一種修辭,而是人類的一種認知方式,人們往往借助其它事物來理解和體驗某一事物。[15]隱喻通過不同概念域間的映射,能更生動地表達抽象的事物,因此隱喻是一種廣泛存在的語言現象。
杜牧的《贈別兩首·多情卻似總無情》描寫了詩人與一位歌女分開時的離愁別緒。兩人之間的感情如此之深,離別宴席上,不知說些什么安撫對方,倒像是彼此無情。舉起酒杯道別,想要強顏歡笑,卻“笑不成”。這首詩在前后兩個不同時期的譯本差別較大。此處我們主要關注最后兩句的譯文。“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這兩句詩,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詩人使用了隱喻的識解方式。第三句,“燭芯”是源域,映射到目標域“人心”這個較為抽象的概念,形成隱喻。第四句,蠟燭整夜燃燒流下的“蠟液”是源域,映射到目標域男女主人公的眼淚,再次形成隱喻。原詩文中的“心”與燭芯中的“芯”同音不同形,“心”在第三句詩文中一語雙關。蠟燭既有“芯”,也有“心”,看著我們分手淚流不止。但“心”與“芯”在英語當中的對應詞分別是“heart”,“wick”,它們既不同音也不同形。原譯文The candle has a wick just as we have a heart.All night long it sheds tears1 for us before we part.Note 1:The melted wax of a guttering candle is compared to tears.[13](P318)雖然也傳達了原作者所描述的現實世界,但所建構的意義似乎沒有原文那么美,也無法傳達出原作者的認知世界。許先生一直提倡發揮譯入語的語言優勢,那么回避劣勢也是譯者應該注意的。因此,改譯文中,譯者依舊使用了隱喻的識解方式,卻通過改變源域及目標域的內容,建構了新的隱喻表達。The candle grieves to see us part: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out heart.[14](P168)“蠟燭”是源域,映射到充滿感情的“人”這個目標域。譯者借助“蠟燭目睹我們分別,痛苦不已,消融在眼淚里”的情景讓譯文讀者感受到原詩人的認知世界。同時,譯者略去了“蠟燭有心”對應的字面意義,回避了英語中“heart”無法一語雙關的劣勢。第四句詩文中,譯者創造性地使用“burnt-out”來修飾“heart”。“burnt-out”既指人心力交瘁,也指蠟燭被燒成灰燼,一語雙關。改譯文既傳達出了原作者的表達意圖,還充分利用了譯入語的語言優勢,令人叫絕!
(四)添加框架語義信息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框架是指與敘述概念相關的概念及背景知識。[16]語言當中概念的存在都是相互關聯的。要理解一個概念,必須要搞清與其相關的其他概念及背景知識,必須清楚這個概念與其他概念相對穩定的關聯。
杜牧的《秋夕》以秋夜幽冷之景,描述了一個宮女感受到的凄涼之情。其中“坐看牽牛織女星”一句涉及中國古代神話知識。漢語中,“牽牛織女星”包含著“愛情”“分離”“團聚”這樣的內涵。讀者們會想到牛郎與織女的愛情故事,從而領會原作者的表達意圖。詩中描述的宮女遙望著銀河兩旁的牽牛星、織女星,自己滿心惆悵,對真摯的愛情充滿向往。由于譯文讀者并不具備相關的背景知識,也就無法產生類似于原文讀者的聯想。因此譯者要想使得譯文讀者和原文讀者的體驗更為相似,不能只追求字面意義的對等的。對比前后兩版譯文,許先生在改譯文中對第四句的改動比較大。原譯文中“She lies watching heart-broken stars shed tears in the skies.”[13](P322)譯者建構出“悲傷的群星在空中落淚”的意義來傳達宮女的痛苦。而改譯文She sits to watch two stars in love meet in the skies[14](P170),添加了“相愛的兩顆星星在空中團聚”的信息,與原語中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吻合。改譯文所建構的意義體現出宮女既惆悵又期待的復雜心情,更能體現出原作者的表達意圖。
三、結語
筆者從認知語言學意義建構的角度,對許淵沖兩個不同時期的譯本做了對比分析,認為許先生的認知變化促使其創造性地轉換了識解視角,改變了突顯對象,調整了源域與目標域的內容重新建構隱喻,根據詞語框架所包含的概念增補信息,從而使得改譯文更符合譯語讀者的期待,更能傳達出原作者的表達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