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與福爾摩斯形象比較論
王 凡
(山東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014)
由荷蘭著名漢學(xué)家高羅佩創(chuàng)作的推理斷案小說集《大唐狄公案》生動(dòng)表現(xiàn)了唐代名臣狄仁杰為官斷獄、誅奸除惡的傳奇經(jīng)歷,其筆下的狄仁杰縝密推理、屢破奇案,成為了這一歷史人物“神探化”形象演變的肇始。而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塑造的福爾摩斯早已成為偵探推理小說史上不朽的藝術(shù)形象。作為東西方世界家喻戶曉的“神探”形象,狄仁杰和福爾摩斯既有諸多的共通之處,又存在明顯的差異。
一、狄仁杰與福爾摩斯的共性特征
高羅佩曾就狄仁杰的形象指出:“正因?yàn)樗碛袛喟溉缟竦穆曌u(yù),他被中國(guó)人視為清官神探,對(duì)中國(guó)人來說,他的名字就如同福爾摩斯對(duì)我們一樣。”[1](P293)可以說,高羅佩在塑造狄仁杰這位“神探”時(shí),也不由自主地將其與福爾摩斯相聯(lián)系,二者確實(shí)表現(xiàn)出諸多相似之處:
(一)超乎常人的非凡智慧 作為偵探小說中的核心人物,偵探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具有超凡的智慧。正如劉半農(nóng)先生所言:“從事偵探者,既不能如法學(xué)家之死認(rèn)刻板文書,更不能如算學(xué)家之專據(jù)公式,則唯有以腦力為先鋒,以經(jīng)驗(yàn)為后盾,神而明之,貫而徹之,始能奏厥膚功。”[2](P566)《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和《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福爾摩斯在這方面可謂是高度的相似:狄仁杰先后破解了公主玉珠失竊之謎(《玉珠串》)、尸身調(diào)換之謎(《紫光寺》)、密室殺人之謎(《紅閣子》、《迷宮案》)、地下幫會(huì)之謎(《湖濱案》)、欽差遇害之謎(《廣州案》)等一系列錯(cuò)綜復(fù)雜的疑案;福爾摩斯則不僅破獲了覬覦遺產(chǎn)的繼父圖謀利用偽裝的毒蛇來戕害無辜少女的“斑點(diǎn)帶子案”,亦成功破解了“四簽名”背后因財(cái)富而引發(fā)的恩怨情仇,更揭開了屢生血案、令人膽寒的巴斯克維爾獵犬真實(shí)的面目以及隱于其后的卑劣陰謀和陰暗人性,其他的疑團(tuán)懸案更是不計(jì)其數(shù)。可以說,面對(duì)這些波云詭譎的疑案迷蹤,狄仁杰與福爾摩斯依據(jù)犯罪現(xiàn)場(chǎng)的蛛絲馬跡抽絲剝繭,順藤摸瓜,最終撥云見霧,始得真相,而這種神乎其技的偵破推理能力表明二人都有其過人之處。
首先,二人均有著豐富的文化知識(shí)積淀。英國(guó)偵探小說家、評(píng)論家朱利安·西蒙斯在談及偵探小說時(shí)曾說:“偵探是社會(huì)的代理人,是唯一可以擁有高超智慧的人。按照一般的標(biāo)準(zhǔn)(即讀者的標(biāo)準(zhǔn)),他可以古怪、奇特,表面上有些糊涂,但他要有廣博的知識(shí)、無所不能。”[3](P11)《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不僅對(duì)儒釋道文化了然于心,于詩畫琴棋等方面也多有涉獵,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助力他在疑云密布的案件偵破中探尋真相。譬如在《迷宮案》中,狄仁杰能察覺倪壽乾畫作“虛空樓閣”中所藏的玄機(jī);在《朝云觀》中,他又能通過玉鏡真人畫作中貓之瞳孔的微妙變化察覺出玉鏡的真實(shí)死因,這皆緣他在書畫方面的審美積淀。在《四漆屏》中,狄仁杰通過對(duì)行院客房中題壁詩的解讀覺察出銀蓮的婚外情,這正是因其在詩歌鑒賞方面的修養(yǎng)才為勘破銀蓮被害案打開了突破口。不同于狄仁杰,福爾摩斯則是精通化學(xué)、解剖學(xué)、生物學(xué)等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正是這些知識(shí)成為他破案的重要基礎(chǔ)。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這個(gè)人頭腦中裝了一大堆生僻的知識(shí),雖然毫無科學(xué)系統(tǒng)性,但這些知識(shí)對(duì)我的業(yè)務(wù)是有用的。”[4](P510)在《馬斯格雷夫禮典》中,他依據(jù)馬斯格雷夫家族的文件記述、運(yùn)用數(shù)學(xué)知識(shí)測(cè)算出禮典儀式所指之物的具體位置;在《四簽名》中,他在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做出的許多結(jié)論亦是拜其對(duì)病理學(xué)、毒物學(xué)深入了解之所賜;《獅鬃毛》、《駝背人》則凸顯出他在動(dòng)物學(xué)方面的見識(shí),而化學(xué)知識(shí)更是被其廣泛地運(yùn)用于許多案件的偵破中。總體來看,狄仁杰精熟和運(yùn)用的多為傳統(tǒng)詩文藝術(shù)方面的知識(shí),投射出其儒家文化背景和士大夫階層的情志意趣;而福爾摩斯則偏重于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折射出其現(xiàn)代科學(xué)理念和理性精神。
其次,二人皆具有目光如炬的觀察力。細(xì)致入微、洞悉一切的觀察力是偵探小說中案件偵破者所必備的能力。程小青先生曾說:“偵探小說的情節(jié)總不外寫一個(gè)偵探,在一件疑案上努力,至于他努力的方式,就著重于觀察、集證和推理這幾點(diǎn)。”[5](P74)倘若沒有針對(duì)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以及相關(guān)嫌疑人的細(xì)致審視和觀察,那么一切看似合理的推斷、假設(shè)都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就有著細(xì)致的觀察力。在《跛腿乞丐》中,他正是通過死者王文軒頭顱傷口處的白瓷屑末以及梁文文房中枯萎的蘭花確定了梁文文的兇犯身份;《紫光寺》中,狄仁杰通過細(xì)查死者尸身識(shí)破了真兇移花接木式的尸身調(diào)換之計(jì);在《迷宮案》、《朝云觀》中,狄仁杰運(yùn)用繪畫知識(shí)識(shí)奸辨惡,這固然與其在這方面的審美積淀密不可分,也得益于他對(duì)畫作的詳觀細(xì)覷。福爾摩斯同樣是洞燭幽微。他曾對(duì)華生說:“一個(gè)善于推理的人所得出的結(jié)論,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覺得驚奇,這是因?yàn)槟切┤撕雎粤俗鳛橥普摶A(chǔ)的一些細(xì)微之處。”[6](P121)他曾舉例說:“除了表和鞋帶以外,沒有什么別的東西比煙斗更能顯示一個(gè)人的個(gè)性了。”[6](P30)在《黃臉人》中,福爾摩斯就從一個(gè)煙斗推斷出其主人身體強(qiáng)健、經(jīng)濟(jì)寬裕。在《賴蓋特之謎》中,他憑借死者手中殘缺的字條便可知曉兩個(gè)兇手合寫了該字條,并進(jìn)一步推導(dǎo)出二人的年齒、性格,亦是其觀察力細(xì)致的體現(xiàn)。可以說,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被害者與嫌疑人身上乃至其他各方面的細(xì)節(jié)都可能成為偵破案件的關(guān)鍵突破口,但這些細(xì)微之處并非人所能共見,這無疑需要細(xì)致的觀察力作為基礎(chǔ),而身處迷蹤的狄仁杰和福爾摩斯也正是憑借這一不俗的觀察力來清除霧障、直搗真相的。
(二)秉持正義、懲奸助善的道德取向 作為通俗文學(xué)中的一種主要小說類型,偵探小說注重通過罪案?jìng)善频那昂笫寄┡c驚險(xiǎn)過程來構(gòu)建情節(jié),以邪不勝正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來完結(jié)故事,并時(shí)常反映出賞善罰惡的道德訓(xùn)誡觀念。而這一道德理念常常被寄寓在作為主人公的偵探身上。《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在偵辦案件時(shí),時(shí)刻謹(jǐn)記對(duì)國(guó)家法度和社會(huì)公理的維護(hù),撫民安邦、除惡扶善。《銅鐘案》中為了使受到皇室庇護(hù)而將免于刑律制裁的普慈寺淫僧靈德伏誅,還眾多受害婦女以公道,狄仁杰巧借民憤將其懲裁。《朝云觀》中,面對(duì)孫一鳴這個(gè)曾為“國(guó)師”、備受皇家寵信的戕害少女案的元兇,狄仁杰并沒有畏其權(quán)勢(shì)而敷衍塞責(zé),即便在無法通過正常司法途徑來將其繩之以法之際,仍巧妙以個(gè)人之力將其鋤滅。《柳園圖》中,狄仁杰雖已偵知藍(lán)白實(shí)為斃殺惡侯葉奎林之人,但卻并未將這位“存大義,全孝道,為母報(bào)仇,為民翦害”[1](P166)的俠女交付有司。“善必勝惡或正義必勝”同樣是福爾摩斯的道德取向,“這不僅體現(xiàn)在正義復(fù)仇者得免于法律的裁決,而且體現(xiàn)在惡人即使逃脫了法律的懲處,也必將意外暴死、遭到天譴。”[7](P54)當(dāng)出現(xiàn)這種案件受害者實(shí)為道德、法律上的悖離者,作案人確為真正受害者的情況時(shí),福爾摩斯便會(huì)義無反顧地站在道德與正義的一方。在《駝背人》中,福爾摩斯鄭重地說道:“伸張正義,人人義不容辭。”[6](P133)在《狡猾的詐騙犯》中,福爾摩斯并未阻止被勒索的受害女子擊斃卑損的勒索者,在他看來這是正義良善擊敗了邪惡貪婪。在《格蘭奇莊園》中,福爾摩斯出于維護(hù)正義和憐憫女性的目的而私縱布萊肯斯特爾爵士被殺案的兇手,在《顯貴的主顧》中,福爾摩斯為獲取罪證,又不惜冒險(xiǎn)潛入格魯納男爵的私宅暗中搜尋。對(duì)此,劉半農(nóng)先生曾評(píng)析道:
或問:福爾摩斯何以成其為福爾摩斯。余曰:以其有道德故,以其不愛名不愛錢故。如其無道德,培克街必為挾嫌誣陷之罪藪,如其愛名愛錢,則爭(zhēng)功爭(zhēng)利之念,時(shí)時(shí)回旋于方寸之中,尚何暇舒其腦筋以為社會(huì)盡力,又何能受社會(huì)之信任?故以福爾摩斯之人格,使為偵探,名探也;使為吏,良吏也;使為士,端士也。不具此人格,萬事均不能為也。[2](P568)
可以說,當(dāng)“法律不能主持正義的時(shí)候,福爾摩斯便自己來主持,他是最高上訴法院,有這樣一家法院存在,盡管只是一種個(gè)體的象征,但對(duì)讀者來說卻是永久的安慰。”[3](P62-63)概而言之,破案緝兇是狄仁杰、福爾摩斯作為案件偵辦者份內(nèi)的職責(zé),也是他們的人生志趣之所在。這些“神探”在面對(duì)社會(huì)陰暗和人性丑惡之際常會(huì)以善良與公義作為自己的行為準(zhǔn)繩,從而作出富于正義感與人性化的正確“裁決”,因此他們并不完全受制于國(guó)家法律,他們能在法律本應(yīng)作出公正裁定,但卻因時(shí)代、社會(huì)乃至案件本身的種種因素而未能施以伸張正義、懲治罪惡之效應(yīng)的時(shí)候,適時(shí)地以自身超越法律規(guī)制的特殊行動(dòng)來實(shí)現(xiàn)上述目的,體現(xiàn)了堅(jiān)持正義、懲奸助善的道德取向。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作者本人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表露出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及傳統(tǒng)價(jià)值觀。
胡明先生曾就高羅佩筆下的狄仁杰評(píng)論道:“狄公往往更像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克里斯蒂的波洛、加德納的海森、西默儂的格雷警長(zhǎng),而不同于包拯、況鐘、海瑞、施仕綸一類的人物。”[8](P36)可以說,《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與《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福爾摩斯表現(xiàn)出的共性化特征代表了偵探小說史上經(jīng)典“神探”形象所具有的基本人物特征。
二、狄仁杰與福爾摩斯不同的人性化呈現(xiàn)
偵探小說產(chǎn)生以來,大家閃耀,佳作頻出,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體。另一方面,偵探小說作者大多用力于奇巧情節(jié)的匠心營(yíng)造,而對(duì)書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描刻或是有心無力,或是相對(duì)輕視。詹姆斯·傅瑞在論及偵探小說人物相對(duì)膚淺這一現(xiàn)象時(shí)曾說:
推理小說讀者對(duì)恐怖事件其實(shí)又愛又怕,就像愛在車禍現(xiàn)場(chǎng)逗留的圍觀民眾一樣,雖然深受事件吸引,但若真的見血,又會(huì)覺得反胃。想與恐怖事件保持距離的這種感受,可能是推理小說讀者比一般小說讀者容易接受膚淺角色的原因。那些單薄、夸張,甚至不真實(shí)的角色特質(zhì),讓讀者可以保持一段安全距離,在閱讀時(shí)降低恐懼感。[9](P95)
可以說,傅瑞從自身的閱讀感受出發(fā),較為合理地分析了讀者對(duì)于偵探小說中的陰謀恐怖場(chǎng)景所持的微妙心理:既想在安定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獲取一種危機(jī)化的非常體驗(yàn),又對(duì)這一過程中的過度精神刺激與驚嚇深感猶疑,這一獨(dú)特體驗(yàn)實(shí)際上與乘坐過山車或觀看恐怖電影的心理體驗(yàn)異曲同工。因此,對(duì)于這類可提供精神消遣的通俗小說所展現(xiàn)的人物、事件的膚淺甚或虛假,讀者大多并不深究,相反,還可因勢(shì)利導(dǎo)地規(guī)避真實(shí)描寫所帶來實(shí)感化的精神刺激。然而,對(duì)于上述可能因讀者獨(dú)特心理體驗(yàn)而造成的人物塑造的程式化趨勢(shì),有的偵探小說家或評(píng)論家并不認(rèn)同。美國(guó)偵探小說家瑪利婭·塔利在談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時(shí)曾說:“一個(gè)有趣的偵探一定要有優(yōu)點(diǎn),但同時(shí)也要有缺陷和弱點(diǎn)。……要從模式化的人物形象中脫穎而出,你的人物必須人性化,而人是有缺點(diǎn)的。”[10](P117)傅瑞更是直言:“偵探英雄要是個(gè)吸睛的生動(dòng)角色,必須擁有完整、立體的性格。”[9](P85)而一些偵探小說的藝術(shù)巨匠更是自覺地追求筆下偵探主人公的真實(shí)鮮活和人性豐滿。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面對(duì)疑案時(shí),從容應(yīng)對(duì),推斷案情,擒獲元兇,智勇兼?zhèn)洹o所不能的神探形象已成為偵探小說發(fā)展史上的經(jīng)典藝術(shù)形象。然而,柯南·道爾也未將福爾摩斯刻畫成為純粹意義上的完美英雄形象,而是表現(xiàn)了他的一些缺點(diǎn),如在《馬斯格雷夫禮典》中提及了他生活無序,在《黑彼得》中又表現(xiàn)他為人倨傲之態(tài)。此外,他還間或表現(xiàn)出自命不凡、譏諷他人的行為,這就令這一人物顯現(xiàn)出豐滿鮮活之色。柯南·道爾將福爾摩斯外在缺點(diǎn)與其“神探”化的基本特征相并置,有助于強(qiáng)化其形象的多面性,卻幾乎未對(duì)福爾摩斯進(jìn)行深層心理和精神世界的開掘以及復(fù)雜人性情感的細(xì)膩描摹。有學(xué)者指出:“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克里斯蒂塑造的波洛、約翰塑造的萊斯·威廉以及程小青塑造的霍桑等這些偵探全都是扁平人物。扁平人物亦稱為‘性格人物’,有時(shí)亦被稱作‘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他們的性格幾乎從開始到結(jié)束都不會(huì)改變。”[11](P221)可以說,福爾摩斯這一人物形象雖有些許人性化的表征,卻與真正意義上的復(fù)雜人物尚有一板之隔。
《福爾摩斯探案集》在人物塑造方面所呈現(xiàn)出的審美缺憾在高羅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身上得到了較好的藝術(shù)彌補(bǔ),這在《鐵釘案》一篇中體現(xiàn)得尤為鮮明。《鐵釘案》中的郭夫人是《大唐狄公案》女性形象譜系中具有獨(dú)特藝術(shù)風(fēng)姿的女性人物,歷經(jīng)婚姻不幸、命途多舛的她在出任女典獄后,不僅將女監(jiān)管理得井井有條,而且表現(xiàn)出不凡的詩歌天賦。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高羅佩有意通過這一女性形象來映射主人公狄仁杰真實(shí)自然的內(nèi)在情感。《鐵釘案》曾兩次表現(xiàn)狄仁杰對(duì)郭夫人的微妙情感。第一次是作為下屬的郭夫人在向狄仁杰例行公事、匯報(bào)女牢近況后,“狄公深深感佩郭夫人的精明干練,也微微被她那意態(tài)風(fēng)神撩起一點(diǎn)迷惘。”[12](P210)第二次則通過更多的篇幅展現(xiàn)了狄仁杰憶及前日在藥師山與郭夫人偶遇時(shí)對(duì)方所提及的詠梅詩,以及他自責(zé)未能吟誦出這首自己熟知的詩作,甚至還為此“喟嘆頻頻、自怨自艾”的獨(dú)特心理活動(dòng)。[12](P229)狄仁杰對(duì)自己未能在邂逅郭夫人時(shí)吟誦出她心儀之詩而耿耿于懷并非是憂心自己被郭夫人竊笑,而是覺得未能由此與郭夫人產(chǎn)生精神交流而抱憾不已,由此足見他在內(nèi)心深處對(duì)這樣一位容貌不凡而又精明能干的女子所產(chǎn)生的特殊情愫。可以說,作品對(duì)于狄仁杰對(duì)郭夫人的這一柏拉圖式的情感表述既不是通過狄仁杰與郭夫人這兩位已婚之人的情感糾葛來刻意強(qiáng)化敘事情節(jié)的曲折性,也不是以英雄難過美人關(guān)的特殊考驗(yàn)來刻意擢拔狄仁杰的思想和道德境界,而是有意通過含蓄幽微的筆觸來呈現(xiàn)狄仁杰這段飄渺隱約的內(nèi)心情感,從而在其志慮忠純、祛邪扶正的性格特征及斷案如神、撫國(guó)安邦的形象基調(diào)中為其增添了一種隱忍持重之意與細(xì)膩溫婉之心,由此彰顯了這一人物情感的豐富變化和真實(shí)人性的復(fù)雜糾結(jié)。
這種由人物內(nèi)在情感波瀾所引起的真實(shí)人性在狄仁杰因郭夫人的關(guān)鍵提示而得以勘破幾令他身陷不測(cè)之禍的陳寶珍鐵釘殺夫案這一情節(jié)段落中進(jìn)一步提升。郭夫人幫助狄仁杰擺脫因開棺驗(yàn)尸而可能罷職丟官甚或身首異處之危境,狄仁杰本應(yīng)對(duì)她感恩不盡,但他卻也于此間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郭夫人釘殺惡夫的隱情。而郭夫人最終選擇了跳崖自盡,這就避免了狄仁杰在國(guó)家法度與情理道義之間的兩難抉擇。高羅佩對(duì)這一過程中狄仁杰的情感變化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刻畫:狄仁杰在案破后的“欣喜之余,不由想起了他的救命恩人郭夫人。突然他想到一事,臉上頓時(shí)似蒙上了一層冰霜。”[12](P281)在對(duì)郭夫人亡夫掘墳驗(yàn)尸后,狄仁杰“臉色蒼白,目光呆滯,好像勘破了陸陳氏鐵釘奇案,反增添了他一層更深重的煩惱和隱痛。”[12](P283)而在目睹郭夫人跳崖后,狄仁杰當(dāng)晚一宿未眠,他“不僅是神衰力疲,身體困倦,而且是對(duì)事物的敏感反應(yīng)都失去了。他覺得自己變得呆癡遲鈍、渾渾噩噩”。[12](P287)通過郭夫人自殺前后,狄仁杰經(jīng)歷的“案破欣喜、飲水思源→頓悟隱情、心生陰影→證據(jù)確鑿、扼腕矛盾→恩人自盡、備受打擊”這一心境起伏脈絡(luò),小說“凸顯出傳統(tǒng)文化視野下情理與律法的矛盾,以此折射出剛正忠直、一心為公的狄仁杰在面對(duì)國(guó)家刑律與天理人情的巨大沖突時(shí)進(jìn)退窘困、躊躇不決的復(fù)雜心緒,從而使這位名臣在‘神探’面紗下所掩藏的思想情感起伏和復(fù)雜心靈世界被自然真實(shí)地烘托出來,令其形象在走下‘神壇’的過程中更具豐富飽滿的人性意蘊(yùn)。”[13]從總體上看,狄仁杰和福爾摩斯一樣具有推理破案、懲惡存善這一神探人物的共性特征,然而較之福爾摩斯,狄仁杰的形象更多地凸顯出一個(gè)真實(shí)生命個(gè)體所應(yīng)具有的復(fù)雜心緒和人性意味,從而表露出更為豐富的“圓形人物”[14](P61)的審美特質(zhì)。
三、狄仁杰與福爾摩斯形象異同的內(nèi)在原因
福爾摩斯和狄仁杰這兩個(gè)形象在“神探”所具有的人物特征方面表現(xiàn)出很多相似之處,卻在藝術(shù)形象的復(fù)雜豐滿程度上存在著顯著的差距,這既源于偵探小說人物塑造的基本程式,又與兩位作者不同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思想訴求息息相關(guān)。
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福爾摩斯對(duì)化學(xué)、生物學(xué)、數(shù)學(xué)等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精熟于心,他將這些知識(shí)成功地運(yùn)用于案件偵破的過程中,許多疑難案件的破獲也正是有賴于這類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的日常積淀。美國(guó)作家蘭薩姆·里格斯就指出:“歇洛克·福爾摩斯是一名推理大師,更是一名科學(xué)愛好者。”[15](P5)英國(guó)學(xué)者馬丁·菲多更直言:“福爾摩斯是一個(gè)科學(xué)家。”[16](P53)可以說,“柯南·道爾塑造了福爾摩斯這個(gè)既是科學(xué)家又是偵探,既是紳士又是超人的英雄。”[17](P35)《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則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方面具有深厚學(xué)養(yǎng),將這些知識(shí)運(yùn)用于案件偵破中,“迷宮案”、“四漆屏”等案件的破獲都是如此。福爾摩斯和狄仁杰在知識(shí)積淀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前者偏重自然科學(xué),后者偏重人文知識(shí);前者折射出西方文化背景,后者透射出東方文化底蘊(yùn)。但總體上看,二人作為“神探”,在廣泛運(yùn)用積累的知識(shí)來解謎破案方面卻是毫無二致的。就兩位主人公秉持正義、懲奸助善的道德取向而言,狄仁杰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公案小說中的“清官”情結(jié)在《大唐狄公案》中的折射,反映了中國(guó)明清小說對(duì)于高羅佩小說創(chuàng)作的潛在影響;而福爾摩斯則間接傳達(dá)了柯南·道爾對(duì)于維多利亞時(shí)代英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狀的獨(dú)特認(rèn)識(shí)和思考。然而究其根本,實(shí)際上是植根于偵探小說作家所秉持的勸善懲惡或賞善罰惡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以福爾摩斯、狄仁杰為代表的“神探”形象是富于社會(huì)責(zé)任感的偵探小說家傳輸傳統(tǒng)道德訓(xùn)誡觀念的特殊載體,也是普通讀者想象性地實(shí)現(xiàn)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罪惡之人施以制裁的某種理想寄托。可以說,偵探將自己掌握的知識(shí)用于破案的模式以及秉持正義、懲治罪惡的人物形象特征是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傳統(tǒng),也是《福爾摩斯探案集》與《大唐狄公案》中偵探形象特征相似的主要原因。
《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福爾摩斯和《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雖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二人在性格的豐富性尤其是人性深度的開掘方面卻是大相徑庭,這同樣有其深刻的根源。美國(guó)學(xué)者唐納德·J·拉奇曾針對(duì)高羅佩筆下的狄仁杰說:“對(duì)西方人來說,中國(guó)小說里描寫的狄公是一個(gè)完全陌生的人物。為增加西方人對(duì)他的信任感,高羅佩設(shè)法將他寫得盡量人性化。比如,他在漂亮的女子面前,有時(shí)也會(huì)變得興奮起來。此外,有時(shí)也對(duì)自己以及做出的決定缺乏自信。”[8](P14)可謂是切中肯綮。除了主人公狄仁杰外,狄仁杰的助手馬榮也具有多面化的性格特征。馬榮武功高強(qiáng)、性情爽朗,在狄仁杰辦案過程中時(shí)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shí),他又不乏魯莽、好色的性格缺陷。這種將英武豪俠與人性弱點(diǎn)正反兩面特征有機(jī)結(jié)合的寫法,與狄仁杰的人性化塑造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大唐狄公案》中這種人物塑造的人性化、多面化訴求不僅反映在正面人物身上,亦在不少反面人物身上有著鮮明的呈現(xiàn)。對(duì)于《紫光寺》中因情犯罪、迷失自我的逃俗僧人“和尚”、《斷指記》中愛子心切、替子掩罪的黃掌柜、《廣州案》中表面上發(fā)奮自強(qiáng)、志趣高雅,實(shí)則暗藏險(xiǎn)詐、野心勃勃的巨賈梁溥這些反面人物,高羅佩不僅展現(xiàn)了他們善惡兼具的性格特征,而且還對(duì)他們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進(jìn)行了細(xì)膩入微的描摹。①可以說,在進(jìn)行《大唐狄公案》的寫作過程中,高羅佩一方面著意構(gòu)建懸疑曲折的推理斷案情節(jié),另一方面也力圖呈現(xiàn)更為復(fù)雜的人性側(cè)面,現(xiàn)傳統(tǒng)偵探小說中正邪善惡二元對(duì)立的人物形象譜系,這既是狄仁杰較之福爾摩斯更具復(fù)雜人性特質(zhì)的內(nèi)在因由,也從某種側(cè)面反映出《大唐狄公案》在人物塑造方面較之一般的偵探小說具有更為深廣的思想蘊(yùn)涵。
不同于狄仁杰形象投射出人物塑造的獨(dú)特審美理念,福爾摩斯的藝術(shù)形象更多地映射了作者所處社會(huì)的時(shí)代精神和文化蘊(yùn)涵。“在福爾摩斯的世界里,英國(guó)是個(gè)正義得到伸張、邪惡必受懲處的國(guó)度,而福爾摩斯則是一個(gè)堅(jiān)守道義、維護(hù)社會(huì)公正的英雄‘騎士’。顯然,作者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形象的科學(xué)稟性和正義情結(jié)之上,投射了他對(duì)英雄及理想社會(huì)的想象。”[7](P62)“柯南·道爾通過福爾摩斯的形象——執(zhí)法者,卻不屬于官方;擁護(hù)法律,但常常自行主張;偏差于法律之外,彌補(bǔ)法律對(duì)正義的無能為力——引領(lǐng)讀者在小說世界參與法律與正義的博弈,尋求一個(gè)比現(xiàn)實(shí)更加完美合理的烏托邦式的解決。”[7](P66)柯南·道爾更重視通過福爾摩斯及其探案歷險(xiǎn)故事來反映英國(guó)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時(shí)代狀況,而相對(duì)忽視對(duì)這位主人公本身形象的豐滿塑造。可以說,狄仁杰和福爾摩斯之所以在人性深度上呈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性,主要是由于高羅佩與柯南·道爾塑造這兩個(gè)“神探”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追求不同:前者在對(duì)異國(guó)文化進(jìn)行思考和體悟的基礎(chǔ)上,力圖將刻畫人物多元性格、展現(xiàn)人物細(xì)膩情感、揭示人物復(fù)雜內(nèi)心等“圓形人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念融入于通俗文學(xué)形式中,后者更注重通過筆下的文學(xué)形象來表達(dá)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變革時(shí)期自己對(duì)國(guó)家政治、社會(huì)階層、社會(huì)觀念、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認(rèn)識(shí)與思考;前者注重于將人物塑造的真實(shí)化理念融入到異國(guó)小說的現(xiàn)代重寫中,后者則相對(duì)偏重于對(duì)自身所處國(guó)度在社會(huì)、政治、法律問題的客觀反映與現(xiàn)實(shí)針砭。
結(jié) 語
高羅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與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福爾摩斯作為在東西方世界具有廣泛影響的經(jīng)典藝術(shù)形象,在偵探文學(xué)乃至整個(gè)世界文學(xué)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二者在人物自身的非凡智慧和解民倒懸、正義必勝的道德取向方面具有高度的共通色彩,這與偵探小說凸顯偵探主人公睿智形象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及勸善懲惡的道德旨?xì)w密切相關(guān)。另一方面,福爾摩斯與狄仁杰在人物內(nèi)心世界、復(fù)雜性格的獨(dú)特揭示也即藝術(shù)形象的人性化表征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柯南·道爾通過展現(xiàn)福爾摩斯的人性弱點(diǎn)來突出這一神探的多面性格,難與高羅佩以對(duì)狄仁杰內(nèi)心世界和復(fù)雜思緒的細(xì)膩揭示來展現(xiàn)其人性化特征相比肩。這是由于高羅佩在通過狄仁杰形象多元化呈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思想之時(shí),亦將其統(tǒng)攝于鮮活豐滿、人性復(fù)雜的人物塑造理念中,而柯南·道爾的作品則是重在將工業(yè)革命后西方所特有的科學(xué)精神融注福爾摩斯的形象中,并以這一形象及其活動(dòng)軌跡來映照英國(guó)社會(huì)、政治以及民眾生活的各個(gè)方面。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狄仁杰的形象是高羅佩將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精神融入于自己對(duì)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文化進(jìn)行文學(xué)書寫和曲折呈現(xiàn)的藝術(shù)產(chǎn)物,福爾摩斯的形在一定程度上凝結(jié)著柯南·道爾對(duì)自身所處的國(guó)度的政治、社會(huì)現(xiàn)狀的潛在關(guān)注。
注釋:
①詳見拙文《論高羅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僧侶形象塑造》(《揚(yáng)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3 期)、《論高羅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商人形象塑造》(《華北水利水電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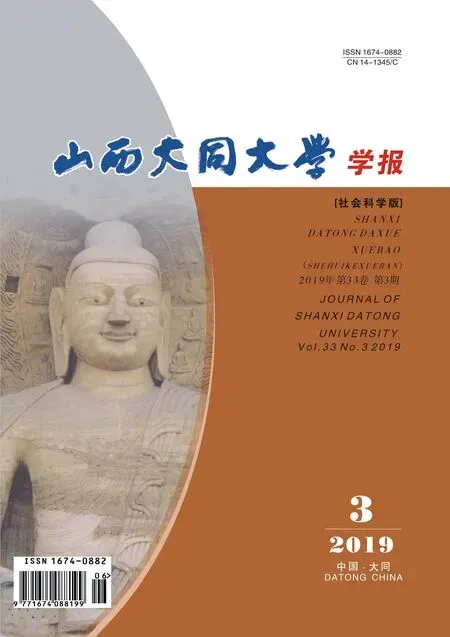 山西大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3期
山西大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3期
- 山西大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西部地區(qū)農(nóng)村精準(zhǔn)扶貧項(xiàng)目瞄準(zhǔn)效果研究
——基于代理家計(jì)調(diào)查法在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應(yīng)用 -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休閑農(nóng)業(yè)與鄉(xiāng)村旅游協(xié)同發(fā)展研究
- 零基預(yù)算法在鐵路企業(yè)成本管控應(yīng)用研究
- 大同市科技資源配置現(xiàn)狀及對(duì)策研究
- 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duì)勞動(dòng)收入份額影響的文獻(xiàn)述評(píng)
- 遼代山西地區(qū)財(cái)政管理變遷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