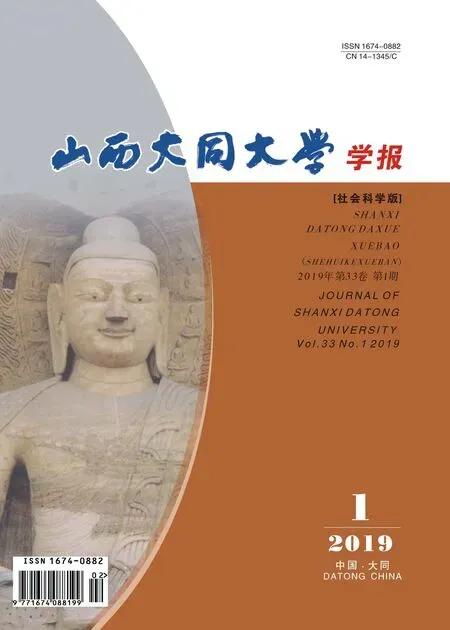從事物間的適宜性角度看美的“關系”
韓守武
(山西大同大學美術學院,山西 大同037009)
1752年,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提出過一個“美與關系”的理論。他說,凡是本身含有某種因素,能夠在我們的理解中喚起“關系”這個觀念的,就叫做美。一個物體之所以美,就是由于人們覺察到它身上的各種“關系”。[1](P23-25)
然而,這“關系”究竟是什么含義?是事物內部各因素之間的關系,還是這一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或者是事物與人類之間的關系?是指特定的某種“關系”呢,或者指所有種類的“關系”?讀者卻不大明白,所以,我國美學家朱光潛先生認為狄德羅對“關系”的看法“極不明確”,其觀點在前后有很大的“矛盾和漏洞”。[2](P276)
的確,所謂“關系”,其種類及數量太多了。且不說人類尚未探究過的宇宙眾多事物的各種“關系”,單是人類已經知道的事物的“關系”,就是無法統計的。有明的“關系”,有暗的“關系”;有近的“關系”,有遠的“關系”:有正面的“關系”,也有側面的“關系”;有好的“關系”,也有壞的“關系”,有善的“關系”,也有惡的“關系”;有美的“關系”,也有丑的“關系”等等。因而,如果說只要見出事物“關系”的概念的,就叫做“美”,那么,幾乎所有的事物都會被叫做“美”了。
因此,如果美是一種“關系”;那么,我們就必須確切知道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們又如何將其中的一些“關系”判斷為“美”,而將另外的“關系”判斷為“不美”?這對于我們進一步了解“美”的本質是至關重要的理論課題。
那么,“美”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一、美的“關系”必須具有客觀性
前蘇聯美學家布羅夫說:“美就其基礎而論是一種客觀的品質。”[3](P172)也就是說,美首先具備客觀性。正如饑餓感是人或動物對食物的一種客觀需要關系一樣,人對美的感知同樣不是純主觀感受的產物,而是對某一客觀存在的關系的稱呼。
狄德羅本人也明確指出這一點,他說:“一個物體之所以美是由于人們覺察到它身上的各種關系,我指的不是由我們的想象力移植到物體上的智力的或虛構的關系,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真實的關系,這些關系是我們的悟性借助我們的感官而覺察到的。”[1](P18)
我們說一朵花很美。當我們對花兒下了這個美的判斷的時候,必然是有一種什么關系被我們感受到了,不論這種關系是由花的顏色引起的,或者是由花的別的屬性引起的,但毫無疑問它實際上表明:花的屬性與人類的屬性之間形成了某種或簡單或復雜的關系。它不是由人們虛構出來的,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而是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關系。
就像花的顏色表明花朵反射的光的波長與人的視網膜的神經元感受性之間形成了某種關系一樣。美的事物也表明它的某些屬性與其他事物或人類生命體之間所形成一定種類的關系。人類自身的感覺系統可以認識和感受這些美的關系的存在,但它并不依賴于人類的主觀感覺系統。
二、美的“關系”是事物或屬性之間的適宜關系
美是事物的某些屬性與其他事物及屬性形成的相適宜的關系。人類社會的“美”指的是人類與事物及屬性在一定社會文化狀態下形成的適宜的關系(即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協調關系)。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都是令人欣喜的美事。雨之所以分外甘甜是因為它和長久干旱的土壤相適宜,能滋潤大地。“故知”之所以分外親切,是因為他和人生地疏的異鄉情景相適宜,使遇之者倍感溫暖。同樣,“洞房花燭”與“有情人終成眷屬”相適宜,因此它分外明亮;“金榜提名”為“十年寒窗”之苦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因此金榜才顯得分外醒目。
美雖然看起來是單個事物表現出來的顯性結果,而其實質則是幾個事物之間的某種相互適宜的關系。所以有一些看起來很奇怪的美的現象,常常另有原因和玄機。“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其中之一。西施之美應該是人人都公認的外表之美,只有能達到這一普遍性標準才可以叫美人。但是,我們想一想,有誰達到過這一要求嗎?沒有。戰國時的西施本人如果能穿越時空到了唐代,她也不見得會被唐人選為美女(實際上環肥已經成為唐代新的美女標準)。可見,美人不是單獨存在的事物屬性,而是反映出她與周圍人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在這些周圍人之中,情人是與她最親近的人,二者構成了最相適宜和最相喜悅的關系。所以也正是情人,會首先發現她的美。托爾斯泰說過,人并不是因為美才可愛的,而是因為可愛才美的。為什么?美不能獨自成為美,而可愛則表明美與他人、特別是情人之間的相適相悅的關系。正如衣服之美要合乎人的身材,鞋子的美要合乎人的雙腳一樣,愛情的美也正在于男女雙方的相適相悅與相知。
莊子也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旅店的男主人,他有兩個妻子,一個眾人以為很美的,另一個眾人以為很丑,但他偏偏喜歡后者,不喜愛前者。別人問他為什么會這樣,他回答說:“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丑者自丑,吾不知其丑也。”也就是說,美不是事物單方面的“自美”就可以的,而是要遇到和它形成適宜關系的“知音”才會形成真正的美的關系。沒有遇到“知音”,與之形成相適宜關系的事物并不能構成美。太陽若不與地球的生命相遇,雙方形成某種聯系,這顆大火球也就無所謂美與丑了。
事物之間能否形成相適宜的關系,是美能否產生的關鍵環節。比如,形式美中最常見的法則之一“對稱”,它之所以成為美的基本形式法則,就是因為它往往適宜于人類對許多事物的形體建造。另外,人體本身的生長結構規律也受著對稱、平衡等形式規律的制約,因而這也是人類與這些對稱的事物之間關系非同一般的重要原因。南茜·埃特考夫在《漂亮者生存》一書中認為對稱與美密切相關,這是因為它是適應生存環境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對稱的動物能更好地應對外界事物,有更高的成活率,生殖力更強,并且壽命更長。同樣,建筑物使用對稱形式,也是為了使它更為平衡穩定,更有利于居住者的生命安全。
實際上,形式美中的許多法則,如對稱、平衡、節奏、統一等等,都是人類在長期實踐中與自然力進行斗爭,最終與自然的規律和原理形成了某些協調和適宜關系的結果。對于這些形式美,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懂得的,這從人類在舊石器時代留下的石器的形狀上可以證明。那時,他們制作物品或建筑房屋和擺放東西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形式法則的“美”。不難想象,人類因為當時的無知而違背這些形式規律,在生活和實踐中,必然會吃到很多的苦頭,受到很重的打擊,比如他們所建房屋因為歪歪扭扭,可能不久就會倒塌,還可能引起人的傷亡。而正是在這些失敗經驗的基礎上,人類才逐步地總結出對稱與平衡的規律,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學會了尊重這些規律,從而開始自覺運用它們。也就是說人類逐漸認識到了這些形式法則與人類生活的相互適宜、協調關系,這些自然形式也便成為人類創造事物的美的形式。
在所有美的事物中,自然美相對說來具有很大的普遍性。這是因為對于人類而言,生命體與自然的關系是最持久、最穩定的關系。所有的人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享有同一個地球。所有生命體都與山川、河流、森林長年為伴,與花草、果實、蟲魚、動物朝夕相處。所以,不管什么膚色、什么民族、什么地區,只要是處于一定時期的人們就必然會有大致相同的與自然不可割舍的依存關系,而這正是人類在自然美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基礎。自然的美來源與它與人類生命的一種協調適宜的關系。
還有些自然物,盡管現實生活中人類對其敬而遠之,但因為它們身上具有某種與人類能夠相協調相適宜的屬性,所以也可以成為人類審美的對象。比如,老虎,沒有人敢于接近它們,它們通常也不對人類顯示任何友愛,然而人類對它們卻似乎鐘愛有加,常常把它們寫進詩歌,畫成圖畫,做成雕塑和各種工藝品,不厭其煩地將贊美贈予它們。究其原因,老虎身上固有的威武、雄壯、勢不可擋的氣質和其引人注目的鮮艷色彩、條紋等屬性,都是人類羨慕與喜愛的對象,都能與人類自身的某些方面形成相適宜的關系。可見,人類審美的范圍幾乎可以延伸到自然的各個角落。只要自然物身上有一點閃光,人們就會把它收集起來,讓它在人類生活的殿堂中散發光亮。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自然美并不是指自然本身的關系而形成的美,而是指自然與人類之間某種適宜性關系。所以它更應該叫做個自然對于人類的美。自然本身是沒有感覺的,自然物只是按照物質的相互作用和規律來運行和發展。而人類的存在是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因此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直接影響著人類本身的生存狀況和感覺狀態,二者相適宜的關系就構成對于人類而言的自然美。比如我們常說的太陽、月亮、花朵的美都是指它們與人類生活之間的那種相適宜關系。太陽給人類以溫暖,月亮給人類以光明,花朵給人類以絢麗色彩和芬芳。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太陽的光所以美,……是因為它使整個大地復蘇,使我們的生活溫暖,沒有它,我們的生活便暗淡悲哀。”[4](P133)
反過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也可能出現不適宜的狀況。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既是不可割裂的,同時也是十分脆弱的。所以人類如果無限度地掠奪和濫用自然,破壞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依存關系。那么自然美就會轉化為自然丑。自然便會無情地懲罰人類,使人類遭受失敗和損失,甚至還可能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
再看藝術美。藝術之美最主要體現在人類的藝術方式的掌握與藝術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等內容的相互適宜關系。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劉勰的《文心雕龍》都談到了如何運用各種藝術結構方法和修辭手段來充分體現藝術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等內容。
古羅馬的賀拉斯在《詩藝》中說:“作家啊,要選擇你力能勝任的題材,想一想你的肩力能否把它挑起來。若是詩人能把主題選得勝任愉快,就不愁條理不清,也不愁缺乏辭彩。……作家既立意寫詩,就要小心和細致:假如你巧于安排,使陳詞富于新義,你就表達得完美;偶或奧妙的主題需要新詞來表意,也不妨創新立異,造一個古羅馬聞所未聞的新字。”[5](P41)這就是說藝術家選擇主題和內容時要適合于自身所掌握的藝術表現手法,在藝術表現時要根據立意和內容表現的需要而靈活地運用相應的藝術手段或創新藝術手段。
中國藝術美學講求“文”與“質”的平衡。《論語·雍也》云:“質勝于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是孔子為古代君子所立的行為標準。后來“文”與“質”被用于藝術理論中。孔子的話可以理解為如果藝術手法過于質樸,就會顯得簡單粗野;而過于講求技藝和文采,又容易流于虛浮油滑。只有文采和質樸兩者適當,才是藝術表現上的“君子”作風。晉代以后“質”“文”的關系,用于指藝術的內容與形式。這時的“質”,指文學藝術作品中的“情”和“理”等內容;“文”則指文采。這時的“文質彬彬”,要求在藝術上充實的內容和完美的形式相互協調融合,相互聯系而又相互促進,做到“華實相勝”。既不能“質勝于文”,即表現藝術內容時過于淺露直白;又不能“文勝于質”,即藝術形式過于華麗,以辭害意。
藝術美的其他所有范疇實際上都是在藝術內容“質”和藝術形式“文”的關系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問題,比如結構、章法、句法、修辭、象征、抽象、表現、再現等。
三、美的“關系”與一定形式的“生命體”特性相聯系
美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事物與生命體(特別是人類)之間的關系。它只對生命體的存在產生意義。一般情況下,我們談的美都是指對于人類社會而言的美,往往并不考慮其他生命體的感受。但實際上,美的關系可能是所有生命體與外部世界的特殊的關系,而非人類社會的專有。肖世敏在《有動物有美感論》中說:“動物有沒有資格成為審美的主體?有。因為這是動物的權利,這是生命的權利;動物有沒有能力成為審美的主體?有。因為動物具有審美生成的基本條件,更重要的是,審美的能力,是一種生命的能力。”[6](P244)他還引用過了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的一段特別有論辯意味的話:“如果你問一個雄癩蛤蟆:美是什么?它會回答說,美就是它的雌癩蛤蟆,兩只大圓眼睛從小腦袋里突出來,頸項寬大而平滑,黃肚皮,褐色脊背。最后,試請教哲學家們:他們會向你胡說八道一番,他們認為美須有某種符合美的本質原型的東西。”[6](P84)
所有的生命體都有自身感覺能力,都會與周圍事物及環境形成適宜或不適宜的關系,它們也有自身的美學系統。人類的美學系統正是在這種生命美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有的生命體都有著相同的審美基礎。
人有一種本能的自我中心主義。這種盲目自尊的天性使人類不可能允許任何動物與他們平起平坐。所以很多人對于從生物學角度來研究美和美感的方法往往采取不屑一顧、甚至極力排斥的態度。每到這時,人們總會拿出動物身上的一些缺點與人類身上的相應的優點進行一番比較,最后證明只有人配得上認識美和理解美。
然而,隨著宇宙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高貴地位越來越不容樂觀。人類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和天然主角,而是和其他物種一樣,都是歷史性地偶然地生活在地球這個在宇宙天體中特別普通的星球上的。人類是地球上生物進化和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物種之一。而且人本身也經過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變化過程。比如,人在最初階段里也曾茹毛飲血,也曾赤身裸體,也曾住在山洞和樹洞里,與猿、猴、熊以及其他許多動物之間的差異微乎其微。人與動物一樣要吃喝、休息、娛樂、繁衍;人與動物一樣有大腦,能思考;人與動物一樣擁有感情、善于傳達;人與動物一樣有生死、有傳承。為此,莫里斯直接把人稱做“裸猿”。
相比較而言,人類在自身發展的早期階段更具童真之心,對動物的偏見和歧視要少得多。他們并不把人類同動植物的世界完全分割開來,許多較原始的民族部落認為所有活的東西彼此都很相似,所有的動物都是“人”。
人類與動物太多的相同之處,決定了人類不可能完全超越動物界,人類的審美也必定與他們的動物特性密切相關。人類有美,動物也有美(這是人類美的初始階段)。人類的美與動物的美應該有相同的發生機制。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說:“在許多重要的事情上,我們是摹仿禽獸,作禽獸的小學生的。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7](P124-125)
不同的動物需要不同的生存環境,這是生物學上的一般常識。每個動物都尋找著能使自己適悅的環境。比如,非洲的斑馬、角馬、牛、羊等都追隨水草不斷遷移,蜜蜂、蝴蝶總圍著花朵飛舞。而人類也在各種環境中安生立命。從心理上說,不同動物(和人)喜歡不同的環境。這種內在的好惡標準,就是動物(和人)最初的審美的尺度。凡與這個尺度相適宜的,就是被主體認為美的環境;反過來也可以說,這個環境對該主體具有“親切愉悅”的感覺特性。人們通常稱之為快感或美感。
有人說,生物追隨環境,是內在功利的驅動,不是審美。比如植物喜光,動物喜食,原生動物向光或向暗,向暖或向寒等。但人類又何嘗不是在某種社會或自然的功利之下追隨事物呢?人類也“喜光”、“向暖”,也喜愛美味食品,喜愛花朵的芬芳,也同樣趨利避害。人類與其他動物的這些感覺在心理過程上沒有本質差別,只有進化復雜程度上的區分而已。它們是動物和人類美感產生的共同的基礎。動物在很多方面實際上都是人類早期生活形態的縮影。
我們把助人為樂稱為美德,而動物中也有互相幫助的事,這是不是美?人類稱母愛是最偉大的愛,許多動物也表現出強烈的母愛,這是不是美?人類會使用工具進行勞動,有的動物,如烏鴉、啄木鶯、猿、大猩猩等也會借助一定的工具來實現自己的意圖。人類通過藝術形式來表達愛情,而許多動物也會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展現自己,爭奇斗勝,贏得配偶。這和人類的愛情之間的淵源關系也是顯而易見的。
可見,人類社會的美與其他生命體的美具有相同的發生和發展機制。人類社會高級的美是以生命體各種低級的美為基礎的。
四、美的“關系”的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關系
自然的美和人類社會的美會隨著自然和時代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著變動。
因為事物之間的適宜或不適宜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美的本質內涵在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是不斷擴大和發展的,它與自然的發展、時代的發展、人類自身的發展緊密相聯。只有在理解這種變化的基礎上,才會理解美在不同的自然或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形態。換句話說,所有的美都是一定自然歷史和社會歷史的美。
人類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提高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認識自然的能力,是美的事物隨時代而變化的客觀的社會的根源。
三寸金蓮之所以受到中國古代人的追捧是因為它適應了當時封建社會對婦女人身自由進行限制的要求,使她們難于遠行,只能待在家中相夫教子,敬奉公婆。因此它這就和封建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形成了相適宜的關系。新文化運動后,封建禮教受到批判,女性有了和男子同樣的社會參與權利,三寸金蓮已不能適應她們奔走社會的需要,所以,自然的天足就必然而然地取代了人為的纏足。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應該是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壞和諧,毫不違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美同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時候,再下一代就將會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誰也不會有所抱怨的。……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給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滿足它們。”[8](P125)世界永不停息地向前發展,不會永遠保持同一個面貌,而是隨著自然和時代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動,人類本身的能力和需求也都會有新的發展和變化。因而,每個新的時代都有與自己這個時代相適宜的新的事物、新的關系和新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