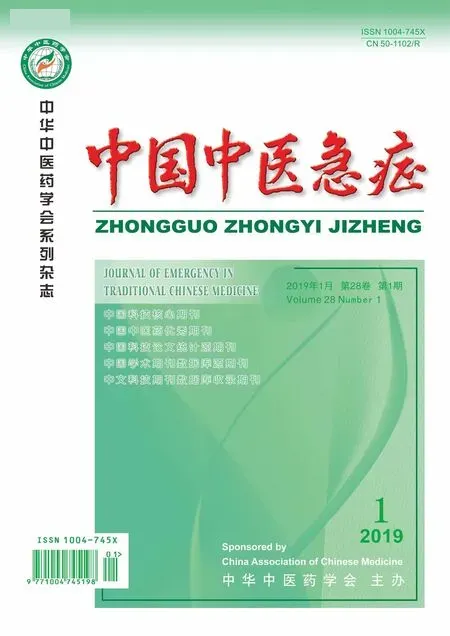瀉肺通腑方干預ICU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肺炎患者的臨床研究*
成向進 林朝亮 朱紅林 張會哲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鹽城市中醫院,江蘇 鹽城 224001)
近年來,隨著人口的老年化,老年感染患者日益增多,加之廣譜抗菌藥物、免疫抑制劑以及糖皮質激素在臨床中廣泛使用,部分患者反復暴露抗菌藥物,以及有創治療手段的豐富,各類手術及穿刺等侵入性操作破壞人體天然屏障,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MDR-PA)在臨床中不斷檢出。筆者所在單位為中醫院重癥監護病房,老年內科患者偏多,肺炎為主要病種之一。痰液中銅綠假單胞菌(PA)分離率高,耐藥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與重癥監護病房回顧性研究病例分析結果相似[1]。
銅綠假單胞菌具有多種毒力因子,致病性強,并能天然抵抗多種抗菌藥物,耐藥機制為產生生物莢膜障礙及外排泵系統阻止藥物到達靶位點,同時在治療過程中容易因突變發生耐藥,所以治療頗為棘手[2]。筆者在臨床中發現多重耐藥菌肺炎老年患者雖然病位在肺,但隨著炎癥因子的釋放、長期臥床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患者多會出現程度不同的胃腸功能障礙,表現為腸內營養不耐受、胃潴留、嘔吐、大便干燥不通等。契合中醫“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肺氣的肅降影響大腸的傳導。針對MDR-PA肺炎對抗菌藥物不敏感,治療周期長,易反復,患者預后差等特點[3],筆者使用瀉肺通腑方藥干預MDR-PA肺炎合并胃腸功能障礙患者,療效滿意。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西醫診斷標準。(1)肺部感染診斷標準:釆用2001年衛生部頒布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中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4]。臨床診斷符合下述兩條之一:①患者出現咳嗽、痰黏稠,肺部出現濕啰音,并有下列情況之一:發熱;白細胞總數和(或)嗜中性粒細胞比例增高;X線顯示肺部有炎性浸潤性病變。②慢性氣道疾病患者穩定期 (慢性支氣管炎伴或不伴阻塞性肺氣腫、哮喘、支氣管擴張癥)繼發急性感染,并有病原學改變或X線胸片顯示與入院時比較有明顯改變或新病變。(2)病原學診斷標準:痰標本按照標準流程獲取,注意無菌操作,避免污染。痰培養連續兩次培養出銅綠假單胞菌或同一培養皿中屬優勢生長。痰培養及藥敏參照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研究院(CLSI)的抗微生物藥物敏感試驗標準進行操作和判斷[5]。(3)細菌耐藥性診斷標準:多重耐藥菌主要是指對臨床常用的3類或3類以上抗菌藥物同時呈現耐藥的細菌[6]。2)中醫辨證分型標準。符合《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風溫肺熱病”的診斷標準,中醫辨證屬于痰熱壅肺[7]。主癥:身熱、咳嗽、咯黃痰或痰中帶血。次癥:氣喘、胸痛、煩渴、汗出、大便干、小便黃。舌脈:舌紅苔黃或膩,脈洪數或滑數。主癥具備2項及以上(“咳嗽、咯痰”為必備),次癥具備2項或2項以上,結合舌脈可診斷。
1.2 臨床資料 選取2015年2月到2018年2月期間江蘇省鹽城市中醫院ICU住院患者70例。按1∶1比例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各35例。治療過程中治療組3例、對照組4例放棄治療,自動出院。治療組32例,男性19例,女性13例;平均年齡(73.62±8.72)歲。對照組31例,男性18例,女性13例;平均年齡(74.81±9.31)歲。兩組性別、年齡等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
1.3 治療方法 1)治療原則:參照《銅綠假單胞菌下呼吸道感染診治專家共識》[8],包括抗感染、加強痰液引流、呼吸支持、腸內腸外營養、免疫調節、維持循環穩定、防止多器官功能衰竭等。2)抗菌藥物選擇:肺炎診斷成立后立即根據臨床和流行病學給予恰當的經驗性初始抗菌藥物,應盡量覆蓋可能的致病菌,在治療前留取病原學培養標本[9]。病原學培養及藥敏回報后根據藥敏結果選擇合適抗菌藥物。療程為10 d,可根據療效適當調整療程。3)試驗用藥名稱和規格:瀉肺通腑方藥物組成及劑量:膽南星6 g,浙貝母12 g,黃芩15 g,山梔子 10 g,知母 10 g,桑白皮 15 g,法半夏 15 g,陳皮12 g,茯苓 15 g,瓜蔞仁 15 g,杏仁 10 g,葶藶子 15 g,生大黃 6 g(后下),厚樸 10 g,枳殼 12 g,甘草 6 g。 每日1劑,煎成400 mL,早晚各200 mL口服或經鼻胃管、鼻腸管飼入。隨癥加減:咳喘劇、咯吐白色泡沫痰,加白芥子、萊菔子;口渴、干咳痰少者,加麥冬、天花粉;咯吐腥臭痰或膿血痰者,加魚腥草、薏苡仁、桃仁;咳喘伴有胸悶或胸痛、下午及夜間發熱、口唇發紫、舌質暗紅者,加桃仁、丹參。4)分組治療:治療組在西醫基礎治療+瀉肺通腑方藥,每日1劑,分2次服用。對照組采用西醫基礎治療。療程均為10 d。治療期間如發生腹瀉,瀉下通腑藥物減量。
1.4 觀察指標 1)綜合療效:判定標準參照2004年衛生部頒發的《抗菌藥物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0],進行4級評定臨床療效。痊愈:臨床癥狀、體征、實驗室及病原菌檢查均恢復正常。顯效:病情明顯好轉,但上述4項中有1項未完全恢復正常。進步:有所好轉。無效:用藥后病情無明顯進步或有所加重。有效率=(痊愈+顯效+進步)÷總人數×100%。2)細菌學療效:評定標準參照2004年衛生部頒發的 《抗菌藥物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0]評定細菌學療效,按清除、部分清除、替換、未清除和再感染5級評定。清除:療程結束后細菌培養無致病菌生長。部分清除:培養兩種以上致病菌僅1種清除。替換:療程結束后原致病菌清除,但培養出新的致病菌,無感染臨床表現,無須進行治療。未清除:療程結束后病原學培養,原致病菌依然存在。再感染:經治療原有細菌清除,再度感染其他細菌,需要給予治療。清除率=(清除+部分清除)÷總人數×100%。3)臨床肺部感染評分(CPIS)[11]:(1)體溫:36.5℃≥體溫≤38.4 ℃為 0分。38.5℃≥體溫≤38.9℃為1分。體溫≥39℃或體溫≤36 ℃為 2 分。 (2)血白細胞數(×109/L):4≤血白細胞數≤11為0分。血白細胞數<4或血白細胞數>11為1分。(3)氣道分泌物:無痰為0分。非膿性痰為1分。膿性痰為 2 分。 (4)氧合功能 PaO2/FiO2(mmHg):>240或無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為0分;≤240或ARDS為2分。(5)肺部影像學:無滲出為0分。局部滲出為1分。彌漫(或斑片狀)滲出為2分。(6)肺部滲出進展:無進展為0分。有進展(排除慢性心衰和ARDS)為2分。(7)痰培養:病原菌無或少量或無生長為0分。病原菌中量或大量為1分。病原菌與革蘭染色相同加1分。4)病情改善程度及感染指標,包括APACHEⅡ評分、感染相關指標(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5)兩組抗菌藥物暴露時間、ICU滯留時間。
1.5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8.0統計軟件。所有統計檢驗均采用雙側檢驗。計量資料數據服從正態分布的以(±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 χ2檢驗;等級資料用Wilcoxon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綜合療效比較 見表1。治療組綜合療效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

表1 兩組綜合療效比較(n)
2.2 兩組細菌學療效比較 見表2。兩組在MDR-PA清除率上差別不大(P>0.05)。

表2 兩組細菌學療效比較(n)
2.3 兩組CPIS評分、APACHEⅡ評分及感染相關指標比較 見表3。兩組治療前CPIS評分、APACHEⅡ評分及感染相關指標均差別不大(均P>0.05)。兩組治療后評分及感染指標均較治療前均改善(均P<0.05),且治療組均優于對照組(均P<0.05)。
表3 兩組CPIS、APACHEⅡ評分、感染指標比較(±s)

表3 兩組CPIS、APACHEⅡ評分、感染指標比較(±s)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 別 時間CPIS(分)APACHEⅡ評分(分)白細胞計數(×109/L)C反應蛋白(mg/L)降鈣素原(ng/mL)治療組 治療前(n=32) 治療后對照組 治療前9.28±0.39 21.03±1.93 16.28±2.19 4.01±0.98*△ 14.01±1.51*△ 8.52±1.41*△9.36±0.43 20.78±2.08 15.92±2.37 87.21±11.82 10.35±1.52 14.22±4.52*△ 0.61±0.21*△85.34±12.35 10.19±1.36(n=31) 治療后5.33±1.11* 16.32±1.14* 9.54±2.01*22.11±6.48* 1.56±0.25*
2.4 兩組抗菌藥物暴露時間、ICU滯留時間比較 見表4。治療組患者在抗菌藥物暴露、ICU滯留時間均短于對照組(均P<0.05)。
表4 兩組抗菌藥物暴露時間、ICU滯留時間比較(d,±s)

表4 兩組抗菌藥物暴露時間、ICU滯留時間比較(d,±s)
組 別 n 抗菌藥物暴露時間 ICU滯留時間治療組 32 10.12±1.31△ 8.07±1.27△對照組 31 13.92±1.62 9.68±1.42
3 討 論
MDR-PA肺炎為中醫學 “風溫肺熱病”“肺炎喘嗽”范疇。其多發生于年老體弱、有多種基礎病或長期臥床者;亦有發病前體質尚好,因吸煙肺部嚴重、反復感染,體質日漸衰弱,引起免疫功能低下,導致肺部感染纏綿難愈,銅綠假單胞菌定植[12]。正符合中醫學“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中醫認為老年人年老體弱,而且往往久病纏身,導致正氣虧虛,臟腑功能失調。正氣不足,易受外感,外感溫熱或風溫邪毒后首先犯肺,傳變入里,煉液為痰,外邪、熱毒、痰濁相互搏結,導致痰熱壅盛,肺失宣肅而發病。肺與大腸相表里,大腸的傳導與肺氣的肅降密切相關,肺失宣肅易致腑氣不通,表現為腸內營養不能耐受、腹脹、腹痛、大便干結。臨床工作中,筆者發現MDR-PA肺炎患者多合并胃腸功能障礙癥狀(中醫辨為腑氣不通)。根據MDR-PA肺炎“正氣虧虛、痰熱壅肺、肺失宣肅、腑氣不通”的核心病機,并結合“急則治其標”的原則,在清熱化痰宣肺的同時,往往給予通腑法,使腑氣通暢,利于促進肺病恢復。確立了“清肺化痰、瀉熱通腑”的治法,在清氣化痰丸的基礎上加小承氣湯歸納出瀉肺通腑方藥。
方中制膽南星、浙貝母,味苦性涼,清熱化痰,治實痰實火之壅閉;黃芩、梔子、桑白皮降肺火化痰熱,以助膽南星之功,瓜蔞仁尚能導痰熱從大便而下。枳殼、陳皮下氣化痰,氣順則一身之津液隨之而順矣。茯苓、杏仁、半夏健脾滲濕,宣肺下氣,燥濕化痰。大黃苦寒,功能瀉熱通便、涼血解毒、逐瘀通經;厚樸、枳殼行氣散滿、破氣消痞。諸藥合用,使熱清則痰自消,氣順則火自降,痰消則火無所附,肺熱瀉則腑氣通;化痰與清熱、理氣并進,通腑與瀉熱、活血合用,諸癥悉除。
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方中部分中藥具有抗銅綠假單胞菌活性。膽南星中有效成分皂苷對大腸埃希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3種細菌都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其機制可能是抑制細胞的分裂[13]。黃芩的主要成分黃芩苷和黃芩素,可對銅綠假單胞菌生物膜的形成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從而抑制細菌的黏附與生長[14]。梔子的主要成分梔子苷能抑制銅綠假單胞菌總蛋白酶、彈性蛋白酶、綠膿菌素的分泌以及生物被膜的形成[15]。大黃可提高MDR-PA對抗菌藥物的敏感性,有效降低阿米卡星和美羅培南的有效抑菌濃度和殺菌濃度[16]。
本研究顯示,瀉肺通腑方藥能夠提高ICU MDRPA肺炎患者在臨床癥狀、體征、實驗室及病原菌檢查等方面的綜合療效;能有效降低感染指標、臨床肺部感染評分及APACHEⅡ評分,提示能更快控制感染、改善疾病嚴重程度;并能縮短抗菌藥物暴露及ICU滯留時間。但在細菌學療效上,未體現清除MDR-PA的優勢。考慮與本研究納入人群大多為老年ICU患者,其反復肺部感染、氣道MDR-PA長期定植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