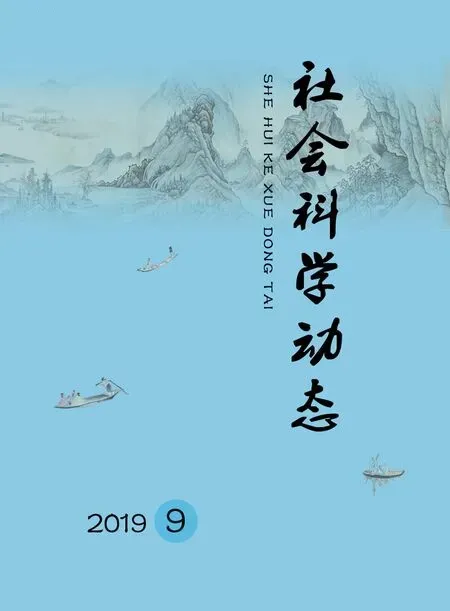射擊影子的方法
廖海杰
曹軍慶最新問世的小說集《向影子射擊》收錄了其近年的代表作品,也體現了其創作的新變。在眾多的評論中,曹軍慶常常被作為一個“先鋒”小說家看待,這自然是因其創作中無處不在的現代或后現代技巧,但“先鋒”這一大概念下亦有不同的小路數——先鋒可以像《褐色鳥群》那樣不及物,也可以像《岡底斯的誘惑》那樣置于遠方。曹軍慶的路數令人想起20世紀拉美文學大爆炸中的主將胡里奧·科塔薩爾——如其《南方高速》《正午的島嶼》 《基克拉澤斯群島的偶像》等名作所展示的,科塔薩爾路數不光意味著“天馬行空”,更重要的是從高度寫實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滑向荒誕,恰如隸書書寫時的一筆“蠶頭燕尾”,起筆時回鋒隆起作蠶頭,似生存之重,到尾上卻不知不覺輕逸上揚,在這種上揚中可能存在非現實的、甚至冒犯的成分,但文學不就是在這一點超越性中顯現?
《向影子射擊》中的故事,發生于縣城。事實上,對于整個中西部的中國而言,縣城一頭連接農村,一頭又是現代都市文明的外省或準備區,是轉型年代中國最重要的顯形之地。縣城是混雜的,在混雜的社會生活、經濟形態、文化力量的多重形塑下,充滿著這一時代的張力和復雜性。立足縣城中國的現實展開文學想象,曹軍慶新近演化出的路數正如本書的名字所示——向影子射擊。
一
“影子”意味著對模仿觀念的反叛。柏拉圖的洞穴假說,將人之所見均視為投射于山洞巖壁上的影子,而理念的真實世界不可知,因此認為詩人無非模仿“影子的影子”,必須被趕出理想國。現實或現象是否是某物之影,對個人而言并不重要,我們所能體驗思考的無非也就是這層影子,重要的是人們一直以來的觀念中“影子”似乎是一個比本體低一級的替代品。影子不同于鏡像,它是一個變異的、粗略的模仿,正如在圖像敘事越來越發達的今天,文字敘事也變得越來越像現實的變異的、粗略的影子,但影子一定低于鏡像、低于現實嗎?這就仿佛說文學低于影視、影視低于新聞報道、新聞報道低于短視頻、在抖音中潛藏著最深刻的時代精神一般,充滿著荒誕的幽默感。或許,在現存的高度復雜的人類協作體中,在高度復雜的現代性面前,文學可以依靠的正是顯形影子、觀察影子、射擊影子的方式,對現實作出回應——照出現實的影子,捕捉現實的影子,才能讓我們更貼近現實。
曹軍慶的這部小說集執著于對縣城中國的“造影”與“捉影”。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問題,如《滴血一劍》 《云端之上》;鄉村開發問題,如《風水寶地》 《我們曾經海誓山盟》;腐敗問題,如《請你去釣魚》 《時光證言》;底層生存問題,如《請溫先生喝茶》 《和平之夜》 《一樁時過境遷的強奸案》……當然,我們不能簡單以XX問題給這些小說安上所謂主題,小說自身的流動性、多義性不能適用這樣的粗暴切割,就像影子難以被確切框定為像狗或像兔。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小說都基于堅實的現實生存之體驗,都關注著縣城中國人們生活中、細節處的煩憂與憤怒。在這之中,《膽小如鼠的那個人》便是非常優秀的一篇對縣城進行“造影”與“捉影”的作品,講了一個頗為傳奇的“翻身”故事:動不動就臉紅的老同學楊光標可謂是一個超級老實人,也由于這份循規蹈矩的老實和害怕爭辯的性格,楊光標四處被人欺負,終于在賣魚的過程中被魚販子們教訓,出了大丑——被霸道的蔣三當街用魚抽了耳光。文中有一段描寫相當精彩:“到底是魚販子,掄起魚來就像掄著兩塊木板子或是兩只鞋。但是魚又活著,在空中能自由擺動,蔣三卻有本事直直地把它抽到楊光標臉上。第一下擊中后,楊光標的臉就開始紅腫。他差點跌倒,搖晃幾下又站定了。蔣三拿手上的魚攻擊楊光標,魚和人的臉皮撞擊居然能發出那么響亮的聲音。”①
楊光標被教訓后,便老老實實和妻子開起了麻將館,但在這一過程中,卻又出了一檔子事:楊光標在自己的店里贏了錢,外面便有人開始傳言麻將機有問題,楊光標得知之后緊張不已,竟主動退錢給同桌打麻將的另外三人,結果這反而坐實了麻將機有問題的猜測,簡直是窩囊透了的行為結果。小說的焦點也在此離開了楊光標,后半段集中筆墨到近年來幸福縣崛起的強人光頭良身上。光頭良出身黑道,擁有縣里最大的商城和最氣派的樓盤,作為納稅大戶,現在是書記縣長的座上客。社會上的傳言都說光頭良殺人不眨眼,他曾經在一次酒局中途出去一趟,解決了一個對手,回頭來喝完了那頓酒才開始逃亡,最后又洗白了身份,光明正大地重新回到縣城活動。總之,就是這么個狠角色,到最后小說尾部發生了情節的反轉——光頭良竟然就是楊光標的兒子。不過,若是光論情節的曲折傳奇,本作還談不上精準的“造影”與“捉影”,真正有意思的是其敘述結構設計:楊光標是“我”的小學同學,而關于他后來的故事,都是“我”另一個做官的同學顧維軍當作笑話講的。前后兩段故事的銜接來自于“我”的故事,即“我”被父親鄙視,而父親崇拜光頭良,侄兒也成了光頭良的親信。最后是“我”在幸福縣駐武漢辦事處的團拜會上碰見光頭良,才解開了他是楊光標兒子的秘密。那么這個敘述者“我”是什么角色呢?“我”外出求學后在省報任記者,但多年來并無一官半職,被長居縣城的父親鄙視,認為沒混得個出息。事實上,“我”這個角色和楊光標構成對位的結構,“我”正是另一個意義上的楊光標。“我的故事”、“父親的鄙視”、“侄兒的經歷”,在前后兩段傳奇故事的轉捩點,照出并捕捉了縣城文化之“影”——父親作為退休教師,深以自己作省報記者的、“沒有能力”的二兒子為恥,但卻以做小混混、因為碰巧搭救了光頭良而混得有頭有臉的孫子為榮。小說寫道:“我父親開始主動找他孫子也就是我侄子搭訕,他這么做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去巴結自己的孫子干什么?……他一定認為他才是我們家庭的希望,能給我們帶來某種榮耀。”②在“我”家內部,“我”成了另一個楊光標,侄子成了另一個光頭良,而平凡的、一輩子生活在縣城的退休教師父親,深深地向往著乃至崇拜著后者所代表的“縣城意義上的成功”。這一段情節看似不長,但卻是全文的亮點所在,正是因為有這段情節的存在,給前段楊光標、后段光頭良兩段極端化、傳奇性的情節增加了厚實的生活底色,使得小說并未淪為一個“故事會”式故事。父親的崇拜,寥寥幾筆,卻在小說敘述的轉捩點上捕捉到了那縈繞在整個小說中的縣城文化魔影——奴性的、對強權的崇拜,即使這種強權只是弱肉強食的原始野蠻。膽小如鼠、老實到極點楊光標之所以要忍辱負重培養出光頭良這樣的兒子,不正是為這種原始野蠻的文化氛圍所逼?與《膽小如鼠的那個人》相似的,還有《和平之夜》 《請溫先生喝茶》 《一樁事過境遷的強奸案》等幾篇作品,不論是中學生對所謂幫派決斗的向往、神秘的民間仲裁者,還是能殺人的街巷輿論,曹軍慶都在“造影”與“捉影”的虛實之間對縣城中國的小角落作深描,這樣的“先鋒”不僅生長于藏污納垢的民間,又有厚實的現實關懷、切實的生存經驗為依托,無疑是更及物的。
二
及物的寫作與批判本是共生的,曹軍慶的文學之根既然扎在縣城中國,自然也意味著對這一責任的肩負。只是,在真理在握的啟蒙姿態已不“流行”的今天,“造影”與“捉影”之后,射擊影子的方法就變得更為重要。曹軍慶在這部小說集中,通過虛實之間的曲筆和留白,完成著對影子的射擊、對現實的批判。
“射擊”本身就是一個有著“強烈”情緒指向的詞,《風水寶地》和《請你去釣魚》兩部題名平和的作品中,便暗藏這種行將爆發的勢能。《風水寶地》中,作為作家的“我”,到行將消失的柳林村,借住于毛支書家里養病和靜心創作。幾天后“我”便發現一個女人來給死去的兒子燒紙,交談中,“我”得知其子死于草皮蟲病,她因留守在村莊缺乏娛樂,天天打麻將而耽誤了兒子的治療。后來,毛支書告訴“我”那個女人叫孫素芬,當時嫁到村里來鬧洞房時曾被以鱔魚調戲,毛支書準備把鱔魚鬧洞房的惡俗作為民俗文化打造旅游項目,但自稱要求一直沒有得到批準。再后來,“我”又從毛支書夫人吳大姐處得知,孫素芬早就死于自殺,因為兒子死后她無法再生育而被丈夫拋棄,而之所以無法再育,則是因為當年被毛支書作為計劃生育典型拉去醫院做了絕育手術。“我”寫完小說后離開了柳林村,但后來又從鎮長處得知,“我”去柳林村時毛支書已死,實際上只有吳大姐一人在照顧“我”的起居。《風水寶地》看上去帶有志怪色彩,又因為“我”本是患病需要休養的作家,使不可靠敘述者得以產生。那么,故事中的種種慘劇及其背后的現實根源——民間的惡俗、簡單粗暴的鄉村計劃生育、留守婦女和兒童的困境、農村的空心化、隱藏著各種欲望的商業旅游開發等等——都成了或許是幻覺里、或許是鬼怪色彩包裹下的故事內核,連柳林村也成了不再存在的村子,但鬼氣和幻覺中農村的種種黑暗,也給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這可謂一種“射擊”。《請你去釣魚》中,“我”的朋友瞿光輝是縣里身兼要職的官員,他包養了一個叫方小惠的風塵女子,正準備給她買套房子,誘其幫著再生個兒子,但方小惠卻突然失蹤了。瞿光輝深受打擊,此后卻愛上了去某個特定的魚塘釣魚。因為領導的這一愛好,吸引了縣里其他機關的“積極”跟進,魚塘老板收入大增,對他點頭哈腰、卑躬屈膝。后來“我”得知,魚老板就是方小惠的哥哥,難怪瞿光輝對他別有照顧。但一次醉酒之后,“我”將魚老板送回魚塘,他突然破口大罵,說要放狼狗咬死這些人、毒死所有的魚。在這個故事中,方小惠為何失蹤、魚老板是否知道瞿光輝與其妹的關系等等,都是未展開的情節留白,但在這留白之中,一種緊張的兩個階層間的對立關系卻毫無疑問地存在著。釣魚活動的平靜之下是暗流涌動,正如魚老板忽然的爆發,正如那兩只“絕對不可能咬人”的狗竟然讓汽車無法挪動,而這一暗流也對位地解釋了方小惠無緣無故的失蹤:這也是她的反抗,只是瞿光輝自己覺得無緣無故而已。在強權者被自己的恩惠所自我感動的時候,在其察覺不到之處,被侮辱者已積累起巨大的反抗欲望。
在虛實之間通過曲筆和留白,制造出巨大的想象空間又帶有強烈批判性的,正是本集中的同名小說《向影子射擊》。在這篇小說中,曹軍慶寫了一個看上去有些超現實的、但又并非沒有現實根據的故事。云嫂生下孩子后,被醫生引薦去了一個神秘院落做奶娘,在這里,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他為何要以人奶為食?與夫人之間又是怎么一種關系?小說里都沒有交代,始終讓這個小院處于迷一般的場域中。不過,這個初看起來頗為架空的故事,卻絲毫不給人任何虛幻之感,相反它具有極強的說服力,這意味著它實現了一種基于融貫的文本內真實性。而“向影子射擊”的意象則出自于先生對云嫂唯一說過的一段話:在合約期將滿之際最后一次哺乳時,先生告訴云嫂他小時候是個孤獨的人,唯一的愛好是用手指比劃成槍的形狀,向隨便什么影子射擊。有意思的是,云嫂的孩子小仁也莫名地有了向墻上影子射擊的愛好,云嫂發現了兒子與先生的相似之處十分高興,還專門為他買了三把玩具槍。這里射擊,也就是槍的意象,意味著反抗的權力,在小說中顯然代表著云嫂一類底層人對那位上過電視、被神秘女人控制、要吸人奶為生的大人物(及其背后的強權)的反抗。但在小說的結尾,當云嫂又一次被保安粗暴地扔出醫院,她為兒子買的玩具槍也摔在路上被往來的汽車碾了個稀爛,這意味著底層反抗的完全失敗。更可怕的是,先生在那唯一的交談中還告訴過云嫂:他最早也是擺地攤起家的。也就是說,吸人奶為生的怪物,曾經也是出自底層。地攤,擺在地上的非正式的商業行為,可謂是最貼近地面的底層,那個在孤獨中用手作槍射擊植物、房屋和人的影子的孤獨小孩,最終在實現了階層躍升后卻又再次成為了加害者。新的被碾碎的槍,要射擊的是搶奪孩子哺乳權的怪物,但這個怪物本身卻也曾是一個底層的反抗者,這真是可怕的歷史循環。此外,小說中塑造出了小院深不可測的吞噬力。云嫂在提供服務一年里迷戀上了先生以及其所代表的生活。這個小院像一個漩渦、一個深淵,一個會回以凝視的深淵,云嫂被小院所吞噬,她一次又一次試圖回去卻淪為笑柄,而乳房再也流不出潔白的乳汁,只能流出變色的污水。這里,讓云嫂所代表的下層與小院的關系除了槍所暗示的對抗,還有一廂情愿的愛慕,兩種互相矛盾的情緒扭結糾纏,再次成為奇妙的循環:底層渴望成為上層,成為新的吸人奶的人,槍被碾得粉碎,畸形的愛只造就乳頭流出的污水和肥胖變形的上身……在對循環和吞噬的書寫中,《向影子射擊》可謂示范了射擊現實之影的方法:用敏銳的感覺制造出文本世界的內真實性,用直擊人心的意象和隱喻,讓讀者在接受中自然感受到隱含的、強烈的現實批判張力。
曹軍慶在小說集《向影子射擊》中實現了對縣城中國現實的“造影”、“捉影”及精準射擊式的批判。其中的寄托不禁讓人想起閻連科所呼喚的“神實主義”,雖然這一理論未必那么精密而富于學理性。在2011年出版的《發現小說》中,閻連科寫道:“今天中國的現實樣貌,已經到了不簡單是一片雜草、莊稼和樓瓦的時候,它的復雜性、荒誕性前所未有。其豐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國今天的現實,與文學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漿湖中淹沒著無數的黃金和毒汞。有作家從那湖中摸到了黃金;有作家只在岸邊嗅到了散發著奇味異臭的氣息;而有的作家,筆下只有毒汞的液體。以文學的口舌,議論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簡單地說‘人心不古’,根本無法理解今天人在現實面前的遭際境遇。”③
也正因為中國現實前所未有的豐富、復雜,使得曹軍慶式的“向影子射擊”之創作傾向,有了更多的時代性,“向影子射擊”不是凌空蹈虛,不是純形式的游戲,而是基于對縣城中國中個體的生命體驗、時代感受細致入微的體察。當然,“向影子射擊”常常要在虛實之間切換,這對于作者構建文本內真實性的功力是一個極大地考驗,如學者趙毅衡所說:“文本要取得這種融貫性,就必須為此文本卷入的意義活動設立一個邊框,在邊框之內的符號元素,構成一個具有合一性的整體,從而自成一個世界。有了這個條件,真實性才能夠在這個文本邊框內立足,融貫性才能在這個有限的范圍中起作用。不僅如此,文本的此種融貫性,也必須與接受者的解釋方式(例如他的規范、信仰、習慣等)保持融貫。”④在這部小說集中,如《滴血一劍》和《云端之上》對網絡游戲世界的想象,就可能存在融貫性上的問題——對部分熟悉游戲世界的讀者而言,可能會產生出作者對網絡游戲缺乏常識的懷疑,進而造成整個文本內真實性質疑的可能。當然,“向影子射擊”既游走于虛實之間的藝術,中間偶有不盡完美之處也再正常不過。我們相信作者在不斷的嘗試和進步中,藝術創作一定能達到更為爐火純青的境地。
注釋:
①② 曹軍慶:《向影子射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308頁。
③ 閻連科:《發現小說》,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頁。
④ 趙毅衡:《文本內真實性:一個符號表意原則》,《江海學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