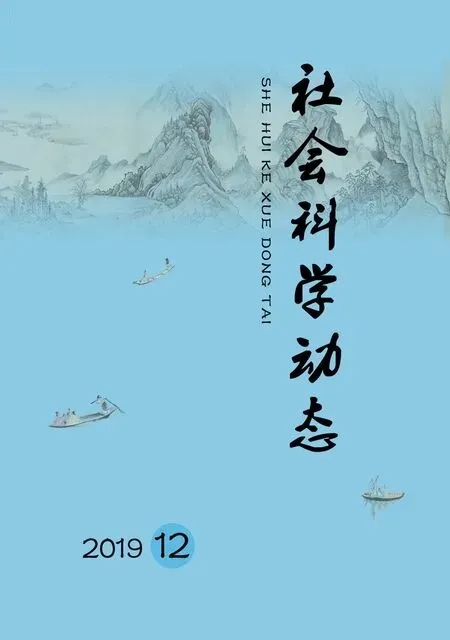論張鐵榮的周作人研究
——以《周作人平議》為例
薛柏楊
《周作人平議》是張鐵榮先生對自己過去一段時期研究工作的總結,1996年初版于國內,大部分是他在日本執教期間發表的文章,有一小部分是之前在國內發表的文章;2006年再版時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內容。總的來說,《周作人平議》不僅是張鐵榮對周作人深入研究的成果集合,同時也很好地體現了他的治學風格。
分析張鐵榮的研究特點,離不開對張鐵榮研究軌跡的梳理:張鐵榮研究周作人始于他在南開大學當講師時,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負責組織全國各大學編輯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資料,張鐵榮和張菊香兩位先生一起受邀參與《周作人研究資料》的編輯工作。《周作人研究資料》和《周作人年譜》這兩本資料的整理出版為之后的學者進行周作人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樣為張鐵榮自身的周作人研究奠定了詳實的史料基礎。1985年9月《周作人年譜》初版時,國內關于周作人的全面研究才剛剛起步,鑒于周作人的“漢奸”身份,很多學者對周作人的研究處在一種觀望的狀態,但這時張鐵榮、張菊香兩位先生已經在用比較公正的態度來細述周作人的是是非非。應該說,這對做學問的人是非常寶貴的學術精神。
這樣的學術開端使張鐵榮先生與其他大部分周作人研究者不同,他的研究更為專注,他對周作人的關注,僅僅是因為周作人值得研究而非其它政治熱點等因素。他對周作人的研究不僅專一,而且常常有新意。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體現:
一、平和的態度,合理的同情
首先說張鐵榮先生研究的姿態。用錢理群先生的話說,就是“張鐵榮先生把他的周作人研究稱為是一種‘平議’,即自視‘平凡之人’,作‘心平氣靜的研究’,力求‘公平的持論’”。①
不管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云怎樣變幻,張鐵榮始終能用冷靜的態度觀察審視周作人身上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尤其是周作人中晚年的生活。這種平常心在研究內容中充分體現。以書中《周作人出任偽職經過》一文為例,一般關注周作人的都知道其有一段頗為不光彩的歷史,但卻對于這段歷史的細節以及內情往往關注得不夠,而張鐵榮并沒有因為周作文這一段歷史的不光彩的名聲而去限制自己研究的寬度,像他所說的:“為了澄清種種混亂和傳聞,有些事情我們還不得不從頭說起。”②為了這一句“從頭說起”,張鐵榮將1938年之后周作人身邊發生的各種事情都尋來細細梳理分析。
作者同情惋惜周作人,但絕對不像有人認為的“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對周作人的人生觀產生了共鳴,于是才‘狂捧周作人’”。③作者曾提到自己為何研究周作人:“我們以往關注的大都是偉大的或成功的作家,而周作人是一個在政治上失敗的作家,因此就更有吸引力,走近他可以警策我們自己由此開出一條反省的路,還可以研究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這樣的研究可以使人冷靜,更容易鍛煉一顆平常心。”④張鐵榮不僅從基礎研究上介入周作人,也在思想研究上體會知堂老人的內心,并沒有在周作人叛國投敵的歷史上有所隱瞞。同樣的態度在對周作人《閉戶讀書論》正名時也可以看到,這種態度區別于某些研究者,用錢理群的話來講,就是“不堪寂寞,還要堅守陣地,會不會產生一種悲壯感或者自我崇高感呢”⑤,很明顯張鐵榮并沒有這樣。
其次是作者能在周作人的沉淪中看到他內心的煎熬,并以合理的同情心去研究。張鐵榮對周作人出任偽職的經過以及佚文進行梳理,發現周作人的思想也有不那么消極的時候,只是這些文章在周作人自己選編的文集中沒有收錄。此外,張鐵榮在《周作人與〈古今〉雜志》中的的考證非常細膩,《古今》雜志是周作人在任偽職期間比較出力的報刊之一,對于分析這一段時間周作人的心思及創作動態的變化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對于這部雜志的研究在當時周作人研究界中尚屬于一個比較薄弱的部分。
在日寇包圍的北京生存,加上疏遠了曾經的摯友,可以設想,周作人的在京生活可能內心也是備受煎熬。作者認為周作人是為了在京求得一個相對講真話的空間,于是多在《古今》雜志上發表想法,但《古今》雜志在本質上卻也是汪精衛那一派的,于是周作人“為了在日據時期的北京爭取一點小自由,他和南方偽組織的關系卻越陷越深了,豈不知汪偽政權也是日本軍閥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⑥。作為周作人黑暗歷史的一部分,張鐵榮先生并沒有回避,而是同樣用公正理性的態度對待,進行詳盡的學術考證,不回避周作人的軟弱、猶疑和虛假,對周作人為什么選擇這種生存方式也給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周作人在不同的時期所表現出的不同的選擇是其人性逃不開的弱點。張鐵榮既不否認周作人歷史上的錯誤,又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周作人的矛盾,于理性中滲透著感性。
二、詳實的內容,嚴謹的行文
正是持有平和的態度,才使張鐵榮在周作人研究中更加注重資料真實性,更加注重實事求是,嚴謹認真地說每一句話。
張鐵榮早期關于周作人研究的文章,資料性都很強,雖然時間過去比較久但仍然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從《周作人年譜》到《周作人平議》,張鐵榮始終將研究中的資料性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一些沒來得及挖掘的史料反而有時能反映出很大的問題,而在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資料性與細節性是很值得重視的,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⑦《周作人年譜》就是一部很重要的帶有研究性質的資料匯編,于廣博中有所篩選。雖然專著不可避免地存在有一些疏漏⑧,但是這樣詳實的內容,更是在當時眾多的理論批評中體現出作者對現當代文學本身的重視,最基礎的研究是回歸的同時,也是一個新的起點。而《周作人平議》則延續了這一方法。
觀點是建立在客觀史料的累積之上,倘若資料不完善,就很難對一事物進行公正的評判。相比思維的新異,張鐵榮本人更擅長進行資料的整理與事實的考證,這在《周作人平議》的《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一文中可見一斑。對周作人遇刺事件的前后背景,有很多人曾進行過不同的分析,但畢竟是一件發生在個人身上的歷史“小事”,各種記述也都不見得真確,這種情況下,張鐵榮對各家之言做了一個總結,就在此文的“附錄一”——《周作人遇刺事件資料分類表》中,作者列舉了范旭新說、周作人原說、洪炎秋之說、盧品飛之說等觀點,以表格的形式一一列舉,并在“附錄二”中記述了當時日本報紙關于此事的相關報道,使后來的讀者可以在全域視野中形成自己的思考判斷。
對于周作人在抗戰時期所產生的文學創作和思想變動,張鐵榮從周作人與《古今》雜志的關系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從他發表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墮落與昏聵、苦悶與煩惱、傷感與激憤、個性與聰敏、空虛與懷舊……周作人在《古今》雜志發表的文章,與他同時期發表的其他文章比較起來看,我認為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說是抗戰時期周作人文學的一個縮影。”他認為,對于《古今》雜志的研究或許可以作為研究周作人的一把鑰匙,用以打開周作人的精神世界。
張鐵榮在書中說道:“如果對于研究對象不能進行科學的討論與評價,實際上真正受到損害的不一定是被否定的對象本身。”⑨一個人的改變是歷史的、多方面的,要用比較嚴謹的表述方式才可以做到不偏不倚。為了盡力還原周作人的心路歷程,他不回避周作人的落水,反而圍繞著周作人的落水展開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不論是周作人與日本方面的交流,還是周作人與國內文人的通信,張鐵榮對此都予以盡量公正理性的評判,從而使得讀者能夠立體地把握周作人不同時段的思想傾向。
三、力求細致而全面的研究方法
不將自己的想法強行添加在讀者身上,而是通過擺出事實來將其中的“理”講清楚,可以說,張鐵榮在“講事實”方面確實做到了細致而全面。前引《周作人遇刺事件資料分析表》自無需多說,在《周作人與文字同盟》這篇文章中也隨處可見作者治學踏實全面的研究風格。
說到周作人就不能不談及到魯迅,魯迅在一定程度上是周作人研究的底色,無論是對兄弟二人其中的哪一位進行專門研究,都離不開對對方的關照。張鐵榮在研究周作人的過程中多次將魯迅擺在自己思想的參照物上。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我深深的知道,從魯迅這里出發,研究周作人就不會偏”⑩,“魯迅研究是我的老本行,從學生期間就讀魯迅的書,自1979年發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經近40年了。”?然而張鐵榮卻不是將焦點聚焦在魯迅身上,這一點上他與錢理群不同。錢理群的研究是總要回到魯迅身上去,盡管他也寫了《周作人傳》,但有一部分內容是回歸在魯迅身上。而張鐵榮的《周作人平議》是將焦點聚集在周作人身上,于是才能在風云變幻中總以平常心來研究周作人的零零碎碎,樂此不疲。雖然研究周作人確實離不開魯迅,但是周作人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在研究周作人時也并非需要時時都與魯迅牽連,在某些方面把他當作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一些問題,可能會更加清晰地發現他本身的特質。
由于周作人與日本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一定程度上結合日本文化的場域才能更好地發現和研究周作人。張鐵榮的日本講學經歷,剛好為其研究周作人提供了便利,《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就是他在日本訪學期間完成的,也是當代系統研究周作人日本文學翻譯的第一篇文章。另外,為了還原周作人最真實的樣子,張鐵榮對周作人不同時期的佚文進行了整理,并且對于1910到1949年之間周作人的佚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并收錄在《周作人平議》中,“周作人解放前的佚文是研究他思想、創作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這些作品可以增強我們對他的全面了解,豐富我們的研究工作。” 同樣的態度,在一些沒有被《周作人平議》收錄的論文中也能看到,為了研究周作人的思路歷程,作者對丸善書店與內山書店進行研究。?與研究對象有聯系的書店的歷史都看得分外認真,可見張鐵榮研究的全面細致。周作人不僅僅是作為一名文學家存在,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張鐵榮于文學性的研究之外,也不忘關注周作人的思想世界,這是非常可貴的。
這種比較細致的研究,對周作人的一些局部問題突破比較大。從一些細小的點出發去研究周作人,也可以為周作人研究開辟出一些新的增長點,比如 《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研究》,對于周作人翻譯手法、翻譯語言的研究都具有一定開創性,同是也是周作人研究比較薄弱的部分;還有《關于周作人的貢獻與評價》一文,將周作人的散文創作從1930年分段,論述了周作人30年代之前創作的散文的魅力、周作人散文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以及這一時期散文被輕視的過程及原因。
四、文集中不可避免的缺憾
筆者認真閱讀《周作人平議》,感覺這本文集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以不同時期發表的論文文集的形式整合成一本專著,存在的缺點就是在體系方面略有欠缺;其次,文集中有幾篇文章是作者早期所寫的論文,有些文字顯得情緒化,比如談到周作人落伍的時候,“如果他真的鉆到藝術之宮去不問天下事,就不會有此大錯,長期以來的研究者們都是在藝術上找他下水的原因,我想這是不對的”?;此外,有些文字也有重復的現象,如論及《閉戶讀書論》時,作者認為 “周作人并不存在被嚇破膽‘躲進苦雨齋’的問題,他住在北京大罵南方的國民黨和蔣介石,應該說是很安全的,但是他不寫或是寫了也不發表,是因為他知道這樣的文章此時發表只能對奉系軍閥有利”。?相似的言論在文集中多處都有出現,如在《關于周作人的貢獻與評價問題》 《周作人的佚文》等文章中,就出現過幾乎一模一樣的句子?,因此從頭看下來偶爾會有重復的感覺。但誠如作者在后記中坦言的,“由于各篇曾單獨發表過,此次合集校讀時感到有個別小的重復,如刪去又恐不妥,只好懇請讀者原諒”。可見,這一問題在合集本中很難合理的解決,也可以理解。整體而言,瑕不掩瑜。
做學問的人盡管對某事物有自己的喜好及心境,但總是要盡量客觀公正地努力還原研究對象的真實面目。在這一點上,張鐵榮與周作人的看法可謂所見略同。張鐵榮沒有為周作人的“落水”粉飾過什么,只是通過分析與全方面考證,盡力還原歷史事件真相。《周作人平議》以事實來表觀點,平和公正,令人敬佩。這與唐弢先生重寫文學史的呼吁精神內涵遙相呼應,“文學史就得是文學史,它既是文學又是史,真正寫出了文學衍變過程和發展面貌的歷史”。做研究要有歷史的心態,張鐵榮先生在盡自己最大程度地還原文學史真正的樣子,這一點有目共睹。
注釋:
①⑤錢理群:《以平常心作平實之研究——讀張鐵榮《周作人平議》,《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
②③④⑥⑨⑩??? 張鐵榮著:《周作人平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8、235、119、11、后序、165、34、31頁。
⑦張鐵榮:《要注意資料和文本的細節——〈周作人年譜長編〉編纂體會》,《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6期。
⑧ 黃開發:《近十幾年的周作人研究》 (上),《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
?張鐵榮:《我的魯迅研究之夢——〈寄意寒星荃不察〉序言》,《上海魯迅研究》2017年第2期。
? 張鐵榮:《丸善書店與內山書店》,《內山完造紀念集》,上海魯迅紀念館2009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