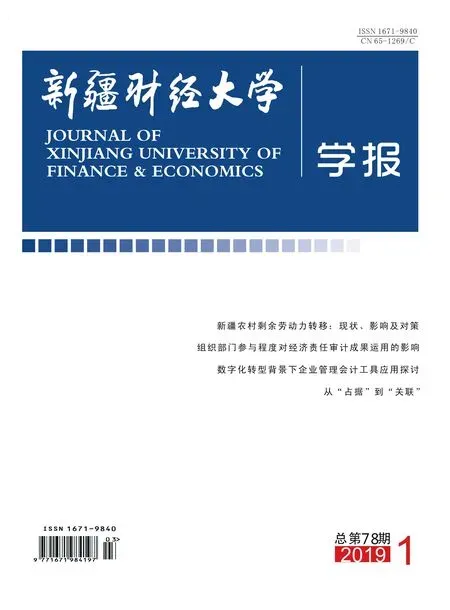約翰·巴斯小說《客邁拉》中的“反傳統”女性意識
王振平,師夢琪
(天津科技大學,天津 300222)
約翰·巴斯是美國當代最具創造力的作家之一,為后現代主義小說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巴斯于1967年發表論文《枯竭的文學》[1],討論文學的表現形式是否已經枯竭以及文學還有怎樣的可能性,其中特別關注了文學中的“反傳統”現象。在巴斯的小說作品中,新的文學形式和“反傳統”的描寫成為后現代主義作品的一大特色。1972年,他的小說《客邁拉》[2]出版,并獲1973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這部小說是巴斯在《枯竭的文學》發表后創作的第二本小說,踐行了其奉行的“反傳統”文學形式。帕維爾認為,《客邁拉》將阿拉伯故事、希臘神話與現代社會現象相結合,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回應,是巴斯為應對“文學的枯竭”而竭力創造的新的文學形式[3]。有學者認為,“巴斯的創作總是有這樣的指向:想(向)古老的敘述傳統回歸,從中尋求小說創作的靈感與營養,通過重寫、重述或修正經典或神話,恢復小說潛在的和原始的敘事魅力”[注]詳見林群著《山魯佐德的重生論〈一千零一夜〉的無限敘事哲學在后現代語境下的延續》,蘭州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頁。。巴斯的改寫常是與傳統相悖的,形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創作理論,這種自相矛盾就體現為一種“反傳統”。這種“反傳統”不僅體現在無限的敘事哲學中,也體現在小說的故事內容和思想意識結構中,正如瓦里克所言,《客邁拉》的故事反映的是“迂回的意識歷程”[4]。其中,巴斯在小說中對女性的描寫方式和敘事口吻獨具特色,體現了作家的女性主義立場,是區別于其他男性作家傳統的寫作手法而進行的“反傳統”描寫。將女性主義立場寓于“反傳統”的寫作之中,不僅體現了作家思想的進步與開放,也為當代文學創作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不可或缺的女性角色與獨特的女性視角
小說《客邁拉》由三部分構成,即敦亞佐德篇、英仙座流星篇和柏勒羅豐篇。巴斯為什么將這三個故事放在一起?名字又為什么叫“客邁拉”?小說的故事線索一直是眾多讀者不斷探究的問題之一。筆者以為,小說以“客邁拉”命名,一方面是因內容確實涉及有關怪獸客邁拉的神話故事,因而將“客邁拉”作為希臘神話中的意象理解更便于讀者理清故事內容;另一方面“客邁拉”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怪獸,由獅頭、山羊身和蛇尾構成,集幾種動物于一身,小說由三個中篇故事組合而成,在結構上恰好與怪獸“客邁拉”的三部分異形構造相對應。三個中篇故事分別是對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敦亞佐德篇)和希臘神話(英仙座流星篇和柏勒羅豐篇)的戲仿,兩種情調迥異的故事并存一體,為小說蒙上了某種怪異的色彩[5]。
小說的故事線索就像怪獸客邁拉所表現的,怪異繁雜,存在多種對應關系,尤其是在兩性關系的敘事上。在故事中表現為多對男女關系,可能是一對一(如敦亞佐德和沙宰曼),一對多(如佩爾修斯和安德羅墨達、美杜薩等),甚至還可能是多對多(如柏勒羅豐和菲洛諾厄、墨拉尼佩、安忒亞,安忒亞和普羅托斯、柏勒羅豐等)。
在這樣的兩性關系設計中,女性角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國王山魯亞爾和其兄弟沙宰曼,還是英雄佩爾修斯和柏勒羅豐,每個故事都由女性人物來點睛。如果沒有山魯佐德和她妹妹敦亞佐德的復仇計劃,敦亞佐德篇中一千零一個故事的智慧將無法充分體現;如果沒有安德羅墨達、雅典娜和美杜薩,佩爾修斯的英雄夢或將無從說起……因此,雖然每個故事的線索并不是完全圍繞女性人物展開,女性人物究其根本也不是故事的幕后導演者,但女性人物在小說中卻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沒有女性人物,人民的智慧無法體現,英雄的故事無從成立,神的情感或也無以表達。
巴斯的女性意識不僅體現在小說中不可或缺的女性人物角色塑造上,還包含在其經常使用的兩性人物敘事和多重敘事策略中。如柏勒羅豐篇,巴斯將該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柏勒羅豐為第一視角敘述整個故事,但后兩個部分中分別增添了墨拉尼佩視角和波呂厄多斯視角。墨拉尼佩是柏勒羅豐的女祭司,既是故事的見證者,也是故事的參與者。她并不認同柏勒羅豐講述的故事,甚至認為他講的故事“全是謊言!假的!漏洞百出!”[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和50頁。。第三部分中的波呂厄多斯視角又回歸男性寫作,對前兩篇中的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柏勒羅豐篇的三個部分既從男性視角的常規寫作中描述故事內容,又從女性認知的角度重新進行詮釋,表現了巴斯對兩性敘述視角的關注,尤其是故事的第二部分,墨拉尼佩視角的敘述對故事的完整和主要內容的解釋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明,通常從男性視角看到的故事,并不一定是非常客觀或完全正確的,柏勒羅豐企圖證明墨拉尼佩是自由之身,認為她是易于滿足的,但事實并非如此。又如敦亞佐德篇中,姐姐山魯佐德講述的一千零一個故事“以其無限的文本消解了敘述的封閉性,穿插在古希臘神話之間,象征著無窮無盡的文本性,以山魯佐德源源不斷的敘述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成為女性敘述文學的代言人”[注]詳見王建平著《約翰·巴斯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頁。。另外,對《一千零一夜》改編后的敘述方式也有所不同,主人公從姐姐山魯佐德轉而變成了妹妹敦亞佐德,特別增加了敦亞佐德視角,并在這篇故事的第二部分中增加了敦亞佐德的番外,多名女性的敘述更豐富了故事的內容,借敦亞佐德的視角轉達國王山魯亞爾對平等愛情的評述:“要想減輕別人不忠而帶給自己的痛苦,只有愛,沒有別的。他選擇了平等的愛情。”[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和50頁。“后現代主義張舉懷疑主義,特別是對現代一元論、絕對理性、單一視角和純粹理性加以懷疑”[注]詳見周敏著《什么是后現代主義文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這種多重視角的寫作方法正是后現代主義對一元論和單一視角的懷疑,是對傳統寫作方法的反叛,是一種文學寫作視角的革新。
二、“反傳統”的女性人物表現
(一)“天使”與“妖婦”的“反傳統”解讀
《客邁拉》中出現的女性人物有很多,大多性格鮮明,特色突出,不同于傳統女性。如安德羅墨達和菲洛諾厄,她們是男性眼中標準完美的女性;再如豬精的新娘,柏勒羅豐的母親歐律墨得等,她們和別人偷情,其行為被男性憎惡,是傳統的壞女人。這兩類女性是傳統男性認知中的“天使”和“妖婦”,是以男性思維定位的女性。但不同的是,她們不依附于男性的思想,不尊崇傳統的男權認知,而且發起了對男權地位的挑戰。她們有思想,有個性,具有一種反傳統的性格。
男性眼中標準的女性形象,是符合傳統道德規范的。安德羅墨達——佩爾修斯的妻子,“美麗”“圓潤豐滿”“有女人味”等,無疑是男性眼中的美女形象;菲洛諾厄,“從來不抱怨”“太完美了”“嗓音像她的身段一樣柔美,三十五載的歲月絲毫沒有改變她的容顏”[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17和234頁。等等。這些女性一般是男性心目中的“天使”,也可能是塑造男性英雄形象的必需品[6]。一方面,她們可能是男人奮斗乃至犧牲的理由和目的;另一方面,贏得她們的芳心或擁有她們或又是男人成功的象征。有時,男人需要得到美麗女人作為妻子來體現自己的價值和成就。就像佩爾修斯后來感悟到的,他之所以成為英雄,不僅是因為斬殺了戈爾戈女妖,更因為解救了安德羅墨達,并娶其為妻。
但是,在《客邁拉》中,這類女性并沒有完全被男性征服。雖然安德羅墨達嫁給了佩爾修斯,但她并不想嫁一個英雄,她真正希望的是做佩爾修斯的妻子,而不是英雄的妻子,但佩爾修斯卻將成為英雄視為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價值。所以安德羅墨達面對已成石像的菲紐斯哭訴,“我已受盡磨難。因為我是輝煌之夢的生活伴侶,夢醒時分,眼前的現實竟然如此:頭發稀疏,大腹便便,未老先衰,深陷過去的輝煌,不能自拔,對我,對家庭,給予的關愛越來越少”[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17和234頁。。安德羅墨達既擁有傳統男性滿意的女性形象,又敢于掙脫這一類形象的固有特點,一反傳統,她不想做男人眼中的完美女性,她要做自己想做的女人。
菲洛諾厄也是“完美”的,她的所有時間和精力都屬于丈夫和孩子,而對自我的忽視和犧牲則使她變得沉悶乏味。但與完全依附男人的女性不同,她對婦女解放運動表現出友好和興趣,能意識到“女人在全神貫注生兒育女的事業時,其他事情都不知不覺從身邊溜走了,等到反應過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變得反應遲鈍,對一切都不感興趣了。而恰好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夫君和我們的婚姻可能需要更新了”[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17和234頁。。安德羅墨達和菲洛諾厄都是傳統男性心目中的“天使”,但她們卻沒有像傳統女性一樣完全認同傳統,尊崇男性至上觀念。巴斯為這類符合傳統審美的女性賦予了“反傳統”的思想,使她們有了更為豐富的性格特征。
山魯佐德最喜歡豬精的故事。這只豬精在婚禮上搶了別人的新娘,將她鎖在一只寶箱內,外面上了七把鎖,鑰匙藏在海底的一個水晶柜里,沒人能找到。豬精每次強奸這個姑娘后都會呼呼大睡,她便從他身下溜走,和路過的男人交歡茍合,每次留下一枚戒指作為憑證,故事結束時她已積累了五百多枚戒指。而愚蠢的豬精卻一直以為這個姑娘只屬于自己。“這個故事與國王每天強暴一名處女的故事形成了對照,曾在小說中幾次出現,可看做巴斯女性意識的體現,性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在兩性關系中,女性應該擁有與男性對等的權利。”[注]詳見吳皓著《論約翰·巴斯與神話重述》,黑龍江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7頁。其實,這個故事貫穿于《客邁拉》整部小說的始終。山魯佐德像豬精的新娘一樣,每天在國王山魯亞爾頭上放一百只角,一直積累到十萬個。佩爾修斯能和達納俄斯成為血緣上的兄弟,是因為他的母親曾悄悄和狄克梯斯好上了,而佩爾修斯的妻子安德羅墨達又出軌達納俄斯。安忒亞是提瑞斯國王普羅托斯的王后,卻不停地勾引柏勒羅豐;而且似乎只有柏勒羅豐的母親歐律墨得知道德利亞德斯和柏勒羅豐的父親分別是誰。小說中的一些女性似乎有些放蕩不羈,但是,在男性可以為所欲為的世界里,她們的行為并非對文明的踐踏,而是要以自己的行為來反抗男權至上的現實世界。
(二)女性人物對權利自由的“反傳統”追求
敦亞佐德篇中,國王山魯亞爾的妻子和別人偷歡,他一怒之下殺死妻子,并因此痛恨女人,在那之后的每一個夜晚都要強暴一個少女,并在次日早上將其殺害。宰相的女兒山魯佐德為拯救無辜少女,主動要求嫁給國王,希望能阻止殺戮。
這一部分改編自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在古老的阿拉伯王國,人們沒有法律保障,生殺予奪盡在國王手中。但越是沒有法律保障,公民權利就越顯得重要。山魯佐德和妹妹敦亞佐德為姐妹的性命擔憂,與國王作斗爭的行為,表現了巴斯對女性生命權的重視。與《一千零一夜》不同的是,敦亞佐德篇著重描寫山魯佐德搜集故事的復雜過程,更加突出了女性生命權的來之不易,以及生命權對于女性的重要。
故事著重強調了山魯佐德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女性,“在巴努蘇珊大學學習藝術和科學,是一年一度校友返校節上的皇后,被推選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辭,還是一名厲害的主力運動員。此外她擁有一個藏書上千冊的私人圖書室,在校園歷史上堪稱一絕。每一所東方大學的研究生院都愿意給她提供獎學金,但是,她對國家的現狀感到震驚,在大學最后一個學期她離開了學校,潛心研究,設法阻止國王對同胞姐妹的殺戮和對國家的毀滅。”[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和56頁。《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魯佐德只是一個愛讀書的人,而《客邁拉》中對山魯佐德的教育狀況卻有濃墨重彩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對女性受教育權的重視。
1970年8月26日是女性獲得選舉權50周年紀念日,美國女性在40個城市舉行了大規模游行活動。在這場運動中,婦女對于性別壓迫的覺醒是女權主義的奮斗目標,“權利”是女權主義活動家大聲疾呼的口號。1972年發表的《客邁拉》,從側面體現了巴斯對女性權利的認知。
與權利遙相呼應的,是巴斯對女性自由的認知。巴斯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色彩,“后現代主義借用福柯的觀點,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輕肉體的傳統,大談身體的重要性及肉體的各種體驗”[注]詳見李銀河著《女性主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在《客邁拉》中,巴斯就對女性的身體進行了大膽而細致的描寫,既不吞吞吐吐,也不羞辱輕視。
男性作家對女性身體的歧視有時可以說是一種常態。早在古希臘時期的12世紀,著名神學家阿奎那就聲言,女性之所以成為女性,“乃是由于發育不健全,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劣于男性”[注]詳見劉巖、馬建軍、張欣等著《女性書寫與書寫女性:20世紀英美女性文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8頁。。一直以來,作家和評論家對女性或女性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歧視,如“1966年英國小說家兼批評家安東尼·伯格斯曾批評簡·奧斯汀的小說,認為小說的缺點是作家缺少男性的勇猛剛強”[注]詳見劉巖、馬建軍、張欣等著《女性書寫與書寫女性:20世紀英美女性文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8頁。。而在《客邁拉》中,巴斯不僅敢于大大方方地描寫女性的身體,而且毫不羞澀地描寫男女間的性關系。如英仙座流星篇中與佩爾修斯相關的三個女人,安德羅墨達身體圓潤豐滿、水晶通透;卡萊西亞像個體操運動員,膚色黝黑、平胸窄臀;美杜薩年輕,身體柔軟,寬胯、窄胸。對于被傳統觀念視為“不堪、下流”的性描寫,他也毫不吝嗇,寫得非常自然。如描寫佩爾修斯和卡萊西亞時寫道,“我(佩爾修斯)紅著臉親吻了她的肚臍”[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和56頁。,等等。這些對故事內容的客觀描述,與小說中壁畫上顯示的故事互相照應,不僅沒有顯得突兀,而且給人一種美的感受。
《客邁拉》中的這些女性在巴斯的筆下是自由的。她們不會因為男性強權而膽怯,也沒有因為展露身體以及開放的性態度而被刻板地、粗暴地定義為淫亂、蕩婦。她們的思想已經掙脫了傳統觀念禁錮在女性身上的枷鎖,她們有辯證思考的大腦,也有勇于表達思想的膽量。
“在宏大敘事之中,女性一般都只能是‘暴君的俘虜、床上的伴侶、英雄的輔佐’,而在巴思筆下,她們不但擁有美貌與智慧,而且還是使停滯不前的男主人公擺脫困境的引領者。”[注]詳見劉巖、馬建軍、張欣等著《女性書寫與書寫女性:20世紀英美女性文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8頁。敦亞佐德篇中的兩姐妹不愿受制于國王,是命運的勇敢抗爭者。在《一千零一夜》中,山魯佐德以講故事的方式說服國王停止殺戮,以兩人結婚為結局。《客邁拉》中山魯佐德也采取了講故事的方式,但目的不僅是要說服國王停止殺戮,更是要為死去的少女復仇。她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愛上國王,而是反抗到了最后一夜。
英仙座流星篇中卡萊西亞對自由的理解尤為經典。安德羅墨達向往“愛情平等”,而卡萊西亞更崇尚“愛慕自由”。她不同意安德羅墨達對平等的理解,認為不可能每個女人都是平等的。愛神阿佛羅狄忒是女人,她卡萊西亞也是,不能因為都是女人,就說她們地位平等。卡萊西亞在許多方面都比男人更優秀,要求男女平等對她來說只是無稽之談。一方面,她能夠辯證地認識“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她又強調自己“愛慕自由”。她仰慕比自己優秀的人,不管他是誰。她沒有大多數女人的依賴感,聰明機智,朝氣蓬勃,善于與人溝通;但她又不自以為是,幻想和杰出人物平起平坐,她喜歡自己,更喜歡比自己優秀的人。她對婚姻并不信任,認為這種永恒關系對相互之間的激情有致命的、無法避免的殺傷力。她追求激情,所以不結婚[注]詳見約翰·巴斯著、鄒亞譯《客邁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3頁。。這是卡萊西亞愛的自由。男女平等、愛情平等、愛情自由的觀念和追求貫穿小說始終。在兩性關系中,這些話題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巴斯將這些話題躍然于紙上,大膽地借人物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當代美國人對美國自由精神的一種新闡釋和新追求。
三、巴斯女性意識局限性的辯證思考
許多批評家認為,巴斯早期的作品中有歧視女性的傾向,許多女性人物經常成為男性追逐理想過程中的犧牲品,結局悲慘。如命運坎坷的美杜薩、西比爾等,她們都是男性強權的犧牲品。美杜薩本來有“少女的驕傲”“花蕊般的美貌”“漂亮的卷發”,她的美麗使她的叔父海神波塞冬欲火難耐,并在雅典娜神殿強暴了她。但雅典娜卻懲罰受害者,讓美杜薩做了女妖,頭上長出了毒蛇,直到佩爾修斯砍下她的頭,她才重獲新生。西比爾仰慕柏勒羅豐,卻被他當成生日禮物送給他的哥哥德利亞德斯。這些女性面對命運的安排無能為力,只能成為受男性欺辱的對象。
其實,巴斯筆下這些女性形象的遭遇,會讓讀者心生一種對于女性的憐憫并對其給以更多的關注和同情。在巴斯之后的小說《最后的航行》)[7]中,也涉及命運悲慘的女性人物。萊利對巴斯進行采訪時,巴斯解釋了塑造這樣的人物的原因:《最后的航行》中,黛西·摩爾、茱莉亞、雅思敏等人的墮落和死亡令人難過,虛構這樣的人物,而不是借用生活中的原型,是不想因為她們的真實存在而傷心。巴斯不贊成以生活中的人物為原型塑造人物,因為他忍不住會想,某個可憐的人要被拖上絞架而后分尸[8]。可見,巴斯并不想以命運悲慘的女性作為戲謔對象,而是想用虛構的人物來烘托戲劇效果。這種虛構的人物既能觸動讀者,讓其心生同情和憐憫,又不至于讓他們對現實中的人物產生聯想,目的在于展現情理,而不在具體的某人某事。
另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女權運動浪潮中,性暴力、色情表演和色情作品等經常被女權主義者加以強烈譴責。有人認為巴斯在《客邁拉》中的性描寫低俗下流,應加以抵制。但是,《客邁拉》中并沒有性暴力和色情描寫,如上文中提到的,相關描寫只是就事論事,既沒有借助其對女性的身體進行猥瑣的嘲諷,也沒有過分強調那些易勾起男性欲望的女性特征,敘述語氣平和,把男女之間的性關系看作平常事。他對男性和女性的身體都有同等程度的大方描寫,作品并不是借“性”出位,為色情而色情。
但是,巴斯對女性的“反傳統”寫作,嚴格來說并沒有與傳統的男性思維劃清界限。因此,他的這些女性意識也不可能讓他完全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在以阿拉伯故事為基礎的小說中,國王仍然掌握著絕對的決定權;戲仿的英雄神話故事中,盡管雅典娜具有智慧和決定的權力,宙斯卻仍是萬物的主宰,女性人物依然無法脫離男性而享有絕對自由。
四、結語
巴斯在《客邁拉》中從男性和女性兩個視角對故事內容進行敘述,突出表現了其女性意識。他借用故事中的女性人物之口,為女性發聲,這是男性作家在女性人物寫作中的一種“反傳統”表現。巴斯筆下的女性人物,有自己的思想和個性,不消極地依附于男性,或盲目尊崇傳統的男權認知。通過對阿拉伯故事和古希臘神話的戲仿,他辯證地解釋了女性的權利與自由。不管巴斯在主觀上有沒有特意強調女性主義,小說《客邁拉》在客觀上都表現出了對女性敘事和思想意識的重視。通過對不同女性人物性格命運的講述,作家強調了女性的重要性,對美國女權主義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客邁拉》的故事體現了巴斯作為男性作家具有的女性主義意識,是男性作家對女性描寫和認識的進步,但同時也反映出他所認識的社會和時代的局限性。不管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女性要想真正取得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地位,道路依然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