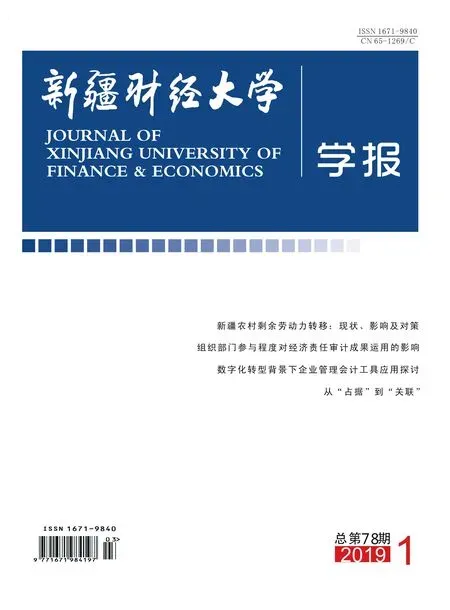從“占據”到“關聯”
——城市空間圖景的演繹與進化
張 莉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830012)
城市最初的樣貌如何?以今天的城市構造與生活節奏已難以想象舊時的城市。城市初建之時,空間概念已相伴而生,舊的街市巷道、古城的真實空間如何演變為今天的高樓林立、虛實交疊?人們感知城市,獲取城市空間為自身知識并進而視其為自己的“地方”,這期間經過了怎樣的變化?在城市空間的演變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和技術介于其中?人與城市的關系在技術介入后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這些問題似乎很難聯系起來,但筆者認為,討論人與城市的關系,必須要將問題放置于事物持續發展的脈絡里,在特定的語境和框架內,才能看到這些問題的參照與聯系。本文試圖描繪城市空間演變過程,并在這樣一個演變的脈絡里,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初步探討與回答。
一、城市空間演變的媒介技術邏輯
很長一段時間里,人是被當作使用工具的動物而認識的,這種對人的定義從某種程度上割裂了人與技術的關系。在現象學家看來,技術并非單純的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是世界構成的主要方式。劉易斯·芒福德認為,技術起源于完整的人與環境每一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技術是人的實現方式。海德格爾認為技術是現代性的突出現象,起著支配與提示的作用,是真理的開顯方式。麥克盧漢認為任何媒介對人和社會的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產生,我們的任何一個延伸,都要引進一種新尺度。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人對技術的認識過程,其實反映著人對自身的認識,也反映著人與技術、人與環境之間某種相伴共生的聯結。這種技術邏輯可以解釋城市空間的演變,其本身有一種內在動力,這一演變與媒介技術發展恰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媒介既呈現著實體空間也創造著新的空間,拓寬并豐富了人對空間的感知。
(一)身體占據的空間與古代城市的出現
人的身體是最直接的媒介,人與外部環境交換信息,獲取對周邊環境的掌控,首先是通過身體。
嬰兒在爬行和翻身的過程中可以感知距離、認識空間,因此人類對空間的最初感知來自于身體。諸如要步行多遠到達河邊,爬上多高的樹能看到多遠的地方……人類在不斷的訓練中拓展著空間概念。但空間本身卻是不斷變化的,因而段義孚說人類智能主要表現在對空間變化的適應上[注]詳見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所以,人們對空間最初也最本質的理解是,空間是一種秩序,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秩序。
那么,作為秩序的空間是如何被感知、被確立的呢?劉易斯·芒福德在談到古代城市的起源與本質時曾指出,古代城市大多始于一些神圣的地點,因其能令散布于各地的人回到這些地點進行祭典儀式,但不論在什么地方,“城市的興起都伴隨著大力突破鄉村的封閉和自給自足”[注]詳見劉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嶺和倪文彥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和105頁。。由此可見,古代城市的誕生有著鮮明的空間拓展的特征,即對封閉的鄉村的突破,這種突破包括地域與空間。古代的社區或鄉村過于封閉穩定,不易接納新鮮事物及其他生活方式,城市由此成為解決此類問題的最好方式。城市空間的拓展性,決定了它可以對各類人物給予接納與包容,陌生人、流浪漢、商人、逃難者、奴隸等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空間,因而城市的“容器”功能成為了其最主要的功能。芒福德因此說,城市是“貯藏庫、保管者、積攢者”,并且“這種為著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大社區邊界的濃縮作用和貯存作用,便是城市發揮的獨特功能之一,一個城市的級別和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這種功能發揮的程度”[注]詳見劉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嶺和倪文彥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和105頁。。作為“容器”的城市首先具有物理空間的可創造性和伸展性,一個實在的空間確立著身體居住的安全感與穩定感。此時,與廣闊零落的鄉村地區相對,城市的建筑、街道、市場、標記指示,都提供了這種空間的參照與邊界,使空間感覺成為人的身體適應與感知,成為具體的身體規范與熟悉程度,最初的客觀秩序也由此建立。
那么,人又是如何獲得空間能力,即把對空間的識別能力變為一種知識呢?或許我們天然會以為這是依賴于人的視覺能力,但事實并非如此。實驗表明,人的空間能力是在一系列的學習活動中發展出來的觸覺動覺模式。人們去往一個目的地時,總是由對近處的方向和判斷等經驗逐步擴展到遠處。比如我們走到一個地標時,根據最近的經驗就會知道下一步往哪個方向走,目標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地標或標識所串聯起來的。所以,當一個陌生人進入一個城市時,總是會以他居住的地點為中心,通常以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為主,慢慢將熟悉的地域擴大。當我們對空間完全熟悉的時候,它就變成了屬于我們的地方。在此,城市為人們提供了發展空間能力的場所。
人們感覺到的空間并非空洞無物,而是充滿了各種約定俗成的意義,也就是物理空間中被人感知到的等級、權力、象征等意義,但對其如何劃分與呈現,實則歸因于人的建構。“由人與世界抽象出的更簡單的思想,即身體與空間,前者不僅占據了后者,而且通過意義控制和規范著它,身體是活生生的身體,而空間是由人類建構的。”[注]詳見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空間中的客觀參照點、地標和主要位置,要符合人類身體的意圖,人在其所掌控的空間中才能感覺到輕松自如。在中國古代建筑中,尤其以北京的都城為代表,皇帝所居住的位置,以及坐北朝南的傳統方向,都是對中心的追求。“從午門進入皇城后,人們會因里面的地面和建筑都沿南北軸線方向修建而感到震撼……本來,紫禁城代表的是皇帝居所,表現的是天體最上方的北極星,即皇帝位于由170多顆星辰組成的星座(紫微垣)中央的情景。”[注]詳見斯波義信著、布和譯《中國都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因為天壇是祭天的地方,因此其外形呈圓筒形(天圓)。壇基也呈圓形,每部分都是9級臺階,是共計3屋(天地人)的設計形式。3層基壇各層的欄桿數都是360根,代表了一年的360天及360度的圓。這些設計都讓人們切身感受到天子是代表天來統治包括首都在內的天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以及廣闊的宇宙。”[注]詳見斯波義信著、布和譯《中國都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頁。這種人為的主觀秩序,規定了人的社會性的生活狀態,它與客觀秩序一道,用 “占據”空間的方式將人納入到城市空間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大眾媒介的傳播與工業化城市空間的形成
“城市空間”這一概念誕生于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西方現代城市化運動。這一不同于鄉村和古代城邦的新型生存空間,體現了信息流動打破空間障礙的質變,從而培育出對空間的興趣和關注[注]詳見殷曉蓉著《傳播學視野下的“城市空間”》,原載于《復旦學報》 2013年第5期,第136~142頁。。
新聞紙出現后,人們開始意識到傳播與城市空間有著內在而密切的關系。首先是因傳播的信息是在空間傳遞與發布的;其次是大眾媒介及其傳播過程本身在創造著超越物質空間之外的某種“媒介空間”,這種看不見卻能感知到的空間,構建起人們精神世界的獨立領地,在討論公共事務以及對民族、國家的形成和認同中開始發揮作用。因此,加布里埃爾·塔爾德認為,在現代傳播媒介產生對社會的聯結作用之前,傳統社會是依靠村落、行業、家庭這些基本單位進行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的;而在現代城市空間中,卻是書籍、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等媒介,使“非常相像的個體”組成集群,并使之“不必謀面或認識就形成了緊密的聯系”[注]詳見加布里埃爾·塔爾德著、特里.N.克拉克編、何道寬譯《傳播與社會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39 頁。。哈貝馬斯也認為因為大眾媒介的傳播,構筑出了一個可以討論公共議題的“公共空間”。他認為的公共空間由咖啡館、出版機構、大學、圖書館等構成,而在咖啡館中舉辦的沙龍尤以閱讀報紙為中心,這個空間呈現的便是“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核心的公共交往”[注]詳見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19 世紀中葉后,城市人了解外在空間和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大眾媒介,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是必要的生活資料,并且成為了城市空間的重要活動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造紙技術帶來的廣泛影響,“造紙工業靠近市區,因為在這里,市場需要紙,造紙用的碎布也貨源充足、價格低廉。造紙工業的發展使寫作從修道院向都市轉移。接著,印刷業促進了都市化的趨勢”[注]詳見哈羅德·英尼斯著、何道寬譯《帝國與傳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2 頁。。20 世紀初,面向大眾的雜志有了各種各樣的類型,雜志雖然晚于報紙出現,但卻集中顯現了城市空間的各種要素,而以“專門化”為特征的“城市雜志”,其內容和發行主要限于城市區域,“側重于提供城市生活、生活方式、娛樂選擇以及社區需求和問題等方面的信息”[注]詳見薩梅爾·約翰遜和帕特里夏·普里杰特爾著、王海主譯《雜志產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8 頁。。在對這些城市雜志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印刷媒體正是通過閱讀的方式展開對空間限制的“突破”和“征服”,但這種“突破”仍然是緩慢的“有限突破”,直到電報的發明,現代電子通訊技術真正打破了空間障礙而實現“瞬間傳播”,成為人類歷史上的首次并最終成為“確定世界遠距離傳播界限的標志”[注]詳見阿芒·馬特拉著、陳衛星譯《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 頁。。
在此,大眾媒介不僅超越了作為首要功能的跨越空間傳播信息的任務,也因其技術本身開辟了傳播空間的研究,實現了對城市空間認識的突破。與身體占有空間以及以象征性劃分空間的等級不同,大眾媒介所建構的傳播空間通過符號的方式進行空間生產,城市空間是構成“象征符號”的主要公共領域。城市的交通信號燈,街頭、電視、刊物上大量出現的圖片、廣告、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作品,商場櫥窗中的裝飾物,商業區內餐廳與咖啡館的裝修風格等,這些符號背后的能指,占據著場所,也表征著場所,并借助符號生產著空間。空間符號因此具有了替代性和生產性。替代性就是當“‘真正的’刺激物在實物形態上并不在場時產生復雜行為的能力”,而生產性是指“掌控符號的人有能力在有限的符號元素基礎上生產無數個表征”[注]詳見詹姆斯·W.凱瑞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頁。。因此,符號的空間是象征的,象征空間的特點在于同構性,在于一旦兩個事物之間建立起同構關系,那么不管它們之間在時空上、在分類上懸殊多大,都將被看成是本質相同的。
(三)電子媒介與流動的空間
齊格蒙特·鮑曼在對現代性的研究中涉及流動的空間,她引用塞納特對城市的定義,認為城市是“一個陌生人可以相遇的聚居地”,從這個角度出發,城市就是人們持續經過的場所。城市中擁有很多公共空間,如廣場、機場、旅館等,但這只是人們禮貌相遇又漠然分開的地點,而大型的購物天堂,也只是福柯意義上的小船,是一個漂移的空間,孤獨而自我封閉。與此同時,城市里還存在著許多人們未曾到達或感覺已經消失了的地方,但實際上它們卻是在地圖上存在著的“虛幻空間”。人們分享并使用著空間,公共空間似乎是固定的,但卻在人的來來去去中被賦予了流動的本質。鮑曼說,因為交通工具的速度越來越快,時間被壓縮的時候,意味著能夠到達更遠的空間征服更大的空間,而沉重的、越大越好的現代性因此轉向輕盈流動的現代性。“空間被控制首先來自于時間被駕馭,并使它內在的推動力變得無效,簡言之,即是時間的一致性和協同性。”流動的空間,來自于“每一時間單位日益增長的吞沒空間的能力”[注]詳見齊格蒙特·鮑曼著、歐陽景根譯《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80~181頁。。在流動的空間中,時間與空間具有了同構性。
鮑曼的流動的空間是在現代性研究層次上的解釋。從媒介角度來看,流動的空間也指電子媒介所建構的某種“虛擬空間”。互聯網的誕生不僅意味著信息傳播與共享方式的變革,也意味著全新社會結構的出現。“在新技術范式的基礎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一種由電子通信技術組成的結構——具有發展動力的社會網絡。當然,它是技術,但它也是網絡化社會結構和蘊含在網絡化邏輯中的具體關系組合。”[注]詳見《信息論、網絡和網絡社會: 理論藍圖》,原載于曼紐爾·卡斯特主編、周凱譯《網絡社會:跨文化的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 46頁。卡斯特指出,這種社會網絡的結構是網絡邏輯和具體關系的組合,因而網絡社會是圍繞信息、技術、資本等的流動而被建構起來的,網絡社會催生了新的空間邏輯,卡斯特將其稱為“流動空間”。“具有完整界定的社會、文化、實質環境和功能特征的實質性的地方,成為流動空間里的節點和中樞。”[注]詳見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譯《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389頁。
在這個流動空間里,節點成為了關鍵詞和新動力,打破了整體與中心的限制,所有進入網絡和網絡社會的機構、企業、個人都是網狀構造中的組成部分,各節點的運動促成了網絡社會的流動,在廣闊的互聯網領域內,大量節點不斷地涌入,不斷地生產與消費,又在不斷地消失,像永不停止的星系運動。它們共享著某一時間里的平行空間,又隨即消解著這一空間;它們即時創造著某種互動通聯的空間,又隨時終結著這一空間。流動性和不穩定性恰恰成為一種常態性與穩定性,因而其所形成的空間結構既非均質也并不對等,亦無法呈現明顯可描述的規律性,并且永遠處于流動之中。“這樣一個流動的空間是一個混合物的世界”[注]詳見約翰·厄里著、李冠福譯《全球復雜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79~80頁。,在這樣的流動空間里,其特征是“流動空間沒有明晰的構造,沒有明確的中心與邊緣之分,而是節點和邊際隨時變化著的、半透明的拓撲空間”[注]詳見馮雷著《理解空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頁。。
那么流動空間中的非均質性又是如何發生的呢?約翰·厄里認為是通過節點對信息的處理來實現的。“各節點通過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更有效地處理這些信息來增強自己在網絡中的地位;而如果它們的表現不佳,其他關節點則會把它們的任務接過……從這個意義上說,重要節點并不是網絡中心點,而是網絡中起轉換作用的關節點,這些‘轉換者’遵從網絡運行邏輯,而不是命令邏輯。”[注]詳見約翰·厄里著、李冠福譯《全球復雜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 頁。流動空間能揭示電子媒介時代城市空間的本質特征:首先,流動是城市空間運動的動力,如果停止流動,那么這個城市空間就不會存在;其次,局部流動的緩與急也解釋了全球性空間為何是不平衡的。
(四)“融合媒介”與關聯空間
流動的空間和關聯空間都與電子媒介技術緊密相關,前者是從電子媒介特征的角度出發來認識空間,而后者則是從空間角度出發來認識的結果。
什么是關聯空間?麥奎爾在《媒體城市》中指出,關聯空間是指社會關系的地平線在其間變得大幅開放的當代狀況,當媒體變得越來越有機動性、可測量性和互動性,媒體城市中社會經驗的新模式就具有了關聯空間的特征。高度開放帶來的是構筑跨越空間和時間的社會關系的新自由,這種新自由無法被拒絕,具有自反性和現代性[注]詳見Couldry Nick 和Anna McCarthy,Media 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這里對關聯性的理解是指一種非結構不可預測的可能性,指某兩種或多種元素的接觸碰撞所觸發的新形態、新表征和新感知等。這種不同元素的接觸類似廣義上的“融合媒介”概念。在今天的城市中,城市居民拓展出了更大的身體感知空間——地下、樓群叢、商業區、廣場、站臺等,在身體的移動中與各種形態的空間發生著穿越、聚合、離散,實現著德·塞托式的散步,包括著德·塞托式的散步,又顛覆著德·塞托式的散步。關聯空間還表現為個體或群體在空間元素的添加和空間創造想象上的自由發揮與特立獨行,如主題電影院、咖啡館,提供餐飲、網絡、觀影及交流區的書店,古代建筑群里的現代商業街,北京798藝術中心各個時期各種類型的藝術空間呈現,等等。“城市不再受制于高高在上的專家,而是變成了可以隨意重置的個人愿望的動態網絡化表達。從空間的角度來看,范圍從房間到城市的老式建筑結構將失去其穩定的輪廓。”[注]詳見斯科特·麥奎爾著、邵文實譯《媒體城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和139頁。基于此,“電子媒體的意義在于其自身的空間屬性以及由此開拓、重塑出更多空間的可能性”[注]詳見斯科特·麥奎爾著、邵文實譯《媒體城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和139頁。。“而空間的意義在于承載于實踐或事件中又帶有空間性所具備的一種‘潛能’,存在于人們‘行動的時刻和呈現的選擇’當中”[注]詳見Jiménez Alberto Corsín,On Space as a Capacity。。
電子媒體本身也在不斷地開拓相關的空間,人們在互聯網平臺上觀看到的直播,以及很多網絡游戲中設置的由真人扮演的角色,在進入到游戲空間中時,已很難分辨網絡空間與真實空間的邊界。在這種情形下,關聯空間擁有了超空間的特征,超空間的顯著特征是空間的非連續性和事物的虛擬性,“我們習慣于認為具有時空統一性的物體或事件才是真實的,但是在超空間中,由于時間與空間分離了,所以物體或事件不具有時空統一性,因此我們便覺得它們是不真實的,或者說是虛擬的”[注]詳見馮雷著《理解空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頁。。電子媒體使時間不斷被加速而空間不斷被壓縮,人們認識的空間形態和劃分空間形態的標準已經開始改變,建構、參與及分配空間的要素越來越復雜多元。超空間阻斷了人對空間的感知與定位,一旦置身其中,人們便無法以感官系統來組織空間體系。“人的身體和他的周遭環境之間的驚人斷裂,可以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征,它意味著我們當前思維能力是無所作為的。”[注]詳見詹明信著、陳清僑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97頁。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周遭世界無從掌握。按照唐·伊德的解釋,在詮釋學關系中,世界首先被轉化為文本,而文本是可讀的。因而借助詮釋學關系,“我們仿佛能夠將我們自己置身于任何可能的不在場的情形中理解”[注]詳見唐·伊德著、韓連慶譯《技術與生活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7和72頁。。
然而詮釋學的文本關系也許需要重新認識,關聯空間的另一種形態可能更值得我們思考,即在人工智能技術支持下,人的身體可以和機器相結合并將拓展出更廣闊的關聯空間,“它是另一種秩序,是我們語言的附加物,是數字的輔助語言,是洞察、剖析和揭示事物的秘密、隱含的意圖和未用的能力的方式”[注]詳見Emmanuel Mournier,Be Not Afraid。。
約翰·厄里也描繪了這種人與電子產品的混生狀態,“這些居住機器是迷你型的、私人的、移動的,而且還依賴‘數字能’。……這些居住機器渴望擁有自己的行為方式,小型化以及輕便化,并且想展示自己與人的身體之間的相互交織的關聯性。……這些居住機器使得‘人們’能夠更迅速地在空間中移動,或者停泊在某一個地方”[注]詳見約翰·厄里著、李冠福譯《全球復雜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159頁。。在這樣的機器秩序圖景中,機器成為人的一部分,人也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人與機器互為功能互為對象,機器與人的共存使人進化為一種“新物種”,虛擬與現實的概念被消融,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進化為一種新的空間形態,被分離的時間與空間再次交織纏繞,人存在于時空交織的網絡中。
二、空間演變中人與城市的關系
人創造了城市空間,還是城市空間塑造了人?在城市空間演變的脈絡里,我們可以梳理出人與城市的伴生關系,城市最初的形成,為拓展人的空間感知能力、為人與空間知識的互動進而將其轉化為人的空間智能提供了物理基礎。而在這個過程中,城市空間的豐富性不斷地滿足著技術發展的需求,技術促進了城市空間的演變以及人們對其所進行的探索與研究。媒介技術的發展,在人對空間認知的轉變以及城市空間研究的豐富性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空間的形態并非依照先后順序相繼發生,如流動的空間和關聯空間可能是重疊的,其區別在于內在的深層形態。電子媒介不僅提高了空間形態的發展速度,也加速了空間形態的進化與裂變,拓展了空間研究的深廣領域與無限可能,但城市空間不管如何演變,仍然有一些可以探討的基本意義。
(一)技術以中介的方式參與空間的演變
唐·伊德在探討人與技術、人與工具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具身”關系的概念。所謂“具身”關系是指“借助技術把實踐具身化,這最終是一種與世界的生存關系”[注]詳見唐·伊德著、韓連慶譯《技術與生活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7和72頁。。比如,不借助任何工具時,我們的視線能夠看到的距離,我們的身體能夠感知到的方向,前后左右等都因具體物體的參照而限定,所以月亮、山脈、遠方等距離或者方向都是穩定的體驗。但人身體的空間感覺是可以借助“人工物”得以拓展的,比如望遠鏡發明后,通過望遠鏡,月亮被拉近到我們眼前,借助工具改變了之前我們對月亮的距離感知。也就是說,空間含義的每一層面都發生了改變。哥倫布的航海是借助把地圖與航海圖上的位置讀成我們身體感知的位置得以實現的;同理,現在的導航技術不僅有平面的方向、距離等,也有俯瞰式的,是多維立體的,使我們對上下左右復雜疊加的空間可以獲得錯落感知,有了比之前更深刻的體驗。
因此,通過“具身”的方式,媒介或媒介技術作為一種中介在城市空間的演變中發揮著作用。在這里對于中介的理解至少應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媒介介質本身,信息得以傳遞,媒介處于觀眾與世界之間,實現著事件發生時超地域的“共同觀看、傾聽與感受”。二是媒介與人的共在關系,使得中介物具有象征性,由于物體介入了人的交流過程,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有可能通過物體的中介來進行,“于是身體的直接交流轉變為依賴于中介的間接交流,這樣,充當中介物的物體便在功能性之外具有了象征性”[注]詳見馮雷著《理解空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頁。。中介是一種能夠把彼此相連的方式與可能,通過中介的方式,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城市空間演變的來源。
(二)關系生產是城市空間的核心
列斐伏爾在空間生產中提醒我們重視空間中的關系生產,社會空間“不僅僅是一個事物、一種產品,相反它不但包容了生產出來的事物,也包納了事物的共時態的、并存不悖的、有序或無序的相互關系”[注]詳見陸揚著《空間何以生產》,原載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198~210頁。。媒介技術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城市構成的基本要素,造就了全新的空間研究的領域與版圖,正是基于此種情況,米切爾才說現代城市是一座“比特之城”,這樣的城市“較少依賴物質積累,而更多地依賴信息的流動;較少依賴地理上的集中,而更多地依賴于電子互聯;較少依賴擴大稀缺資源的消費,而更多地依賴智能管理”[注]詳見威廉·J·米切爾著、吳啟迪等譯《伊托邦——數字時代的城市生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約翰·厄里也說電子媒介發展了諸多網絡構造了諸多“關系”,同時也只有“關系”才是根本[注]詳見約翰·厄里著、李冠福譯《全球復雜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空間構成因素的變化,信息流動、電子互聯、智能管理等,將人與電子的關系納入城市空間的領域與層次中,那么如何理解新型電子媒介與人構造出的關系呢?或許克勞斯·布魯恩·延森的思路會帶來更多啟發。延森將人的身體、大眾媒介及數字元技術視為三重維度的媒介,他認為以數字化的元技術為邏輯,三重維度的媒介交融在一起,會整合為全新一代的媒介[注]詳見克勞斯·布魯恩·延森著、劉君譯《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媒介既不能與實在割裂,也并非受到實在的推動而發展,它們的交往實踐構成我們感知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方式,亦成為我們擁有‘世界’的基礎。”[注]詳見黃旦和李暄著《從業態轉向社會形態:媒介融合再理解》,原載于《現代傳播》2016年第1期,第13~20頁。人與媒介、人與世界這種多元交織、相融一體的關系,恰恰是當下城市空間的屬性,也是空間研究的核心意義。
(三)人是城市空間研究的落腳點
空間的物質形態在發生變化,但單純的物理空間本身并不構成城市與國家,西美爾認為“社會性”才是社會空間的真正意義,城市的凝聚力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而非物理的和規模的,“單純的地理要素不能構成國家和城市,各種精神力量和心理力量才可以建成它們”[注]詳見蓋奧爾格·西美爾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這種認識與芒福德不謀而合,其認為城市是為使人類的生活更美好而存在,這也是城市存在的根本意義,因此城市不是一種實體存在,而是一種文化存在。
在城市發展史上,近現代大城市的發展崛起與大工業生產和工業化進程緊密相關,大工業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空間集中促成了現代工業城市的誕生與發展。在這種邏輯關系下,“工業城市巨大的物質生產力,表征著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向著擺脫人的依賴的新的依賴狀態的邁進”[注]詳見孫江著《“空間生產”——從馬克思到當代》,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30頁。,但同時,工業化生產方式下的空間延伸又造成了空間的新的斷裂與差異,“它冷酷而又堅決地把原本黏合成一個整體的空間撕裂開來,把一部分人變為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成鄉村動物,用其固有的、與生俱來的交往理性銷蝕農業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造就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注]詳見崔波著《芻議城市傳播研究的空間進路》,原載于《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第2~7頁。。不可否認,類似工業化的現象既是城市發展的動力,也是城市存在的問題本身,甚至在今天的有些時候,光怪陸離的城市空間景象與美麗鄉愁的鄉村想象都是被作為對立面來看待的,城市空間的這種斷裂性提醒我們,空間研究并不是脫離人的純粹與虛擬的空間研究,就如芒福德所言,應該是新型的文化現象的研究。
那么,作為文化現象的人工智能及電子媒介技術帶來的全新的空間狀態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新媒介帶來的不僅是信息傳播的速度與范圍,還是標準、規則、感知比率等的全新塑造[注]詳見麥克盧漢關于“媒介即訊息”的觀點。。全新的空間感提供著新的尺度,激發出人與城市相處依存的新形態,現代城市聚焦了大量的人群,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物質產品,有序而規則運行的系統化生活,將每一個個體附著在電子關聯的大網上,城市居民的距離與彼此的依賴感前所未有地更緊密、更強烈,但人與人心理上的感覺也必然更親近、更熱情了嗎?城市依然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家園嗎?從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發展是合規律的發展,總體趨勢符合人性并有利于人性發展,城市的空間生產是人與城市和諧共生的要義,也因此,只有建立在此種認同基礎之上展開的空間研究,才能在城市如何使人更美好的問題探索中有扎實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