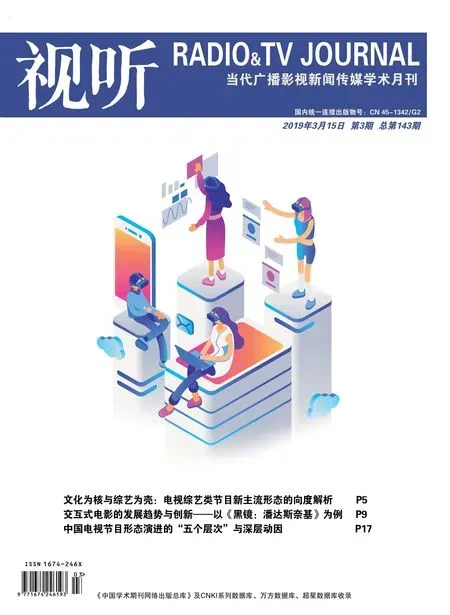論奧斯卡表演類獎項的發展軌跡
□ 王曉彤 居瑤
奧斯卡獎最早的獎項設置中,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都出現在了獎項名單之中。第一屆獲得最佳男主角獎的是埃米爾·雅寧斯(Emil Jannings),而獲得最佳女主角獎的是珍妮·蓋諾(Janet Gaynor)。最初的奧斯卡最佳男女主角獎獲獎人員并不是憑借唯一一部影片獲得提名。前者以 The Last Command、The Way of All Flesh兩部影片中的精彩表現獲獎;后者以7th Heaven、Street Angel、Sunrise∶A Song of Two Humans三部影片獲得了殊榮。在最初三屆奧斯卡獎評選中,一個演員可以憑借多部影片獲得提名。而在1930年第三屆奧斯卡獎舉辦之時,學院改變了規則,開始以一部影片的表現來提名獲得表演獎項的演員。這個變化既是學院完善評獎規則之舉,也是奧斯卡獎評選中,以影片為參賽基本要素的一種體現。1937年的第9屆奧斯卡獎新增了兩個獎項:最佳男配角獎和最佳女配角獎,提名的數量也限制在5部影片/演員,這個規則沿用到了今天,構成了一套完善的評獎系統。
一、成立初期:以傳記片為主,獲獎影片類型多樣
在《海斯法典》出臺的1934年之前,表演獎的獲獎影片類型多樣,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奧斯卡獎頒獎側重于傳記片。如兩位英國演員分別因扮演英國首相和英國國王獲得了獎項,這種帶有歷史劇風格的傳記影片由于在突出人物形象、展現演員演技方面具備先天優勢,在此后的奧斯卡表演類獎項中屢屢獲得成功。但除了傳記片以外,一些類型片也成為了演員們展現演技的角斗場。弗雷德里克·馬奇在《化身博士》中一人分飾杰克爾醫生和海德先生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導演魯本·馬莫利安極具表現主義的電影風格中擯棄了以往臉譜化的表演,將人物的雙重性出色地表現了出來。
1934年—1941年是奧斯卡獎從《海斯法典》的奠定到二戰爆發的時間段。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基本保持了積極樂觀的心態,在銀幕上也保持了較為保守的姿態。1934年弗蘭克·卡普拉執導的浪漫喜劇《一夜風流》不但使導演本人在電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跡,男女主演克拉克·蓋博、克勞黛·考爾白也分獲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的桂冠。1940年上映的《費城故事》同樣也是一部浪漫愛情喜劇片,詹姆斯·斯圖爾特在評選中戰勝了同樣獲得提名的卓別林(《大獨裁者》)、亨利·方達(《憤怒的葡萄》)、勞倫斯·奧利弗(《蝴蝶夢》)、雷蒙德·馬西(《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等諸多強勁對手。在最佳女演員方面,1937年第9屆奧斯卡獎中,路易絲·賴納憑借《歌舞大王齊格飛》獲獎,與商業類型片相比,大部分獲獎的影人都出演了戲劇風格強烈的電影或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傳記片。不少影片和著名的角色形象雖然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提名名單卻并未獲獎,例如《亂世佳人》中克拉克·蓋博扮演的白瑞德、《史密斯先生游華盛頓》中詹姆斯·斯圖爾特扮演的杰弗森·史密斯。在黑幫片《疤面煞星》中嶄露頭角的保羅·茂尼在《巴斯德傳》中扮演了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因此,奧斯卡表演類獎項并不是完全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進行表彰,其中綜合了各大電影制片廠之間微妙的政治平衡,以及業已成名的明星演員之間的角力。顯然,類型電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得到奧斯卡獎評選委員的認可要比得到市場認可顯得更加困難,這也反映出奧斯卡獎評選自身的保守性。值得一提的是,海蒂·麥克丹尼爾因在《亂世佳人》中出演奶媽瑪格麗特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這也是非洲裔美國人第一次獲得奧斯卡獎。
二、戰后好萊塢時期:方法派盛行
二戰及戰后是古典好萊塢由盛轉衰,進而變革的年代。隨著方法派演技逐漸進入好萊塢,美國電影在表演上日益進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論基礎,涌現出一大批演技出色、氣質獨特的明星演員。馬龍·白蘭度、威廉·霍頓、格里高利·派克、查爾頓·赫斯頓、伯特·蘭卡斯特等當時的新生代演員先后獲得了奧斯卡獎,英格麗·褒曼、奧黛麗·赫本、格蕾絲·凱莉、伊麗莎白·泰勒等巨星的表演也備受肯定。這些明星不僅是當時的票房保證,在獲獎影片的演技上也近乎無可指摘。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傳記片在評獎中不再像之前占據了較大比例,戰爭片、史詩片、歌舞片等不同類型電影均有角色獲獎。由于戰后美國戲劇創作的發達,一批劇作家如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的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這些戲劇改編電影不但擁有內涵較為豐富的主題,且更加側重于塑造性格復雜的角色,為演員出色的表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費雯·麗、雪莉·布思、伊麗莎白·泰勒獲獎的影片都有戲劇改編的作品。
戰后好萊塢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冷戰格局的形成,美國擴大了其全球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力,這也使得奧斯卡獎的國際性大大增強。除了在1957年正式設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在奧斯卡表演類獎項中,外國演員的加入豐富了好萊塢電影的人物形象,不少外國演員以全新的角色形象讓觀眾眼前一亮。安娜·馬格納尼在羅西里尼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名作《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嶄露頭角,后被邀請主演了田納西·威廉斯的戲劇《玫瑰紋身》改編的同名電影,飾演的意大利移民媽媽時而陰郁時而奔放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更有甚者,同樣來自意大利的女星索菲婭·羅蘭憑借《烽火母女淚》成為了有史以來以非英語影片獲得最佳女演員獎的第一人。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種族平權運動的興起,有色人種的銀幕形象日益受到重視。好萊塢作為一個政治傾向較為明顯的社會群體,也自然對社會思潮有所回應。1963年,西德尼·波蒂埃憑借在電影《原野百合花》中的表演成為第一位贏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黑人演員。
三、新好萊塢時期:與各項民權運動同步的評選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隨著新好萊塢時期的來臨,“作者電影”的概念在好萊塢逐漸普及,導演的個人風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這一時期依然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喬治·斯科特主演的《巴頓將軍》盡管是一部傳記片,但經過編劇、導演和主演的通力合作,將巴頓將軍這一具備復雜人格的歷史人物全方位地展現了出來。馬龍·白蘭度出演《教父》之后,徹底擺脫了事業低谷,在中年時期迎來了演藝生涯新的高峰。而杰克·尼克爾森、達斯汀·霍夫曼等演員則在類型片的基礎上貢獻了更為細膩的表演,進而得到了獎項的肯定和表彰。一些在電影史上地位舉足輕重的電影和它們的男女主角并未獲獎,如《邦尼與克萊德》《畢業生》《出租車司機》,從另一面反映出學院評選獎項時展現出一定的保守性和滯后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保守主義的盛行,在銀幕上也有一定體現。《金色池塘》用一出家庭之間的溫情故事,緩解了兩代人之間的矛盾,這部電影在當年的評獎中大放異彩,獲得了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劇本在內的多個獎項。現實中的方達父女這對特殊的明星父女一度反目,而作為女兒的簡·方達主動策劃了這部影片,為從未獲得奧斯卡影帝的父親爭取實現最后的心愿,這在充滿了沖突和撕裂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極具象征意義,代表了渴望安定、互相妥協的社會心理。隨著《甘地傳》主演本·金斯利的獲獎,一些表現二十世紀世界各地歷史人物的傳記片接連出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奧斯卡獎發展進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最佳女主角獎更多考慮了性格堅強的女性形象,如朱迪·福斯特(《沉默的羔羊》)、霍利·亨特(《鋼琴課》)、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冰血暴》),隨著性別平權意識的新一輪熱潮,美國電影在二十世紀末迎來了新一輪變革。
1999年第72屆奧斯卡獎分別將影帝和影后頒給了凱文·史派西的《美國麗人》和希拉里·斯萬克的《男孩別哭》,巧合的是兩部影片都有著同性戀元素。《美國麗人》以家庭情節劇的形式揭示了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分崩離析的過程,而主人公的死來源于鄰居的恐懼同性戀的心理。《男孩別哭》改編自真人真事,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不一致的主人公遭遇了現實社會的殘忍對待。這兩部電影的獲獎標志著好萊塢電影在性別議題上有了新一輪突破。2006年獲獎的《卡波特》和2009年獲獎的《米爾克》將視角對準了不同領域中具有同性戀身份的歷史名人的生活,李安執導的《斷背山》雖然沒有獲得表演類獎項,但也收獲了男主、男配、女配三項提名。
四、新世紀:傳記片回潮
進入新世紀的另一個回潮乃是傳記片的重新崛起。最佳男主角方面,2002年的《鋼琴家》、2004年的《靈魂歌王》、2005年的《卡波特》、2006年的《末代獨裁》、2008年的《米爾克》、2010年的《國王的演講》、2012年的《林肯》、2013年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2014年的《萬物理論》、2017年的《至暗時刻》都有真實的故事原型,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傳記色彩。最佳女主角的傳記片相對男主角較少,但也有2002年的《時時刻刻》、2003年的《女魔頭》、2005年的《與歌同行》、2006年的《女王》、2007年的《玫瑰人生》、2009年的《弱點》、2011年的《鐵娘子》等帶有傳記元素的作品。由于傳記片所述傳主一般廣為人知,其自身命運有著一定的傳奇色彩,加上這類影片常有明星助陣,使得傳記片在制作、發行乃至評獎等諸多環節中備受各方青睞。但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當下的好萊塢電影創作越來越缺乏優秀的原創故事和原創人物,而更多依賴于明星和人們熟悉的題材。明星演員在挑選劇本時慎之又慎,為了能夠突出自身在作品中的絕對主角地位,會有意識地將這一類“大男主”或“大女主”電影作為自己工作的優先選擇,以便沖擊影帝或影后的榮譽。這使得奧斯卡表演獎的評選存在著套路化的風險,難以選拔出在藝術上有創新意義的作品和表演創作。
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到,在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的評選中,一些影片中過目不忘的角色得到了學院的關注。如賈維爾·巴登在《老無所依》中扮演的冷血殺手Chigurh、希斯萊杰在《蝙蝠俠:黑暗騎士》中扮演的小丑、克里斯托弗·沃爾茲在《無恥混蛋》和《被解救的姜戈》中分別出演的納粹軍官和善良牙醫,以及安妮·海瑟薇在《悲慘世界》中出演的芳汀。縱觀奧斯卡表演類獎項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的電影創作對演員和明星產生的影響,而優秀演員的表演也常常超越了影片本身,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如何排除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使奧斯卡獎能夠真正提升表演創作的品質,而非形成庸俗化的套路,是今后奧斯卡獎必須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