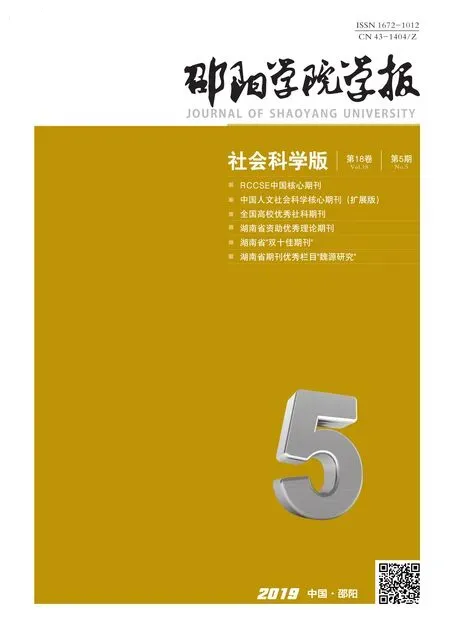“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邏輯:跡象、成因及適用場(chǎng)域
——以司法實(shí)踐中的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為樣本
袁翠嬋, 聶昭偉
(1. 邵陽學(xué)院, 湖南 邵陽 422000;2. 浙江省高級(jí)人民法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傳統(tǒng)罪刑關(guān)系理論認(rèn)為,犯罪與刑罰之間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引起與被引起的“單向制約”關(guān)系。[1]23為此,“司法人員必須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時(shí)間順序,不能把量刑提到定罪之前。否則,后果不堪設(shè)想”[2]。但是,在面對(duì)難辦案件(hard case)時(shí),司法人員時(shí)常會(huì)反其道而行之,沿著“由刑及罪”的路徑逆流而上。[3]30-35在此基礎(chǔ)上,有學(xué)者遵循逆向司法邏輯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量刑反制定罪”說。[4]可是,這個(gè)觀點(diǎn)提出后,“隨即遭致理論通說的當(dāng)頭棒喝,認(rèn)為這種離經(jīng)叛道的做法是一種中國(guó)式司法的奇技淫巧,是對(duì)罪刑法定原則的反動(dòng)與背叛,必須予以拋棄”[5]。面對(duì)來自于理論“專業(yè)槽”疾言厲色的呵斥,這種逆向司法邏輯像受驚的魚兒一樣即刻沉入水中,秘而不宣地散見于刑事司法實(shí)踐的各個(gè)角落。[6]德國(guó)哲學(xué)大師黑格爾之“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xiàn)實(shí)的”[7]43-58所言極是。那么,作為一種隱性刑事裁判知識(shí),逆向司法邏輯究竟存在于哪些場(chǎng)合?其產(chǎn)生的背景與成因又是怎樣的?能否為其尋找到一些知識(shí)上的根基,進(jìn)而可以生成一種定罪的新理論?針對(duì)上述問題,筆者擺脫形而上的理論研究范式,俯下身來從一系列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出發(fā),試圖讓這種只可意會(huì)不能言傳的“隱性知識(shí)”浮出水面,外化為一種可以言說的顯性知識(shí),使其能夠名正言順、揚(yáng)長(zhǎng)避短地服務(wù)于當(dāng)下中國(guó)的刑事司法實(shí)踐。
一、“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邏輯在實(shí)踐中之體現(xiàn)
通過長(zhǎng)期研究我國(guó)的刑事司法實(shí)踐案例,不難發(fā)現(xiàn),盡管常規(guī)案件的定罪問題可以遵循“由罪及刑”正向路徑來解決,但是在“面對(duì)那些是罪還是非罪,是此罪還是彼罪的案件的時(shí)候,法官不會(huì)再局限于犯罪構(gòu)成,而是反向思維進(jìn)行考量。也就是基于量刑的妥當(dāng)性反向考慮與之適應(yīng)的構(gòu)成要件,再考慮該定罪與否、此罪或彼罪”[8]。針對(duì)這種從量刑到定罪的逆向司法邏輯,有學(xué)者將其稱之為“倒置的三段論,‘上升式的’或‘逆退式的’三段論”[9],筆者謂之“由刑及罪”逆向思維邏輯。(1)針對(duì)這樣一種逆向司法邏輯,學(xué)界賦予了各種稱謂,如“以刑制罪”“以刑定罪”“量刑反制定罪”等。筆者認(rèn)為,“制”、“定”容易讓人誤讀為量刑決定定罪,容易招致反對(duì);倒置三段論僅表明在選擇罪名之前適當(dāng)考慮量刑的妥當(dāng)性,故筆者傾向于使用“由刑及罪”概念。參見:袁翠嬋.“由刑及罪理論”研究現(xiàn)狀分析[J].法制博覽,2017(2):52-53.
(一)罪與非罪認(rèn)定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中“……都是犯罪,但是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rèn)為是犯罪”這樣的規(guī)定是典型的“但書”條款。由于“刑罰是一種易感觸的力量,故在經(jīng)驗(yàn)的世界里,人們都是通過刑來認(rèn)識(shí)罪的”[10]56。同樣,針對(duì)罪與非罪臨界點(diǎn)上的危害行為,在適用“但書”條款做出入罪或出罪決定之前,我們需要預(yù)先考慮刑罰適用的必要性,這實(shí)際上就是一個(gè)“由刑及罪”的逆向司法過程。
1.法律文件對(duì)“但書”條款的直接規(guī)定
其一,針對(duì)一些違禁或管制物品,如果是因?yàn)樯a(chǎn)、生活需要而持有,且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司法文件明確要求適用“但書”條款排除出罪。如針對(duì)禁用劇毒化學(xué)品:《關(guān)于辦理非法制造、買賣、運(yùn)輸、儲(chǔ)存毒鼠強(qiáng)等禁用劇毒化學(xué)品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本解釋施行以前,確因生產(chǎn)、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yùn)輸、儲(chǔ)存毒鼠強(qiáng)等禁用劇毒化學(xué)品餌料自用,沒有造成嚴(yán)重社會(huì)危害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guī)定,不作為犯罪處理”。
其二,針對(duì)情節(jié)輕微的未成年人犯罪,為了避免對(duì)其適用刑罰所帶來的交叉感染,司法文件明確要求適用“但書”條款不作為犯罪處理。如《關(guān)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和第九條都有相關(guān)規(guī)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fā)生性行為,情節(jié)輕微……不認(rèn)為是犯罪。”“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實(shí)施盜竊行為未超過3次……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認(rèn)定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rèn)為是犯罪。”
2.法官對(duì)“但書”條款的直接適用
針對(duì)那些不值得科處刑罰的危害行為,即使缺乏法律文件的相應(yīng)規(guī)定,法官仍然可以直接適用“但書”條款宣告無罪。對(duì)此,早在1989年11月4日,最高院在《關(guān)于一審判決宣告無罪的公訴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fù)》中答復(fù)說“對(duì)……但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可在宣告無罪判決的法律文書中……引用刑法第13條作為法律根據(jù)”[11]。
(二)此罪與彼罪區(qū)分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除了罪與非罪的認(rèn)定以外,“由刑及罪”逆向司法現(xiàn)象同樣體現(xiàn)在此罪、彼罪的區(qū)分當(dāng)中。首先,當(dāng)某一行為觸犯了數(shù)個(gè)罪名,或者行為人所實(shí)施的數(shù)行為之間具有特定關(guān)系時(shí),需要遵循“從一重定罪”原則,通過比較法定刑輕重來最終確定具體罪名;其次,在對(duì)許多常見犯罪進(jìn)行區(qū)分時(shí),也需要預(yù)先考慮法定刑,從中獲知構(gòu)成要件的信息。
1.“從一重定罪”原則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邏輯首先體現(xiàn)在法條競(jìng)合當(dāng)中。在“法條競(jìng)合”情形中,一個(gè)行為同時(shí)符合了特別條款和一般條款所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由于特別條款系為了保護(hù)特殊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往往要重于一般條款所規(guī)定的刑罰,故適用特別條款就能夠保護(hù)該種特殊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此所謂“特別條款優(yōu)于一般條款”原則。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一般條款處罰反而更重,此時(shí)就應(yīng)當(dāng)依照一般條款來定罪處罰。例如,在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當(dāng)中,當(dāng)行為人生產(chǎn)、銷售的并非普通商品,而是《刑法》第141條至第148條所列的產(chǎn)品,如假藥、劣藥、不符合衛(wèi)生標(biāo)準(zhǔn)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等時(shí),既構(gòu)成這些特別條款所規(guī)定的罪名,又構(gòu)成一般條款規(guī)定的罪名。由于《刑法》第149條明確規(guī)定“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故直接依照該規(guī)定認(rèn)定為一般條款規(guī)定的罪名即可,這種因刑罰輕重而決定罪名的做法正是“由刑及罪”逆向思維的體現(xiàn)。
2.常見犯罪區(qū)分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刑法適用的過程就是刑法解釋的過程。在解釋過程中,學(xué)者張明楷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對(duì)相應(yīng)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解釋,受法定刑的影響和制約。因?yàn)椋ǘㄐ谭从沉藘蓚€(gè)問題,一是國(guó)家對(duì)犯罪行為的否定評(píng)價(jià),二是國(guó)家對(duì)犯罪人的譴責(zé)態(tài)度,所以,在解釋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時(shí),解釋者善于聯(lián)系法定刑的輕重成為必須,以便在重法定刑的犯罪構(gòu)成中排除輕微行為,而只將嚴(yán)重行為納入重法定刑的犯罪構(gòu)成之內(nèi)。”[12]
其一,故意殺人、傷害案件認(rèn)定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故意殺人、傷害案件系常見的多發(fā)性案件,多數(shù)時(shí)候能夠較容易地完成事實(shí)與規(guī)范的對(duì)接,但在另外一些時(shí)候,為了能夠做出更為妥當(dāng)?shù)亩ㄐ裕痉ㄈ藛T需要預(yù)先考慮法定刑輕重、是否需要限制減刑等刑罰問題。
一方面,對(duì)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認(rèn)定,其首要制約因素是對(duì)某一行為是否需要判處死刑。《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明確規(guī)定,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當(dāng)無從輕、減輕情節(jié)的時(shí)候就首選死刑;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所以如果不是在情節(jié)特別惡劣的情況下,很難適用死刑。在司法實(shí)踐中,很多案件屬于臨時(shí)起意,也有概括故意情形,這些在性質(zhì)上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區(qū)分難度很大。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擺脫單純從犯罪構(gòu)成來考慮的概念之爭(zhēng),對(duì)是否需要適用死刑綜合考量。在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xiǎn)性等各方面的情況后,認(rèn)為最恰當(dāng)適用刑是死刑,則可以考慮認(rèn)定為故意殺人罪;否則,選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更妥。”[6]
另一方面,對(duì)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認(rèn)定,另一個(gè)制約因素是限制減刑制度的確立。《刑法修正案(八)》規(guī)定了“對(duì)被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等八種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jù)犯罪情節(jié)等情況可以同時(shí)決定對(duì)其限制減刑”這個(gè)規(guī)定里面列舉了八種犯罪,“故意傷害罪”不在這個(gè)范圍之中。可在司法實(shí)踐中,故意傷害罪是判處死緩刑較多的犯罪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考慮,對(duì)于需要從嚴(yán)懲處、適用限制減刑的案件,宜認(rèn)定為故意殺人罪”[6]。
其二,綁架案件認(rèn)定中的“由刑及罪”逆向思維。
對(duì)于綁架罪,我國(guó)刑法在量刑上表達(dá)了異常嚴(yán)厲的態(tài)度。然而,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一批雖控制人質(zhì)但惡性不大的案件。為避免對(duì)這類案件以綁架罪科以重刑,有必要嚴(yán)格解釋綁架罪的構(gòu)成要件,對(duì)控制人質(zhì)的手段、不法要求的程度等進(jìn)行限制性解釋。
一方面,當(dāng)控制人質(zhì)的手段具有極端性是成立綁架罪的關(guān)鍵性條件。單純的誘騙勒索財(cái)物與綁架罪的客觀行為不符,認(rèn)定為敲詐勒索罪更妥當(dāng)。另一方面,“重大”范圍內(nèi)的不法要求是綁架罪成立的又一重要條件。也就是說,勒索巨額贖金、提出其他重大不法要求的才考慮成立綁架罪。[6]如果犯罪嫌疑人控制人質(zhì)的方式是普通暴力,或者想要勒索的財(cái)物數(shù)額不大,或者只是提出了些許的不法要求,不宜認(rèn)定為綁架罪。
對(duì)于綁架罪的成立,還需要考慮一個(gè)因素:犯罪嫌疑人勒索的財(cái)物是沒有任何依據(jù)的。像那種二者之間存在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hù)的非法債務(wù)糾紛時(shí),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非法拘禁罪或者敲詐勒索罪,而非綁架罪。(2)“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hù)的債務(wù),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規(guī)定(即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最高院《關(guān)于對(duì)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hù)的債務(wù),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
其三,搶劫、尋釁滋事案件認(rèn)定中的“由刑及罪”思維。
在搶劫、尋釁滋事等犯罪案件中,為了獲取被害人的財(cái)物,行為人均會(huì)使用暴力手段,在認(rèn)定罪名時(shí)容易發(fā)生混淆。此時(shí),我們同樣應(yīng)當(dāng)采用“由刑及罪”逆向思維,根據(jù)法定刑輕重來認(rèn)定“暴力”的強(qiáng)度。其中,搶劫罪因刑罰較重而要求較高強(qiáng)度的暴力,故對(duì)于那些暴力程度輕微的案件,應(yīng)當(dāng)考慮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罪。
二、“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邏輯之正當(dāng)性成因
在面對(duì)定性爭(zhēng)議案件時(shí),“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邏輯客觀、真實(shí)地存在于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這種做法明顯顛覆了傳統(tǒng)罪刑關(guān)系,那么其正當(dāng)性依據(jù)何在呢?我們認(rèn)為,其正當(dāng)性源自以下兩個(gè)方面:其一,在定性爭(zhēng)議案件中,司法人員需要運(yùn)用“由刑及罪”逆向思維來尋找作為大前提的刑法規(guī)范(3)不僅如此,法官在探索、發(fā)現(xiàn)小前提即事實(shí)真相過程中,也會(huì)依據(jù)其對(duì)定罪與量刑的預(yù)定,去尋找與之符合的犯罪事實(shí),這種由結(jié)論到事實(shí)的認(rèn)定過程同樣是逆向的。;其二,犯罪的“應(yīng)受刑罰處罰性”特征內(nèi)含著“由刑及罪”的思維邏輯,要求無論是在立法設(shè)罪還是司法定罪時(shí),均需要考慮刑罰的必要性與妥當(dāng)性。
(一)定性爭(zhēng)議案件對(duì)“由刑及罪”逆向思維的需求
長(zhǎng)期以來,在司法論證過程中,經(jīng)由事實(shí)、規(guī)范最后到結(jié)論的三段論演繹推論模式頗受青睞。的確如此,在大量存在的簡(jiǎn)單案件中,由于案件事實(shí)與刑法規(guī)范簡(jiǎn)單明晰,人們把法官比喻成“一臺(tái)自動(dòng)售貨機(jī),人們向他饋送事實(shí)和法律規(guī)則,就象是向自動(dòng)售貨機(jī)投放硬幣,然后便可從機(jī)器下面得到相應(yīng)的結(jié)果”[13]62-71。可是,在定性爭(zhēng)議案件中,定罪、量刑并非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先后過程。對(duì)于這一點(diǎn),張明楷教授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diǎn):“幾乎在所有爭(zhēng)議案件中,法官、檢察官通常都是先有一個(gè)結(jié)論,然后再去找應(yīng)當(dāng)適用的法律條文,看這些條文文字是否能包含案件的條件,這就是國(guó)外學(xué)者常說的三段論的倒置或者倒置的三段論。”[14]同樣,即使在普通法系國(guó)家也是如此。美國(guó)大法官霍姆斯曾指出:“普通法審判的特征之一,就是首先得出判決結(jié)論,然后才決定判決原則。”[15]724-726弗蘭克大法官也認(rèn)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各種各樣的判斷(包括判決)都是帶有一個(gè)或明或暗的既有結(jié)論出發(fā)的。一個(gè)人通常以這一結(jié)論為出發(fā)點(diǎn),然后努力尋找能夠證明這一結(jié)論的依據(jù)。”[16]100可見,疑難案件中的定罪論證過程,案件結(jié)論實(shí)際上提前參與到了對(duì)法律規(guī)范甚至案件事實(shí)的認(rèn)定當(dāng)中。
對(duì)于這種逆向司法邏輯的正當(dāng)性,中外學(xué)者都是認(rèn)可的。中國(guó)學(xué)者馮亞東認(rèn)為“定罪前預(yù)先考慮定罪后對(duì)犯罪嫌疑人帶來的后果,這在罪與非罪的決斷時(shí)是一個(gè)很重要的因素。這種做法是有高度的合理性的,同時(shí)也具有相當(dāng)?shù)目赡苄浴<词褂幸欢ǖ囊軘喑煞衷趦?nèi),但也是在理性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相對(duì)于那種只是局限于考慮行為本身的事實(shí)情節(jié),而直接作出抉擇的那種臆斷模式,還是略高一籌的”[17]。同樣,德國(guó)的考夫曼教授也認(rèn)為,“案件判決之前,法官對(duì)案件的先前判斷和理解是完全可以的,我們不必對(duì)這種情形進(jìn)行責(zé)難,畢竟一切理解都是建立在先前理解基礎(chǔ)之上的”。相反,“如果不進(jìn)行這種先前理解,法官就需要查閱細(xì)究法律條文,漫無目的又漫無計(jì)劃,試圖找出一些適當(dāng)?shù)囊?guī)定”[18]113-115。挪威學(xué)者斯坦因·U·拉爾森亦認(rèn)為,“法官那種先憑直覺預(yù)測(cè)結(jié)果,再對(duì)這種預(yù)測(cè)結(jié)果找到邏輯理由加以支撐。這種現(xiàn)象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現(xiàn)象,不足為怪。從法律秩序的促進(jìn)目的方面來看,也是相吻合的。法官對(duì)非常熟悉的目標(biāo)通過職業(yè)活動(dòng)形成一個(gè)理性結(jié)果,可能已成為其本身天性的一部分。形成這個(gè)理性結(jié)果時(shí),不事先表明所有論點(diǎn),而是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找出這種理性結(jié)果的理由,或者使這種理性結(jié)果合法化”[19]304-309。
(二)犯罪“應(yīng)受刑罰處罰性”特征導(dǎo)致的對(duì)“由刑及罪”逆向思維的需求
我們知道,“刑法和其他部門法區(qū)別的標(biāo)準(zhǔn)是他的特殊的調(diào)整手段——刑罰,其調(diào)整對(duì)象不能做為標(biāo)準(zhǔn)”[20]1-13。也正因?yàn)槿绱耍袑W(xué)者認(rèn)為,“應(yīng)受刑罰懲罰性是犯罪的本質(zhì)特征,因?yàn)檫@種應(yīng)受刑罰懲罰性對(duì)犯罪的本質(zhì)能夠加以直接而又全面的反映,人們通過直覺就能把握住,這也是區(qū)分犯罪與其他行為的科學(xué)標(biāo)準(zhǔn)”。[21]這就要求我們?cè)谂袛嘁粋€(gè)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之前,應(yīng)先考慮適用非刑罰措施能否達(dá)到懲治目的,“由刑及罪”的逆向邏輯就此展開。
體現(xiàn)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在劃定犯罪圈時(shí)需要以“應(yīng)受刑罰處罰性”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此,我國(guó)臺(tái)灣學(xué)者林山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犯罪化“是針對(duì)某一種破壞法律權(quán)益的不法行為,通過對(duì)刑事立法政策的全面深刻考量,對(duì)使用不動(dòng)用刑罰的法律制裁手段,還是沒有辦法判斷其惡害程度,或者沒有辦法加以有效遏阻的不法行為,通過刑事立法手段來創(chuàng)設(shè)刑事不法構(gòu)成要件,從而對(duì)該不法行為賦予刑罰的法律效果,使之成為刑法明文規(guī)定處罰的犯罪行為”[22]127-129。可見,從立法劃定犯罪圈的過程來看,“行為犯罪的性質(zhì)取決于多種因素和條件,例如行為自身的危害性、行為自身的危害程度、認(rèn)定為犯罪后處罰的方式、處罰的效果等。或者也可以這樣說,行為犯罪的性質(zhì)在考慮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嚴(yán)重的社會(huì)危害性的同時(shí),也要在必要性層面對(duì)行為主體是否應(yīng)受、在可行性層面考量行為主體是否能受刑罰處罰的問題進(jìn)行細(xì)細(xì)考量,那么那種不應(yīng)當(dāng)或不可能受到有效刑罰手段處罰的行為或者行為人,是不能入罪的”[23]。這便形成了刑罰在先,犯罪在后,刑罰產(chǎn)生犯罪的刑罪因果關(guān)系。
刑事立法完成之后,緊接而來的是刑法的適用。刑法的適用過程,也可以說就“是刑法的解釋過程。對(duì)于解釋的方法,我國(guó)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符合立法本意”[24]。為此,我們?cè)诿鎸?duì)存在多種含義的刑法用語時(shí),需要站在立法者的立場(chǎng)上,在定罪過程中適當(dāng)考慮刑罰的必要性及妥當(dāng)性。這種從刑罰角度出發(fā)考察并選擇罪名的做法,在許多國(guó)家的犯罪論體系甚至刑法典中均有體現(xiàn)。其中,在德日刑法的犯罪論體系中,在認(rèn)定犯罪過程中需要考量刑罰的可罰性程度,“對(duì)于某種行為是否成立犯罪,首要因素是在法律上一般規(guī)范地被評(píng)價(jià)為違法,然后在刑法上需要被判斷為可罰,可罰違法性是犯罪的最后一般要件”。[25]71-92而在另外一些國(guó)家,則通過刑法典直接將“應(yīng)受刑罰懲罰性”內(nèi)容納入其中。《瑞士刑法典》有類似的規(guī)定,“本法典、其他法律和行政立法性文件規(guī)定的應(yīng)受本法典之刑罰處罰的行為是犯罪”。《俄羅斯聯(lián)邦刑法典》也有,“本法典以刑罰相威脅所禁止的有罪過地實(shí)施的危害社會(huì)的行為,被認(rèn)為是犯罪”。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一切危害社會(huì)的行為,依照法律應(yīng)當(dāng)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綜上可見,通過“可罰違法性”以及“應(yīng)受刑罰懲罰性”要件的設(shè)定,原本應(yīng)當(dāng)屬于刑罰論范疇的處罰問題被前移至犯罪論體系,成為制約犯罪成立的條件之一,這一過程所體現(xiàn)的正是“由刑及罪”的逆向司法邏輯。[26]
三、“由刑及罪”逆向路徑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guān)系
如前所述,從最高法院發(fā)布的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來看,“由刑及罪”作為一種法律思維方法,在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爭(zhēng)議場(chǎng)合存在用武之地。然而,這種逆向模式因其反傳統(tǒng)從提出開始,就遭到了許多專家學(xué)者的反對(duì)。這主要原因是罪刑法定原則是現(xiàn)代刑事法治基石的觀念深入人心,對(duì)該原則的違背當(dāng)然是大逆不道的。為此,探尋“由刑及罪”逆向思維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個(gè)繞不過的話題,有必要單獨(dú)予以討論。
(一)敵人抑或朋友:“由刑及罪”逆向思維與罪刑法定原則
梁根林教授在當(dāng)初提出“量刑反制定罪逆向路徑”的設(shè)想之后,即表現(xiàn)得惴惴不安,擔(dān)心“這種反制定罪是否與傳統(tǒng)的刑法教義學(xué)理論相違背,更或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帶來破壞法治的嚴(yán)重后果”[27]。而鄭延譜教授則明確表示了反對(duì),認(rèn)為“在司法實(shí)踐中,量刑失當(dāng)現(xiàn)象不斷發(fā)生時(shí),對(duì)該條文法定刑的設(shè)置進(jìn)行修訂成為立法者的必須。量刑反制定罪中對(duì)罪刑關(guān)系進(jìn)行批判,這是沒有道理的,以刑制罪理論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的,對(duì)刑事司法有利無弊,須拋棄”[5]。另有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針對(duì)疑難案件,必須“尋找破解困境的方法需要從刑法教義學(xué)入手,直接走‘量刑反制定罪’之道,這不僅僅是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葬送刑事法治的可能性都有。這樣看起來,‘量刑反制定罪’帶來的不是‘刑法福利’,而是‘刑法災(zāi)難’了”[28]。
我們認(rèn)為,“由刑及罪”逆向思維與罪刑法定原則并非水火不容,二者具有相同的趣旨,用之得當(dāng)能夠相輔相成、相得益彰。[29]我們知道,罪刑法定原則發(fā)展到現(xiàn)代,增加了實(shí)質(zhì)側(cè)面的內(nèi)容,開始關(guān)注刑罰法規(guī)內(nèi)容的適正性,趙希認(rèn)為“抽象意義上的濫用司法權(quán)以及違反傳統(tǒng)以罪定刑的觀念無法形成有力的批評(píng),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構(gòu)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對(duì)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該理論的合理性所在,這種解釋論意義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30]。從前述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來看,“由刑及罪”思維主要適用于兩個(gè)方面:其一,針對(duì)罪與非罪問題,“但書”條款通過將那些形式上符合犯罪構(gòu)成,但不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排除出罪,體現(xiàn)的是一種出罪功能,與罪刑法定原則禁止處罰不當(dāng)罰行為的內(nèi)在要求不謀而合;其二,針對(duì)此罪與彼罪問題,所得出的結(jié)果更多的也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輕罪裁判。[31]因?yàn)椤跋拗茋?guó)家權(quán)力,保護(hù)國(guó)民權(quán)益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核心,能夠?qū)⒂凶锝忉尀闊o罪、將重罪解釋為輕罪的,都是不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32]。
(二)定性爭(zhēng)議案件:“由刑及罪”逆向司法的適用場(chǎng)域
如前所述,“由刑及罪”作為對(duì)傳統(tǒng)三段論邏輯的補(bǔ)充,在當(dāng)下中國(guó)有其現(xiàn)實(shí)的合理性,且與罪刑法定原則的宗旨一脈相承。為此,有學(xué)者立足于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主張將這種思維方式推而廣之。如刑法學(xué)者們所認(rèn)為的,最有意義的是量刑,故我們“虔誠對(duì)待定罪沒有必要,犯罪構(gòu)成不是不可逾越的禁區(qū)”[33],“在根據(jù)犯罪構(gòu)成進(jìn)行判斷后,得出的罪名使得量刑明顯失衡的話,可以通過適度變換罪名來實(shí)現(xiàn)量刑公正,讓罪名為公正的刑事責(zé)任讓路”[34]。這種觀點(diǎn)實(shí)際上夸大了“由刑及罪”逆向思維的適用范圍,而忽視了其內(nèi)在隱憂。因?yàn)椤坝尚碳白铩毕狄环N先入為主的倒置思維,其中對(duì)刑罰妥當(dāng)性的判斷又是一個(gè)見仁見智的問題,因而我們認(rèn)為,這樣的思維邏輯并非一種常規(guī)和首選的解釋方法,而主要是在定性爭(zhēng)議案件中發(fā)揮一種補(bǔ)充性功能。對(duì)此,正如我國(guó)法理學(xué)者所言:“司法常用的方法一直是三段論,不過三段論不適合解決疑難案件,在解決簡(jiǎn)單案件和一些典型案件上大可用上派場(chǎng)。”[35]也就是說,只在那些定性存疑的特殊案件中,當(dāng)我們依照正向三段論邏輯得出的結(jié)論明顯不合理時(shí),才需要轉(zhuǎn)換到“由刑及罪”的逆向路徑上來。需要指出的是,在遵循“由刑及罪”逆向路徑來解釋、選擇構(gòu)成要件和罪名時(shí),并非直接以處罰妥當(dāng)性的需要來解釋刑法,而只是以其為出發(fā)點(diǎn),仍然需要通過采用擴(kuò)大解釋、限縮解釋等傳統(tǒng)解釋方法,在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內(nèi)確定構(gòu)成要件的具體內(nèi)容。意思是為實(shí)現(xiàn)處罰的必要性與妥當(dāng)性,某種行為盡管并不處于刑法用語的核心含義之內(nèi),但仍然需要處于該用語的邊緣含義之中,而不能突破其邊界進(jìn)行類推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