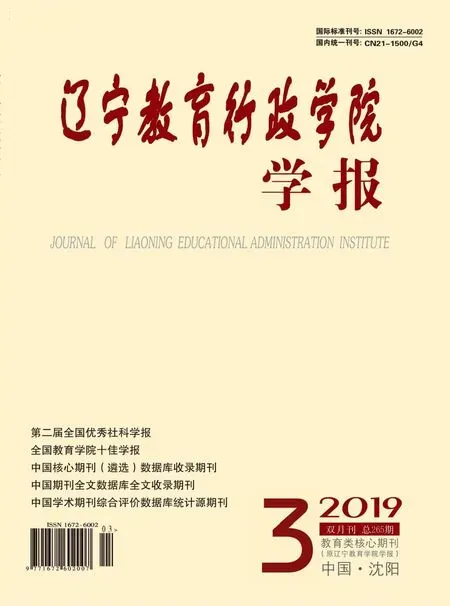狄考文的學校管理思想與實踐研究
李 濤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登州文會館是晚清時期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 Mateer)于1864年創辦的一所現代學校,經過不斷發展,從小學到中學,到成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辦學成就為世人所矚目。在四十多年的辦學歷程中,狄考文所創辦的登州文會館在學校管理方面有其特色,值得后人研究和學習借鑒。
一、登州文會館的時代背景
狄考文夫婦是1864年初從美國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山東登州的。1864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以天京陷落為標志,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歷經十多年的奮戰之后最終失敗。而在此之前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清政府被迫與英、法、俄等國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了大片國土,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不斷深入。面對嚴重的統治危機,清政府被迫開始改變。一部分洋務派官僚看到時局的巨大變化,開始主張接觸和了解西方。在他們的推動下,1862年清政府在總理衙門下創辦了京師同文館,以培養和西方打交道的外交和翻譯人才。隨后,1863年4月,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了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后改稱廣方言館)。1864年6月署理廣州將軍庫克吉泰等奉命在廣州設立了廣東同文館。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各地新式學堂,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江南水雷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等也逐漸成立。這些官辦的學校,加上各地陸續出現的由傳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為中國接觸西方的科學知識打開了一扇門。
但是在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的是,傳統的封建教育——舊式書院、國子監、府州縣學、八旗官學以及科舉考試,依然在統治著全中國。在整個士大夫階層中,除了少部分開明的洋務派官員外,大多數封建頑固派官員依然習慣于昏暗愚昧的生活,這些官僚士子們難以接受低首俯心地向洋人請教,多方抵制學習西方。而普通民眾熱衷的依然是讀四書五經,視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走上仕途為正道,對去新式學校就讀的興趣并不大。
因此,狄考文在來到中國之后,首先投身于自己最初設定的本職工作——傳教中,狄考文為給妻子提供一個活動場所,于1864年9月創辦了登州文會館的前身——登州蒙養學堂,主要是招收幼童,由狄考文的妻子狄邦就烈負責學校的日常所有事務。但狄考文在山東各地幾年的傳教后發現,要在儒家的誕生地山東傳播基督教并非易事,而由妻子操持的登州蒙養學堂辦學效果也并不理想,雖然投入巨大,除免學費外,學生的“一切衣履靴襪,飲食筆墨紙張醫藥燈火,以及歸家路費等皆出自學校”,但逃學退學及被開除的學生很多,幾年下來,“有用于教會者僅一人”。[1](P51)這樣的情況讓畢業于美國杰弗遜學院的狄考文決心下力氣對學校進行改造,使學校培養的人才符合教會的設想。
對于傳教士究竟應該是聚力于主業“傳教”還是以“辦學”為主業,在華傳教士內部對此多有爭論,但主流意見還是認為傳教士應該專注于“傳教”,反對將有限的人力、精力和時間浪費在辦學上。狄考文從傳教轉向辦學,無疑承受了來自教會內外的壓力。1877年基督教在華傳教士第一次全國大會上,狄考文發表了《基督教會與教育的關系》一文,結合自己在登州文會館的辦學經歷,對宗教與教育的關系進行了闡述,認為“青年教育一直是教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能把這項偉大的工作留給世俗社會去辦”。[2](P77)
二、狄考文的“全面教育”思想與登州文會館的辦學成就
狄考文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1890年他將自己的思想概括為“全面教育”(A Through Education),他在解釋這一思想時指出“所謂全面教育,是指要對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和基督教真理有一個較好的了解,接受這種教育需要十到十四年的時間”。這里全面教育有兩層含義:一是學習內容廣泛,建立以中國古籍經典、西方現代科學和基督教知識為主干的課程體系;二是學校規格提高,不僅有從事基礎教育的小學,還要有進行中高等教育的中學和大學。
狄考文認為,教會學校應以“培養教員、工程師、測量員、機械師和領袖人物為主”,通過教育培養精英,通過精英來影響民眾,“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一支點燃著的蠟燭,未受過教育的人將跟著他的光走”。[2](P62)全面教育一是提高了對人的心靈和性格產生深遠影響的時間和機會。要使學生能成為在社會上和教會里有影響的人物,成為一般人們的教師和其他領袖人物,在學生整個受教育期間,教師是靈性生活和認真工作的榜樣。二是全面教育將使人們獲得有影響的社會地位。必須培養受過基督教和科學教育的人,使他們能夠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任何一個精通西方科學,同時又熟諳中國文化的人,在中國任何一個階層都將成為有影響的人。三是全面教育有助于破除迷信和培養開明的基督徒品質。由近代文明所發展的精神與物質規律的知識,對于破除多種形式的迷信,諸如妖術、泥土占卜、占星術、巫術等是有巨大作用的。四是全面教育給家長們以有益的吸引力,送兒童來上學。要建一所學校,必須要有吸引力。唯一合適而有益的吸引力是對教育本身的要求。要使這一吸引力有效力,教育必須面向一生事業的成功,面向易得的職業,面向學生家長和朋友稱心的職業。用母語教學,又精通數學和西方科學的全面教育,必將引導青年人走上崇高的、成功的職業道路。[3(]P13~17)
狄考文強調,全面教育中,用中國語言施教,是教會學校在中國的教育取得成功的關鍵。這是因為,只有全面地進行中文教育,才會對學生有幫助。一是全面的教育保證學生學完全部的課程,全面教育所給予的聲望以及掌握它所提供的前景,會把學生留到完成學業為止。二是本國語言的全面教育,是一個人在本國人民群眾中取得學術聲望所必需的。三是中文教育能使人有效地應用他的知識。四是中文教育引導受教育者與人民打成一片并且影響他們。五是中文教育與英語教育相比,不至于使受教育者高人一等。在這一點上,狄考文的想法和做法與大多數強調英文教育的教會學校不一樣。之所以如此,是基于當時中國剛剛向西方敞開大門的社會狀況,他擔心如果以英文授課,不僅會使學生學了英文后中途輟學去當更賺錢的買辦等,更擔心那些受了英文教育的人并不能和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反而妨礙了擴大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
事實上,正是因為堅持了全面教育的思想,狄考文創辦的登州文會館在四十年的辦學歷程中才逐漸發展壯大,1877年,登州文會館舉行了首屆畢業生典禮,距其最初創辦登州蒙養學堂已有十三年,雖然只有三名畢業生,但寧缺毋濫,這三名畢業生在畢業答辯期間的優秀表現,代表了登州文會館的辦學水準,后來由文會館逐漸擴充發展而來的齊魯大學的學生,將這屆畢業生視為第一屆校友。其后,1884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批準登州文會館具有大學文憑。在長達四十年的辦學歷程中,登州文會館以其出色的科學教育及良好而完備的物理化學實驗儀器設備而聞名,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因為接受了良好的西方科學教育和中國經典教育,成為當時各地的教會學校和新式學堂的重要師資來源,其良好的辦學聲譽得到了當時學界的公認。
根據登州文會館畢業生王元德、劉玉峰于1913年出版的《文會館志》中“同學齒錄卷四”統計,在登州文會館畢業同學齒錄中統計的170名歷屆畢業生中,被各地書院、學堂聘為教習擔任教師的就有121人,比例高達71%。其中,有多名畢業生在上海圣約翰書院任教,如1879年畢業的張豐年、1889年畢業的曹金崗、1891年畢業的李星奎,而上海圣約翰書院之前在很多人心目被視為中國近代第一所教會大學。有多名畢業生擔任京師大學堂教習,如畢業于1881年的于志圣、畢業于1885年的仲偉億、畢業于1888年的朱葆琛、畢業于1896年的連英煌等。[1](P133-153)山東師范大學郭大松教授在其《登州文會館: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中,將其視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這是因為,不僅登州文會館在四十年的辦學歷程中,建立起了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的完整的辦學體系,更是因為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在諸如上海圣約翰書院、北京匯文書院、通州潞河書院、京師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山西大學堂等大學任教,為這些大學提供了當時難得的師資。
三、登州文會館的學校管理特色
登州文會館的卓越辦學成就的取得,是與狄考文在辦學過程中秉持“全面教育”思想,嚴格學校管理所分不開的。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一)管理團隊精干
1864年成立登州蒙養學堂時,學校的日常管理人員僅有狄考文的夫人狄邦就烈一人,1972年起,狄考文將主要精力從傳教轉到登州文會館的辦學上,即使1882年赫士來到登州文會館協助其教學管理擔任第二館主,及后期柏爾根到文會館接任館主,整個管理團隊也不過三四人。這些管理人員,都參與學校的教學授課,不只是純粹的學校管理者。
其管理團隊的精干,固然與狄考文有意保持登州文會館的辦學小規模有關,也與其作為教會學校的私人辦學特色有關,有效地保證了學校的高效運轉。
而同期的官辦學堂,比如京師同文館,管理團隊十分龐大。作為總理外交事務衙門的下屬機構,在1884年以前,京師同文館學生也不過數十名,教習不過十幾名,而管理者則有總教習、幫提調、提調、專管大臣、總管大臣等官員。同文館內部充滿著官場惡習,因循敷衍、貪污賄賂之風,不下于一般的官府衙門。[4](P86~101)
精干的管理團隊,不僅有利于節省開支,也有利于簡化管理程序,使學校的日常管理更高效。
(二)各項規章完備
根據《文會館志》記載,登州文會館的條規有六條,分別是禮拜條規、齋舍條規、講堂條規、放假條規、禁令條、賞罰條規。[1](P73-75)
禮拜條規主要是用來規約學生參加基督教的禮拜活動。齋舍條規主要是用來管理學生在宿舍的活動,包括每周安排一個學生值日。規定了每天的晨起、早餐、午餐、晚餐、熄燈等作息時間,以及對寢室的整潔要求。
講堂條規,主要是規定每天各時間段上課、下課、背書、自修等時間要求。放假條規,對寒暑假、清明、端午、中秋三節放假做了安排,也對學生的課后自由時間做了說明。
禁令條,主要是規定學生在校期間禁止從事之事,以吸鴉片為首要禁止項,一經查出,即行開除處分。而吸煙、飲酒也是學校禁止的,一經發現,定必重責。
賞罰條款,主要是對學生每學期在校期間的爭執、肆罵、吵鬧等登記在冊,每周由學校監督進行處理。學生遇有緊急事件,監督隨時邀集教習會議,斟酌詳細,賞罰等差一例持平,以讓學生心悅誠服。此外,學校還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處理諸如學生撒謊、偷竊、口角、貪吃等五花八門的違規違紀行為。
除了這些條規外,登州文會館還對學生的入學、畢業及學生行為不端的處理等事項做了相關的規定。由于這些規程非常完備細致,因此登州文會館的管理顯得井井有條。
(三)嚴格學生篩選
加強對學生的篩選和考試管理,是狄考文在登州文會館的學校管理中的一個亮點。
在入學方面,登州文會館于1878年訂立了招生章程,對不同年齡、不同基礎的學生入學后的就學級別和學習年限做了詳細規定。在制定招生政策時,對學生的品行道德和身體素質都做了詳細規定,要求“凡入館者,必品行端方人也”[5](P3)。根據《文會館志》記載,文會館有嚴格的入學考試,“學生初到館時,必詳為考試,考準者方蒙收納”。
狄考文在《振興學校論》中指出了中國傳統科舉考試中考試的弊端:一是“不能辨真假”,考試命題不外乎四子之書,行之年久。二是“不能斷舞弊”,考場中的夾帶抄襲、冒名頂替,考場外的串通漏題等。三是“啟人干俸祿”,讀書只為當官,并非求學問成為專才。四是“拘定學經書”,只學四書五經。[6](P238~241)
除了入學考試之外,登州文會館的日常考試分為三類:日考、季考、常年考。日考,除算術和理化實驗之外,都是由教習口問,學生口答,老師記下分數。季考由教習命題,令學生在考卷上筆答。五十分為及格,及格者可以升級,不及格者則必須原班復學或遣之歸家。
年考為每年舉行一次,凡是正齋的學生,每年都要對數學、代數、地理及五經進行考試。分數達到100分者,下學期免考,不及格者則要復學。在最初的十年里,由于管理嚴格,被剔除出去的學生人數是第十年年底時在校人數的兩倍還多。[7](P86)
通過考試及品行考核等手段,狄考文堅持寧缺毋濫,雖然最終畢業的學生并不多,總共也才二百多人,但都具有良好的聲譽,獲得社會的公認。
(四)加強師資挑選
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是學校辦學成功的重要前提。和當時大多數教會學校一樣,登州文會館的教師主要由教授宗教知識與西方科學的傳教士教師和教授中國傳統經典的中國籍教師組成。初期狄考文是在中國的基督徒中挑選中文教師,但在最初的十年里,雖然五易中國籍教師,仍然不能讓狄考文滿意。后來,狄考文解聘了原來的所有中國籍教師,重新在非基督徒的中國學者中挑選教師,將宗教活動與學術性課程分開,中國籍教師只負責與中文讀寫相關的中國傳統經典課程,并尊重中國籍教師的教學風格。
擔任西方科學課程授課的教師,除了狄考文本人外,第二任館主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和第三任館主柏爾根(Paul D.Bergen),都是在各自領域具有非凡成就的博學之人。赫士精于拉丁語、希臘語、倫理學及物理化學諸科,編譯了《聲學揭要》《光學揭要》《天文揭要》《熱學揭要》等著述二十多種,1901年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邀請帶領文會館6名畢業生赴省城濟南創辦了山東大學堂。柏爾根1901年繼赫士之后擔任文會館第三任館主,教授博物學、圣經入門等課程,1904年隨文會館遷到濰縣,擔任廣文學堂監督,在登州文會館發展為齊魯大學的過程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著名來華傳教士、美國教育家路思義(HerryWinters Luce)也在登州文會館講授過物理學,在他的促成下,登州文會館舉辦了山東有史以來首次籃球比賽,其后為舉辦齊魯大學而奔走募捐。此外,哈丕森夫人、狄莉蓮、富知彌、文約翰等外國傳教士,都通過不同方式給予文會館的發展以不同程度的幫助。
(五)注重社團建設
學生社團是現代大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培養學生的自主自立精神和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蔡元培先生在執掌北京大學時,就尤為注重學生自立精神與自愛意識的培養,提出并貫徹了“自尊、自治、自學、自省、自動、自助”的“六自”方針,鼓勵學生成立各種社團。
登州文會館作為我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狄考文同樣把學生社團建設作為學生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學生立會。根據《文會館志》記載,登州文會館的社團有兩種:一種是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的社團,比如辯論會。這樣的社團是作為課程,其目的在于養成學生自治自立的行為習慣,社團里的條規都由學生自己自行商議,學校的監督并不干預,只是給予指導和點評。另外一種社團是學生自愿發起的社團,學生自愿加入,規章條例都由學生自行議決,旨在培養學生的自重自善之心。這樣的自愿社團有新聞會、戒煙酒會、青年會、中國自立學塾會等。[8](P86~87)
辯論會創立最早,成立于1866年。該會以交換知識、練習口辯,造就共和國民為宗旨,因此取名為辯論會。根據《文會館辯論會章程》,辯論會設有正副會長、書記、檢點、稽察、司庫各一人,來操辦會務。以上這個成員每四個星期必須另行選舉,且不得連任,為的是讓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參與鍛煉。會員每人繳納會費二十文。新會長接任時,即派會員四人聽差,分別執掌燈、布座、分布選票、評票等事項。
辯論會每周六下午兩點進行,每次開辯論會,都由念論、講論和辯論三項事,每項事兩個人參與。
念論是將自己所做的論說對現場聽眾高聲念出來,以聽眾聽不出念者是在念書為最佳。
講論是將自己所做的論說對現場聽眾從容演講出來,以聽眾聽不出演講者是在背誦為最佳。
辯論是找一個可從兩個方面來辯論的話題,兩人各執一端,以辯明其理由。辯論時,兩人各輪流登臺兩次,第一次說明自己這方的理由,層層證明。第二次是辯駁對方的是非,層層反駁。
每場念論、講論和辯論,會長都要臨時聘請三位評議員來判決雙方勝負。在辯論會上要求使用官話,不得使用文言或土話。
在辯論會章程的規條里,對辯論會的相關事項還做了進一步更精細的規定。比如念論必須5分鐘以上不超過6分鐘、講論必須6分鐘以上不超過7分鐘,違者罰金十文。在會場言笑、偶語、不恭者,罰金十文。來遲者罰金十文,無故不到者罰金二十文。[8]另外,規條里對辯論會的議事事項的發起、設置、擱置,發言的次數、時長,糾紛的解決等,都進行了嚴格規定。
從這些規程中可以看出,登州文會館的辯論會設置的嚴格的議事規范,可以讓學生習得公共事務的處理能力,在公眾面前的演講和辯論能力,這些能力對學生走向社會成為一個行動力強的人才至關重要,從而有別于傳統的一心只讀古書的文人。拿《文會館辯論會章程》與著名的羅伯特議事規則比較,就可以看出,文會館章程較好地體現了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精神,符合了議事的基本原則,即一人一票原則、一時一件原則、一事一議原則、多數票決定原則和法定人數生效原則,對培養學生的主體參與精神,維護學生的民主自由權利以及對規則的遵守與敬畏,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盡管辯論會章程規定“以練習口才、增進學問為范圍,不得提倡實行,致起各界交涉”[9](P104~207),但學生在畢業后依然投身于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浪潮,有的還為推翻清朝統治而英勇獻身(如1899年畢業生王以成),這無疑是文會館學生自立精神的體現。
(六)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登州文會館是狄考文一手創辦的,在多年的辦學歷程中,狄考文一方面在學業、品德上對學生嚴格要求,“對于那些壞孩子,要不斷進行勸誡和批評,有時還要予以懲罰或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手段,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孩子們聽話、誠實和正直。我們還力圖培養他們養成勤奮、堅強和獨立的品質,否則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對他們來說都會變得毫無意義”。[7](P88)另一方面又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給學生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狄考文在一次交談中說到“我意識到我們必須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這些孩子們,因此,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中來”。[7](P80)“勤苦治事,常時率以五點半晨起,十點半晚睡,日間則碌碌不輟”,一方面親自授課,擔任多門課程的教習,“凡理化、天算諸科,皆須先生親授”,同時親自編撰教科書,“有心算初學、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官話類編”等出版,以及“理化實驗、電學全書、測繪全書、微積習題”等講稿,還設立制造所,制作物理化學等實驗器具,“凡學堂用品,強半能仿造之,且精巧堅致,不亞泰西之品”。在授課及管理學校的同時,狄考文始終注重對學生的言傳身教。據狄考文的學生王元德記載,狄考文“精神活潑,剛果善斷,學生畏之如神明,而愛之如父母。有越矩者,則嚴正以則之,而一過輒忘,不復記憶。有困難者,則設法周恤之,而處置得當不示其恩”。[1](P52),其人格魅力,贏得了學生非同尋常的尊敬和愛戴。
綜上所述,登州文會館作為我國現代第一所大學,在許多方面做了開創性的拓展,其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尤為重要,值得后學加以研究和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