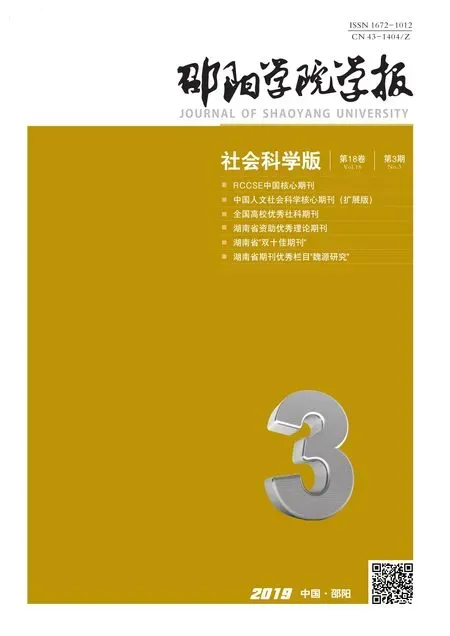陽明后學中的神妙境界
阮春暉
(邵陽學院 政法學院, 湖南 邵陽 422000)
陳來先生在《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問題》中指出,理性主義一直占據著儒學的主導傳統,但古典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中也包含有神秘主義傳統,其中明代儒學的神秘體驗發展得最充分,并列舉陽明后學中數位具有典型經歷的學者加以說明。盡管存在著此種神秘體驗,陳先生認為無論從動機或結果來說,心學的神秘體驗追求的并不是靈魂、空無或最高存在,而是一種精神境界。[1]390-413順此話題,本文以陽明后學為主要討論對象,就有關神秘體驗的話題再作出分析說明。不過,本文把陽明后學中的神秘體驗理解成“神妙與神圣的境界”,神妙指向幽隱天道,神圣指向現實人道,體驗對象和良知心體、圣賢之道、萬物一體等儒學主題有關,追求的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境界,故不妨以“神妙境界”名之。
一、道之神妙性
在心學,道有心體、道體、道心、真體等稱謂,我們可以說道乃平常應用之理,但心體的神妙浩淵,在陽明后學中仍多有提及。泰州學者徐樾(字子直,號波石,?—1551)有言:“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2]727這是從“心之量”的角度來說心體。何為“心之量”?泰州另一學者方學漸(字達卿,號本庵,1540—1615)說過“人心之量本自高大”[2]838,這是從高遠宏大方面來說;從徐波石語意看,心體在空間上沒有邊際,在時間上也無有窮盡,同時心體也涵泳萬物,這是陽明所說的“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3]109。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存心盡心,也就是存盡心體之量,故江右學者劉元卿說“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2]499。心體高大無窮盡,卻可以通過由我及物、由近及遠、由有限至無限的方式加以把握,顯示出心體神妙莫測的一面。
心體悠遠宏大,決定了道的“無方體”性。泰州學者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1515—1588)有語:
精氣為物,便指此身;游魂為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以通貫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4]70
道無固定形體,因而不可以具體物事來衡量,這是近溪的基本看法。與近溪之說相應,北方王門學者尤時熙明確指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2]642也就是說,如以具體聞見來界定道,顯然是背離了“道無方體”這一事實。其實,朱熹以無極說太極,無極便是“無形器方體可求”[5]1506;陽明寫有《博約說》一文,其中有“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3]298之語,在對道之無方體形像的認識上,各學者的態度大同小異。不過在近溪這里,則將道的神妙與生死相聯。黃宗羲指佛氏“專理會生死一事”[2]8,表明佛家在生死方面有較多關注,但佛家出離生死以顯真覺,以人倫庶物為幻妄,一切不管,與心學中的“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2]212截然有別。陽明講“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3]123,又講“道無生死,無去來”[3]1060,已指出身與道的關系問題。然作為良知的信奉者與踐行者,需在“不易”與“信得及”中把握道之神妙。在陽明后學,“不非生死之說”已較普遍,且將生死之身與良知之道相聯。浙中學者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1528—1611)就有此說:“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耳矣。”[2]306論生死與儒家大公至正之道有關,在這種情況下,關于生死的話題已與佛氏有別而帶有儒學的意義。陽明二傳弟子李材(字孟誠,號見羅,1529—1607)言:“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默,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即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2]698李見羅一方面指出人有肉身的生死之限,另一方面指出人的遭際事為也是人之生死的一種表現,而作為真性的良知則是超越了一切具體的生死而具有“聲臭俱無”的形上程度。將有關生死的話題與良知意涵相聯,既以之指明良知內涵特征,又使良知之道帶有神妙成分,這種解說現象在陽明后學中多有見到。
與“道無方體”相關,關于心體神妙性的認識還表現在“不睹不聞”上。浙中學者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1491—1562)指出: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睹聞。學者于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臆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2]337-338
對于何為“不睹不聞”,東廓曾指“無形與聲,便是不睹不聞”[2]342,這是從無形與無聲兩方面來說明。當然,在陽明后學中,對于“不睹不聞”有不同說法,如聶豹(字文慰,號雙江,1487—1563)講“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2]378,這是從心體之寂然不動方面來說“不睹不聞”。李見羅謂“渾然不睹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2]695,則是從心體未發動時來指稱“不睹不聞”。泰州學者耿定向(字在倫,號楚侗,1524—1596)另從“心體盡頭處”來言之:“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為,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睹不聞處也。”[2]816無思無為、無聲無臭、思慮未起,此是性之真體,是心體盡頭處,也是不睹不聞之意。從各學者的說法來看,良知之“不睹不聞”是指良知作為絕對主宰的存在樣態,它無起滅無方所,不容擬議摻和,不可睹聞描摹,這也是良知作為道體之神妙性的主要體現。
道無邊涯、無方體,也不可睹聞,并不意味著良知自我封閉。《周易》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之說,以其變化無端、妙應萬物而不可以具體之形來描摹,故謂之神。道的這種“妙應性”在陽明后學中亦有表達。江右學者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1529—1593):“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于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于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2]567道無體無方無聲無臭,通過陰陽二氣顯示其存在和神妙變化,然而道并非僅存在于太虛之中,人間事理和人之性理都由道變化而來,因此道既是形上的,也是形下的,這正是道之神妙處。另一江右學者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1496—1554)將神與知置于一起:“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為知,知感動而萬物出焉。萬物出于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物有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為也。”[2]367-368南野所說的知,即指良知,良知與道、神實際是同一序列的概念,都是杳寂莫測、無形無體卻又變化莫測、充滿生機活力。南野以我之良知統合道之神妙與事之準則,良知之神不可測則愈見其深,良知之道的“不可得而測而窮”與《周易》所謂的“陰陽不測之神”在陽明后學的思想視域中得以融合。
陽明后學在道體上的認識與先秦之學有關聯。《詩經》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威”字便顯出天之深遠與莊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乃“天所賦之正理”[5]173,是上天意志的人間化,孔子將畏天命置于先,意含君子當先畏天命,對大人和圣言才自會畏之。但孔子對“何為天命”未多做解釋,只是因天之神秘崇高而視其為敬畏對象,并將之作為君子道德層次的重要依據。《中庸》言:“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孔子之“畏天命”轉意為對天的仰望與贊美。《孟子》中有:“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孟子在承認君子作為的同時,也指出人力有所不及而將之歸之于天。荀子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他也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顯示出以天為大、以命從天的思想。在對天道的態度和認識上,陽明后學繼承并拓展了先秦已有的思想視域,是天道觀在心學體系中的獨特反映。
二、道之神圣性
天之道在儒學系統中,從來就不是作為單一幽遠的神妙對象而存在,它總會指向現實人生而帶有道德成分。《周易》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孔子講“畏天”,其實在《論語》中亦處處可見孔子對天之崇高性的贊美,如云“天生德於予”,亦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后來陽明亦有“人能修道,然后能不違于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3]43之說,修道即是將道之本性施用于社會生活,與《周易》、孔子之說遙相呼應。
當道之神妙性被賦予道德性,對天道的敬畏就轉而為對人之道德價值的追尋,道之“不容說”也就轉化現實人生中對道德價值之神圣性的希冀與實踐。這種理論對應,在陽明后學中亦復如是。江右學者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峰,1488—1572)謂:
用因萬事萬物而顯,真體非因萬事萬物而有,是故體物而不可遺,體事而無不在。日與斯世酬酢,變通不窮,而吾之真體未嘗起滅加損也。雖無起滅加損,而天下之道,無不原于此。[2]432
此語說的是體用關系,其中的“用”即指道之神妙性在日用酬酢中的體現,這實際上也體現了良知真體“徹上徹下”的融通性,尤其點出了良知真體之于天下之事的源出意義,天下之事乃是良知真體在生活世界的真實呈現。這樣,良知“徹上性”也就通過“徹下性”表現出來,相應地,良知之神妙性也就轉化為良知之神圣性。當然,良知意域中的“神圣”,主要指現實人生中的圣賢之道和日用人倫之道,這樣,崇高莊肅的神妙天道就下貫為圣賢之道、人倫日用之道。需說明的是,良知之徹上與徹下、神妙與神圣,實不可分言之,我們在這也只是為了言說的方便,才采用兩分法對之加以說明。
就神妙天道下貫為圣賢之道而言,這點在先秦儒學中早已有之,如《易經·系辭》有“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中庸》有“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文王,峻極于天”,此后這種圣賢意識就一直流貫在儒學的整個進程之中。周敦頤的孔顏之樂、張載之“四心”、朱熹“豁然貫通”之境、陽明的“光明之心”,莫不如此。陽明后學是儒林中的重要群體,這種精神也引起了他們的廣泛共鳴,茲舉幾例: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后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2]660-661
此語為粵閩王門弟子薛侃(字尚謙,號中離,1486—1546)論天德王道之事。依其所語,“廓然”是天道之寥廓明著,雖然如此,但物來則知,我們只要順天道之本來,則天德自現,人世王道也能成為現實。人間王道本神圣事,是圣賢之道的根本體現,在薛侃看來,這其實不難實現,關鍵在是否順應天德而為。
浙中學者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1496—1574)亦云:
圣人于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眾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跡者,良知之體也。[2]227
“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跡”說的是良知真體的神妙性,圣人可以與道之神妙相感應,體悟到良知的千變萬化。當然,圣人悟得良知真體的方式是放下習心,方能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在這里,圣人實際上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是體悟到神妙心體的存在及其表現形式;二是以先知先覺的道德榜樣啟悟后知后覺者,在社會實踐中將道之神妙性轉化為道之神圣性,從而成就自身的圣賢道德地位。
鄒東廓有“天心”“圣心”之說,其語謂:
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注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圣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圣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圣學之全。[2]340
東廓以為濂溪之靜即是道之真體,它展開為兩個維度:天心與圣心。“天心”無聲無臭而又主宰綱維萬化,“圣心”不睹不聞而以仁義中正為根本;“天心”以元亨利貞促萬物之生,“圣心”以仁義中正形萬物之成,“天道之妙”合“圣學之全”就體現在其中。從此看,東廓所說的“天心”即是我們前文所說的神妙之道,“圣心”是生活世界里的神圣之道,二者并無高低層次的不同,是道之體的兩個不同方面。
道之神圣性的另一表現是人倫日用之道,錢緒山講“于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圣”[3]1520,說的便是人倫日用與神圣之道的關系。人倫日用之道在陽明后學中有多種表達方式,以下就此略述之。
在會稽,集同門講于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自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于學則可,謂之聞道則未也,賢智之過與仁智之見俱是妄。一時學者有省。[6]72
此段是王心齋論“百姓日用是道”的語錄記載。在心齋看來,童仆往來雖是日用間常見細小之事,但其由道德主體發出,符合天道自然和社會人事準則,則它便具備道德與神圣之意。其實,道德與神圣無關于事之大小與人物身份高低,童仆“順帝之則”的往來與名臣賢相的道德功業,沒有道德等級的區分,心齋指童仆往來“至無而有,至近而神”,說的就是這層意思。擴而展之,百姓日用是由童仆往來這等常見之事擴展、組合而成,凡是合于天道之則,那么百姓日用即是道。
羅近溪亦有“捧茶童子是道”之說,近溪謂:
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圣成神也。[4]45
“知有兩樣”并非有兩個“知”,而是指知所具之二重性:童子捧茶之自然而然,不著思慮人為,是天之知;人能以自身之智慮覺其所以然,屬人之知。可以看出,近溪所謂“捧茶童子是道”是從天之知這一角度而言。當然,如能從眼前的童子捧茶行為中自覺地返歸天道,也能實現神妙與神圣的合一,從而將童子捧茶之類的即時行為與道相聯。
除此,泰州學者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1547─1629)有“手持足行是道”之說:
蓋視聽行持,本來是道,所以非者,只因著些私心故耳。心茍不著,渾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趨進而趨進,視即為明,聽即為聰,率其視聽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7]466-467
周海門在這里將日用常行中的視聽行持等同于道,實際上是預設了一個前提,即不能著些私心,如此方能使視聽行持之行為歸于神圣之道。因此當我們在分析陽明后學中提出的人倫日用之道的說法時,要看這種說法是基于道之神妙這一前提而發,近溪所說的“捧茶童子是道”,亦是基于“戒慎恐懼”這一前提。在這些前提的規約下,“童子捧茶是道”“視聽行持是道”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當然,心齋、近溪、海門關于人倫日用之道的說法亦有區別。心齋語意中的人倫日用,其范圍要廣,童仆往來、視聽行持只是人倫日用中的一個特例。且心齋之說是基于當時致良知之“致”用得過多,茫茫蕩蕩無實落處而言。近溪和海門之說顯然由心齋而來,但兩人都強調片段性、偶發性行為所具有的道德含義,其中近溪的“童子捧茶”帶有隱喻的意味,而海門的“手持足行”則涉及生活中的平凡瑣事。然不管如何,人倫日用只要帶有道德之意,而道德又無關于事物的大小、高低、圣凡,則其就是神圣可為的。
三、神妙與神圣的合一
神妙與神圣之道,如果僅停留在理論說教層次,則這種道體要么只能仰望,要么便是虛置或空幻。對于信得及良知之學人,他總在探求這樣的問題:良知真體究為何種存在?如何在生活世界里貫徹良知之用,以便實現道之神妙與神圣的合一?在陽明后學中,這種探求表現為對道體的神秘體驗及體驗之后的社會實踐。
陳來先生認為宋明儒學中神秘體驗的基本特征有自我與萬物為一體、宇宙與心靈合一、“心體”呈現、一切差別的消失、突發的頓悟、高度的興奮愉悅以及強烈的心靈震撼與生理反應(通體汗流)等,其形式則分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外向體驗與“宇宙即是吾心”和“心體呈露”之內向體驗,并以陽明后學中的王龍溪、徐愛、聶雙江、羅念庵、萬廷言、胡直、蔣道林等的神秘體驗為例,對此加以說明。本文主要從陽明后學中幾個典型學者在神秘體驗時所涉及的良知形態及其本性方面作一簡要探討。
陽明弟子對于良知這一學問源頭自無疑義,但在良知的具體內涵及其表現形態上卻有不同看法,這一看法的形成與神秘體驗有關。王龍溪有“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之說,學稱“四無論”。“四無論”的正式提出,是在陽明征思田的前夕,即1527年,在此之前的1523年,龍溪在禮部考試不弟之后,陽明為之治靜室,使其靜心思考學問精髓。龍溪居之逾年,終悟得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8]823從龍溪居靜室、居之逾年的情形看,這一過程充滿神秘色彩,而且龍溪悟有所果,即“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這一理論成果當和“四無論”直接相關,因為在此之后,龍溪“遂自信自成,不屑屑于世人之議稱跡,其所為常有獨往獨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8]846可見此時龍溪的學術自信。因此,龍溪神秘體驗的結果,便是悟得良知之無,并就此樹立起自己的學術方向。
黃宗羲嘗論聶雙江為學經歷:“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神秘體驗有一重要特征,即眼前所見皆光明洞徹,感覺物我為一,所有思慮關礙全被打通,這種神秘境界顯然非常人所能做到。聶雙江主張良知本寂,良知不賭不聞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這樣方能避免將良知之已發等同于良知之未發。但陽明之謂良知,是未發即在已發之中、道無分于動靜,聶豹先求寂體再論感通與發用,引起王龍溪、鄒東廓等同門的反對,但聶豹對于通過神秘體驗獲得對于良知真體的認識深信不疑,故而始終堅持己學,不過聶豹通過神秘體驗獲得的是“良知本寂”這一結果,這與龍溪所悟良知之“四無”有不同。
良知本體無方所,湛然虛明,不可執著,不容擬議,只順其本性即可,但在實際工夫中,往往以“強力”手段來識取心體,結果不僅扭曲良知本性,還給體悟者帶來認識障礙。羅近溪就有此種經歷,周海門對此有記敘: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構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暝,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里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學脈循軌。[4]860-861
在此之前,近溪曾拜師顏鈞(字子和,號山農,1504—1596),學習“七日閉關法”,有一段“體仁”的經歷。[9]32-33海門所記的這一年是嘉靖癸丑(1553),距嘉靖庚子(1540)近溪拜師山農已有十幾年之久,從老翁“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暝,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以及“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的語意來看,可見近溪是以強力方式來識取心體,以致執著過多,反而并未悟到活潑脫灑之真正仁體,還沒有形成獨屬自己的學術主張。海門的記載是間接描述,實際上在此之后近溪還有關于神秘體驗的直接描述,可以與海門之述相映照。近溪謂:
予初年也將自己本心,勉力探討,于生來氣性,亦強力調攝。及弱冠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想圣賢或可有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謂賢輩為學,盡在辛勒,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用者不是真功,乃妄意欲希圣賢,此何異吹噓螢火以燃燈燭,滿蓄汞銀以供灌溉?徒竭心神而后悔莫免也。予時聞言,亦為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甚不甘心。因思圣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于今見在,于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而一時透脫,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片大海,其海亦不見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闊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其生化雖混涌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靈妙。……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4]355-356
從這里看,海門所述近溪之神秘體驗,是近溪自述的第二階段。近溪指高人來自外道,當指佛氏無疑,陽明心學與佛氏有思維形式上的關聯,但佛氏隔斷天地萬物和人倫日用,與儒家經世盡倫不同,故近溪“甚不甘心”,于是再從儒家經典探尋原義,以神秘體驗的方式,終得換過一番的“身家境界”,與儒家神圣之道融為一體。近溪晚年強調“不學不慮”之學并將之視為為學宗旨,此次體悟當是重要促轉。由此亦可看出,如近溪等陽明后學,他們的神秘體驗,并非追求與人倫世道、圣賢功業相離,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與之相接,以實現儒家所倡導的人身價值和社會理想。
在悟得良知心體之后,更重要的是將良知心體的本有要求貫徹到生活實踐之中,以實現神妙與神圣的合一,對此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例子來加以說明。黃宗羲贊龍溪“先生林下四十余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不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為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2]237。這是龍溪在神秘體驗之后的為學實踐。據《年譜》記載,心齋53歲時,家鄉大饑,心齋勸鄉之富者賑濟災民,同時面見御史讓其“充惻隱之心”,并申之以“某固不忍民饑,愿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不忍民饑,充之以及民何如”,御史聽后“慨然發賑,造門謝先生”。[6]74這是心齋以民為親的生活實踐。羅近溪記顏山農:“后潛居山谷,歷九月余,歸則與兄論倫理道義,沛然若決江河,鄰族爭聽,興起聯會,人皆躬行實踐,無不改舊從新,遂名‘三都萃和會’”。[4]677山農所建“萃和會”盡管成立不久就消失了,但其社會實踐意義卻不容忽視。吳震先生在詳盡分析近溪的生平學履和哲學思想之后,認為近溪“略帶神秘色彩的悟道體驗,以及積極從事講學化俗的社會實踐,也處處體現出泰州派下的心學家的行事作風”[9]517-518,可以看出近溪的神秘悟道和社會實踐并不矛盾,而是將道之神妙和神圣融合在一起。此外,如徐愛、聶雙江、羅念庵等人,在神秘悟道之后,他們的社會實踐更篤定,其行為也更具道德示范作用。此類社會實踐的代表人物,不能盡言,我們在這僅以此為例,約略可以窺見陽明后學是如何將道之神妙性和神圣性流貫在他們的生活世界里。
陽明后學這種對心體本性的體悟模式和社會實踐的展開方式,在陽明時早已有之。陽明被貶至貴州龍場后,生存環境惡劣,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然而正是在極端困難條件下,陽明“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3]1354。這次神秘體驗確立了陽明對“吾性自足”的認識,陽明由此拋棄朱學求理于事物的模式,轉而建立起心學體系的理論根基,自此汲汲于行道,終得光明之境。龍溪、心齋、近溪等陽明后學的體驗與實踐之路,與陽明有一致之處。
陽明后學中的神妙境界論,帶有傳統儒學與陽明思想的痕跡,但又從不同側面豐富和發展了傳統儒學,對陽明創立的良知學說也有繼承和傳揚。他們神秘悟道的經歷,雖有離奇成分,但他們所悟之道都和良知心體有關,或指向良知之“無”,或體現為日用之“有”,或標識萬物一體,或表征真切的道德生活實踐,始終未離儒學矩矱,傳統儒學關注個人心靈和社會責任,與這種思想體悟有相契之處。此種神妙體悟,與其說是個體心靈糾結之后的瞬間洞達,倒不如說是這些儒者對道德性命不懈追求的社會責任,這種境界只有大智大慧的儒者在貫之以永不停歇的道德實踐之后,才能順利實現。這樣一來,神妙體悟其實就是一種境界,而且是極高的一種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