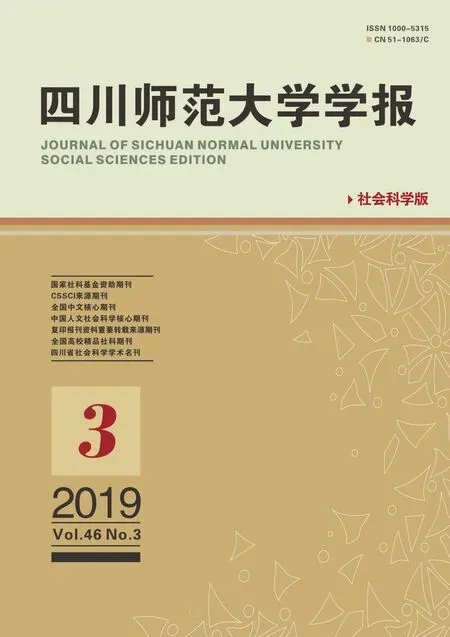經濟發展與勞動者處境惡化
——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內在社會根源
(四川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成都 610066)
明治后期,日本產生了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出現,從外部考察,是由于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從內部考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明治時期,由于新政府“殖產興業”國策的推行,社會經濟出現了迅猛發展的態勢,各行業經濟部門的勞動者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二律背反”現象——生產力和社會進步導致的社會經濟發展與勞動者處境日益惡化的這一現實矛盾卻并未能避免,勞動者的待遇和處境并未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迅速提高和改善,反而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地勞動者處境惡化的信息不斷流傳于世,引起了輿論的強烈關注,社會對勞動者的人文關懷因此與日俱增。隨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這種人文關懷思想逐漸演變,導致社會主義思潮的萌發。因此,要研究日本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生長,不能不深入考察明治時期生產力發展前提下勞動者的處境惡化狀況。本文擬依據當時的史料,對這一問題作深入考察,以探索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萌發的內在社會根源。
一 明治時期日本經濟迅猛發展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依靠國家的力量,在日本全國推行“殖產興業”的國策。政府施行各項政策,推動資本主義產業在日本各地興起和發展。在這種政策的扶持下,各行各業迅速崛起,加上歐美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社會生產力迅猛提高。到明治20年代后,日本經濟呈現出百業興旺發達的局面。
日本明治時期經濟迅猛發展的表現之一就是鐵路大量開通。“經濟發展,交通先行”的規律,在日本得到充分展現。鐵路建設投資較大,一般是先由國家籌資興建。所以,率先興建的大多是國營鐵路,主要有1872年東京-橫濱鐵路、1874年大阪-神戶鐵路。以后,隨著私人資本的積累,私營鐵路也很快出現,具有代表性的是由華族出資的私營鐵路公司“日本鐵道”,1884年興建了上野-前橋鐵路。所謂的“鐵路熱”開始興起。1886年就有伊予鐵道、山陽鐵道、甲武鐵道被計劃組建,到1890年又有干線大鐵路、地方性鐵路的規劃接近50條。[注]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鐵道史研究》,東京:日本評論新社,1963年,第34-35頁。到1885年有100條私營鐵道線路運營,到1889年達到了516條,實際數量超過了官營鐵路。1889年官營東海鐵路線的新橋-神戶線,1891年日本鐵道的上野-青森線,1894年山陽鐵道的神戶-廣島線等主要干線全部貫通。1892年的《鐵路敷設法》確定了日本全國鐵路網絡的基本構想。1886-1893年,在礦工業運輸部門社會資本金12382萬中,鐵路資本占了41%。[注]④⑥⑦山本義彥:《近代日本経済史》,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92年,第32頁;第33頁;第34頁;第35頁。鐵路運輸在當時的亞洲首屈一指,它不僅直接創造了產值,而且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帶動了其他各行各業的迅速發展。
在各行各業中,棉紡織業的發展較為突出。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紡織設備的更新,日本國內棉紗生產和出口呈上升趨勢,相反國內進口棉紗則呈下降趨勢。國內棉紗生產若以1880年指數為3,到1890年上升到100,而到1902年則迅速上升到735,比22年前擴大了244倍;出口棉紗到1890年才開始起步,指數只有0.2,到1902年出口指數上升到了188,12年擴大了940倍;相反,進口棉紗數量則大幅度下降,1880年的指數為88,1902年下降為9,經過22年幾乎下降了90%。[注]高村直助:《日本紡績業史序說》上,東京:塙書房,1971年,第146頁。這說明棉紡織業的水平在短時間內已大幅度提高,逐漸向歐美各國靠近。同時,日本棉紡織業的規模也逐年擴大。1883年,機械紡紗開業的只有大阪紡織的1萬錠規模的公司,到1887~1889年則有10家左右同類公司開業。由于不少原本與棉紡織業無關的大城市商人、地方商人、地主等加入投資,棉紡織業規模迅速擴大,1887年達到7.6萬多錠,1889年猛漲到21.5萬錠,1893年再度上漲到38萬多錠④,是1887年的5倍多。到了1912年(明治45年),紡錘數(包括捻線紡錘)達到了210萬錠[注]⑧⑨⑩帝國通信社:《明治大正產業史》上卷ノ二,東京:クレス出版社,1999年,第1332頁;第147頁;第35、36頁;第13頁。,相當于1893年的6.3倍。大量的紡織工人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
明治日本經濟發展另一個突出的經濟部門,就是采礦業和與之相關的冶煉業的迅速發展。例如銅礦生產發展較快,銅的生產量1881年為4772噸,1892年達到2萬噸,為1881年的4.2倍,11年間增長了300%,其中80%以上的銅用于出口。當時有三大著名銅礦:別子、小坂、足尾。其中,足尾的銅礦還建成了日本最早的水力發電所,1890年豎坑排水已電力化;由于電纜索道搬運的近代化,1893年又采用了轉爐,將以前需要32天的冶金工程縮短為2天。⑥這樣,到19世紀90年代前半期,足尾銅礦完成了采礦、搬運、制銅的近代化。
這一時期日本煤炭業也取得了長足發展。19世紀80年代日本煤炭業迅速擴張。1883年,日本煤生產量為100萬噸,1894年便增加到427萬噸,翻了4倍,其中出口量占40%-48%。筑豐地區用揚水泵解決了排水問題,導入一部卷揚機,使煤炭出井機械化,再由鐵路運往各外貿港口輸出。這些煤礦最大的特征,就是大多由國家開發后賣給私人企業,如三池、高島、別子、足尾、小坂等煤礦分別出售給了三井、三菱、住友、古河、藤田等與政府有關系的政商財閥,使他們私人的資本在煤礦業中占據很大比重。另外,與設備近代化的趨勢相反,三池銅礦利用犯人勞動,煤礦和礦山建立在庫房和工地宿舍制度基礎上的過分殘酷的持續勞動也使人難以忘卻,并引起社會關注。⑦
明治20年代以后,日本農業比起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來說則顯得相對緩慢。本來,由于受到較重剝削的農民不斷騷動,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已經將農民的地租稅率從3%下調到2.5%,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稅負,加上銀價和紙幣價格下跌、糧價上漲,農民獲得的實際利益大為增加。⑧但是,整個農業比起工業來說,其發展顯然緩慢得多。例如,糧食省產糧1878~1887年的指數如果為100,1888~1897年只上升到120。糧食雖然百分之百能夠自給,但國家對農業稅征收仍顯較重。據統計,當時國稅中有50%~60%來自于地租⑨。對于本來就不太發達的農業征收重稅,勢必造成農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總之,到明治晚期,日本完成了第二期的產業革命⑩。由于生產水平在亞洲首屈一指,并迅速縮小與歐美各發達國家的差距,產品質量在亞洲領先,使日本的出口額逐年快速增加。1882年,全國出口額為0.3億日元,到了1897年上升到1.24多億日元,比15年前上漲3.1倍;到了1908年,出口額達到4.24億多日元[注]帝國通信社:《明治大正產業史》上卷ノ二,第312頁。,比26年前上漲了13倍!這使日本積累了大量財富。據不完全統計,到1910年,日本的固定資產已達到294億多日元[注]日本銀行統計局:《明治以降本邦主要経済統計》,東京:並木書房,1999年,第20頁。,國家經濟實力大增。
二 勞動者的處境惡化
按常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相應的物質文明的提高,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的待遇和處境也會得到同步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屬于后發的趕超模式,無論是生產部門的安全設施還是資本家管理的文明程度都遠遠沒有同步跟進,以致在極短的時間內資本原始積累尤為迅猛,各行各業勞動者的處境卻愈加惡化,呈現出一種“二律背反”現象——即經濟發展與勞動者待遇成反比。這一狀況比較典型地表現為煤礦礦工處境悲慘、其他行業勞動者處境惡化、農民及城市貧民生存異常困苦。
(一)煤礦礦工處境悲慘
最為典型的是當時私人經營的高島煤礦工人的悲慘處境。高島煤礦作為三菱資本的一個據點,位于長崎港。它“系30年前荷蘭人某某所發現,其后經10余年,由后藤象次郎創辦采煤事業。后將之讓渡給三菱公司”[注]④⑥⑦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東京:日本評論社,1993年,第3頁;第3頁;第4頁;第4頁。。這座煤礦從外觀看“壯麗罕見”,似乎工人們所處環境很好,但實際上在里面的礦工工作狀況卻異常艱辛。高島煤礦工人的悲慘處境,被親自到煤礦考察的政教社社員松岡好一、吉本襄以及作家今外三郎等人所揭露。
松岡好一撰寫的《高島煤礦之慘狀》一文,于1888年6月18日登載于政教社辦的《日本人》雜志上。據該文報道:“三菱公司一取代后藤氏執掌炭礦事業,便設立千古未曾有之壓制法,將作為人類的三千礦工使役驅逐,連牛馬也不如。慘淡狀況如佛教所謂閻羅殿,礦工宛然如餓鬼。事務員、海岸管理員、小工頭、宿舍監、計數員等,如青鬼赤鬼,礦井宿舍長如閻魔大王。”④礦工的工作時間乃為12小時,大致分為白日方和夜晚方,白日方早晨4點下坑、下午4點回宿舍,夜晚方下午4點下坑,次日早晨4點回宿舍。礦工不僅勞作時間超長,而且勞動強度異常高。據該文描述:“其礦工所干12小時勞業苦役,首先在坑內一里到二里的場所,從脊背也無法伸直的煤層間屈步曲立,用鶴嘴鋤、地雷、火棒等,一塊一塊采煤,然后裝入竹畚。重量15貫至20貫,邊忍邊爬,一町二町地擔著,運到蒸汽軌道。還要擔任其它如碎巖、搭框等危險工作,看門、通風等煩惱的任務,實在是慘不忍睹的場景!”除此而外,勞動環境也十分惡劣。據描述:“由此漸漸進步,若下到被稱為‘蒸汽卸’之大道,恰如東京的瓦斯燈,照著千百盞洋燈,明晃晃的情景,感覺在地底看見了不夜城。煤箱升降其間,轟轟貫耳,行步之危險亦不可言。氣溫隨著下到地底而逐漸炎熱。到最極端溫度計達華氏百二三十度[注]華氏120度相當于攝氏48度。。礦工在炎熱瘴煙之間不間斷勞作,汗流如洗澡。空氣稀薄,呼吸困難,煤臭穿鼻,幾乎不可忍受。”⑥可以看出,盡管采煤、照明硬件設施已經大為進步,但有關人身保障的通風設備、運輸設備等卻沒有同步改善,導致工人勞作條件異常艱辛困苦。在管理方面,資方也完全無視工人的基本權利。據該文描述:“盡管在如此令人驚訝的環境從事勞作,但作為煤礦宿舍的規則,也不給予分秒休息。擔任小工頭者,在采煤場所巡視監督,若有稍微懈怠者,便以攜帶之棍棒毆打苛責。是余目擊小工頭等,豈有不稱為青鬼赤鬼之理?又礦工中有人不堪過度勞累申請休息,或有違逆宿舍監之意者時,為警告眾人,將其礦工反手捆綁,吊在梁上,雙腳離地數尺,加以毆打。讓其他礦工觀看之。”⑦如果礦工不堪礦業待遇,企圖脫離該島,但若逃跑失敗,便會被海岸管理員等逮捕和處罰,“或踢或打,或倒立或懸吊,其苛責之殘酷,茍具備人情者不能為也”。管理人員完全將工人當作牲畜對待,沒有絲毫人權可言。即便工人有病也不給認真治療,而是為了保住煤礦,采用消滅病人的殘忍手段。據該文報道:“明治十七年夏,該島被霍亂病侵入,三千礦工之大半即超過1500人因該病而死亡。然而,煤礦宿舍不問其死者或未死者,從發病一天起,就將之送至海邊焚燒場。放在大鐵板上,5人或10人一組焚燒。”[注]②③④⑤⑥⑦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4頁;第7頁;第7頁;第9頁;第14頁;第22-23頁;第24頁。尚未病死者也被焚燒,礦工處境真是慘不忍睹!
另一政教社社員吉本襄到高島煤礦呆了一年,親眼目睹了礦工的悲慘遭遇。1888年7月,他將親眼所見寫成《向天下人士訴說》一文,揭露了高島煤礦的礦工慘狀。文章認為,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步,所有的資本經營都“不可不圖欲使社會幸福進步之事”,決不能公開施行違法之事,但他在高島煤礦之所見卻十分怪異,“三千余名同胞無罪而在孤島中成楚囚之身,無故而在無限之坑底嘗努力之苦。其悲痛慘酷之狀況,以涂炭倒懸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會旁觀之不動手相助”。②文章指出,從事采礦業本來就是百業中最艱辛的行業,“其勞多,其樂少。素來作為其業,根據勞苦的報酬,工資較其他力役者,常常不得不貴幾成”,即工資應當更高一些,而且礦工可以根據身體耐勞狀況,決定自己是否繼續在煤礦中工作,“礦工自身任意出入外,不能從旁干涉”,但高島煤礦的實際情況卻是礦工“日益勤勉卻日益困苦,愈益勞作卻愈益貧窮。欲去而不能去,欲訴而無處訴”③,礦工處境猶如囚徒。不久以后,吉本襄又發出《陳述高島煤礦礦工之慘狀,稟告社會志士仁人》檄文,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高島煤礦礦工的悲慘處境。他指出,這些礦工與社會普通人一樣,都是日本的善良百姓,都應當受到政府法律保護,成為擁有相當自由權利的人,但他們“一旦被誘拐入彼島,下到黑暗得白天如同黑夜之數十仞之井下,呼吸冬季仍達百余度以上之炎炎空氣,過度勞動傷害肢體,深埋于塵芥,一身比昆侖奴還黑。雙眼炯炯,與手足一起恰如石榴之裂口。鬢發蓬松亂垂,身著一寸布帛,疲憊困頓,晝夜搬運煤塊。其狀態,曾聞鬼界之流人也蓋不至如此”;接著,他又進一步從人的正常需求分析了礦工們的絕望境遇:“生于人間,終身沒有夫婦團樂、父子兄弟相見之期。旭日東升時,遙望東方,空慕家鄉。夕陽西下時,面向西方,祈愿早至死期。悲愁哀鳴無處訴說,或從千仞絕壁投身成海底之藻屑,或向百丈巖角撞頭灑鮮血于綠苔。憐火陰陰,冤鬼夜哭,悲風颯颯,游魂彷徨于何處?滿島荒草,共顯悲哀之色,環海激浪,互呈忿怨之狀。嗚呼傷哉彼等之境遇!嗚呼悲哉彼等之心情!世雖太平,而彼等常倒懸受苦,時雖豐饒,而彼等常不免凍餓之憂。”④吉本襄飽含對勞動者的同情之心,將礦工們遭受的極度悲慘境遇揭露得淋漓盡致,力圖喚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想法拯救礦工于水深火熱之中。
這些有識之士的揭露文章流傳于社會之后,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針對高島煤礦的礦工悲慘遭遇,社會媒體展開了熱烈討論。例如1888年7月6日的《福陵新報》就發表社論《誰說高島煤礦無慘狀?》,生動描述了高島煤礦礦工遭受的非人待遇:“至五六年前,有違背該礦規則者,被倒懸于‘警眾臺’,用生松葉熏之。擔心其嚎叫之聲外泄,用線縫塞其口,或恣行慘毒,用木棍插入其肛門等”,礦工們甚至連人身自由也喪失了,“一旦陷于該島者,終身無脫離之期。不免空成孤島望鄉之鬼,與以前無異。故雖其后,平安無事返回鄉里,與父母妻子再聚,得到一家團樂之歡者,始終未有一人”。⑤社論深刻揭露了高島煤礦礦工的悲慘現狀,礦工不僅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而且受到類似前資本主義社會奴隸般的超經濟強制。另一位作家今外三郎于1888年在《日本人》發表評論文章《高島煤礦》,揭露了高島煤礦礦工因過于勞累而不能持久工作的狀況。他從生理學角度考察認為,人的勞動最大限度不可超過12小時,但是高島煤礦的礦工不僅僅是勞作時間超長,而且工作環境十分惡劣,“無法適宜保持生理循環,則不能維持生命”;他進而指出,“此所謂12小時者,乃云尋常一般之勞動。并非云在如彼之高島煤礦極熱之場所,呼吸最臟之空氣,從事牛馬也不如之勞動也。想來高島煤礦之礦工,服人類無上之苦役,卻不能永久保住生命也”。⑥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辛苦勞作的工人們生活待遇如何呢?他一針見血地分析道:“何況如彼之食物,終究并非按勞力構成正常比例者呀!彼之礦工乃人類也。若然,沒有被排除此生理原則之外者。如今日,或可堪一時,但至后來,消耗復補不得其當,營養組織不能完成其功能,以至運動器官不能發揮作用,只能擺頭臥死病床。……余輩于此斷言,如使役高島煤礦礦工之今日,就生理上而論,決不可永久持續!”⑦這種竭澤而漁式的沉重剝削和人身壓迫,最終將會導致正常的煤炭生產難以長久持續。
1906年4月,另一進步雜志《光》發表《高島煤礦之內幕(三菱公司的暴行)》,也披露了煤礦工人遭受迫害的情況。文章指出:“高島煤礦與其他地方不同,作為從海底挖掘的礦井,在水面下,淺有五六百尺,深則達千尺到二千尺。這樣,由于通風的不充分,在最底下時,呼吸不暢會感到非常痛苦。若非相當熟練者,簡直難以忍耐。尤其是在夏天,溫度異常高,達到華氏100度至120度。在這樣的坑道內作業的礦工,其艱難隨處可見。本來高島煤礦煤層厚重,瓦斯頗濃。雖然公司也加強注意,但正如前述,若不能使通風充分的深井,動輒有爆炸的恐懼,但禁止談論危險。而且,坑道內十分傾斜,坡度至少有二十五六度至四十度,這樣,即便用蒸汽力搬運的采煤箱,也會一天數次翻倒或脫線,殺傷人或撞壞坑道內支柱,導致天棚塌下等,危險狀況不勝枚舉。”[注]②④⑦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第31頁;第32頁;第35頁;第15-16頁。在這種狀態下,平時即便瓦斯不爆炸,每天也會看到工人傷亡。根據礦工所說,每天只死2名是公司所預期。文章哀嘆:“嗚呼!可怕的資本家!他們認為傷害工人的生命,比拋棄一塊煤炭還要輕。”②文章還揭露了煤礦管理人員對工人的身心迫害情況。當時的監工等管理人員,如果對工人有所不滿,便采取各種手段迫害工人,最輕的是罰款,即克扣工人應得的工資,重則采用人身傷害,“懲罰最重的,是在他們中被稱為‘鮪’的刑罰。其法是將雙手捆綁在背后,以腳趾頭剛剛接觸地面為尺度吊起來,暴曬于坑道口人流最多處。其狀態很像吊鮪魚[注]鮪魚即大金槍魚。,故得名”④。這種壓迫實際上也已類似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超經濟強制。
(二)其他行業勞動者處境惡化
除了煤礦工人處境十分悲慘之外,其他企業的勞動者境遇也日趨惡化。1890年10月26日,《讀賣新聞》發表了山口縣人北公輔寫的紀實文章。他在旅行途中遇到3人,聽聞東京北邊37里遠的野州足尾銅礦的礦工處境悲慘。他將三人所談記載如下:“若世界上真有地獄,那銅礦正是現世之地獄。我們3人不曾知道銅礦實況,最初的目的是決心在這個地方打工幾個月,然后買些衣服,攜帶旅費就回家。豈料在銅礦不僅每天1錢也存不起,而且還增加了借債,離開無期。偶爾患病希望休息1天,但那些殘酷的飯場長不會輕易批準之。疾病日益加重,借債逐月累積,進退維谷,遂產生逃走之念頭。然而如果暴露,會蒙受殘暴的斥責,有時幾乎置于死地。因此,不能企圖輕易逃脫,何況老幼耶?只有日夜仰天嘆息不幸。我們3人僅僅能夠脫離虎口,出到獄外的世界,但身無分文,昨天起便沒有吃飯。然而,若追憶在彼之銅礦之當時,空腹豈難忍受耶?”其中有一人甚至將監獄和銅礦的條件和待遇對比后說:“我曾于鄉里醉酒后與人打架斗毆,因傷人而被關進監獄。但獄吏待遇比飯場長更優厚,何況獄中重視衛生,故如其伙食遠遠優于銅礦。若礦工為不顧廉恥者,皆更喜歡去進入監獄。”[注]⑥北公輔:《足尾銅山坑夫の慘狀》,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社會篇下,東京:日本評論社,1993年,第219頁;第228、224頁。聽了這些訴說,將信將疑的北公輔親自以礦工身份進入足尾銅礦開展調查,他發現礦工在里面除了勞動艱苦、收入很低之外,根本沒有人身安全保障,工人們的生命完全被視同草芥。例如出入礦井必須攀登很高的直立梯子上下,經常很多人同時攀登;如果其中1人不慎從上面跌落下來,下面的人也將會被砸中,一起跌落井底喪命;如果有人設法逃走,被抓回來后,將會被活活打死,而礦主不負任何法律責任。⑥這與高島煤礦礦工受到的超經濟強制大同小異。同時,由于規模擴大過于迅速,安全設施無法同步完善,導致銅礦中毒事件時有發生而遠近聞名。
紡織行業的工人狀況也大同小異。1904年2月7日,《平民新聞》第13號刊登文章《紡織女工之實狀》,揭露了紡織女工的悲慘境遇。文章指出,女工通常13歲以上要簽3年的合同。按合同規定,每天勞動時間12小時,分晝夜兩組輪流,每月休息4天。工作這么長時間的女工,每天收入僅有18錢,月收入僅有4元68錢;伙食1天有1次添加煮蔬菜,其余2頓僅有咸菜,“見到她們在宿舍中起居的模樣,大抵臉色蒼白,瘦弱,全都有氣無力,如睡著了一般,呆然張口,熟睡得連躺到枕頭外都不知道……患病主要是砂眼和肺病也。可能是處在如煙般的棉塵中之結果。平常大約有30至70名住院,但去年末大概患病者也要出工,所以僅有16名住院者。特殊重癥者迅速送還鄉里”,而且該文在比較其他公司后指出:“此公司女工待遇被稱甚為良好,而其實狀如此。其它各公司之殘忍可想而知。”⑦可見,日本近代紡織行業的迅猛發展,無不浸透著紡織女工們心酸的血淚。
1898年2月初,工人們手中流傳的《促進改善待遇大同盟》的秘密出版物,也強調了日本鐵路司機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該出版物指出:“公司方面對我們的待遇,是越來越殘酷,不!簡直是在愚弄我們……司機們不得不俯首帖耳,像奴隸般勞作。一旦表示不平,便會被放逐到人人厭惡的五線區去,像懲罰仇人一樣暗地里白做苦工。如此這般,若不堪忍受不平等待遇,為了一身清凈而欲辭職,也不易獲得許可。若硬要辭職,則不是被免職,就是在采取各種妨礙其就業的手段之后,才獲得允許。妨礙自由權利也甚為厲害。大公司剝削人的手段真可謂無所不盡其極!”[注]②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202-203頁;第214頁。火車司機應當是技術性很強的工種,他們都受到如此待遇,其他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工種的工人待遇可想而知。兩年以后,東京馬車鐵路公司的工人們對進步報紙《萬朝報》記者訴說自己的處境惡化,報紙作了詳細報道。據工人訴說:“我們清晨五點就得上班,晚上過了十二點才能歸家。偶然有事,又得增加一、二小時的勞作。但次日上班若遲到,便會受到很重的罰薪處分。一旦被馬車鐵路公司雇用之后,都必須宣誓:無論發生任何事情,皆不得辭職。然而,公司方面雖然明確表示,連續服務二年以上者,可領取一百余元的賞金。但迄今為止,幾百名司機、售票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者,不,就連服務五、六年以上者,也幾乎沒有得到那種賞金者。真是奇怪至極!”工人們還對公司強加給自己的超長工作時間表示了極大憤懣:“我們每天要從事19小時的勞動,而且還動輒要延長到20小時以上。在這期間又無分時休息,甚至連吃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一個月所得,僅僅十一、二元。世上勞動困難者素來不少,但還有比我們的勞動更困難者嗎?我們被馬車鐵路公司雇傭之后,必須預先繳納保證金若干,接著每月要繳會費若干。它雖名為會費,但其實不外乎仍為用來束縛我們不得離開公司的保證金。故工作不滿2年而離職者,會費就被全部沒收。”②鐵路工人們不僅受到殘酷的經濟剝削,實際上在人身上也被資本家束縛而失去了自由。
不僅私營企業的工人處境艱難,而且連官營企業的工人處境也同樣日趨惡化。例如1907年7月《社會新聞》第6號發表文章《佐世保工廠之現狀》,揭露了位于長崎的大城市佐世保的官營工廠里勞作的童工慘狀:“佐世保很有名的是死傷者多,童工多,待遇慘絕悲絕。特別是童工的實情,就是在夏天都要打冷顫。還天真無邪的十一、二歲的兒童600多名,全都赤裸裸地勞動。而他們全身都有燒傷。只有一只眼睛閃閃發光,站立著勞動。看到他們從早到晚,被趕進大人無法出入的很小的鍋爐升降口洞內,目光呈現出悲哀,實在是此等少年也。”[注]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44頁。這些尚未成年的兒童都受到如此虐待,無法受到法律保護,說明作為出資辦廠老板的政府,與殘酷剝削工人的其他資本家一樣,并無本質區別。
(三)農民及城市貧民生存異常困苦
當時農民和城市貧民的生存狀況也不容樂觀。自由主義思想家大井憲太郎(1843—1922)歷來對下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十分關注。他針對社會上有人說農民困苦是源于懶惰的論調,分析了農民的困苦狀況及其原因:“山間僻村之民當然是一般農民之狀態,大體相同。周歲無一天之快樂,披星而出,戴月而歸。若問衣食,僅不足承受饑寒。至極貧者,特嘗辛酸,粟飯芋餅,敝衣跣足。以至發出感嘆,將人幾乎等同于牛馬!”大井深刻地指出這種狀況并非個別現象,而是當時農民普遍的生存狀態:“夫如是農民一般之情態,盡管勤勞簡樸,但家無儲糧者比比皆然。若見勤勞節儉如彼,卻幾乎不免凍餒,則可推斷得知,皆由我國稅法苛刻,故只能使農民無法富裕。”[注]大井憲太郎:《時事要論》,平野義太郎:《馬城大井憲太郎傳 主要著作》,東京:大井馬城傳編纂部,1938年,第371頁。他認為,政府對農業征稅過重,是導致農民雖然辛勞卻不得溫飽的根本原因。
對此,大井反思了日本農業發展的歷史與農民處境的關系,認為:“這樣,在我國農民中,因無多余收入,一旦家庭遭受不幸災厄,數代不能償還之。耕種三代或四五代之前就已典質之田地,雖然名為自己所有地,但實際上變成了佃農。又有數代之前便租借他人土地耕種而謀生者。若直言,我農民概數代之前便已成為窮人也。在農民中,能獨立生存于安心之地者,寥寥無幾。夫如是,我農民中,大農即有相應資產者,不足十分之一。十之二三為中農,其他應為窮民。則僅怠惰便致貧之評論失當也。今之貧民,大抵乃世襲貧乏者也。故縱然沒有怠惰,但素來無多余收入之貧民,數代之間,必然由于疾病或其它災厄,流離顛沛,雖不想陷于貧困卻不可得也。”[注]大井憲太郎:《時事要論》,平野義太郎:《馬城大井憲太郎傳 主要著作》,第371-372頁。而且大井認為,這種農民貧困狀況,不但沒有因明治維新后政府法令規定地租減輕而有所改善,反而有逐年加劇的趨勢,“至近世,世事愈益極其紛擾,世間加倍疲弊人類生計之困難,一日甚于一日。蓋由此陷入多重困難。今既觀平民社會之現狀,食就粗惡,衣極襤褸,鵠形菜色,簡直難以避免饑餓。實堪憐憫!若徐徐推論其慘狀,還不如寧愿成為受人喂養之牛馬。人若無愛惜生命之天性,皆只有不堪勞苦而上吊了事。”[注]③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13頁;第342頁。也就是說,如果繼續維持現狀,而不實行社會改革,貧困農民只有死路一條。
社會主義者鈴木生也在《社會新聞》1910年第66號發表文章《橫暴的地主》,揭露地主通過提高地租加強對農民剝削的社會情狀。文章指出:“租米1石不通用1石,必然每石分派額外增加5升米,稱之為‘込米’繳納給地主。此已成地方持續之習慣。于是,此次因重新訂立加租契約,佃農方面當然認為這種不合理習慣應當廢止。去年冬天基于加租規則欲繳納年貢米的時候,地主方面稱不能改變習慣而要求込米。佃農不答應之,遂提起此次訴訟,直至被強制執行。”文章進一步指出,這種強制執行加租是十分蠻橫,不顧農民基本生存條件的野蠻行為:“而且此強制執行極為酷烈,聞所未聞。若舉其一例,佃農感到最痛苦的是,連日用品都被沒收。佃農交租要做各種準備,特別挑選品質而包裝庫存,所謂年貢米不能到手,就沒收充作食糧的粗雜米。佃農在租米上有一定規矩,不能將年貢米充作食糧,即事實上構成奪走食糧之殘酷。可云真是極為橫暴!”③通常說的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言下之意,還留下了維持生存的必要勞動力價值。但是,由于農村文明程度更低,所以甚至連農民維持生計的必要勞動力價值也要被掠奪,農民的極端困苦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近代著名的社會主義者片山潛(1859-1933),1903年曾在政論著作《我社會主義》中細致分析了當時日本貧民大眾的悲慘境遇:“若夫妻倆平安無事勞作,一日收入50錢,一月所得14元,經營6人的家庭生活,彼等乃貧民窟之居民也。房租1月3元,6人之家庭每月用12、13元維持生計。常食南京米,丈夫有時因感冒休業,收入減少時,妻子只能暗地里以剩飯度日。一日飯米至少也得1升5合,每月4斗5升,雖下等南京米也要支付6元。剩下3、4元,從蔬菜到豆醬、醬油、燃料、油,以及其他衣服、鞋襪等,也必須支付。偶爾有孩子生病,也不能請醫生治療,要買藥充分服用也很困難。”而且他還指出,這是在經濟比較繁榮的順利時光里勞動者的狀況,但若遇到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大大增加的困難時期,勞動者又如何生存呢?他指出:“若一朝因產業不景氣而失去工作,處于失業狀態,又因歉收而物價騰貴,此家庭之困難,遠非通常人之智能所能想象的。南京米變成剩飯,放棄豆醬、醬油而用鹽。在如此場合,孩子由于饑餓而悲鳴、痛嘆,會妨礙母親工作。老母親由于貧血病而身體無法動彈,丈夫因感冒而終成肺病。母親操心的結果,引起神經疼,一家內的慘狀呈現無法描述之悲慘。此決非吾人僅僅記載特殊家庭之狀況,如今城里150萬人口中,沉淪于如此悲慘境遇者,實為多數也。”[注]片山潛:《我社會主義》,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5卷,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第46頁。由此可見,城市底層勞苦大眾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已成普遍狀態。
三 對社會不公正的譴責、反思及其應對
經濟迅速發展與勞動者生存環境惡化的現實矛盾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不少有識之士對這種不公正狀況進行了強烈譴責和批判,同時也表達出對下層人民的同情與關懷,并開始反思如何改變這種不公正狀況。
例如高島煤礦工人們的惡劣境遇,引起了社會廣泛的同情心。當時的思想家將這種殘酷對待工人的制度斥責為“奴隸制”。著名思想家、社會評論家三宅雪嶺(又名三宅雄二郎,1860-1945)就認為礦工受到的是奴隸般待遇。1888年,他在《日本人》雜志發表文章《應當如何對待三千奴隸》,將高島煤礦壓迫礦工與古代奴隸制下對奴隸的虐待相比較后指出:“一聽就厭惡的奴隸陋習,近來存在于肥前之高島也。虐待奴隸,將人與牛馬同樣對待,被認為是前代異域之惡弊,今存在于號稱我國第一煤礦的肥前之高島也。無罪而受皮開肉綻之鞭笞,成為奴隸之地位。日夜孜孜勞動,而苦死于路旁,乃奴隸之命數也。世上雖有種種值得憐憫之事,但就中沒有比奴隸更可憐,沒有比奴隸更可嘆,沒有比奴隸更應需要迅速救助。嗚呼!彼高島實際大約三千人在勞苦、痛疾、呼號、困倒,繼續降于餓鬼之道,將墮落于阿毗地獄。”[注]②③④⑤⑥⑦⑧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14頁;第17頁;第7頁;第7頁;第9頁;第8頁;第10頁;第24頁。三宅雪嶺在文中,將掙扎于煤礦井底的工人們與地獄中受煎熬的奴隸們相提并論,對煤礦工人們奴隸般境遇進行強烈抨擊的同時,其深切同情也溢于言表。不僅如此,三宅雪嶺還進一步指出,這種極不公正狀況是阻礙日本文明進步的不可忽視因素。他說:“高島煤礦方虐使三千奴隸,乃將妨礙正當之工業者也。高島煤礦方虐使三千奴隸,乃毀傷具有慈仁之名的帝國人民之體面者也。高島煤礦方虐使三千奴隸,乃欲消滅銳意推進文化之東洋全般之榮光者也。高島煤礦方虐使三千奴隸,乃欲阻礙經千載萬載進化發展而來之人類社會之大道者也。”既然如此,他強調,為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必須想方設法解救這些類似奴隸的工人,“居住煤礦之三千奴隸,當然必須急速救助。今聞非常之慘狀,意迫語盡而不知所言。待情緒之穩定,更欲陳辯救助之企圖”。②
吉本襄在揭露了煤礦內工人們的種種慘狀之后,強烈抨擊這種剝削制度超過了遠古時期的奴隸制,“至如疲憊困頓,只能等待朝暮死去的高島煤井礦工,吾人即便欲坐視之,卻不忍坐視也。高島煤井礦工不能沒有工資,然而,實際上卻有種種詭計奪取也,一錢也不許到手。高島煤井礦工雖非失去進退自由之人,然而,實際上遭受嚴厲管束,一步也不能走出島外。驅役比牛馬更甚,束縛比奴隸更甚”③。他在此分析了礦工們的實際處境,名義上是有工資的雇傭工人,在法律上也是自由人,但這些法定權利皆被資本家剝奪。他們一方面工資不能按時按量領取,另一方面連人身自由也受到極大限制,比起奴隸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譴責了社會上大多數人和國家法律制定者對礦工的悲慘境遇無動于衷的冷漠態度,“其悲痛慘酷之狀況,以涂炭倒懸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會旁觀之不動手。幾乎如為秦越之思。故抑果如何”④?他主張應當千方百計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勞動者,因為“彼等與余輩同為日本良民,與余輩同受日本政府之保護,成為擁有相當自由和權利之人”⑤,所以政府和社會對此決不能袖手旁觀。他向社會有識之士發出號召:“志士仁人豈可有一日安然,將此視為對岸之火災耶?應共同憤然崛起,將此等人民拯救于涂炭之中。不可不使此等兇漢絕跡于社會。”⑥他希望能有人想出萬全之策,拯救這些處境艱難的勞動者,而且表示自己愿意為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工人兄弟傾盡全力。他說:“作為吾國人士,茍有相親相愛之情者,見同胞沉于如此慘境,豈可袖手旁觀、不為之謀劃一策、拯救其危難哉?余輩不顧微力,今與同志密切相聯結,傾注心血,將之訴于輿論,乞于官衙,盡力所及,從事其救援,欲死而后已。余輩最敬愛之志士仁人諸君喲,希望添加一臂之力,以不堪至懇望上為國家謀劃擴張人權,下為欲賜予解倒懸之苦難也。”⑦即無論是向社會媒體披露,還是向政府請愿,自己都愿意盡一份力量。
今外三郎在揭露了高島煤礦的工人悲慘處境后,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反思,上升到社會現代化的高度。他指出,這種殘酷剝削工人的不公正狀況,如果不立即糾正,“不僅為彼三千礦工之不幸,而且我國后來應當勃興之事業,其萌芽也將受阻止也”。⑧即像現在這樣只顧眼前利益,竭澤而漁地壓榨剝削礦工,最終將會阻礙日本正在勃興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發展。
針對紡織女工的悲慘處境,1907年9月《大阪平民新聞》第8號也刊登專題文章《紡織女工》進行強烈譴責:“柔弱而無抵抗力之婦女工人們,無論如何哭泣悲慘之境遇,但由于如此周密之工廠的充分防范,而無法被社會了解。僅僅有泄露而聽聞之事實,不禁使人想起一個世紀前英國的棉紡織工廠中流行的‘奴隸之下的奴隸’。請牢記吧!資本家的財富和榮華,都是這樣從我們姐妹那里榨取的血液。”[注]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23頁。媒體這段生動的描述,不僅揭示出當時日本紡織工業繁榮背后工人們血淋淋的遭遇,而且試圖喚醒當時的人們透過經濟“繁榮”的外表,認識到勞動者所遭受的極不公正待遇。
另一方面,思想家們還從社會貧富懸殊的鮮明對比的視角來譴責這種社會不公正狀況。如社會主義者片山潛從對資本家階級奢侈生活的描述,揭示出日本社會貧富懸殊的驚人狀況:“聽聞大隈重信以其庭園壯觀美麗而夸耀。而彼即便在寒冷中,其溫室里也種有蔬菜,在與貴客共賞雪景時,可以吃到瓜、茄子等任何蔬菜。回顧一下,他一點不勞動,而每天有五、六十名園丁勞動,支持他一身。而為此,不知有幾千萬勞動者付出勞動。又聽聞資本家巖崎(彌太郎)在城里深川有別墅,其園丁乃不通日語之外國人。是其意在于擔心普通人民知道別墅內部。而其連古代帝王都自嘆不如之極端奢華,若不能保守秘密,因過分奢華之故,以至于害怕社會攻擊。真令人嘆為觀止。”[注]②片山潛:《我社會主義》,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5卷,第47頁;第469-470頁。這里說的巖崎彌太郎,就是三菱公司的創始人,也是前述高島煤礦的老板。可見,他們通過殘酷壓榨勞動者的血汗,使自己過上了奢侈的生活。而對于勞動者水深火熱的處境,身處優裕環境中的資本家們是不可能關心,也不打算改善現狀的。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社會制度,僅僅希冀資本家“發善心”來改善勞動者的處境,是不現實的。
社會主義者森近運平于1907年7月至9月在《大阪平民新聞》發表連載文章《勞力的掠奪》,也從這一視角譴責了貧富懸殊的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每日每夜汗流浹背勞動之人,應該貯存非常多的財產,衣食住都十分優裕。然而事實完全相反。帶著最痛苦的神情勞動的人們,沒有絲毫貯蓄,買米的錢也不夠,一年連一次有趣的游玩都不可能。”反過來對比那些靠剝削工人過活的資本家,“隨心所欲地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專門雇進人研究無用的游戲,并且還有用不完的收入。假定有錢人完成一份生產也同樣是人,那么普通工人斷無完成千倍萬倍生產之道理。彼等收入之大部分,不,其全部不外乎掠奪多數工人之勞力而取得之物”②,揭示出工人辛勤勞動的成果被資本家掠奪,是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的原因。
那么應當采用什么辦法來改變這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呢?社會各階層都在反思。顯然,這種狀況是與政府的監管責任缺位密切相關的。于是,當時有人提出由政府興辦企業,在善待工人方面,為私營企業做出榜樣。但是,嚴酷的現實卻粉粹了這種美好構想。20世紀初的日本,正演變為帝國主義國家。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明治政府更加重視軍事工業的發展,于是大力興辦兵工廠生產戰爭武器。在這些工廠里的勞動者,受到的苛酷待遇比起私營企業的勞動者有過之而無不及。1908年1月,《日本平民新聞》發表連載文章《大阪炮兵工廠之內幕》。文章作者非常感嘆地認為,作為應當保護國民權益的政府,居然比資本家還惡劣:“資本家的權力強大,強大到可以虐待工人,我們常常有所目擊。這樣可以明白,比起其他的資本家的工廠來,在政府的工廠中,工人的狀態更加悲慘。有種說法,將其在鐵路國有之前和之后比較便可明白。考察印刷局、造幣局和郵政局等部門的實況時,便不得不產生‘政府乃最暴戾的資本家’之感覺。尤其是在絞盡我們血汗的陸海軍的工廠中,會看到工人之狀況可以稱為最惡中之極惡。”[注]④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50-51頁;第51頁。文章針對有人提出政府興辦的企業為私營企業做表率的主張,指出:“社會上也有人認為,政府的工廠應當向其他資本家工廠展示出楷模。但那終究不是在當今的社會組織下可以商談執行的事。那無論如何都是不必要的設置過大的陸海軍,使我們工人陷于涂炭之苦。驅使本來可以生產自己衣食的工人,去制造令人恐懼的殺人武器。在今天政府的工廠——其殺人武器制造所大阪炮兵工廠,是如何虐待酷遇工人的呢?打算恭賀新年的人們,在以喝一杯新年酒的心情,熱衷于資本家報紙的恭喜發財中的今日此時,將會破滅之,從資本家社會的惡酒之醉中醒來吧!”④文章筆鋒犀利,抨擊尖銳,不僅揭露出殖產興業方針指導下的官營企業對工人剝削壓迫同樣沉重,而且力圖喚醒人們放棄希冀政府“能夠保護工人”的幻想。
既然政府不可依賴,于是有人提出用宗教信仰來拯救受苦受難的勞動者的主張,但這種作用能否奏效也受到懷疑。倫理學家大西祝(1864—1900)曾發表文章《社會主義之必要》,譴責了宗教家們對勞動者所受苦難無動于衷的不作為。他指出,今天我們大家都應當高聲“倡導平等之福音”,因為弱肉強食、富勝貧敗成為社會一大事實。但是,宗教家們都不愿意與窮人做朋友,更沒有譴責為富不仁的勇氣。現實社會中,“自我主義、爭斗主義”成為推動社會的動力,人們動輒為了私利而爭斗,宗教家難道沒有責任“矯正其弊害之義務耶”?大西祝強調,人們很容易趨之若鶩的這種相互爭斗,不可能帶來社會全面進步。而對此種現象,“宗教若不宣傳博愛,宣傳大慈悲心,主張一視同仁之平等主義,何者能為之”?對于因社會不公正而受苦受難的不幸之人們,想法給予他們平等待遇,“難道不是宗教之義務耶”?然而在現實中,宗教家們為了宣傳虛張聲勢的教義,“動輒欲獻媚于種種階級的、血統的、財產的、權勢的、國家的、社會的差別,這算什么事”[注]大西祝:《社會主義の必要》,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集》II,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第160頁。。他實際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維護現存統治秩序的工具,不能指望宗教界能在改善勞動者處境方面發揮什么有效的作用。既然如此,就只能如同這篇文章的標題所示,尋求一種能改善勞動者境遇的新制度已成為必要。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逐漸萌發。
四 結語
從上述考察可以深切地了解到,明治維新后日本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使日本在亞洲率先邁入到近代化行列,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尤其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家“發家史”,無不是以勞動者被殘酷剝削甚至超經濟強制作為沉重代價的。正如經典作家指出的那樣:“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7頁。盡管維新后官方提出了“四民平等”的人際關系原則,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但在社會實踐中,勞動者的權利仍然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殖產興業”國策大力推行和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的情況下,廣大工農勞動者的經濟待遇并未相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工作環境日趨惡劣,生存狀況愈益悲慘。這種狀況在當時日本出現,除了世界各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共同原因外,還有其特殊因素。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新政府為了盡快趕超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力推行“殖產興業”國策,使日本在極短的30余年時間內,經濟迅猛發展,但許多前資本主義時代對勞動者實行超經濟強制的習慣做法仍然繼續保留下來,難以在文明程度尚未提高的極短時間內消除。脫離封建時代不久的資本家們,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榨取最大利潤,除了增加工時以榨取勞動者的絕對剩余價值外,還往往盡量降低生產成本,甚至包括必要的自動化生產設備和安全防護設施的配備和完善也被忽視,因而導致勞動者的處境不但沒有伴隨經濟發展而得到明顯改善,反而呈現日趨惡化的態勢。這一切構成了日本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深刻社會根源。為了改變這種社會現實,日本思想界產生了對勞動者的人文關懷的輿論環境,并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逐漸萌發出日本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關于這種人文關懷和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的萌發,筆者將另文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