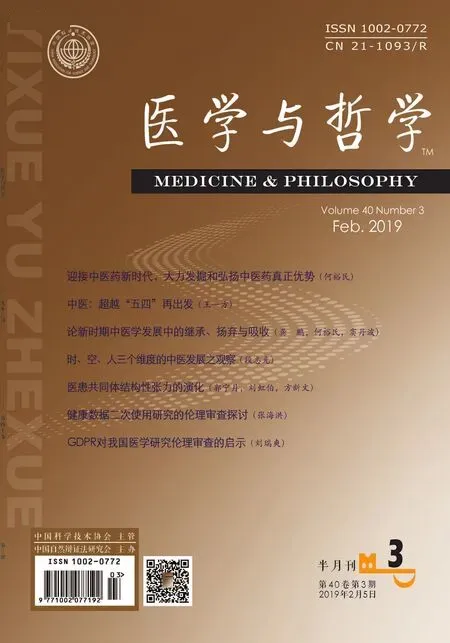中醫:超越“五四”再出發
王一方
對當代思想家而言,100年前“五四”運動是一個巨大的光環,也是一個強烈的光暈,令人們不自覺地陷入炫光之下的盲目或刻舟求劍的話語慣性之中,無法拒絕、擺脫“五四”路徑、話題、范疇、敘事框架的鉗制。無疑,“五四”的基調是積極的,但也有偏激的一面,在啟蒙-救亡、奮發-自新的同時,也在全面摒棄傳統,割斷歷史根脈,逐步墜入民族文化虛無論、破產論泥沼,接納全盤西化的文明進化觀,歷史滄桑,百年巨變,中華民族歷經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長斜坡,抵達國家昌盛、富強、民族復興的高原,如今中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國家治理都已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站在新的歷史地平線上,我們應該摒棄激憤、偏狹的情緒,不再秉持矯枉必須過正的信念,不再拘泥于新-舊、古-今、高-下、科-玄之間非此即彼的認知范疇,重新審視傳統,為民族復興積聚根植于主體性的文化自信。
歷史是一個巨大的鐘擺,鴉片戰爭以后的100年,華夏民族墜入危厄的深淵,風雨如磐之下,家國傾覆,情理俱亂,經歷了從文化焦慮、恐慌到文化自損、自卑的精神滑落,新中國的70年又將中華民族推舉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復興高地,重新找回文化自信的精神振作。對此番變遷,有必要對這一歷史脈絡與路標進行重新發現,重新思考,第一個路標是“西學東漸”,思想界展開中體-西用(道-器論,本-末論)的討論,隨著文化碰撞(對抗)的日漸加劇,“改良中學,適應西學”成為思想界的共識,期望中國文化完成創造性轉換,實現中西合體互用,但遭遇了不可通約性,于是“全盤西化”的觀點甚囂塵上,成為第二個路標[1],在全盤西化論者那里,中國文化已經僵化/僵死,甚至徹底破產,與之對應的是一系列文化自貶、自棄行為,無論是砸爛孔家店,還是廢止中醫,都透出決絕傳統,擁抱新學的偏激,背后有日本近代脫亞入歐的示范效應,滿目都是新-舊對立,傳統-現代的差異歸于高-下、優-劣、清-濁的較量,非黑即白,殊不知,西方的現代化并未貶棄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先賢,古典學系、古典學說依然是世界名校、學術名流的精神源頭與價值堡壘,現代醫學依然不舍“蛇杖精神”,依然尊崇古希臘醫圣阿斯克勒庇俄斯、希波克拉底。那些以為徹底拋棄傳統才能步入現代化的想法與看法恰恰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幼稚與狂躁,如今,中西文化雙峰并峙,二水分流,互鑒互學,對話交流,步入“古為今用,古慧今悟”的第三期,中西學術由融匯逐漸到貫通,通過部分融通過渡到深度融合。總的趨勢是倡導對話,而不是對抗。新傳統觀秉持兩點論,既尊重傳統、發掘傳統,又質疑傳統,批判傳統,當下的中國文化的使命是返本開新,既要返本,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又要開新,開啟文化創新的航程,二者保持必要的張力。其實,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流漩渦中,也有“接續主義”和“協力(調和)主義”的理性聲音,《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對其十分推崇并介紹給國人,“蓋接續云者,以舊業與新業相接續之謂。一方面含有開進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面對激進思潮的旗手們割裂歷史,劍走偏鋒,矯枉過正的狂飆言論,杜亞泉的剖析頗為深刻:這些人文化上具有雙重性,“一面是貴族性,夸大傲慢,凡是皆出于武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另一方面是游民性,輕佻浮躁,凡是傾向于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往往同一人,處境拂逆則顯游民性,順利則顯貴族性;或表面上屬游民性,根底上屬貴族性。”[2]這種心態正是后來諸多文化轉型節點激進主義幼稚病發作的基本病因[3]。
“五四”前后,中醫的命運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如同置身于時代跌宕的過山車上,遭逢傳統禮教崩塌,文化自信喪失,價值跌宕迷亂的籠罩,也面臨著傳統中醫元典與現代醫學新知的強烈對撞,中醫科學化運動又產生了實驗室里的中醫(既有屠呦呦新藥的發現,也有中藥毒性的揭露)與博物學視野中的中醫(山水-田園詩境與文化藥理學的詠嘆)的交鋒,此時此刻,中醫行進在歷史的鋼絲繩上,一要回應社會科學化與醫療技術進步的挑戰,又要接受科學主義與技術主義的苛責,二是堅守民族文化自立自強,也要防范民族主義,江湖異化,迷信歧化的滯擾。
“五四”倡導科學與民主,將其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價值啟蒙,“五四”思想家們(陳獨秀、胡適之、魯迅、傅斯年)對待中醫的態度也是基于倡導科學的醫學,繼而推進科學的社會化(生活化)的初衷,當年余云岫廢止中醫,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可作簡單化解讀、有著不可抗拒的潛意識的推助),意在拷貝東洋成功模式,實現民族精神價值、思想觀念、行為意識的脫胎換骨,由思辨化轉向科學化,詩化轉向物化,以達成救亡、啟蒙的使命,若是以中醫邊緣化換來救亡、啟蒙為先導的國家強盛,似乎可以算作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必然代價。那么,中國如今已步入強盛的快車道,是否依然需要以中醫來殉道,值得深刻反思。回望近代史,對全盤西化思潮,亟待深入檢討,它不僅帶來中國文化自信的纖弱,西方文化中夾雜的過度物化、功利化的價值追鶩也使得東方道德傳統得以稀釋甚至丟失,道德重建進程中依然需要借鑒傳統文化的滋養。近50年來,東亞經濟圈的集體雄起也證明儒家文化與現代化之間并不抵觸。同樣,看中醫,吃中藥并不會妨礙現代科學思維的建構。現代物理學可以從東方神秘主義中汲取思維靈性,中醫認知也可能為人文失血的現代性迷失帶來某些價值對沖。此外,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醫科學化運動以及隨后的中西醫結合探索,中醫科研機構基本完成了科學化、技術化的學習、借鑒、補課,以富有特色的中醫研究成果為現代醫學提出諸多學術特色與創新性思維的啟迪。當今,許多大中型中醫醫療機構朝著“中醫有特色,西醫也一流”的目標進步,聲光電磁等大型設備,輔助診斷儀器也一應俱全,新一代中醫早已告別“一個枕頭,三個指頭,幾根銀針看病”的臨證模式,學會中西醫兩種學術體系,兩種算法、陣法之間的變頻、變軌、變奏,針對患者的不同訴求,不同階段,不同狀態,中西互用,雙軌診療。也不再是阿司匹林加白虎湯的中西藥合用,發展到針推與中西藥物合體,現代護理與經絡護理并行,或參中衷西,或參西衷中,左右開弓,左右逢源,自成一系,許多現代醫學大師也在中醫學理上孜孜以求,在疑難病的會診中尋求中西醫互補互進,在難治性疾病診療上接納、汲取中醫的整體思維,體質學說,調養一體思維,奇特的遣方用藥思維,慢性病危機中暫避鋒芒,撇開病因,培本為先,以退為進,時間換空間的緩和醫療思維。
將醫學等同于科學是一個分類譜系的誤判,醫學不是世界普同一律的物理學、化學,而是一門有限的、不充分、不純粹的科學,在西方學術分類中就有科學、技術與醫學三分認知,毫無疑問,近現代醫學的科學化趨勢十分強勁,也無法改變醫學的不確定性和藝術性特質(奧斯勒的直覺),以及基于人文性、社會性的地域文化特征。無論發病、診療、康復都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和不可遮蔽的文化心理投射,南橘北枳,即使在一個國度里,國人的健康觀、疾苦觀、生死觀、醫療觀也是千差萬別,疾病的證據譜系或許相近,但醫生、患者的價值觀卻各異,從敘事醫學的角度看,疾病同一,但生命書寫(疾苦敘事,死亡想象)多樣,疾病隱喻,心靈干預多軌、多元,臨床即生活,既是多樣的,也是多彩的。超越臨床技能,臨床規范,臨床路徑,還原臨床的本質。蘊含著生物與生命,規律(必然)與宿命(偶然),理性與經驗/感性/悟性,軀體與靈性的分野與張力。疾病與醫學的全球化并未改變這一鏡像。在西方哲人那里,一個人不能第二次踏進同一條河,強調的是認知的個性、主體性、主客間性,同樣,世界上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自然也沒有兩位完全一致的患者,每一位患者都是唯一,每一次診療都是迷霧里前行的探索(張孝騫先生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慎)。所謂循證的醫學也只是相對的“規矩”,而非絕對的“金標準”。醫學究竟是什么?一百年來,西方源頭的醫學將還原論、決定論奉為圭臬,身體還原成軀體,苦難還原成圖像,疾苦還原成疾病,生命還原成為生物,心靈還原為心理,在科學化、技術化道路上迅跑,但不確定性、多樣性、感受差異性的罩門,使得醫學無法抵達純粹科學的彼岸,醫學依然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是科學技術之外的另類。而且,科學化、技術化裸奔帶來了醫學的現代性魔咒。讓人們重新回到“醫學是人學”的認知上來。我們還沒有走出柏拉圖的洞穴囚徒困境,也沒有走出笛卡爾的身心二元斷裂,敘事醫學的興起,全人醫學觀念的普及,使得身心社靈一體化的關懷成為終極追求。在許多疾苦、生死轉折點上,照顧大于治療,陪伴勝于救助,救贖/救渡/拯救大于救治,苦難、生死的豁達勝于永不言棄的干預。因此,那些認定有了西方醫學就可以取締中國醫學的人不僅患上了文化(歷史)虛無的頑疾,而且還將迷失于醫學現代性的泥淖之中。
一百年來,中醫總是與傳統為伴,傳統又與玄學有染,其實,中醫有兩面,既有傳統中醫的一面,也有現代中醫的一面,既是玄學(玄妙)的中醫,也是科學的中醫,但人們總是盯著一面責難。相形之下,西醫總是與現代、科學相綴連,于是,中西醫選擇便演變為傳統與現代,科學與玄學的抉擇。中醫也常常被稱為草根醫學、民間醫學、祖國醫學,但是,“五四”以來,文化根脈已經被無情割斷,草根已經滿目凋零,外來文化強勢占優,民間不再淳樸,祖國也已經被某些世界主義者拋棄,這樣的名實關系解讀自然顯得蒼白。此外,譯名寓意的偏狹也構成挨罵的名聲的緣由,因此,傳統中國醫學(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應該正名為中國范式(類型)的生命、健康、疾病調適與干預體系(Chinese Style Medicine,CSM),屠呦呦摘取拉斯克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青蒿素項目就是一次類型意義的突圍,源自《肘后方》的青蒿素抗瘧路徑顯然有別于西方的金雞納抗瘧路徑。TCM將自己定格為傳統范疇,將1930年代之后的中醫科學化努力與成績完全排斥在外,辯護的空間很有限,僅限于妙的傳統,活的手藝,即使在中國傳統學術流脈中,中醫一直秉持實學(格致)立場,反對空談性理,實學恰恰是最早與西學攜手的本土知識與方法體系。CSM的辯護空間加大,強調其類型意義,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凸顯中國意識,中國范式的健康觀、生命觀、身體觀(別樣的經絡體驗)、疾苦觀、救療(救渡)觀,中國路徑的臨床思維,剿撫并用,三分治七分養,內病外治,外病內治,上病下治,下病上治,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經絡護理等。費俠莉(Charlotte Furth)在《繁盛之陰》中就曾將中醫的類型意義定義為“黃帝的身體”(特色的藏象、經絡現象)與“藝術的別方”(特色的植物藥、方劑學),算是對中醫類型特色的基線式把握[4]。
凸顯類型意義在于擺脫時間維度的古今、新舊的意念糾纏,而是將中西分野還原為健康生命認知方式、醫療思維路徑及行為模式之別,從內涵上包容了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現代醫學方法對于中醫范式的闡發與延展,也就是說包含了一部分尊重中醫主體性的中西醫融合創新的成果,但那些只是將中醫認知、經驗作為素材與借鑒,違拗中醫主體性,丟失中醫價值靈魂的創新雖然也有實證意義,但只能算作非CSM的成果。強調類型意義的另一重意思是在某種程度上堅持類型路徑的獨立發展,才能在價值論層面造就“中西并重”的研究氛圍,而非預設某種前提,揚西抑中。當然,中醫不能故步自封,閉門發展,已故國醫大師陸廣莘先生生前反復講“研究中醫”與“中醫研究”的分殊,前者可以廣羅原野,博采眾長,多學科,多團隊,多手段,不拘一格,但后者必須循著中醫類型、軌道前行,兩者不可竄亂,也不可混淆,不能以“中西融合”(倉促結合只能是以西化中)論取代“中西并重”,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中西并重的深入研究與學術發展,就不會有中西融合的新格局出現[5]。
20世紀的藝術教育中,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中與西關系也曾經引起激辯。如中西繪畫,藝術思想、意境可以互學互通,但技法不可輕言融合,因為油畫用油彩,畫在麻布上,國畫用水墨,畫在宣紙上,一個重寫實,一個重寫意,一個講筆觸,一個講筆墨,筆墨不是筆觸,筆墨寄托了更多中國人的修養和精神性內涵,象征著中國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與審美情趣(物與神游)。在中西繪畫交集與對話語境中,國畫巨擘潘天壽先生有“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的睿思,這一論點對中醫未來發展道路也富有啟迪。近代中國藝術的走向有二,一條道路是中西融合論(徐悲鴻、林風眠),另一條道路是中西距離論(潘天壽),但前者受到普遍的擁戴,是畫壇與醫界追鶩的主流意識,后者則相對落寞,是沉寂的思想支流,其實,兩者并不矛盾,因為中西要融合,必須認清拿什么(優勢)去融會,繼而融合,融會-融合點在哪里?必須在兩者相離的狀態下才能仔細甄別出來,沒有距離,就沒有主體性,也就沒有主體間性,草率融合,莽撞而粗泛,庸俗融合,則可能被技術主義、消費主義劫持。不如保持距離,各自沉淀精華,累積特質,相互欣賞,分享優長,撞擊火花,方能融會融合。于是,潘天壽先生又提出“(中西)兩端深入”的觀點作為補充,“拉開距離+兩端深入”,構成一個完整的傳統畫風、技法在守成中發展的策略,并且在中國美術學院切實推進,在潘天壽先生看來,崇古、習古并非泥古,回到古法,更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在與古人的心境契合、精神交集、價值對話之中自我創新,不只是古為今用(今人可用的或許不多,也未必會用),更多的是古慧今悟,守正出新,在妙悟中前行。其子潘公凱先生后來主政中央美術學院,也在嘗試推行這一路徑,不管日后中西繪畫是否融會、怎樣融合,都為各自發展開啟了二元選擇的道路,不必困于“中西融合論”一隅,甘陽先生在評論中西距離論時提出,這一路徑選擇應該擴大到整個人文學術,作為一個總綱,在21世紀的中國文化境遇中,尤其應該堅守[6]。林懷民先生主持的云門舞集是傳統到現代的精彩涅槃,據《呂氏春秋》記載,“黃帝時,大容作云門,大卷”。云門是中國最古老的舞蹈,始于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早已失傳。1973年,林懷民借此名,創辦現代舞蹈藝術團云門舞集,再現了中華古老舞蹈藝術的神韻。
醫學中的藝術思維問題是一個流淌于醫學歷史長河里的古老命題,中醫早就有“醫者藝也” 的直覺,現代臨床醫學大師奧斯勒也宣稱醫學不僅是“不確定的科學”,還是“可能性的藝術”,以容涵臨床醫學中的主體間性和意向性,解讀生命的多樣性、風險的不可測性,醫療技能的訓練歷經生境、熟境,抵達純境、化境,臨床大師心摹手追的巨匠意境,常常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此時,意會大于言說(得意忘言、得意忘形),譬如中醫正骨、中醫推拿、中醫針法、經絡護理的個體化就是中醫診療不同于現代醫學,構成類型意義的重要側面,從道與術(器)的關系層面剖析,藝術化醫療的背后是物與神游(握針如握虎,下刀如有神)的美學境遇,是生命哲學(無常與豁達,尊嚴與關懷,立命與安身)的藝術呈現,是信仰療法(化蝶遇仙,躋身瑤池,神迷桃花源)的文化基因與基石,是抵達全人醫學的中國路徑。
21世紀中醫的命運如何?道在心中,路在腳下,要前行,不要停滯、要虛心,不要心虛、要自信,不要自負、要民族性,不要民族主義、要科學性,不要科學主義。依照20世紀的生存與發展慣性推延,大致有三途:一是甘居二流,繼續作為補充/替代醫學;二是為源自西方的科學化、技術化的醫學奉獻生命體驗、臨床早期經驗、研究靈感與素材,成為待驗證的假說庫;三是學術主體性的充分張揚,成為中國類型的醫學,在某些領域(亞健康調養、老年疾病、慢性病、失能診療)趕超西方類型醫學,創造新的診療特色和市場格局。很顯然,我們期待第三種可能,那么,中西醫“拉開距離,兩端深入”的戰略不失為明智的選項。從哲學上看,中醫學術的深入開掘必須遵循“醫者易(意)也”的價值內驅,在主體性、主客間性、體驗性、思辨性、藝術性等向度發力,倡導四個回歸:其一是回歸門診(場所精神),其二是回歸辨證論治,其三是回歸經方,其四是回歸手法,唯有回歸經典診療模式,中醫傳統才能得以在學術與職業信念純粹的境遇中從容地堅持與保存,才有中西醫互通、融會與融合過程中的主體性,才有中醫現代化的基石。相反,將客體性、對象化、物象性、還原論、決定論作為唯一的研究綱領,必然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失去自信。
中醫復興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會一帆風順,當務之急有四個主題值得積極推進,一是攀高枝,增自信,弘揚中國醫學的文化與道德優勢,融入國家價值觀體系,開創傳統文化“返本開新”的典范。二是培土固本,將中醫知識納入民族優秀文化普及活動之中,推動“公眾理解中醫”,將近年熱門的自主、自助型“養生”“治未病” 活動引向深入。三是自己出題自己做,繞開對象化、標準化兩塊石頭,發揮中醫整體調治優勢,研習一批疑難雜癥中醫綜合(針-藥并用)治療(辨體-辨病-辨證)的新路徑。尤其要花氣力深入研究經絡護理的原理與實務,開啟中醫特色護理的新模式。四是打造診療特色與特區,順應慢性病取代傳染病的疾病譜變化及社會老齡化趨勢,開展慢性病、老年疾病療效、老年生存質量提升的臨床攻關,開辟“療-養結合”“身-心-社-靈結合”的慢性病、老年病防治新模式……再列舉下去就犯忌了,因為,思想史研究奉行遠距離沉思,而非近距離丈量。
撫舊追新,歷史永遠是一面銅鏡,映照出前行的路,從這個意義上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反而觀之,一切當代思想境遇都是歷史敘事的歸宿,或許,思想史書寫看重的不只是歷史素材,而是思想的裁紙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