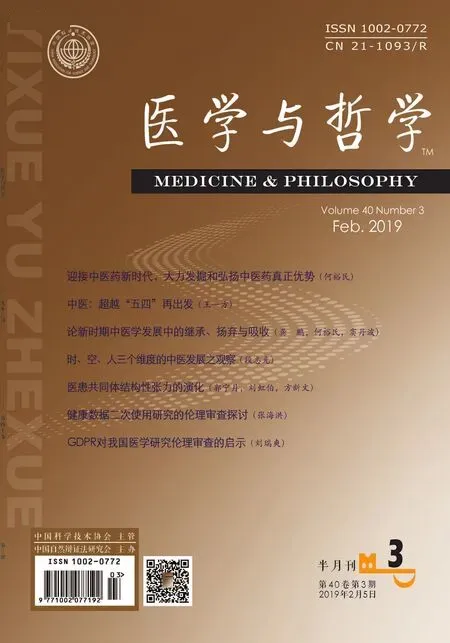論新時期中醫學發展中的繼承、揚棄與吸收*
龔 鵬 何裕民 竇丹波
自西學東漸,中醫學和其他中國亞文化一樣,都一再被追問將往何處去。最初,西方醫學對中國的滲透剛開始,并不順利;人們也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科技裹挾下的醫學之威力,中國社會顯得有點漫不經心。但鴉片戰爭后,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1 此路不通: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西方科技蘊藏的巨大潛力,反思自己文化,卻發現沒有可以抗衡的力量,甚至也難以發現可以促成現代科技生發的精神資源。這一刻,中國人的自信心崩塌了,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成為知識精英的共同選擇。自然,作為傳統科技代表的中醫學就成為眾矢之的,被批得體無完膚。全盤西化,廢除中醫等的論調一時間甚囂塵上。當時有名的“廢止舊醫論”、“廢醫存藥論”等從本質上說,指向的不僅是中醫學,也包括中藥及所有其他傳統科技。反中醫者心里也清楚,廢了中醫,中藥等也就成不了氣候。然而,中醫藥雖不斷被削弱,一點點地喪失了主流醫學地位,但基本盤還在。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傳統文化科技分支卻在這過程中被徹底瓦解了。
在西方科技沒有進入中國之前,中醫(藥)學的發展有自身內在規律。主要路徑就是誦讀經典、詮釋經典和應用經典。因此,那個時期,中醫學發展的主要脈絡就是繼承。雖也有各家學說之爭鳴,但脫離不了以古證今、以經解經的學術常規。西方科技大舉進入中國后,中醫學自我封閉、內圈式循環發展的環境氛圍消解了;因其合法性受挑戰,生存都陷入危機;面對外部強大壓力之際,救亡圖存的最好對策就是變革。當時中國社會彌漫著的革命思想正是這種壓力的反射。作為反彈之勢,中醫學術共同體空前團結起來,為中醫學命運奔走呼號,并提出了變革主張。遂西化論、中西匯通、中體西用等大行其道。西化論并不成功,當時也沒有形成大的影響。中西匯通派則講“衷中參西”,引進與調和,如制度層面欲引入西方醫事和醫學教育制度,器物和方法層面則大量引入西方檢查手段、分析工具以及西藥等;也嘗試用西醫學理論來解釋中醫藥理論,為中醫藥學尋找合法性依據。中西匯通派在一段時間里確實引起了廣泛注意,取得一定成果,并為后來的中西醫結合論提供了鏡鑒;但中西匯通論并沒有真正為中國醫學界所接受——西醫學認為這是在做垂死掙扎;中醫界認為它“非驢非馬”。當時,社會還流行一種中體西用思潮,為洋務派所倡導,也波及中醫學。但一方面因其體用分離而違悖體用統一之規律;另一方面強行推斷中學優于西學之說,有別于真實世界之圖景和人們的直觀感受,故中醫學的中體西用論最終流產了。可見“中體西用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卻不是科學的命題”[1]。
時空流轉,今日世界,已大不同于往昔。當今,中醫學復興之夢正逐漸演變為現實;傳統文化再一次被聚焦。為中醫學未來發展道路計,有必要認真檢討歷史與重新思考。
2 中醫學的精神文化是繼承的核心內容
傳承與創新是中醫學的兩大主題詞。因此,中醫學界對繼承是有共識的。師徒傳授綿延數千年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不缺乏繼承的基因。難點在于繼承什么?如何繼承?當前流行的中醫繼承有一定復古傾向——古中醫旗號頗有號召力;各類拜師活動如火如荼;讀經典、賽方歌的活動一浪高過一浪;一些國學課程也紛紛加入中醫藥學內容。對注重繼承的熱情加以反思,不難發現,這里有國家強大、民族主義崛起等的背景性因素。過去積貧積弱,窮則思變,老想著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東西是不是阻礙了我們的發展?今天強大了,發展比他人快,就開始琢磨興許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都是些寶貝。在中華文明復興的大背景下中醫學的繼承自然得到應有重視。另一方面,近百年來,中醫學長期被擠壓、被邊緣化,中醫學有很多技術方法被遺棄或有意無意地遭忽略;因此,滋生了較強的尋找失落文明之反作用力。中醫學的繼承就被擺到了突出位置。一個典型事例是對民間中醫的熱情似乎又被點燃了——如國家出臺確有專長人員參加醫師資格考核注冊管理新辦法,在院校教育之外給師承和術有專攻者開辟一個獲得合法行醫資格新的途徑。政策出臺初衷,是要撿拾繼承散落在民間的中醫特色(技術方藥)。再者,是中醫學難以現代化:中醫學理論和運用技巧難以被現代科技所揭示,很多細節以現有技術條件既不能被證實,又不能被否證;現代科技無法為中醫藥提供一個實用操作指南。在這種情況下,繼承就是不二選擇了。
繼承的復古傾向者在下意識中認為“今不如古”:他們看到中醫臨床陣地正在萎縮,常用藥物和技術逐漸衰減,病種越來越局限,中醫師的中醫思維能力有欠火候,等等。的確,有些中醫方技已經失傳。但其中多數應該屬優勝劣汰之結局。這種現象在各專業門類中都存在,不值得過多嘆息。醫藥領域也一樣,西藥明顯比中藥強的,中藥就被替代;就是中藥自身也存在新舊替代之類問題。因此,繼承絕不是沒有選擇的——已被證偽了的、喪失生命力的、已全面被替代的技術并不在需要繼承的清單之內,也不必經過解構和揚棄過程。
按照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文化分類法,技術和藥物主要包含在物質文化的范疇內。文化學者普遍認為:物質文化的發展態勢是不斷更迭的,總處于長江后浪推前浪狀況,曾存在的物質文明總歸要被后來者超越的。基于上述考量,中醫學有一些優勢技術,還有一些雖喪失優勢但在某些細分領域仍具有補充價值的技術,需要加強繼承工作,但中醫學繼承的重點并不在物質文化層面。因為隨著時代之演變,物質文化層面的中醫藥學后世勝于前世之勢是鐵板釘釘子的。而人類的精神文化卻并不是直線演進的。軸心時代人類的精神文化發展即達到空前高度。之后起起伏伏,但都難言全面超越。因此,繼承的核心應該是精神文化。而制度文化的發展,介于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間。繼承中醫藥學,也包括對中醫藥學制度文化的繼承。但其重要性相對弱于精神文化。怎么理解?例如,今天中醫院的組織方式明顯不同于過去的坐堂,有一定先進性。但坐堂、診所等形式也沒有完全消失。近些年來,隨著備案制的推行,還有回歸之趨勢。類似的中醫把脈問診方式、廳堂的布置等也需要選擇性地繼承。綜上可見,籠統地講繼承,是有欠缺的。一不小心,就會陷入誤區之中。如有人聲稱繼承了懸絲診脈的方法,還有人說是繼承了中醫的五行理論,開發了五色帖,堂而皇之進入大醫院等,就是這種迷思的體現。
民間一技之長者可能真有本事,但不能放大其能力;一技之長者繼承的主要還是物質文化,不經考試只是幾個專家的一場考核來認定其醫師資格潛藏巨大風險。中醫學的繼承不能沒有前瞻性和制度保障。不能不管不顧為了繼承而繼承,一股腦兒全部接收。
對中醫學的精神文化成果進行凝練,就是中醫學的核心價值體系[2]。繼承中醫學的精神文化成果,則應重點聚焦于中醫學核心價值體系。“每個民族都有一套獨特的價值系統,它是一種文化的本質,也是自我認同的基礎。”[3]重讀經典的出發點很好,但要通過經典掌握中醫學的思想精髓。如中醫對氣一元論、對天人關系的理解,對疾病本質、自我行為與罹患疾病關系以及對陰陽平衡、對表里、對寒熱、對虛實的深刻見解等,然后在此基礎上深化成對藥性與組方用藥規則等的掌握。繼承的目的是為了讓傳統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在合理性復活,讓這種合理性指導今天的中醫學及整個人類的保健實踐。同時也應注意,中醫學的變革(或說革新)也已成為傳統的一部分。比如,今人所總結的辨證論治體系、整體觀念、正氣觀、抗癌力等,都是中醫學自求變革之結果;它們的合理內核也是繼承的對象。
3 揚棄的目的是實現新舊范式轉化
中醫學界講繼承講得多,講創新也不少。而且經常繼承創新連著講。但很少有人靜下來思考:在繼承和創新之間就沒有過渡帶嗎?繼承好了就能創新嗎?實際上,繼承和創新之間存在一個遼闊的過渡區間。首先,要搞清楚繼承什么東西?再次,要鑒別繼承下來的在今天還有沒有比較優勢?有沒有前瞻性意義?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分析哪些東西還可繼續挖深挖透!在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條件下能不能進一步做出改良、提升或重構!用一個哲學詞匯來凝練——就是揚棄!即發揚舊事物內部積極、合理的要素;拋棄其內部消極、喪失必然性之成分。
一說揚棄,一些原教旨主義者就會條件反射般地跳出來,認為是自掘墳墓!他們把揚棄當成了革命。揚棄和革命不是沒有一點關聯性,只不過揚棄繼承了革命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拋棄了革命的激進主張;取而代之的是承認原有事物的現代價值,但需有所取舍。因此,中醫學的揚棄,其出發點是積極的,目的是要促進中醫學持久地發展成長、生存下去,而不是消滅中醫藥學。
揚棄,必然涉及一些解構工作,以適應今天的現實需要。人們在閱讀經典時,因并未置身當時文化氛圍背景,其實際指向經常是不清晰、不準確的。沒有解構,就不能還原當時場景;所謂繼承,到底繼承了什么內容,是不是念歪了經,就無從知曉。解構同時要做分析,把過去的經驗和總結放在放大鏡下進行審視,對照今天的研究成果,借鑒現代科學手段,進行鑒別。當然,解構是建立在繼承基礎上的,而不是相反。李澤厚先生當年曾提出:“我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是一個龐然大物,首先必須分析它、解構它,然后才可能談得上繼承和建設。”[4]這顛倒了繼承與揚棄之間的承繼關系。李澤厚稱這是西體中用的模式。如按此思路,中醫藥學只會剩下幾片殘磚斷瓦。解構分析在先的,繼承在后的,最后常常將走向全盤西化;只不過說法上溫和一些罷了。
繼承的下一步是揚棄;而揚棄的目的并不是再去繼承,應有更高遠的目標——和吸收新要素相結合,實現新舊范式的轉化。揚棄過程實際上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過程——在從舊范式中把有價值的內容甄擇出來、發揚彰顯之際,新質已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這種吐故納新的新質就像酵母一般,“在舊的文化系統內部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一系列的變動、調整與革新。在這個過程中,新舊因素相互影響、相互適應、相互促動,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范式。”[5]就像把“辨證論治”從浩如煙海的中醫古文獻中總結出來一樣,緊接著辨證論治新體系被搭建起來;之后遂有辨病論治、辨證與辨病相結合、辨證/辨癥與辨病“三位一體”等新主張、新范式的相續問世。我們30年前就以當時熱門的腎本質研究為例,發現腎陽虛與神經-內分泌某些參與代謝的軸關系密切,提出目的不是重新闡釋腎陽虛是什么,而是建立新的概念[6]。
中醫學術可分為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在中醫學知識體系中,變化較大,揚棄現象突出,新舊范式轉化快;而中醫學的價值系統,尤其是核心價值體系,承啟舊有精華更多,表現出更明顯的恒常性和穩定性,新舊范式的轉化通常很慢。
4 吸收時要構建自主性知識體系,擺脫路徑依賴
談中醫學,不得不談到“他者”——現代科技及西醫學。揚棄是針對自身而言的,是一種自我檢討;吸收是向外的;中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吸收現代科技和西方醫學精華。吸收和揚棄相結合,就構成中醫學自身的新陳代謝。吸收是指將外界之物通過一定渠道、借一定方法轉化為自身組成部分/或自身所需能量。它是個內化過程——將外在之物轉化為內在之物,將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因此,吸收的主客體是明晰的,絕非交出主動權,把自己托付出去;亦非將自己轉變為異己之物。中醫學發展中的吸收應注意保持主體性。毋庸諱言,過去一段時間,中醫學發展有西化傾向。西化的本質特征是以西方觀點來看待中醫學,將中醫學視為被觀察、待驗證的對象;一旦沒通過其設定的篩選機制,就被拋棄;而通過其認證的則被納入西方科學體系,它和原生文化并沒多大關系。正如有學者所言:“在其后的歷史中,對西方知識的吸收卻往往超出‘改良’的范疇,作為外來者的西方知識越來越成為中國學者的思想本位,而中國素有的古老文脈則愈發顯得遙遠而陌生。中國與西方在知識場域中的主客關系被顛倒了。”[7]中醫學現代化過程中,也許西化在某些方面、某些階段有一定合理性。但越到后來,這種思路的弊端就越發明顯。因為此類研究本質上是“研究中醫”,而不是“中醫研究”。而以單體化合物發現為主的方法,也面臨巨大瓶頸,既無法整體闡釋中醫藥原理,更不可能根本改變中醫學面貌和指導臨床實踐。不能否認,中醫西化的慣性力量十分強大。今天習用的許多管理思路仍可以看到此類痕跡。如在學科評估中,片面以SCI、自然基金等量化指標論英雄;在新藥評審中,多采用西方的評審體系,難以形成中醫藥自主評價模式。這些都有待突破改進。
歷史上,中醫學不乏同化吸收外來文化之例:如薏苡仁、胡麻、犀角、蓽茇、丁香、胡椒等。引進后,再根據中醫理論和臨床實踐,賦予這些藥物歸經性味和功效。這些引進完全突顯了中醫學自身主體地位,取得了很好效果。中醫學發展至今,如果認同其理論的周嚴性和可外展性,那就不能忽視其消化與吸收。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醫學對現代科技的借助非但不應減少,還會更加豐富,但不能放棄主體性。中醫學不能僅充當西方醫學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不然中醫學遲早被碎片化,走向解體。“我們已經來到了思考如何與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歷史階段。這種并駕齊驅,意味著我們不能再以西方、以他者來定義自身,而是必須具備真正的自主意識。”[8]中醫學的發展一定程度陷入了路徑依賴之窘境——即離開西方業已成熟的評價機制,就無所適從。然而中醫(藥)學的客觀實際又決定了難以沿用西醫(藥)學的評價標準。例如,在各種植物藥中,以銀杏的標準化程度最高,主要是因為它在遺傳上的高度同源性和穩定性造成了各植株間差異極小;而絕大多數中藥不具備這特性。不同地域的中藥差異甚大,就連同一苗圃的、有母子關系的中藥材,其差別也常是明顯的。又如,各人體質、證候辨別也是千差萬別的,藥物進入人體后的藥效發揮機制極其錯綜而不明朗。中醫藥的使用不像樂器獨奏,更像眾人大合唱。中醫學核心價值體系是“總指揮”,學科范式具體“協調”其怎么組方,怎么唱,最終形成一曲美好的“旋律”,這和以單體化合物為主的西藥情況不能相提并論。因此中醫藥的效果評價須另辟蹊徑,建立自主的知識發展體系。
5 在繼承、揚棄、吸收與創新間保持適度張力
今天的中醫學,已擺脫被開除出世界醫學舞臺之風險。但歷史虛無主義、激進革命主義、文化守成主義等思潮仍然不時回潮。“告別中醫”,“變亦變,不變亦變”,“尊經尚古”等口號雖未掀起大波瀾,但時時提醒人們中醫學的發展路徑仍存在不確定性,也提示我們反思在繼承、揚棄、吸收上的失誤與不足。
中醫學發展過程中,繼承、揚棄與吸收必須是同時并存的,且有前后承啟相續關系,不同時間階段還有輕重緩急之取舍,但這三者是貫穿在中醫學發展始終的、不可分割的。突出強調某一方面的工作并不利于中醫學的發展。庫恩曾說:“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然同時顯示維持傳統主義和反對偶像崇拜這兩方面的性格。”[9]這種必要的張力,這種繼承既往基礎上的叛逆,也正是中醫學發展所必需的。中醫學是在醫學實體基礎上雜糅了一些哲學概念。哲學思維和思想實驗的痕跡十分明顯。體系化的努力一直在路上,但不如意者眾多。通過繼承,可以讓中醫學的思維和文脈得以延續,讓中醫學界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園,有助于形成科學家共同體、行業共同體,但不能止步于此,需要必備的“叛逆”精神。不管揚或棄,都是繼承基礎上的“叛逆”。揚棄標準并不完全取決于今日之科技。理論某種程度上是被構建出來的,是在現實基礎上想象加工之結果。所以,不必特別汲汲于所謂的“科學性”。一如經絡學說,在統合針灸治療理論方面有明顯優勢,易于識別記憶和傳承;在臨床上也安全有效,構建了中醫學自我認同的一大基礎;不能因為經絡未發現解剖學實體就給予否定。
揚棄之后也存在著一個再檢驗問題。一時之所“棄”,因為有了新的發現,或有了新的解讀,還有可能重新“揚”起來。當然“揚”之后也可能再出現“棄”的現象。總之,在核心思想基本穩態情況下,不斷要有新瓶來裝,允許有反復,允許螺旋式上升。吸收時,也存在一個合腳不合腳的問題。
在繼承、揚棄和吸收之外,還存在創新問題,相互之間也要有適度張力。中醫學在走向世界過程中,面對新的人種、新的地理氣候條件以及直面癌癥、艾滋病、阿爾茨海默癥等新疾病譜系時,中醫(藥)學缺乏可以直接繼承、揚棄之資源和經驗,也難以簡單吸收現代科技成果,這就需要創造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理論、方法及操作規范,摸索一些新的經驗及應對措施,且須盡可能地將地方性知識擴展為全球性知識。保持適度張力,就是要維持這幾者微妙的平衡,防止簡單化解讀,并持之以恒地堅持。這也是中醫學發展的內在動力。
6 結語
中醫學光談繼承,沒有發展前景,無法憑自我完成現代化轉型提升,故亟需做好必要的揚棄/吸收工作;但揚棄和吸收時,又需保持自身的主體地位,不能一談現代轉型就落入西方話語體系之窠臼,失去自己領地。今天,中醫學面對的已不再是生死存亡,而是普遍的戰略焦慮和恐懼,需在繼承、揚棄、吸收以及創新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應倡導包容性發展——在核心價值上強調“堅守”,在理念上主張“優化”和現代“落地”,在技術上追求“突破”,強調“可操作性”,且善于缺什么補什么,充分發揮中醫(藥)學在系統綜合調治,挖掘內在自我康復潛能,擅長生態改善等諸多方面的優勢,貫徹“好醫學”的精神實質[10],推動科學合理、自然合理以及生態合理之匯流,基于此,中醫學定會有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