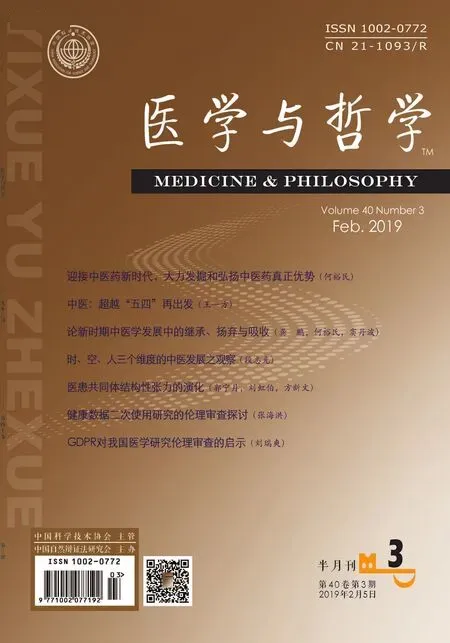論精神失常研究的當代學理視野*
張勝洪
精神失常研究的當代學理視野考察主要圍繞精神病學展開。本研究將“mental disorder”譯為“精神失常”是因其兼涉日常-學科話語兩個層面,而“當代”則主要是指對啟蒙理性的局限性進行質疑與反思的廣義“后現(xiàn)代”。西方文化自啟蒙時代以來,理性的凸顯導致了以下后果:其一,為促進社會的規(guī)范化而導致對精神失常者的大禁閉;其二,希望用技術手段解決人的問題而產(chǎn)生了人的科學。此外,對自我主體性的探索產(chǎn)生了現(xiàn)象學和精神分析。因此,大禁閉、人的科學以及現(xiàn)象學和精神分析的結合產(chǎn)生了以人的精神世界(如精神失常、“瘋癲”等)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病學[1]6-8。這一背景是對精神失常研究的當代學理視野進行考察的基礎。
1 精神病學的學理-實踐后效
1.1 軀體損傷與心理學轉向
在18世紀結束以前,并不存在諸如精神病學這樣的學科。產(chǎn)生于歐洲的精神病學是啟蒙理性的產(chǎn)物。傳統(tǒng)上,對于基督教徒,異常通常被診斷為是超自然,他是邪惡的或神圣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和科學理性推進了醫(yī)學中的自然主義思想。當癲狂和憂郁出現(xiàn)的時候,機械哲學不認為是由于邪惡的控制所致,啟蒙時代的醫(yī)生堅持瘋癲不是源于上天而是在于軀體,不正常是由軀體原因導致的。在笛卡爾和牛頓的框架中,靈魂神圣不可侵犯,醫(yī)學將不正常的原因解釋為是由于身體受到損傷。例如,美國精神病學之父拉什(Benjiamin Rush)在1786年就說過:“那些作為大腦智力錯亂或缺失而痛苦的人被認為非常適合作醫(yī)學的主題;有許多記錄的病案證實這種醫(yī)術已經(jīng)治愈了他們的病癥。”[2]
洛克的思想促進了精神病學的心理學轉向,認為“精神病學應該基于心靈哲學。”精神病學在歐洲不同的國家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在法國式的精神病學中,如沙可(Charcot)強調歇斯底里不是不可理解的秘密,而是和其他的神經(jīng)障礙一樣,有確定的、邏輯的、可預測的臨床標記;德國的精神病學主要與大學的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精神病學開始強調文化的差異,出現(xiàn)諸如“英國式的憂郁”、“美國式的精神緊張”。
1.2 理性獨白與相互對話
在精神病學的實踐中,精神病學在美國被用于控制移民;精神失常者的絕育手術也在希特勒的德國出現(xiàn)。基于心理疾病不是心因性的,而是具有生物學基礎這一信條,精神失常者陷入更沉默的境地。瘋癲的責任主體一旦被確定,生理和心理的區(qū)別與主次也就產(chǎn)生了,瘋癲成為單純的精神疾病,也就意味著身體需要保持沉默[3]。理性時代的科學革命將人視為機器,因此,對疾病的描述和精神失常者自身的傾訴被降低到從屬地位。“最吵鬧的病人,被鎖了起來,……沒有人愿意去聽他們的訴說,交流……”[4]精神病學成為關于“瘋癲的理性獨白”(福柯語)。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學院精神病學更為關注生理學的研究,還原主義(reductionism)的解釋傾向更加明顯。還原主義相信發(fā)生在不同層面的所有事件都可以被解釋為(或還原為)一種類型的知識。在精神病學領域,還原主義認為個體有意義行為的各個方面(例如擔心、遺憾、恐懼、信仰、希望、愛和懷疑)都能基于基因、神經(jīng)遞質等實體并最終在原子和分子層面得到完全的解釋。還原主義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學院精神病學的主導思想。
后精神病學(postpsychiatry)采用解釋學作為一種方法去超越還原主義,嘗試去獲取一條在醫(yī)學層面可以適當?shù)乩斫鈧€體的心理問題和精神失常的道路,而解釋學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解釋方式[5]。后精神病學的解釋學取向,不是以“專家意見”去對個體進行研究,從而解釋癥狀和診斷疾病。解釋學認為心理健康從業(yè)者應該給予其服務對象以權利,使他們能了解和共同面對其自身的心理現(xiàn)實,以及其心理問題是如何被界定的。目前,英國有為數(shù)眾多的踐行著對話的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是“Survivors Speak Out”[6]。
精神病學的解釋學取向的核心是關注語境(context)。認為只有將精神失常置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理解文化是如何賦予我們的生活事件、歷史運動以意義的,同時這些意義又是如何塑造我們自身的生活的,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瘋癲和抑郁的意義。解釋學取向為精神病學從傳統(tǒng)走向當代,從精神科醫(yī)生對精神失常者的理性獨白走向與“精神失常者”的共同解釋與對話提供了學理支持。
2 精神失常的現(xiàn)象心理學
2.1 胡塞爾-雅斯貝爾斯傳統(tǒng)
一個精神科醫(yī)生或心理學工作者,能夠通過所謂的同感而感受到與精神失常者一樣的體驗嗎? 這個問題很難用任何方式具體回答,這涉及哲學中最為艱難的主題,即胡塞爾所提出的“交互主體性”問題,即一個人怎樣才能與另一個主體的體驗產(chǎn)生同感,并且進行真正有意義的交流。這一問題涉及到的是“在世生存”現(xiàn)象學的核心——人和世界是如何相互建構的。
精神失常作為一種人們對之有著敬畏、驚詫、嘲弄、害怕、恐懼、恥辱、排斥等負面情緒的存在,需要對其進行廣義的現(xiàn)象學“厚描”,這一現(xiàn)象學“厚描”自然展現(xiàn)出的意義,已頗具解釋學的特點,與上文論及的后精神病學的解釋學取向亦有重要的相通之處。對哲學家來說,現(xiàn)象學意味著“胡塞爾傳統(tǒng)的哲學”,對精神病學家而言,現(xiàn)象學則意味著“雅斯貝爾斯傳統(tǒng)的精神病理學”。
在雅斯貝爾斯《普通精神病理學》的前言中,Anderson曾寫道:“現(xiàn)象學方法涉及了關于個體病人意識層面上認真的,細致的和艱苦的事實觀察和研究”[7]。這種現(xiàn)象學的理解引領了20世紀后半期主流精神病學關于評估和診斷的思想。英國精神病學家Mortimer[8]將現(xiàn)象學簡單地定義為“精神病理學的精確描述”。與精神分析的模糊推測形成對比,現(xiàn)象學的方法作為更清晰和精確的方法被提出。大多數(shù)當代的精神病學家認為他們的評估涉及到一個關于病人癥狀不偏不倚的真實描述,同時還有對個體心理狀態(tài)的清晰分析,這就是當代精神病學實踐里關于現(xiàn)象學這一術語的含義。在當前的精神病學實踐中,現(xiàn)象學不僅僅意味著對病人癥狀的描述和組織,這里還涉及到一個基本假設:我們的心理現(xiàn)實,可以像我們的生理癥狀一樣以相同的方式來描述。亦即精神病理學與生理病理學沒有根本上的差別。第二個假設:心理事件可以獨立于其產(chǎn)生的意義背景,并被可靠和精確地描述。現(xiàn)象學被看作是價值中立,科學描述病人主體世界的方法[8]。
2.2 癥狀描述的解釋學轉向
在隨后的幾十年中,歐洲大陸現(xiàn)象學的解釋學轉向為現(xiàn)象心理學理論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意義和背景不再是理解心理現(xiàn)象的困擾,轉而成為被關注的中心。海德格爾在超越被胡塞爾所認同,且被雅斯貝爾斯明確使用的“心靈世界”的分離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他關注的問題是:世界是如何“呈現(xiàn)”給我們的?我們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如何可能的?對雅斯貝爾斯而言,“病人的心靈”是某種通過經(jīng)驗科學的審視而相遇的某物。精神病理學尋求去分析、分類以及給這個實體(指病人的心靈)貼上標簽,現(xiàn)象學實質上是使這種分類得以可能的方法。海德格爾則反對以經(jīng)驗科學方式去審視人類現(xiàn)實,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有責任讓世界首先存在。他認為個體或人類所面對的世界與其他物種所面對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人類的身體及其生理構造方式意味著某種類型的世界是向我們“開放”的,人類現(xiàn)實是具體的現(xiàn)實和文化的現(xiàn)實。笛卡爾式的方法將心靈世界與身體分開,并認為可將心靈從其生存的社會背景中分離出來,但是笛卡爾式的觀點不能反映我們作為人類存在的事實。海德格爾提供了一個比笛卡爾、胡塞爾和雅斯貝爾斯更接近生活經(jīng)驗的,關于人類存在的說明。
3 精神失常的心理哲學-精神病理學
3.1 哲學精神病理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
1994年,George Graham與G. Lynn Stephens編輯出版了《哲學精神病理學》(PhilosophicalPsychopathology)一書,對瘋癲或廣義的精神病理現(xiàn)象,結合精神病理學在哲學層面展開了一系列考察。哲學精神病理學的出現(xiàn)時間較早,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作《人類理解論》中,對各種心理疾病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討論。200年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其《心理學原理》中,把心理病理現(xiàn)象作為一種資源來推進其哲學論爭。
近年,哲學精神病理學有了新的發(fā)展。哲學家對精神病理學進行的研究,影響了涉及精神病理現(xiàn)象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同時對精神病學分類學及其對心理問題的科學假設也影響重大。現(xiàn)在,已很少有哲學家會懷疑精神病理學在推動和激發(fā)哲學思考中的作用。近年來,精神病理學的哲學思考,大多是從個案研究展開。精神病理學的個案描述包括患者表現(xiàn)出的障礙,以及醫(yī)生對障礙的診斷,這反映出“精神病理學”這個術語的雙重含義:它既涉及精神障礙自身,同時也涉及醫(yī)療實踐的分支領域和研究這些障礙的心理學。
在此,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哪一種個案是哲學精神病理學適合的研究對象。首先,精神病理學中的個案,大都具有行為怪異和非理性的特點,如多重人格障礙和妄想癥。由于飲酒等原因導致的遺忘癥,一般不是精神病理學最為關注的對象。其次,盡管很多精神病理學的從業(yè)者認同這些障礙有器質性的基礎,但他們并不認為精神病理現(xiàn)象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器質性問題導致的。同時,對精神障礙的理解和解釋也主要采用精神動力學的術語,如否認、壓抑、應激、悲傷等。具體而言,該領域尚缺少系統(tǒng)的文獻概述。George Graham與G. Lynn Stephens編著的《哲學精神病理學》一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該領域的不足。
3.2 心理哲學研究的關鍵問題
當代,心理哲學開始從對心理概念進行清晰的分析轉向更為廣泛、整合、經(jīng)驗的理論化研究。這種經(jīng)驗和整合的趨勢,是由于哲學家受到神經(jīng)生物學,比較和發(fā)展心理學以及信息加工過程等領域的影響所致。同時,這一趨勢同哲學家關注對特殊心理現(xiàn)象的解釋有關。唐平[9]認為:關于異常心理的研究,心理哲學的發(fā)展一直就隱含著物理主義的思想路線……用整合的物理主義理論來分析和考察異常心理現(xiàn)象,如神經(jīng)癥、抑郁癥和精神分裂癥等,可以形成一系列的關于異常心理的哲學見解和理論。由于經(jīng)驗科學的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哲學關于心理活動的概念將被重新考察和界定。現(xiàn)在,心理哲學在解釋具體心理現(xiàn)象時,總是與相關的科學領域結合,而精神病理學對異常心理現(xiàn)象的經(jīng)驗研究為這種交叉和應用研究模式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基礎。
心理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人類的行為、智能和經(jīng)驗能不能被科學地理解?自然科學為心理學提供了一個可以模仿的模型,還是心理學的解釋與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當前對這一主題的討論集中在常識或 “民族心理學”(folk psychology)。我們對自我及他人的日常歸因是否因科學的研究而重新界定。精神病理學研究為我們重新考察和推進關于這些主題的討論提供了大量的機會。當前,這些討論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精神失常的醫(yī)學模式,科學哲學和精神病學哲學以及精神病理學和民族心理學。
精神病理學的研究主題是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對精神病理學實踐的倫理和精神異常者體驗的思考產(chǎn)生了兩類問題:第一類問題與法律和道德責任有關,例如,我們當前的心理健康觀念和服務理念能否去理解和干預那些處于不同病理狀態(tài)的人;第二類是精神病理學實踐產(chǎn)生的問題:個體或群體健康的,或者是至少可以被容忍的生活觀念,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精神病理學理論所塑造、理解和面對的[10]。
4 精神失常的話語分析與文本解釋學
4.1 循證醫(yī)學:個案史的實證主義話語分析
在精神病學領域,話語的建構性影響無處不在。福柯是對話語作出界定的最為重要的理論家,他的“話語/權力”概念已不僅僅是學術概念,而已成為一個實體。在哲學、文學研究、批評語言學中,話語組群具有實踐的反映性和建構性。傳統(tǒng)醫(yī)學和精神病學的實踐是循證醫(y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主導個案史記錄的是實證主義思想。
個案史在醫(yī)學和精神病學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希波克拉底將個案史作為一種系統(tǒng)方法去描述疾病的自然歷程,即所謂的病歷。在19世紀,病歷達到了它的最高點。精神分析和生物精神病學的建立就是基于個案史,而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的著作《歇斯底里研究》即是這種傳統(tǒng)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試圖將個案研究方法做成科學的。盡管在弗洛伊德給Fliess的信中,弗洛伊德表達了他的個案研究并不是足夠科學的[11]。今天,個案史并沒有超出自然史的形式,就如Oliver Sacks注意到的,在個案史中幾乎沒有個體人性層面的存在。病人個體獨特的生活故事,面對疾病的個人斗爭,在疾病中幸存下來或者康復,在現(xiàn)代的個案中只有很小的意義或幾乎沒有意義[1]192-193。
毋庸置疑,個案史在我們理解疾病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也為不同治療方式的效果評估提供了證據(jù)。EBM認為,在治療中存在獨立于主體的疾病,這種疾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種客觀事實的發(fā)現(xiàn)依賴于實證方法,比如說統(tǒng)計技術和數(shù)學方法。憑借著實證主義的根基,EBM認為專業(yè)知識和專家,知識和認知者之間有著區(qū)別,這個區(qū)別反映出笛卡爾式的主體和客體的二分思想。EBM在精神病學里開辟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被專家關于另一個人的“事實”說明所主導。非常明顯,EBM視角下的個案史預設認為它描述了疾病的“客觀事實”,但是,當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關注個案史的敘事維度及敘事心理以及敘事方式的建構性影響的趨向。這一趨向從時間的維度展開,通過討論和寫作關于病人的疾病,從而建構出關于疾病的故事。但是“個案史”所包含的內容不僅僅只是疾病的自然歷程,它同時也是建構一個人的方式[12]。
4.2 敘事醫(yī)學:個案史的敘事及其文本解釋
精神病學是技術性的醫(yī)學模式還是人性的道德事業(yè)?這樣的思考凸顯了精神病學實踐中客體性和主體性之間的張力。在某些情況中,個案被視為一個對象化的客體。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個案可能被視為一個被賦予了主體性和意向性的人。社會的規(guī)訓機構(如收容所)通過諸如會診、檢查、臨床記錄以及個體的個人傳記的方式去建構精神失常者的主體。但是,醫(yī)學是科學的,更是人文的,是“人學”,醫(y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有很多重疊的資源幫助我們理解精神失常。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人類學、文學理論和審美理論用于分析精神病學個案,導致了“EBM”向“敘事醫(yī)學(narrative-based-medicine,NBM)”的轉向。病歷記錄在精神病學的實踐程序中極其重要。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uer)就說過:一個文本的意義在于將來的可能性解釋[13]。
個案史的撰寫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臨床醫(yī)生對病人的診斷和治療。亦即個案史的文本撰寫決定了什么會被言說,而對這些言說的解釋決定了什么將被記錄。病人常常不知道關于他們的什么內容被記錄,但醫(yī)生卻能決定與病人面談時要記錄的內容,并基于此而提問。這個循環(huán)影響并決定了病人如何去解釋他們的生活及其體驗。個案史的敘事作為一種工具,構造了心理異常者的歷史。其敘事功能可能不是導向自由,而是產(chǎn)生控制、界定和限制,它表明了敘事是如何在精神病學成為一種“建構和交易”,并服務于專業(yè)的利益。
5 文化研究——精神失常考察的跨學科視野
5.1 學科視野中的“精神病”
近代學科建制后,學科語境中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癥”等詞匯逐漸流行于日常生活中,對具有以上某一特點或某幾個特點的人我們稱之為“瘋子”。“精神失常”、“瘋癲”或廣義的“心理疾病”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以某種面目展現(xiàn)出來,或者被建構成某種樣態(tài)而展現(xiàn)給我們,精神失常成為一個關涉生理、心理、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的現(xiàn)象和主題。誠如Angela Brintlinger與Llya Vinitsky在其所著的《俄羅斯文化中的瘋癲與瘋人》中指出的:madness、insanity、lunacy,這些在不同時期被用來描述心理疾病的詞匯,即使某些看起來是“有時代錯誤的”,但我們并不將這些語言除去。這種語言的包容性和擴展性超越了將瘋癲作為個體病理學的概念,除了作為一種“疾病”,“瘋癲”也是一個文化象征、一個隱喻、一種符號等[14]。我們需要在日常生活層面和學理反思層面,對精神失常展開多維度的考察,而“不廢個體而超越個體的批判性文化意義關注,強調多維度、跨學科展開的當代學術領域,文化研究為尤著者之一。”[15]
5.2 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意義
具體而言,精神病學已經(jīng)成為一種強大的全球化力量,這種力量影響著我們如何去談論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情緒以及我們的思想。同時精神病學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控制力量。當代是個理性化的時代,對理性和秩序的關注,要求消除社會中的“非理性”現(xiàn)象。一系列旨在對瘋癲、異常者進行控制、治療的觀念出現(xiàn)了。在理論層面出現(xiàn)了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咨詢心理學。在實踐領域出現(xiàn)了收容所、精神病院、心理咨詢中心等。這些理論和實踐的從業(yè)者正在尋求消除或改造人類異常行為,幫助人們找到形成健康自我的途徑。
在GoverningTheSoul一書中,社會學家Nikolas Rose描寫了 “自我管理”是如何成為現(xiàn)代社會政治統(tǒng)治的基本原則。政治對自我認同一直存在著影響,Rose認為在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社會,這種影響正在迅速擴大。Rose將精神病學的上升、擴展定位在這樣的背景:“一個個新的專業(yè)團隊正在不斷成長,每一個(團隊)都宣稱其具有對心靈進行分類、測量以及預測心理變化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診斷困惑、開出方子的精湛技巧。”[16]這些“主體性的專業(yè)知識”的出現(xiàn)形成了福柯意義上的權力/話語空間,并在對精神失常進行控制、治療的實踐領域體現(xiàn)出“效果”。
在精神病學的臨床實踐中,通過語碼的轉換可以將日常話語轉換成專業(yè)話語。這一過程是通過提取患者表達其心理體驗的語言并以精神病學的話語去重構而完成。如在醫(yī)學實踐中,“肚子痛”在醫(yī)生的語言中是“左側小腹疼痛”。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可能抱怨“空虛”、“沒有方向”、“厭倦”或簡單的“痛苦”情感,這些情感經(jīng)常與不愉快的人際關系、困難的工作狀態(tài)或者與身體不健康聯(lián)系起來。而在精神病學家的話語中,這些感覺成為“焦慮情緒”或者“抑郁癥狀”。一個人因生存的痛苦而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盡管其間伴隨著文化的、宗教的、個人的以及家庭含義的多樣的細微差別,但在精神病學話語中卻可能被簡單地認為是“自殺意念”。這一過程是試圖將精神病學的實踐變得更科學,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通過語碼的轉換而獲得一種對異常心理現(xiàn)象進行精確描述的語言。
從文化研究視野對精神失常進行多維度、多學科的研究,關涉到精神失常現(xiàn)象和主題所具有的復雜性、艱難性以及敏感性。在當前的學術語境中,其關涉的絕非僅僅技術而已,更為重要的是自我反身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