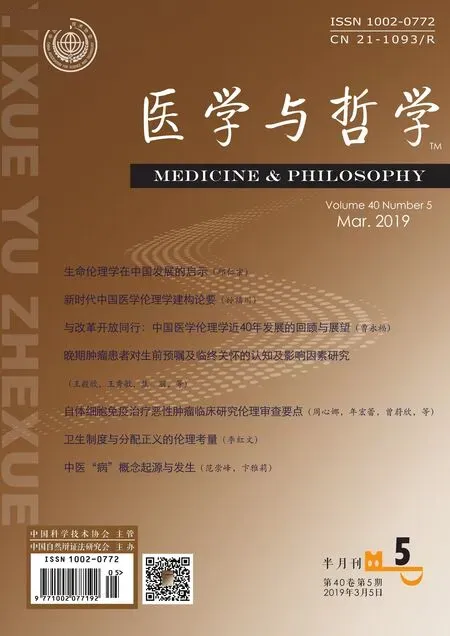中醫隱性知識的特征及其形成緣由研究*
曾 智 申俊龍
①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經濟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廖育群[1]認為,中醫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其神韻正在于它具有“可以意會,難于言傳”這種特性。他指出,中醫的核心觀念在于“意”, “中國醫學理論的神秘性、治療方法的靈活性、醫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個‘意’字來體現。”的確,“醫者意也”,中醫的神韻正在于“只可意會,難于言傳”的特性。所以說,中國傳統醫學(中醫學)就是一座偉大的“隱性知識”的寶庫。
1 中醫隱性知識的含義
在過去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醫學逐漸形成了在傳承和實踐的基礎上創新而來的獨特知識體系,中醫辨證施治過程蘊含了中醫專家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診療經驗和治療方法,因而缺少廣泛的臨床實踐和專家指導很難體會中醫理論的深奧微妙。事實上,無論是“醫者意也”,抑或是“意者醫也”,這其中的“意”就能彰顯中醫學理論和實踐的“神秘性”。
首先,“意”是中醫學理論發生與發展的基礎。中醫理論構建的依據具有很強的個人化色彩,而其實踐探索或者實踐證明又采取的是極具個人化的內證實驗的方式進行說明;其理論解釋則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即將自然界的“大宇宙”和人類個體的“小宇宙”加以同構分析。另外,即便獲取、吸收和消化由個人直覺領悟所形成的中醫學理論,也并非能提供一種外化的客觀性的實驗證明過程,而是和其形成的過程一樣,需要個人產生內證式的領悟。李時珍在其著述《奇經八脈考》中有句名言“內景隧道唯返觀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謬也。”[2]這里的“內景隧道”就是我們所說的“經絡”,“返觀者”是指一個通過修行內煉而真氣充盈通達奇經八脈的人。概而言之,要懂得經絡的奧妙所在,只有那些修行內煉成功了的人才能真正領悟到。這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具備“內證實驗”的能力,才能真正理解和領悟中醫學理論。
其次,“意”是中醫臨床思維的主要形式。“夫醫道之為言,實惟意也;故意神存心手之際,意析豪芒之理,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3]這就是說,中醫醫家在對患者進行診療救治時,一定要做到專心致志,心領神會、心意相通。而且,“意”在中醫臨床中還代表一種靈活性,即針對不同的病患應該做到辨證論治,善于用意。正如唐代王燾在其《外臺秘要方》中所言:“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蓋以其意量而得其節,是知療病者皆意出當時,不可以舊方醫療。”[4]也就是說,一個好的醫生應該能夠根據病患的病情而靈活辨證施治,絕不能拘泥于經典,墨守成規地套用某些現成的方藥,而是要做到知常達變,靈活地選擇正確的治療方案。的確,在臨床實踐中,無論脈診之意還是用藥之意;無論針刺之意還是醫案之意,其無處不體現中醫臨床思維中“意”之靈魂所在。
借鑒西方現代知識管理中有關隱性知識的相關理論,我們不難發現,無論中醫理論之“意”還是中醫臨床之“意”,都充分反映作為“技道融合”的中國傳統醫藥學知識中其絕大部分的知識是符合波蘭尼所提出來的隱性知識之界定與區分標準。中醫知識是一種具有突出“隱性知識”特性的知識體系,是一座偉大而卓越的隱性知識寶庫。據此,中醫隱性知識可以界定為:“中醫隱性知識是中醫學家在臨床實踐過程中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為個體所擁有的,難以通過語言文字表述以及傳授的知識和體驗,主要包括理論認知方面的中醫隱性知識(即中醫經典中所包含的知識)以及技術操作方面的中醫隱性知識(即中醫醫生在臨床實踐中所運用到的、難以用言語表述出來的知識)。在臨床教學實踐中,我們所分析的中醫隱性知識更多的是醫家個體臨床實踐中所形成的隱性知識。”[5]
2 中醫隱性知識的特征分析
作為一門獨具特征的傳統醫學,中醫學蘊藏著大量的隱性知識,號稱“一座隱性知識寶庫”。但由于中醫及中國傳統文化“取象比類”、“以言立象”等思路,導致中醫醫者個體隱性知識有著與其他隱性知識不同的特征。
2.1 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具有個體內在性
中醫,作為一種醫學科學,其知識的獲取過程及存在形態似乎很難徹底消除其個人的因素。因此,學習中醫比學習西醫要難得多,學習西醫可以借助現代科學技術的手段,學習中醫則需要個體借助自身的感覺器官、直覺思維和體悟等來認知與診治疾病。這種內在的心智模型完全依賴于個體,正如野中郁次郎和斯滕伯格也都將心智模式看作隱性知識的重要構成要素[6]。這種個體內在認知所形成的中醫個體隱性知識既是一種個體在臨床實踐過程中由頓悟或者直覺所獲得的個體經驗,又是一種與醫者個體無法分離且很難以正規的形式進行傳遞的感悟和體驗。
2.2 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具有不可充分表達性
西醫在更多時候所呈現出來的是“規范性知識”,非常注重診治過程中標準的探索與確定;中醫在更多時候所呈現出來的是“個體內在性知識”,中醫醫者即便研讀同樣的中醫經典,在結合其臨床經驗時,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體悟,所以,中醫非常注重診治過程中的個人體悟和中醫知識的內化。這種用心領神會的方式所形成的個體隱性知識往往很難進行充分表達。但需要指出的是,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很難加以充分表達或者不可充分表達,并不是不可表達,因為它可以通過內居方式模糊地表達出來。
2.3 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具有文化依附性
美國學者Hamel等認為:“隱性知識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實踐情境和社會關系之中,它具有很強的情境和歷史依賴性。”[7]中醫個體隱性知識也和其他隱性知識一樣,總與一定文化傳統中人們所分享的語言符號、概念、思維方式、知識體系分不開,處于不同文化傳統中的人們往往也分享了不同的隱性知識“體系”[8]。中醫,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代表性文化符號,其產生、形成、發展和傳承都離不開我國傳統文化背景及特殊目標情境。一方面,中醫知識有著中國傳統文化共同的特征,常常運用指示、隱喻、象征的語言來分析和論述。就如同《黃帝內經》在描寫“四時脈象”時就采取了這樣的方式進行解析,“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余;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另一方面,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必須依附于中國傳統文化這一特定的文化情境才能更加穩定、持續地發展和傳承下去。所以,中醫個體隱性知識的文化依附性要求中醫傳承過程中師徒之間擁有相同或者相近的信仰、語言符號、價值觀、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等。
2.4 中醫個體隱性知識具有情境依賴性
中醫個體隱性知識是在一定的“問題情境”中觸發的,也是在一定的“問題情境”中才能加以展示,只有中醫醫者親臨具體的情境(接觸到患者)才能全面把握隱性知識的真正含義。因為中醫醫者在針對每個不同的疾患病人,其辨證論治、理法方藥都體現較強的個體性和針對性。即便某些方劑的使用和方藥的配伍,一旦與某些特定情境相分離,其理解就有不同,意義往往也會產生失真[9]。中醫傳統的師承模式一直倡導的是身教為主,言傳為輔的教學方式,就是師徒處于同一問題情境,通過觀察、模仿師父診治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將師父的隱性知識轉化為自身的個體隱性知識[10]。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情境依賴性主要指的是中醫個體隱性知識的生成和轉移總是與某些特定的情境(如某些特定的任務或者特定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是認知主體對這些特殊情景所產生的一種直覺體驗和感悟[11]。
3 中醫隱性知識形成的緣由分析
3.1 中醫隱性知識的形成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投影
由于中國傳統哲學是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在認識生命現象時也必然體現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原理。中醫隱性知識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投影,它以中國傳統哲學中自發的辨證論思維和古代樸素的唯物論來構建其基本理論體系,如五行學說、精氣學說和陰陽學說等[12]。
3.1.1 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基礎的中醫知識
縱觀整個人類歷史,無論中外,人類先民在探尋生命現象時都采取了具象型的哲學思維方式,以原質認知世界和認知生命是當時世界各種族、各民族和各種文化之流行文化,其初始思維都是具象性所致[13]。在這些古代文明中,唯獨中國文明與文化下誕生的中醫學既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其他各種文明所誕生的醫學有著深刻的不同,其理論根基——陰陽五行學說。
五行學說在中醫學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以五行具象之特性來分析人體的臟腑、形體、經絡、情志等組織器官和身心活動,構建了以五行對五臟的中醫學基礎理論體系和天人一體、相生相克的個體生命系統,并以此來指導個體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這種具象性的中國傳統哲學思維就是隱性知識最初的根源之一,其在臨床實踐中無論對于學習者還是實踐者都是“只能意會,難以言傳”。
陰陽之道被看作是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的規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14]根植于中國傳統哲學的中醫學在其產生與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陰陽學說”為基礎的特有的思維方法,將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結合起來闡釋個體的各種生命活動現象,并指導人們認識疾病發生的原因、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由此可見,中醫理論既根植于這一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又從生命現象本身及疾病的防治角度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其產生和發展都反映了中國古代先民對自然現象、對生命現象的高超智慧和覺悟。這種智慧和覺悟從一開始就帶有超越語言的特性,是很難用語言來加以描述的,也很難用語言進行交流和分享,真可謂“道可道,非常道”。
3.1.2 以“象思維”為核心的中醫知識
“象思維”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源頭,它是指運用帶有形象、直觀、感性的符號或者圖像等“象”工具來探尋和闡釋世界萬事萬物的本質規律,通過象征、類比、隱喻等手段把握世界萬事萬物之間的聯系,從而構建宇宙統一模式的思維方式。《易經·系辭》已有“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之說[15]。中國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指出,“營天下而皆‘象’矣”。由此可見,“象思維”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形成與發展都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其應用也是非常廣泛。
源于中國傳統哲學的中醫學也蘊含了豐富的“象思維”,并且將“象思維”運用到了疾病的病因分析、診治手段等各個方面。中國傳統哲學中最具特色的思維方式是“象思維”,即比類取象,中醫亦不例外[16],而且“象思維”是中醫思維的核心,是中醫最為獨特的思維形式,其涵蓋并體現了中醫藥理論整體、變易、中和、虛靜、直覺、順勢、功用等思維的特點。
“象思維”作為中醫思維的核心,從而導致中醫理論成為了以“象”為主要內容的學術體系。由“藏象學說”中“藏象”之名便可知道,中醫是以顯之于外的“象”來分析和把握藏之于內的“臟”的各種現象或者征象,即所謂“執其功見其形”。中醫學理論基于中國傳統醫學古代解剖學的思想,結合“象思維”對生命現象及其機理進行了深刻的探討。例如,《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將“心”描述為:“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通于夏氣。”從這段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醫學所描述的“心”與建立在現代解剖學基礎上的西方醫學所描述的“心”似乎差異很大,在中醫學里,心已經不是一個簡簡單單解剖學形體上的身體器官,而是個體生命中一系列生理現象和機能在人腦中所形成的綜合之象。中醫學正是通過對人體各種表象的直接觀察,然后效法自然界的各種外顯之現象進行歸納和描述。這種基于“象思維”對個體生命現象的認知和闡釋盡管可以通過隱喻、取象等方法來傳遞和分享給其他人,但仍存在難以理解、難以言說和難以表達的特征。
3.2 中醫隱性知識的形成是“內證”文化的體現
中醫學既是一門形而上的學科,又是一門形而下的學科,其本身就體現了“陰陽”兩面。就形而上而言,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就是一些難以言說、無法用邏輯命題進行表達的神秘之物;就形而下而言,也許很多人不太好理解,畢竟在中醫學里沒有西醫學理論中那樣廣泛存在的各種實證實驗,也沒有西醫學所擁有的現代醫學解剖,但這并不能說中醫學就完全沒有實驗,中醫學也有許多很精深而細微的內證實驗,成為了一門形而下的學科。只是,中醫與西醫之間由此而產生的不同在于:中醫學除了分析、探尋和治療人的內體,還會從人的“精、氣、神”的角度進行診治,比如說五臟六腑、經絡穴位等,這些都是與西醫完全不同的概念,充分體現了中醫“內證”實驗的結果。這些形而下的內證實驗不能像西醫學那些形而上的運用小白鼠實驗那樣可以言說。正因為如此,中醫學無論其所依托的中國傳統哲學背景,還是其自身的“內證實驗”及臨床感悟,都蘊含著豐富的隱性知識。
由于現代醫學建立在科學的實驗基礎之上,其西醫理論是源于實驗才提出來的,因此,一些抨擊中醫的學者就認為,中醫無論其理論還是其診治技術都是沒有實驗基礎,所以不科學。對此,中國學者劉力紅在其《思考中醫》一書中提出了強而有力的看法。他認為,中醫學作為世界上延續兩千多年的一種醫學體系,其理論構建和臨床技能的探尋只是一些古代先民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能實現的,其肯定是理性思考和實驗研究相結合而形成的結果。但中醫學理論構建和技能探尋的實驗研究不同于西醫的實驗,中醫學的內證實驗是一種直接在理論構建者自身內部所進行的精微而深入的實驗。在上古醫學的傳說故事中就有“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這種從自身口嘗鼻嗅、體味心識入手的認知百草之藥物屬性的方法就是典型的“內證實驗”。所以說,這種源于實驗者自身的內證實驗是中醫學認識個體生命現象和天人、自然之間關系的重要方法。
所以說,中醫學的神秘正是源于內證實驗這一系統、細微而精深的探尋生命現象的方法,只有真正理解中醫學的“內證實驗”才能深入認知中醫藏象、氣化、名門、經絡等中醫學基本理論。也因為如此,正是這種“內證實驗”使得中醫學理論與臨床技能表現出難以言說的特性。
不難發現,就知識的特征而言,中西醫就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西醫在更多的時候所呈現出來的是“集體規范性知識”或者“顯性知識”,非常注重診治過程中標準的探索和確定;而中醫在更多的時候所呈現出來的是“個體內在性知識”或者說“隱性知識”,中醫醫者即便研讀同樣的中醫經典,在結合其臨床經驗時,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體悟,所以,中醫非常注重診治過程中的個人體悟和中醫知識的內化。所以說,中醫是一門“技道融合”的中國傳統技藝,它既有“器”或者“技”的一面,又有“道”的一面。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中醫學里面蘊含著豐富的顯性知識,但就知識擁有者來說,其個人性、文化依附性、情境依賴性又是不可回避的。正因為如此,中醫的傳承長期以來都很強調師徒授受的模式,這種師承模式所倡導“身教為主,言傳為輔”的教學方式,就是師徒處于同一問題情境,通過觀察、模仿師父診治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將師父的隱性知識轉化為自身的個體隱性知識;同時,師父也只能借助一定的問題情境才能將自身的隱性知識分享給徒弟。綜上所述,“中醫具有隱性知識特征”、“中醫學是一座偉大而卓越的隱性知識寶庫”。要想厘清中醫學中“道”的真諦及其“隱性知識”的核心特征,我們就必須明白其隱性知識形成的緣由,這也是獲取中醫個體隱性知識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