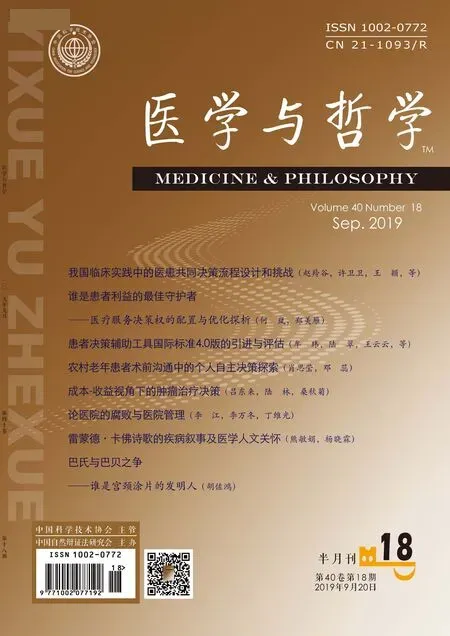雷蒙德·卡佛詩歌的疾病敘事及醫學人文關懷*
熊敏娟 楊曉霖②
詩歌敘事是最古老、最具特色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文學在敘事醫學人文教學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敘事文類。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1988年)是美國最著名的極簡主義短篇小說作家之一,然而,他在詩歌創作方面也非常有造詣,只是沒有受到文學評論界的關注。在醫學人文領域,他的詩歌作為非常有價值的閱讀和闡釋的素材,能夠有效地引發醫學生和醫學教育者的深度反思。本文中卡佛的詩歌主要參考克萊普(Sandra Lee Kleppe)在《卡佛詩歌中的醫學人文》一文中所列詩歌,詩歌的中文翻譯引自舒丹丹譯的《我們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詩全集》,部分譯文有細微調整。
卡佛自20世紀80年代從“生存現實主義”向“人文現實主義”轉變[1],從這一時期開始,他的詩歌作品中開始大量出現后現代元病理人文元素。本文從醫學人文視角對卡佛的詩歌進行研究,并分析作為一名詩人,他是如何背離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范式,創作出充滿醫學人文關懷的詩句。
1 疾病敘事:疾病類型與敘事視角
卡佛的前半生充滿了苦難與失望,失業、酗酒、破產、妻離子散、友人背棄,晚年又罹患肺癌,50歲便英年早逝。他曾說:“我覺得詩要比其他作品更接近我、更特別、更難能可貴……所有的詩都有一個‘自傳’的成分在。有些情節的確很像某個時間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情。”[2]因此,他的詩歌中涉及到酗酒、癌癥、失眠癥等疾病題材的作品占了相當的分量,甚至有些詩歌以此為標題,如《駕車時飲酒》(DrinkingWhileDriving)、《酒》(Alcohol)、《干杯》(Cheers)、《冬季失眠癥》(WinterInsomnia)、《患癌的郵遞員》(TheMailmanasCancerPatient)、《煙斗》(ThePipe)、《藥》(Medicine)、《煙灰缸》(TheAshtray)等。
卡佛詩歌的敘事視角也靈活多變,內視角、外視角交替出現,或是第一人稱的回顧性視角,如《運氣》(Luck):“那時我九歲。/我的生活里一直/離不開酒。我的朋友們/也喝,但他們能節制”。或是第一人稱的旁觀視角,如《巴爾扎克》(Balzac):“我想起戴著睡帽的巴爾扎克,/在他伏案寫作三十小時后,/霧氣從他臉上升起,/長袍睡衣黏著他毛茸茸的大腿”。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變換自如,卡佛筆下的人物是丈夫、妻子、兒子、女兒,也是朋友、陌生人,甚至是一具冰冷的尸體,如《解剖室》(TheAutopsyRoom),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他們大多數都是藍領階層的窮人——推銷員、侍者、理發師、清潔工、看門人等。他們喜歡蜷縮在家里,或躺在沙發上,或看電視,或吃零食;或聽人講故事,或給人講故事;即使在外工作,也或是銷售員,或是酒吧招待。這些人沒有宏大理想,但真實得如同你我;這些人一般不試圖思考生活的哲理,即使偶爾嘗試,也往往無果而終。這些人按理進不了神圣的文學殿堂,但由于卡佛,他們生動地存在著,照亮了讀者內心暗存的卑微和無奈[3]。
2 疾病隱喻功能的構建
2.1 社會與生命困境的隱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為現代的疾病隱喻與傳統不同,“傳統的疾病隱喻主要是一種表達憤怒的方式”,“現代的隱喻卻顯示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而社會被看作是個體的對立面。疾病隱喻被用來指責社會的壓抑,而不是社會的失衡”。癌癥作為一種“伴隨情緒消沉而來的疾病——這既指生命力的萎縮,又指對希望的放棄”[4]。卡佛[5]95在《患癌的郵遞員》中生動地記錄了一個垂死之人的困境:
患癌的郵遞員
成天閑在家里
那個郵遞員從沒笑過;他容易
疲勞,身體正在消瘦,
只是這樣;他們為他保留那份工作——
再說,他需要休息。
他不愿聽見大家談這事。
他走在空空的房間里,
想起一些瘋狂的事,
比如湯米和吉米·多西,
在大古力水壩
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握手,
還有他最喜歡的新年派對;
他告訴妻子的事
多得可以寫一本書,
她也愛想一些瘋狂的事,
但能照常工作。
有時候在夜里,
郵遞員夢見他從床上起身,
穿上衣服,出門去,
高興得發抖……
他恨那些夢,
因為醒來后
一切都不曾留下;仿佛他
哪兒也沒去過,
什么事也沒做過;
只有那房間,
那沒有陽光的清晨,
門把手慢慢轉動的
聲音。
此詩刻畫了一個潦倒的勞動人民的形象,郵遞員表現出的疼痛、焦慮、厭世、恐懼等情緒就是對社會和生命困境的重要反饋。夢與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詩歌充滿抒情力量的簡單意象。比如,“門把手慢慢轉動”營造了緊張的氣氛,郵遞員“夢見他從床上起身/穿上衣服,出門去/高興得發抖”,他卻想保持清醒,因為夢讓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因疾病導致的疲憊不堪的生活,門把手代表著從生命到死亡的通道,代表著走向另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而大家對他的議論更暴露了溫暖的匱乏、人情的涼薄,卡佛就曾在《你們不知道愛是什么》(YouDon'tKnowWhatLoveIs)的詩歌里發出這樣的質問:“你們有誰知道生活是什么/你們有誰懂得哪怕一丁點兒?”
2.2 精神的暗疾與隱喻
失眠癥作為一種心理疾病,是作家鐘愛并藉此來探索人性和精神圖景的方式。卡佛把失眠作為他的一個文學主題,同時也是一種暗喻的符號。他在詩作《冬日失眠癥》中這樣寫道:“腦子想從這兒跑出去/跑到雪地上。它想要奔跑/跟隨一群粗毛野獸,滿口利齒。”失眠者在黑夜中有一種全然的清醒,這是正常人所沒有的清醒,失眠者沉浸在黑暗世界里做著痛苦的空想,然而“在月光下,穿過雪地,不留下/任何腳印或蹤跡,身后什么也沒有”。卡佛筆下的失眠者常常會不同程度地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與無助,所以沉睡就成了避難所,一個暫時能獲得片刻寧靜和安全的空間,把自己與身邊的人群隔開,以此來逃避生活,驅散內心的紛亂。如《睡眠》(Sleeping):“他睡在公共汽車上,火車上,飛機上。/睡在崗位上。/睡在路邊。”甚至,卡佛在《舊時光》(TheOldDays)中寫道,“上床睡覺時/真希望就這樣一睡不醒”。
酒在卡佛的人生中占據著重要意義,亦在他的詩歌中反復出現。雖然確切地定義“酗酒癥”并非易事,但眾所周知,生理特性、負面生活事件、文化因素、抑郁癥、焦慮癥和其他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礙都可能導致酒精成癮。因此,酗酒癥可被視為一種精神疾病[6]。卡佛筆下對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酗酒行為的描述生動揭示了他們對心碎回憶的逃避、難以忍受的孤寂和面對生活中那些迫在眉睫的困窘時的無能為力。對于處在現實重壓下的人來說,酒就是一服具有安慰效用的精神藥劑。《駕車時飲酒》描繪了兩個男人一路飲酒作樂的場景:“我很快樂/和我兄弟駕著車/喝了一品脫‘老鴉’酒。”《干杯》中的酒鬼像是在喃喃自語:“喝了伏特加之后用啤酒漱口/……他們不明白,我很好/我在這兒好著呢,現在每一天/我都會很好,很好,很好……”而酗酒者清醒之后又會陷入到痛苦掙扎、進退兩難的境地,這個階段的心理活動會更加復雜、豐富,顯示出一種與生活融合無間的立體感與真實感,能夠令讀者深切地體會到人物的焦灼不安與迷惘。如在《我父親二十二歲時的照片》(PhotographofMyFatherinHisTwenty-SecondYear)一詩中,卡佛表達了他與父親一樣都是酗酒者的絕望之情:“父親,我愛你/但我怎么能說謝謝你?我也同樣管不住我的酒。”而在《給我的女兒》(ToMyDaughter)中有這樣的詩句:“你必須這樣——就是這樣!/女兒,你不能喝酒。/它會毀了你。就像它毀了你媽媽,毀了我。/就像它曾經毀了我們”,人物的憤怒與無助躍然紙上。
3 醫學人文關懷的彰顯
3.1 醫患溝通
卡佛的詩歌提供了許多有關醫護人員與患者如何溝通的例子:為什么,怎樣,在哪兒,溝通成功還是失敗,等等。如在《醫生說的話》(WhattheDoctorSaid)一詩中,當醫生要告知病人面臨死亡的訊息時他并沒有選擇專業術語。醫生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接近患者面臨死亡的現實,而且更要超越這個現實。在詩中,醫生說道:“你信教嗎,你會不會跪在/森林的小樹叢里讓自己祈求神助?” 通過使用“神助”這類的語句,醫生對治療和愈合進行了區分。治療可以消除疾病,但愈合卻能幫助患者成為一個健康而完整的人,勇敢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患者沒聽懂,“也不知道該做些什么”,于是跟醫生握了握手,說了些感謝的話。這是一個異樣的,甚至尷尬的反應,但它表明,患者已經接受了醫生的說法,甚至認為“是他剛剛給了我/這個世上別的人不曾給過我的東西”,——面對死亡時一個似是而非的生命禮物。通過握手這個動作,醫生和患者都從自己的空間里跨出了一步[7]。
與《醫生說的話》中成功的交際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首《求婚》[5]287。詩歌的第二節這樣寫道:
幾天前一些事情變得清晰
我們一直憧憬的未來的這些年月
都將不復存在了。醫生終于談到我將留下的
“這副軀殼”,他正盡最大的努力帶我們逃離
眼淚和兇兆的深淵。“但他愛他的生命。”我聽到一個聲音說。
她的聲音。年輕的醫生,幾乎沒有停頓,“我知道。
我想我們不得不經歷那些生老病死。最終
你們會接受。”
在詩中,盡管患者和他的家人非常痛苦,醫生還是頑固地、一板一眼地告知事實。這首詩表明,這位醫生受過的培訓以及他的年輕不成熟讓他面對患者時就像閱讀一本教科書似的古板,而不是以適當的方式回應患者的情況。
3.2 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是對瀕死患者進行的治療和護理,其本質是緩釋或者消除患者死亡時精神上的恐懼與肉體上的痛苦,讓他們保持著人的尊嚴,接受死亡,平靜地邁向死亡。《我的死》(MyDeath)一詩非常形象地展示了瀕死患者臨終前的渴望:“我希望,某人會給每個人打電話/說,‘快來,他不行了!’/他們就來了。”這首詩寫于卡佛去世前四年,它為親人提供了具體的指導:他們應該如何回應?患者又希望他們對那即將到來的痛苦作出怎樣的反應?卡佛在詩中寫道:“如果幸運,他們會走上前……/他們會舉起我手說‘鼓起勇氣’/或‘會好起來的’……/為我慶幸吧,如果我能在朋友和家人的注視下/離去”。卡佛通過創建這種死亡模式,呼吁家人能夠給予臨終患者充分的情感照顧和生命尊重,更希望人們能夠坦然無畏地面對死亡,就如詩中所說的那樣——“我多么愛你們,多么高興/這些年有你的陪伴。無論如何/別為我太悲傷”。
3.3 解剖室人性再現
在卡佛的好幾首詩里都可以找到對尸體的描述以及尸體對凝視者的情感沖擊,如《給普拉特醫生,一位女病理學家的詩》(PoemforDr.Pratt,aLadyPathologist)、《照片上的威斯·哈丁》(WesHardin:FromaPhotograph)等。20世紀60年代中期,卡佛在薩克拉門托的一家醫院做過一段時間的看門人和護工。《解剖室》[5]32一詩對尸體解剖室的情況描述可能源自卡佛自己的這段經歷,他以“元病理書寫”的方式描述了解剖室的內部人員面對現代醫院中尸體的處理方式表現出的痛苦矛盾之情,詩歌的第一節這樣寫道:
那時我還年輕,像十歲孩子一樣精力充沛。
對任何事都是如此,我以為,盡管我夜間的部分工作
是等驗尸官的工作完成后
打掃解剖室。但偶爾
他們下班太早,或太晚。
老天作證,他們會把東西遺漏
在他們特制的桌子上。一個小嬰兒,
安靜得像塊石頭,冷得像雪。另一次,
一個白頭發的黑人大高個,胸部
已被打開。他所有的生命器官
都擺在他頭部旁邊的一只盤子里。
軟管里的水在流,頭頂的燈發出白光。
還有一次是一條腿,一條女人的腿,
擺在桌上。一條蒼白的線條優美的腿。
我知道是什么。從前我看過。
但它仍使我透不過氣來。
此節對解剖臺上發現的內容的描述是從一個整體轉移到部分:先是一個嬰兒,然后是一個男人的部分軀體,最后是一條女人的腿。同時,這三具尸體代表了不同的年齡、性別和種族,因此也代表了人類的形象:為了進行科學的研究,人類逐漸衰退的軀體完全暴露在解剖室光亮的“頭頂燈”的照射下。隨著現代診斷和治療的高科技設備的出現,患者變得越來越物體化,人性的成分越來越少[8]。以尸體舉例,醫生和研究與采取行動的科學“對象”(即尸體)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寬,并且對“患者”人格的漠視的傾向也愈加強烈。然而,《解剖室》這首詩的敘事者并不是一名醫生或醫學生,他只是“看門人”和清潔工,在他看來,擺在他面前的不是專業人士口中所謂的研究對象,而是獨立存在的主體。所以,尸體擺放方式(物體化的、非人性的殘肢)所展示的殘酷現實與他人性的本能產生的沖突使得他非常震驚和困惑。
第二詩節中,主人公回到了現實,當他看到一個真正的女人的腿,活生生的腿時,他奮力做了兩個動作——“我會睜開眼睛,盯著天花板,或者/地板。然后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她的腿”——緊跟著說:“什么事也沒發生。一切都正在發生。” 他對妻子撫慰的話語和親密的舉止表示出抗拒,似乎完全不想跟妻子傾訴自己的痛苦。
然而,這首詩通過轉喻和共情的方式向讀者展示了重拾人性的過程。殘肢代表整個人是一種本能的感覺,這種充滿憐憫的情感讓主人公有足夠勇氣去面對那冰冷的解剖臺展現在他面前的殘酷現實。正是這種姿態,如同悼念中要尷尬地表現出“悲傷”一樣,與試圖將破碎的肢體與一個完整的身體聯系在一起的行為同等重要。同樣,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經歷所導致的笨嘴拙舌以及手足無措也被認為是溝通中努力人性化的表現[7]。
《解剖室》精確描述了一個外行人如何在醫學背景下與非常具體的死亡場景做斗爭的情況,是個體對重拾人性所做的努力。與解剖相關的詩歌,醫學生還可以讀到詩人西爾維爾·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尸解室的兩個畫面》(TwoViewsofaCadaverRoom)和醫生戴安·羅斯登(Diane Roston)的《學習解剖》(OnStudyingAnatomy)。伯納德·莫克漢姆(Bernard Moxham)曾指出:“對于今天的許多醫學生來說,熟悉人類尸體將是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這種經歷,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是非人性化的。然而,如果制定一些對策,就可以使它成為一個積極的經歷。”[7]卡佛的這首《解剖室》可能有助于找到解決這種困擾的對策。
4 結語
詩歌閱讀能夠幫助醫學生構建共情想象空間,促進醫學生感受故事和情緒的力量。閱讀敘事詩歌或抒情詩歌所獲得的共識不是經由推理(reasoning)而來,而是經由感同身受的認同和想象得來。雷蒙德·卡佛的詩歌中對人性的冷靜拆解其實是對20世紀后期的醫學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而根據醫學人文學家的觀點,這個時期的醫學已經禁錮在科學術語的誤區,患者的人格和身體被簡化為隱喻文本一般,供冷漠的專業人士“閱讀”。
卡佛在訪談錄中曾提及自己的寫作目的,是“要證明每一首詩或每一部小說都可以被視為……作者的一部分,被視為他對他那個時代的世界的見證的一部分”[9]。卡佛作為短篇小說家因其后現代極簡主義風格而聲名鵲起,但在21世紀的今天,研究學者看到了作品中展現的醫學人文主義要義。同樣,他的詩歌也是一種人文關懷的抒情表達,這種醫學人文關懷的體現有助于重建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共情聯系,有助于重拾現代衛生機構背景下“將患者看作完整個體”的人性化理念。
敘事醫學人文教育提倡醫學生廣泛閱讀甚至創作與生老病死、疾病和療愈相關的詩歌,達到提升自我職業認同、患者心理狀態理解和職業壓力自我緩解等目的。除此之外,敘事醫學還提倡醫生在必要時根據患者具體情況向患者有針對性地推介詩歌進行閱讀,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患者健康素養提升和自我疾病狀態認同等功效。每天推薦患者讀一首十四行詩雖然不能幫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但可以幫助患者預防糖尿病倦怠——亦即糖尿患者對控制病情感到精疲力竭的心理狀態。詩歌不僅能夠幫助連接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鴻溝,而且對患者心理上的治愈具有重要的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