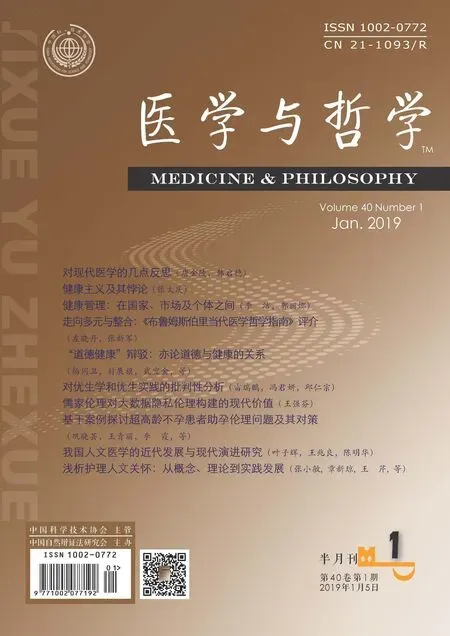我國人文醫學的近代發展與現代演進研究*
葉子輝 王兆良 陳明華
醫學的現代發展展現出科技進步對人類健康維護的強大現實支撐。特別是生物技術、基因技術、手術機器人的臨床應用,推動醫學實現對人類健康全過程、全周期的維護,卻也存在著醫患關系緊張、缺乏人文關懷、扭曲生命價值等倫理問題。人文醫學的興起發展是從最初的理念、理論逐步發展成為具有理論基礎和知識體系的新興學科[1]。人文醫學在我國的發展先后經歷先天不足、中西醫的交互影響和回歸本質發展的階段,我們需要進一步梳理現階段人文醫學發展的腳步,研究其內在的發展邏輯、探索人文醫學的發展路徑。現代醫學在我國的傳播發展,在最初的預冷、后期的火爆,其中也穿插著與本土中醫的市場、政策支持、社會話語權的爭奪,既有過廢除中醫的政治風波,也出現過西學中、以服務人民為背景的社會運動。
1 人文醫學,現代醫學傳播中的先天不足
人文醫學在我國的發展存有先天不足的情況,其主要原因是現代醫學在我國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并非是通過內生型社會科技發展促進現代醫學誕生,而是外源性技術通過技術輸入式的形式在我國傳播發展,我國在清末民初時期并未形成或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現代科學體系和社會環境。現代醫學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存有“輸入式”和“引進式”兩種傳播形式。輸入式即外籍醫生在國內執業行醫,同時兼以傳授知識和技術[2];引進式即中國學生前往國外學習現代醫學技術后回國執業行醫并傳播[3]。無論是“輸入式”還是“引進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技術與社會認知脫節的情況,即社會對現代醫學的認知和社會意識的形象表達并非如西方現代醫學發源地一般[4],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的認知存在很好的良性互動,即醫學中缺乏人文屬性,這一階段自現代醫學傳播以來為伊始到建國前。
現代醫學在我國的發展是以技術為傳播先導,作為現代科學體系的傳入晚于醫學技術應用在國內的開展,最初作為“奇淫秘技”的現代醫學產生了顛覆傳統認知的社會性恐慌[5]。相比較于我國傳統醫學,現代醫學有著治療效果更佳等優勢,但在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社會認知中,是以一種“技”的形式存在。在“技”的認知社會背景下,現代醫學的發展傳播也僅以技術傳播的形式展開,在其傳播伊始便存在缺乏與之相適應的社會認識和社會理論支持系統,特別是缺乏西方現代醫學發展過程中伴隨之發展的醫學倫理學和醫學哲學,即扎在現代醫學頭上的“緊箍咒”。兼具傳教士身份的醫生和醫學教育者們在進行技術傳授的過程中,難以在東西方文化背景差異的情況下有效地將醫學本身的人文精神內核進行傳授。同期中國的留學生在西方學習現代醫學的過程中同樣存在重技術輕人文的潛意識。
現代醫學的外在規范和社會共識規范形成是在一個長期的科學與愚昧的互動斗爭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外在的人文性、社會性規范是針對醫學科學技術可能存在的惡而產生的[6]。醫學的傳播缺乏與之相適應的社會規范話語體系,因現代醫學相較于傳統醫學有更為明顯的治療效果,進而醫學在身體控制和疾病治療方面形成了絕對的話語體系[7]。
20世紀初的現代醫學,在傳入我國的伊始已經是幾乎接近成熟的科學技術,能夠有效維護人類群體健康、延長群體生命、保護人類免受傳染病的襲擾。早期的醫學教育培訓并未有與之相適應的人文理念進行傳授,國內最初的現代醫學高等教育的發軔多是以教會醫院為基礎的師徒傳承制的形式展開的。“醫學救國”的口號更是將技術作為核心理念深入留學生的內心。“醫學救國”是近代以來對醫學的社會意識,認為可以通過對機體的技術性幫助實現國人強健和國家富強。同時現代醫學的發展傳播過程中存在以否定中醫的形式推動現代醫學走進社會和為民眾所接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醫存廢之爭”亦是一種重技術輕人文側面的反映[8]。
在存有先天不足的情況下,人文醫學的早期起步與發展,從最早的協和中文部誕生開啟人文醫學與醫學人文等相關問題的討論,作為現代醫學人文反思的開端[9]。醫學法學、醫學倫理學、醫學史等醫學人文課程和研究在醫學院校的引入,開始推動人文醫學在我國的發展。對醫學的認識初步從技術的單一狹窄視角轉換到相對更為全面、帶有人文屬性的視角后,醫學科技的發展表現出更為強勁的生命力。人文醫學在經歷民國時期的發軔后,遭遇了外在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戰爭、動亂都給醫學人文前進的腳步帶來新的坎坷。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醫學的發展傳播、推廣呈現出的是不可逆的歷史時代潮流,這種潮流下卻也存在有社會的盲目認同和不分主次的接受。醫學科技的快速發展和專業化的精進,呈現出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性規范脫節。
2 政治推動下的人文醫學發展
建國以后,人文醫學的傳播與發展主要體現在“西學中” 和“醫學應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等政治運動中,同時因為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對醫學全過程的參與,進一步推動了人文醫學的發展。
初期在全國衛生政策的道路選擇上存在對中醫有失偏頗的方向,直接促成了毛澤東同志做出西醫應當向中醫學習的指示,“西學中”運動,客觀上推動了人文醫學的發展和醫學人文理論的提升,其關鍵在于通過“摻沙子”運動安排中西醫工作者一同工作學習,實現將中醫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帶入到西醫中去。這彌補了現代醫學在我國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先天不足。
建國后經歷了十余年的發展,我國的醫藥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依舊存在重要的問題,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便是體現,即醫療衛生資源發展的分布不均和城鄉差別較大,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并未實現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維護,這顯然與黨和國家的人民群眾路線相違背。國家的經濟社會建設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利益,并為人民群眾服務,醫療衛生發展亦是如此。因此,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在醫療衛生體系內開展“醫學應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政治運動,這客觀上也進一步推動了人文醫學發展和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本土化。
在院校教育中,馬列主義教研室實現在國內醫學院校全覆蓋,黨、團、工會等政治組織也以不同形式進入到各類醫療機構中,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深入到醫學臨床實踐中,人文的腳步以另一種形式進入到醫學教育體系和臨床服務中。現代醫學在我國的傳播發展中人文的腳步以別樣的形式重新進入了醫學的視野,相比較于西方醫學人文發展中的生命倫理學、敘事醫學等學科的興起和發展,以自然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將醫學的科研和技術運用落在“實用主義”的范疇,即以中國現有技術實現對所面臨問題的最大限度解決。同時,以政治視野看待中國醫療問題,實現以為人民群眾服務、“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為核心的醫療服務精神在醫療行業的傳播,實現政治通過醫學對人實施關懷,實現政治人文關懷和醫學人文關懷的結合,推動人文醫學的實踐發展。
與同期西方國家的人文醫學發展相比,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醫學教育和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在學科交叉與社會思潮的影響下,人文醫學發展在20世紀中葉實現了“從靜水流深到漣漪漾起”的轉變[10]。
3 回歸應有之路的人文醫學與多元化發展
人文醫學在我國近代現代醫學的傳播發展伊始所存在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回歸科學與人文發展的應有之路。醫學有著自身固有的邊界,醫學應當在求“真”的同時更應該求“善”,這其中的“善”便是醫學的人文[11]。新時代人文醫學的發展進步與醫療衛生政策的推進,醫學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在逐漸增大,已經由“治病救人”拓展到“健康中國”的更廣闊的天地,人文醫學的發展也應抓住人文的本質順應時代的潮流實現多元化拓展。
3.1 回歸應有之路
改革開放后,中斷數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再次開始,在醫學科技發展和臨床技術應用等方面中國再次認識到東西方的差距,要注重技術的引進和人員的交流。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逐漸走向深入,西方的第二波醫學人文研究成果也逐漸被翻譯到國內,隨著西方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思路的引入,學者也逐漸認識到醫學的人文屬性和人文醫學的發展影響現代醫學的發展和社會接受。我國學者也在認清差距后積極加入到第二次生命倫理學研究的浪潮中,1979年召開的全國醫學辯證法講習會以及《醫學與哲學》雜志的創辦,呈現出內生型發展與外源性輸入并存共榮的局面。
人文醫學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為其帶來最為直觀的體現便是醫學人文課程在醫學院校的增加,人文醫學專業的研究生培養也在幾所高校做了嘗試,人文醫學專業人才的培養為人文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醫學哲學專業委員會、中國醫師協會人文醫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也將人文醫學的研究學者逐漸凝聚起來,形成學術合力推動人文醫學的理論發展。與此同時,執業醫師資格考試中增加了人文執業理論考核內容,近年來在全國范圍推廣實施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也要求將人文執業和醫學人文的內容融入培訓的全過程,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醫學為人服務。
課程的增加、考試內容的增加、培訓過程的重視,這一切都是外在的形態變化,在逐本溯源的過程中推動人文醫學的發展。逆專科化的臨床學科設置讓患者的就醫過程不再只是單純的“治病”,轉而是以人的機體康復為重要目的,將人放在臨床治療中的首要位置,實現醫療全過程服務于人的健康。
人文醫學的發展推動醫學人文關懷的理論基礎建設,其中最關鍵的依舊是解決現階段我國社會發展對醫學最迫切的要求才是真正關懷人的醫學。人文醫學的理論發展與中國的醫學發展實踐相結合,同時也受我國衛生政策發展所影響。人文醫學的理論發展回歸學科發展的規律,卻也面臨著醫藥衛生體制變化的不確定性,呈現出發展的艱難性。
人文醫學發展中理論的宏大敘事與現實的執行無力彰顯出人文醫學的發展過于注重理論,進而忽視理論應與實踐相結合。縱觀理論研究,從一線臨床護士到高校理論教師都在談人文醫學與醫學人文,卻未將人文如何走進醫學、走進臨床,如何推動醫學服務模式的改變作為問題。如同近年來臨床實踐所面臨的“博士不會看病”的尷尬境遇一樣,人文醫學也面臨著“空談”的問題。人文醫學的發展更多地需要推動醫務工作者,特別是一線的臨床醫生和護理人員能夠理解醫學的人文性,將人文醫學的發展融入到臨床實踐中。人文醫學的發展只是醫學人文性展現的外因,關鍵在于將外因傳導作用于實踐醫學的個體中,并改變現有的醫療服務模式,真正做到以人為中心。
3.2 人文醫學的多元化發展趨向
醫療行為從傳統醫學的熟人社會和家庭醫療方式逐步轉變為具有統一標準的工業化社會形態,流水線作業式的醫療模式逐漸呈現出將人的個體獨立性融入到社會化生產的群眾中。
人文醫學發展最直接的目的即是人的健康,延伸的發展就是機體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并存,同時以“治未病”更好地促進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人文醫學是融入在醫學中的人文價值,是在具體實踐中從醫務工作者的個體勞動中呈現出的群體效應,即醫學為人的健康存在服務發展。人文醫學理念的提出呈現的以人類社會在面臨醫學所支配的話語體系中要求醫學的發展應當更尊重人,其發展更是以話語體系展現關于文化和價值的思考。健康中國事業的推進與人文醫學的發展呈現出一種新的交織發展形態,在醫學深度參與日常生活的過程中,人文醫學的發展應更好地推動醫學在融入社會日常的過程中保持決策的被動性,即保持人的主體自覺性。
人文醫學的發展同時,國民經濟水平和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升,社會大眾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從基本機體健康轉變為對生命質量的追求。伴隨醫學快速發展的還有不斷擴大的疾病譜系和復雜疾病的發病率,受醫療服務資源分布不均衡、水平發展不充分,居民在某些程度上獲得的醫療照護并未呈現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提升。在現有條件下醫療服務資源將被最大化地利用,實現對人民健康的最優服務,人文醫學發展的道路依舊漫長且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