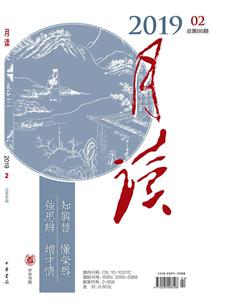說“裳”
富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大詩人李白的這首《清平調詞三首(其一)》,不僅感動了作為當事人的楊玉環和李隆基,而且將后世很多人引入到對美人美貌以及那場繁華如夢的盛宴的無限遐想之中。連云彩都想擁有跟楊貴妃一樣的華麗衣裳,連花兒都想擁有像楊貴妃那樣的嬌美容顏……這樣極盡浪漫的詩句,讓人分不清到底是人更美,還是詩更美。當我們從沉醉和想象中抽身,細究字詞時,會發現詩中的“衣裳”并不同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衣裳”。它們的區別究竟在哪?這還要從“裳”字說起。
“裳”由“尚”和“衣”組成,“尚”表示字的讀音與“尚”字接近,“衣”表示字的意思跟衣服有關。“裳”最初是指穿在下身的衣裙,屬于裙子的一種,而不是褲子。這種“裙子”,無論男女皆可穿著。它的讀音是cháng,而非我們今天常讀的shang。

明代赤羅朝服。上衣為交領右衽,裳為一圍裙;衣、裳都以輕薄鮮艷的赤羅衣料制成。
“裳”與“常”曾經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說文解字》將“裳”附于“常”后:“常,下裙也。從巾,尚聲。裳,常或從衣。”后來,二字逐漸有了分工,“常”用于其他意義,而“裳”表示“下身穿的衣裙”的意義則沿用下來。
古人的服飾與今人不同。上衣和下衣是分開的,“上衣下裳”;上衣和下衣連在一起,則為“深衣”。“上衣下裳”和“深衣”此消彼長,曾經是不同時期的主流衣著方式。而且,古時男人和女人的衣著差異也不像今天這樣顯著,“裳”這種“裙裝”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男女共通的服飾。
《詩經·豳風·七月》:“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講的是用鮮亮的紅色給貴人做裙裳。《世說新語·言語》:“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褰裳濡足”,直白地說就是撩起衣裙,打濕雙腳。如同身著褲裝的現代人下水之前需要挽起褲腳一樣,身著裙裳的古人自然也需要撩起下身的衣裙。因此,“褰裳”是古人涉水前的一個必要舉動,如《詩經·鄭風·褰裳》有“褰裳涉溱”“褰裳涉洧”,晉代葛洪《抱樸子外篇·廣譬》有“褰裳以越滄海”等。后世又以“褰裳”比喻不辭勞苦,急于為國事奔波,例如清代黃宗羲《錢忠介公傳》:“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
當作為“上衣”的“衣”和作為“下衣”的“裳”并舉,出現在古詩文當中時,二者往往各司其職。例如《詩經·邶風·綠衣》:“綠衣黃裳。”《離騷》:“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以及《詩經·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后面兩句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把衣服穿顛倒了,而是說在慌亂之中把上身穿的衣和下身穿的裙裳弄顛倒了。
跟最初專指“上衣”的“衣”可以發展為“衣服”的通稱一樣,專指“下衣”的“裳”后來也可以泛指衣服。例如《樂府詩集·木蘭詩》:“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以及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等等。
在中國古代傳說中,神仙以云為裳,因以“霓裳”一詞指仙人所穿的衣服,例如屈原在《楚辭·九歌·東君》中贊頌身為“太陽神”的東君:“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霓裳”后來也指《霓裳羽衣曲》或《霓裳羽衣舞》,例如白居易《琵琶行》:“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為《霓裳》后《六幺》。”以及清代納蘭性德《明月棹孤舟·海淀》詞:“一片亭亭空凝佇。趁西風、霓裳遍舞。”《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宮廷舞曲,曾經盛極一時。關于此曲的由來,有不同說法。據傳,它描繪的是身著霓裳羽衣、蹁躚起舞的仙女形象,大概由此而得名。
既然上為“衣”,下為“裳”,上下合在一起為“衣裳”,那么,“衣裳”演變為衣服的通稱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衣”和“裳”皆可泛指衣服,“衣裳”連用泛指衣服也是順理成章的。乃至到了后來,“裳”逐漸失去了獨立的身份,成為附著于“衣”的成分,讀音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shang。由此,就有了今天“衣裳(shang)”的“裳”。
可見,古代的“衣裳(cháng)”并非今天的“衣裳(shang)”。了解了這一點,當我們再次讀到“云想衣裳花想容”或者談及《霓裳羽衣曲》的時候,是否會有不一樣的想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