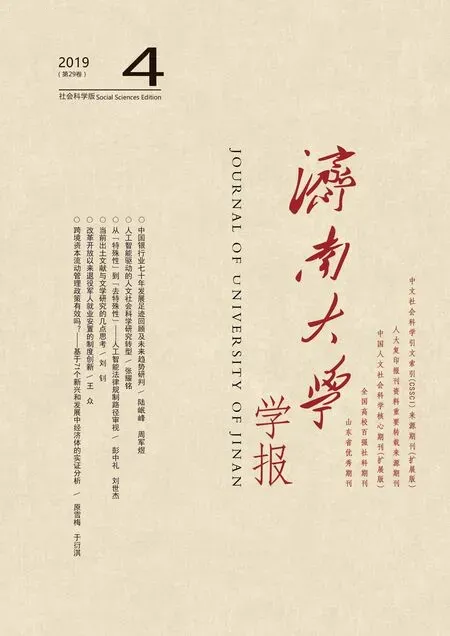“智能+”模式下裁判形成的過程分析
謝 慧
(山東師范大學 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表達司法裁判的形成,它大致可以描述為法官是用何種方法來解決具體案件從而獲致判決的一個過程。早在19世紀,裁判的形成過程被簡化為形式邏輯三段論,法官應受“法律嚴格的赤裸裸的條文”約束,“其行為不應外乎將提交的案件與條文比照,且不考慮法律的意義和精神,在詞語的聲調為譴責時表示譴責,在條文沒有規定時,沉默無語。”[注][德]費爾巴哈:《庫爾-法耳次-巴伐利亞公國刑法典克萊因施羅德草案批判》,1804年,Ⅱ第20頁。轉引自[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無疑,這種法官僵硬機械遵循法律的觀點在20世紀受到了強烈的批判與攻擊。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與法律的遭遇卻使不斷被嘲諷的“自動售貨機”理論開始成為了現實。
當然,人工智能遠比“自動售貨機”智能的多。四十多年前,Buchanan和Headrick在《關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問題的考察》一文中,就已經對人工智能應用于司法裁判的形成提出了預見性觀點,在他們的意見中,司法人工智能系統并非如馬克斯·韋伯所言的“自動售貨機”那般“投進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用,送出來的是判決”,而是強調類推的重要性與法律推理模型的可行性,借助于計算機編程來建立裁量模型,同時運用各種法律知識,通過計算機模擬人的法律推理過程[注]Buchanan Bruce G, Headrick Thomas E:“Some Specula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 Stanford Law Review,1970, 23(1) .。時至今日,這一在當時具有前瞻性的理論正在逐步實現,從基于規則模擬歸納推理的JUDITH律師推理系統,到整合了主體思維結構的TAXMAN系統[注]參見張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法理學思考》,《法學評論》,2001年第5期。,直至借助PROLOG程序語言的推理功能實現了國籍法實務的人機對話[注]參見[日]松尾宏:《英國國籍法的邏輯程序化》,載[日]吉野一編:《法律專家系統的基礎》,日本吉幽塞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頁。轉引自季衛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司法權之變》,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人工智能可以運用諸如消解原理、規則演繹系統、產生式系統、不確定性推理與非單調推理等推理技術和系統,來處理復雜的問題。智能技術群的形成推動著萬物互聯邁向萬物智能,快速將我們以及我們的社會帶入了“智能+”的時代,裁判的形成終于不再只限于對法官行為與思維的討論。
在交通、制造、金融、商業、醫療、教育、農業、政務等實務領域紛紛對接人工智能的大潮中,“智能+司法”在各國亦是風起云涌。美國Blackstone Discovery公司開發了能夠為法官提供法律分析的e-discovery系統,哥倫比亞在此基礎上研發出可以根據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為決策者提供有價值信息的ASSYST系統,而我國隨著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發布,“智慧法院”的建設更是如日中天。深圳鹽田區法院開發建設的金融類案件全流程在線辦理平臺率先實現了金融類案件從立案、審判到執行全流程在線辦;各地法院相繼開發了各自的類案推送系統,或者在智能輔助辦案系統中嵌入了類案推動應用模塊[注]例如,貴州省高院的“類案裁判標準數據庫”、北京市高院的“睿法官系統”、蘇州中院的“案件裁判智能研判系統”、上海二中院的“C2J法官智能輔助辦案系統”、河北省高院的“智審1.0系統”等等。參見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探索“類案類判”機制確保法律適用統一》,載《人民法院報》,2018年1月26日;李希:《北京法院探索建設“智慧法院”“睿法官系統”正式上線》,http://www.bj148.org/zzgjj/zzdt/201612/t20161214_1277407.html,2019年5月1日訪問;羅書臻:《挖掘“富礦”“反哺”審判——運用裁判文書大數據促進司法公正的地方經驗》,載《人民法院報》,2017年9月1日。高紹安:《上海二中院“智慧法院”的探路者 里程碑意義的C2J法官智能輔助辦案系統正式啟用》,載《人民法院報》,2017年7月10日第1版;吳曉霞:《河北法院“智審1.0上線運行”》,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7月5日第1版。;2017年“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206系統)誕生,它在對上海幾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書數據進行學習后,已具備初步的證據信息抓取、校驗和邏輯分析的能力;2018年人民法院的“智慧法院導航系統”和“類案智能推送系統”正式上線運行,實現了精準定位導航信息以精準投放訴訟服務,以及快速查詢和智能推送信息,輔助量刑決策、規范司法裁判尺度以統一法律適用的目的。
在“智能+”模式下,法律推理系統、法律模擬分析系統、專家系統等技術開發以及案件智能推送、裁判結果預測、裁判文書自動生成等審判創新在司法過程中接踵而來,裁判披上科技的外衣,獨角獸幻化出雙翼,司法裁判的形成是否正在經歷著一場“革命”?人工智能的介入又將在多大程度上改寫了司法的過程?有人歡喜,有人憂懼,本文從裁判形成的一般過程,審視人工智能的司法介入方式與運作機理,以期還原“智能+司法”的本來面目。
一、規則&法官:裁判形成的理論解析
就形式而言,司法裁判的形成一頭系著法規范,另一頭連著特定的生活事實,裁判的獲得過程便是將抽象的、規范性的法律規范應用到具體的、經驗性的生活事實中,從而妥當處理特定社會糾紛的一個過程。這種從規范到事實最后推出個案結論的過程也被理論化為法律涵攝理論,而司法涵攝是否僅僅依靠形式三段論推理而發生,這向來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議題。
(一)法律適用的邏輯骨架
上升到理論來看的話,裁判的形成實質上關乎法律適用理論。受近代自然科學思想的影響,傳統的法律適用模式一開始就試圖按照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目標來發展自己[注]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在自然科學觀看來,法律適用是邏輯三段論的演繹系統在法律領域的使用過程,即通過將特定的案件事實歸屬于某一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而將一定的事實作為小前提,在該事實符合大前提所規定的各項要件特征時,則以一定的法律效果為內容的結論將確定地產生[注]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這被拉倫茨稱之為“古典的”涵攝模型[注][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4頁。,它對法律邏輯的一慣性和體系性推崇極致,強調“法律推理應該依據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以及邏輯去解決一切為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假如法律能如此運作,那么無論誰作裁決,法律推理都會導向同樣的裁決。”[注][美]史蒂文·J·伯頓:《法律和法律推理導論》,張志銘、解興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法律適用理論由此建構了一個由概念構成的體系世界和邏輯世界,而“概念的譜系學”又保證了規則對于法官的嚴格約束,以及所有實現規范所規定的條件的案件事實均受到相同的處理,因而由此獲得的判決,便是客觀的,也是正確的。
自然,上述以概念為主要方法的推理模型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礎在晚近以來遭到了諸多詬病,因為“一個無視人類作品目的的,亦即,一個無視人類作品價值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對法律的,或者對任何一個個別的法律現象的無視價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注][德]G·拉德布魯赫:《法哲學》,王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20世紀以來,法律適用理論開始超越單純的三段論,集多種方法與多種思維為綜合一體。然而,盡管幾乎所有的批判者都智識性的認識到傳統涵攝模型的缺陷,但是都并未將其作為排除在法律適用的思維過程之外的理由,相反,他們無一例外的都不否認涵攝仍具有一定的功能和價值[注]德國的考夫曼在哲學詮釋的影響下,雖然認為傳統的涵攝模式實際也是一種類推,并指出法律適用不再是一個嚴格的邏輯三段論的推論過程,而是一個文本不斷被理解不斷被反思的過程,但他并非徹底反對邏輯本身,而是認為三段論的邏輯涵攝并不能反映法律適用過程的全部面相,它不過是法律適用的最后階段,是在將法律規范與生活事實以一種目的論的程序使兩者進入一種類似性關系之后才發生的。考夫曼在其書中說道:“其實按照我的學說,也有邏輯三段論及涵攝。只是在進行以前,必須規范及個案成為有涵攝能力。”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吳從周譯,顏厥安審校,臺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頁、第171頁。而德國另一位學者恩吉施則是通過將傳統的法律解釋方法進一步精致化,以試圖說明建立在三段論基礎上的法律適用大體上仍然是可行的。他指出:“……只有基于屬于法的更大范圍的、制定法與之適應的價值,才能適用、解釋制定法,在必要時補充和續造制定法。……對制定法的逐字逐句的適用,會阻礙制定法原本的理性目的,還有,在處理立法者本身的‘公道法’(ius aequum)的時候,將求助于非制定法的價值,關于填補制定法漏洞需要的認識和用超制定法的價值來校正制定法的價值的必要性。最終,超制定法——盡管不是超法的——權衡,決定著解釋本身的方法,尤其是決定著解釋手段的次序,決定著解釋中的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的正確性,不是嗎?”參見[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鄭永流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頁。此外,英美法中以“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這一名言而著稱的霍姆斯,在事實上并非反對邏輯的作用,而只是反對將邏輯看成是案例適用的全部內容、唯一起作用的因素的觀點。“……簡單地說,霍姆斯的反邏輯其實是反對當時的形式主義的傾向。他反對的只是認為法律中唯一起作用的是邏輯的觀念,而不是反對邏輯的作用。或者說它是深刻認識到邏輯的局限性才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參見張芝梅:《法律中的邏輯與經驗——對霍姆斯的一個命題的解讀》,《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因此,雖然事實上的法律適用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但以“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為框架的三段論模型依然被視為法律適用的基本“邏輯骨架”,也即“特定的法律人將一個法律規范N適用于由事實構成的一個案件C,得到一個正當的法律決定D”,這一基本模式可以簡單的表示為:法律規范(N)→案件事實(C)→法律決定或判決(D)。
(二)裁判形成的多層結構
如果對概念法學和形式主義法學批評者的論述作一個總結,我們不難發現,盡管表達方式各異,但他們的觀點卻有著明顯的相似性,也即他們都從單純的邏輯推理發展到了兼采邏輯推理、利益衡量、價值判斷、公共政策、后果考量等等方法的綜合性力量。
具體來說,三段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大小前提都真實的基礎上的,但是大小前提并不能保證自身的真實性,如果對大小前提尤其是大前提本身提出質疑或者其本身就存在疑問,那么這種推理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注][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1頁。。因此,一個單純的三段論“邏輯骨架”是無法完成一個完整描繪法律適用過程的重任的,其間,法官要確定一個可以足以使公眾信服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它是“為給一個決定提供充足理由的過程”[注]Aleksander Peczeink, on Law and reason, Dordrech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156.,這被學者定義為“證成”,阿列克西認為,法律規范的適用就必然地包括了法律規范的證成,前者的結果依賴于后者[注]Robert Alexy,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rms, In:Rotio Juris. Vol.6 No2.1993,p.169.轉引自王夏昊:《法律決定或判斷的正當性標準》,《法律方法》(第八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證成”又被阿列克西分為“內部證成”與“外部證成”:內部證成處理的問題是,判斷是否從為了證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邏輯地推導出來,也就是說一個決定是否是從它的前提中按照一定的推理規則推導出來的;外部證成處理的對象是,對內部證成所適用的各個前提的證立[注][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舒國瀅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85頁。。如果將內部證成看做是一個“邏輯三段論”的運用過程,那么外部證成則是為了完成內部證成中需要的大前提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說明。
在三段論的基本模式中,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N并非是現成擺放好的制定法條款或判例法規則,而是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并結合法律規范及其他因素的說明而建構的裁判規范(Ni)。因此,裁判規范的生成過程是一個法官對法律文本以及各種規范進行發現、理解和闡明的過程,也是一個“外部證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官要運用一定的法律或法學中的理由,來揭示、選擇或確定某個法律規范的某個意義,構造裁判規則,并以此作為裁判的大前提,這便需要我們將裁判形成的過程延展到形式推理“大小前提”獲得的活動之上。此外,司法實踐也告訴我們,法官裁判的真正思維并非是“規范—事實—結論”的單向路徑,而是以其先接觸到的事實為思考起點,是一種目光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進行流連往返”的活動,其大致路徑為“事實—規范—事實—決定”。將上述作為“邏輯骨架”的三段論補充血肉之后完整地展現開來,則表現如下:雙方爭議事實的識別與確認(F)→法律文本的尋找與確定(S)→法官解釋(TR)→裁判規范(Ni)→經法官采信并認定的特定案件事實(CF)→法律決定或判決。也就是說,在許多案件中,“事實并不能輕易地為公認規則所歸攝,而且規則本身尚需要進一步解釋,合適規則還需要法官花心思尋找,更確切地說,從事實到裁決之間的思維有所跨躍(jump),裁判的思維通道可能是曲徑通幽。”[注]李安:《裁判形成的思維過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4期。
質言之,裁判形成的過程不是單純的演繹或者歸納,而是包括邏輯推理在內的多種方法、多種思考方式綜合作用的結果,在這一個過程中,法學的傳統、邏輯的理論、歷史慣例、價值判斷、利益衡量、人們的道德感、法感情以及人們不能言說的種種知識、偏見、下意識都有可能潛入其中。法官不是一臺機器,而是一個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被賦予必要的主觀能動性和法律推理的靈活性;規則(無論是制定法還是判例法)如哈特所言存在著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它原本自身就沒有應對現實世界變化無窮的能力,只不過是人們應對當下生活的一種書面規則而已,能夠感知不斷變化的生活繼而做出相應變化的只有人的認識和思想。
可以說,裁判的形成是一個規則與法官共同作用的過程,它既強調規則不可或缺的意義,又反對規則決定論;既拒絕法官完全按照自己的預感來隨意判案,又不得不承認其直覺的存在。在這一點上,龐德所言可謂中肯:“法律的歷史表明,人們始終是在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之間來回擺動,在據法司法與不據法司法之間不斷循環反復。”[注][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曹玉堂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而另一位作為“實用主義”的美國法官及法學家波斯納在探討法律決定制作時亦是一方面承認邏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拒絕夸大的法律形式主義[注]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頁。。
二、數據&算法:司法運行的“智能”模式
如前所述,裁判形成的過程經歷了從形式主義到實質主義的發展,這一理論脈絡打開了計算機法律推理模擬的思路。形式主義強調規則,于是便出現根據規則進行形式推理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式;實質主義注重個案,于是便出現根據個案進行非單調推理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式。盡管人工智能與人腦結構不同,但在抽象層次上二者卻越來越具有相通的功能表述。繼AlphaGo與AlphaGo Zero棋壇神話之后,“Alpha法官”的出現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可能[注]2015年11月,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用于庭審,其設計者認為這是“機器人法官”的雛形;2016年,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引入機器人輔助判案系統,并形象地將該系統稱為“阿爾法法官”。將司法大數據運用到司法輔助、辦案參謀、智能咨詢及決策分析等環節,法官輸入案由、情節等案件事實,機器人自動彈出應適用的法條,并顯示量刑建議,在法官確認之后,判決書便一鍵生成。參見《機器人法官的宣傳雷區——從南京中院“法律機器人”爭議說起》,http://www.jcrb.com/IPO/yjjj/201701/t20170119_1708642.html,2019年5月3日訪問。事實上,一位人工智能法官已經能夠評估法律證據,同時考慮倫理問題,然后決定案件當如何判決,它能夠準確預測歐洲人權法庭大多數的裁定,或很快能夠對案件作出重要裁定。參見楊帆:《機器人法官來了:AI計算機預測案件的準確率達79%》,http://tech.ifeng.com/a/20161025/44477016_0.shtml,2019年5月3日訪問。。那么,果真如此嗎?
(一)司法人工智能的運作機理
司法運行的“智能”模式,實際上依賴于目前人工智能的新技術,即計算機能力的提升、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以及其學習技術的發展。嚴格來說,人工智能是計算機學科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讓機器人來模擬人的智能,處理一些特定場景和應用的問題。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的開發者主要關注對于一個具體任務的解決方式和應用潛力方面,也即其“內部智能”,而非其所呈現出具有奇妙感的外部效果。因此,盡管已獲得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的索菲亞機器人引爆了人類無數的追捧或恐慌,但事實上,由于其遠還未達到在開放領域進行流利的自然語言對話的程度,人工智能技術派并未對她寄予太多的“智能”期望;相反,對于可以自動作詩的“九歌”,研究人員卻因其基礎技術已涉及到語言本身的復雜性、多樣性、歧義性以及遞歸性,將其視為突破NLP領域最上層也最艱難的任務的一個典范。所以說,“機器人能否像法官一樣判案”這個問題只有在真正了解一些技術能夠達到的真實水平的時候,才會變得有意義。
萊布尼茨曾設想法律和哲學都可以依據經典幾何學模型對第一原理進行演繹,像數學分析那樣通過推論予以解決,他說:“我們要造成這樣一個結果,使所有推理的錯誤都成為計算的錯誤,這樣,當爭論發生的時候,兩個哲學家同兩個計算機一樣,用不著辯論,只要把筆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盤面前坐下,兩個人面面相覷地說:我們來計算一下吧。”[注][德]W·肖爾茨:《簡明邏輯史》,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85頁。萊布尼茨將法律進行理性演算的設想,在人工智能那里成為可能。通俗地講,人工智能學習的一般原理為要素化、規則化、圖譜化及模型化,它以法律知識圖譜、案件情節提取、類案識別、模型訓練、量刑預測和偏離度預測等為技術路徑,在實踐中表現為案件智能推送、法律模擬分析與推理、裁判結果預測、量刑輔助、偏離預警以及裁判文書的智能生成等應用。不過,從技術層面來看,無論是可以進行智能案情分析和律師遴選的“法小淘”,還是智能研判系統“睿法官”,如果去掉附著在它們身上的擬人化想象,它實質上是基于算法通過數據自主學習的一套計算機制,其本質在于算法和數據。也就是說,通過機器學習,機器要對海量數據進行自動挖掘與預測,以形成統一的智能化算法或參考指引[注]參見蔡自興,劉麗玨,蔡競峰,陳柏帆:《人工智能及其應用》(第5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頁;胡凌:《人工智能的法律想象》,《文化縱橫》,2017第4期。。
在司法過程中,具有大規模、多樣態、快流變、高價值特征的大數據為人工智能的知識生產提供了空間[注]See.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et al,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Analytics, 2011.,不管是識別和提取法律事實和情節、自動推送關聯法條和類案,還是推薦量刑和生成法律文書,甚至通過深度學習不斷提高裁判的準確性,數據都是萃取人工智能所必須的火焰。隨著儲存人類活動信息的各種資料實現電子化,大數據技術能夠綜合處理各種類型的數據,從而得出其數據背后的知識或隱藏的信息[注][美]托馬斯·埃爾,瓦吉德·哈塔克,保羅·布勒:《大數據導論》,彭志勇、楊先娣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數據帶來了可以讓機器具備認知與判斷能力的算法,也即機器的學習,這為人工智能提供了核心的運作方式。大數據的日漸發展不斷為機器學習算法提供更強勁的技術支持,進而又能夠產生更大的實際應用。大致而言,機器的算法有兩種類型,即基于先前知識的推理和基于大數據而發掘數據背后的規律[注][美]溫斯頓:《人工智能》(第3版),崔良沂、趙永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60頁。。前者實質是一種處理自然語言過程的問答技術,例如人工智能Ross律師與前文所提的索菲亞機器人,它讓人的自然語言與機器的代碼語言形成溝通,使機器能夠回答人類提出的問題。其運作是先“理解”和確定人類所提出的問題,再通過分析不同的文件內容找到合理的答案[注]Rhinehart Craig. 10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Technology Behind Watson.轉引于江秋偉:《論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空間及限度》,《學術交流》,2019年第2期。。它可以在同一時間內運行不同的算法來解決同一個問題,而當不同算法以不同方式運行都得到相同或相似的一個答案時,所得結果就是“真實的答案”[注]Thompson Clive. Smarter than You Think: What Is IBM’s Watson?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6-16. 轉引于江秋偉:《論司法裁判人工智能話的空間及限度》,《學術交流》,2019年第2期。。后者則是20世紀中后期以來發展的機器深度學習,主要有決策樹學習方法、類比學習方法以及人工神經網絡方法[注]參見[美]Start J.Russell,[美]Peter Norving:《人工智能——一種現代的方法》(第3版),殷建平、祝恩、劉越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在接受了用戶提交的數據之后,機器可以通過數據進行自我學習,僅依照系統規定的算法便能進行運作,而不需要用戶根據數據特點再進行算法調整[注]朱福喜:《人工智能》(第3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頁。。也就是說,機器從司法大數據中提煉出共性規則,然后根據不同的司法場景提取不同的規則進行匹配,形成類似于人類的信息提取能力與邏輯分析能力。
(二)深度學習下的智能裁判
從人工智能的發展路線來看,機器的深度學習推動了第三波人工智能熱潮興起[注]參見李開復,王詠剛:《人工智能》,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并使司法人工智能從使案件處理的自動化轉向了案件審理的自動化。其中,功能最強大、應用范圍最廣且居于主要地位的當屬人工神經網絡方法[注]參見蔡自興,姚莉:《人工智能及其在決策系統中的應用》,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頁。。人工神經網絡系統是模擬人腦及其神經網絡行為特征而發展出來的非線性運行模式,它由眾多神經元的連接權值連接而成,具有良好的深度學習功能[注]參見[美]雷·庫茲韋爾:《人工智能的未來》,盛楊燕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頁。。在知識圖譜構建的基礎上,人工神經網絡系統通過對知識圖譜數據特征的學習,從數據樣本中學習到數據的本質特征,從而提供對未知事件的分類和預測的精準性[注]參見吳岸城:《神經網絡與深度學習》,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在司法裁判中,人工神經網絡系統中的神經元節點通過對各裁量因素的擬合來滿足裁量因素復雜性的需求,而無需對各裁量因素進行精確的數字化表達或者事先設定各裁量因素的權重,同時,它可以對裁量因素進行層次性選擇,通過定義匹配規則來實現知識轉化,并在分類規則基礎上進行大數據學習,從而使自己具備預測新數據的能力[注]參見[美]Start J.Russell,[美]Peter Norving:《人工智能——一種現代的方法》(第3版),殷建平、祝恩、劉越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頁。。
具體地說,人工神經網絡系統在司法裁判中的運行運作機理和技術路線如下:首先進行由詞法、結構、過程等構成的語義網絡知識建模,即針對某特定領域建立知識圖譜,構造內部知識庫,以此作為分詞設置的基礎,同時對各分詞予以屬性標注以及各分詞的關系予以關系標注,以便作為在構造抽取規則時的信息提取點,然后將案件分解成最基礎的A、B、C等若干要素,要素對應若干分詞,以運算法則生成假設,并將假設與待決案件所包含的要素A、B、C進行對比,若干吻合或類似,則可適用同類規則[注]參見高翔:《人工智能民事司法應用的法律知識圖譜構建——以要件事實型民事裁判論為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6期。。其裁判過程可以簡單表述為:案件情況文本輸入→文本信息初步分類→文本信息精準分析→適用條文選擇→結果輸出。
這樣看來,司法人工智能的裁判方法與傳統的要件事實型民事裁判方法并無二異,它們都是按照“識別請求權基礎規范→請求權基礎規范的要件分析與結構→爭論點整理→證明責任分配→爭議事實認定→涵攝得出結論”的路徑而展開[注]參見高翔:《人工智能民事司法應用的法律知識圖譜構建——以要件事實型民事裁判論為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6期。,事實上,這一過程也大致契合實踐中法律適用的“事實—規范—事實—決定”的模式。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盡管其基本的“邏輯骨架”為“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但實際上裁判的形成過程具有多層的復雜結構,即雙方爭議事實的識別、確認與分析(F)→法律文本的尋找與確定(S)→法官解釋(TR)→裁判規范(Ni)→經法官采信并認定的特定案件事實(CF)→法律決定或判決。基于前文分析,我們得知人工智能可以像法官一樣行為,但它能否“像法官一樣判案”最終卻取決于它能否像法官一樣思考。
三、從前提到結論:智能司法還差什么?
對于一項特定的活動,有學者認為可以區分為觀測、分析和行動三個部分[注]Woodrow Hartzog, Gregory Conti, John Nelson, Lisa A. Shay, "Inefficiently Automated Law Enforcement", Mich. St. L. Rew. 1763(2015), p.1769.,而如果將一項司法裁判看作是一種對特定事件進行法律評價、判斷并處理的機制,那么這一項復雜的活動將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信息的獲取,即將特定案件中的事實問題轉化為有待進一步識別和處理信息;第二個層面為信息的分析處理,即將事實與特定法律規范的要件相匹配,確認待處理事件應該適用何種法律規范以及產生何種法律后果;第三個層面為信息的輸出與實現,也即通過一定的思維與行動機制,將上一環節的結果輸出到現實世界,對法律后果予以實現。
(一)裁判小前提的形成
第一層面信息的獲取,是通過證據推理發現小前提的過程。如麥考密克所言,“小前提并非一類可以由諸如大法官的意見或者議會立法等權威命令‘賦予’真實性的命題。它是表示特定歷史情境的命題,因此它需要借助于特定的相關證據加以證明。”[注][英]尼克·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姜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在這一過程中,法官會根據庭審中所接收到的碎片化證據,通過區分生活事實與法律事實以及基于證據的相關性、證明力以及可采信性,對于爭議事實進行識別與確認以提取其中具有法律意義的因素。其中,起到主導作用的是證據的可采信性,也即何種證據可以進入裁判門檻以及何種品質的證據可以進行推理。
關于證據的可采性,法官一般遵循“不相關的證據不可采”和“相關證據排除規則”[注]張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兩個難題和一個悖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后者涉及到相互沖突的價值之間的平衡,例如非法證據的排除,法官所需要權衡的便是證據的求真目的與諸如人權、秩序、正義等價值矛盾;關于證據的可信性,則涉及到對話者之間信息傳送、接受和加工所必需的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誠實性和敘述能力,它需要法官更多的經驗智慧[注]張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兩個難題和一個悖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而無論是價值權衡還是經驗體會,對于人工智能來說,都是一項極為艱難的工作。
此外,事實認定不僅需要識別證據的相關性或不相關性,證據推論亦是一個經驗推論的過程,它需依賴于法官個體知識庫的建立,“個體知識庫包括個人的生活經歷,是理解證據、選擇概括的基礎。”在很多時候,證據的推論背后隱含著法官個人的自由心證、內心確信、經驗法則以及信念,因此同一組證據的推論卻極有可能走向相反。例如,圣經中所羅門對“幼子之爭”的裁判與我們對“昭儀殺女”的判斷,便分別由“虎毒不食子”與“無毒不丈夫”的信念所支使[注]張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兩個難題和一個悖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而這兩種信念表面看來是完全沖突的,它需要法官結合雙方當事人的身份、地位、行為動機、社會關系、社會環境以及糾紛發生背景等具體情況來做出概括。人工智能不僅難以構建起一個個體經驗庫,更無法在常識、經驗等背景知識中做出暗合社會主流價值和樸素正義的抉擇。
(二)裁判大前提的建構
第二層面信息的分析處理,為事實與規范的匹配階段,它包括法律規范的發現與闡釋,進而形成裁判規范以構建大前提的階段。作為人類用以認識自己、表征自己以及認識周圍事物和相互溝通的工具,法律規范往往被認為是語言符號系統的一部分。索緒爾認為,人的語言是一種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客觀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后者不是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這聲音的心理印記,我們的感覺給我們證明的聲音表象[注][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明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1頁。。可以說,語言在人的思維交換過程中產生,它是組織在符號表達中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又具有社會性,也即語言符號和他所代表的意義是通過社會中的“常識”確立起來的。因此,人工智能對于法律規范的處理正是建立在對自然語言處理的基礎之上,語音識別和圖像識別正是被普遍認為的人工智能的基礎技術。
然而,人工智能與人對于語言處理的最大區別是,機器是在“感知”的基礎上進行“認知”,從而為“判斷”奠定基礎;而人更多是基于“常識”來進行“認知”,進而作出“判斷”。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常識”是其難以逾越的屏障,而語言是否能夠被作出恰當的理解與認知,在很多時候卻恰恰離不開“常識”的作用。例如對魯迅先生家門口“一顆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需切身置于作者當時的環境和心境,才不至認為其是廢話;對“能穿多少穿多少”同一句話,需基于冬天和夏天或者北方和南方的氣溫常識,進行不同的理解。
人工智能若需具備一定的“常識”以達到人類“認知”的能力,就需要首先對每一個可能的概念項進行預先建模,構建無以計數的數據標簽來幫助它理解某一個特定的概念,這將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不僅如此,當我們終于辛苦構建完這一系列標簽之后,我們發現在場景變化之后,之前的大部分標簽卻難以復用,例如面對“呵呵”一詞背后所隱含的各種表情、態度、看法、思想或無意義,人工智能則將陷入又一輪的迷茫。更何況,在法律糾紛的場景中,實際還存在著眾多紛紜的子場景,例如“蘋果”,它可以是電子產品、果蔬產品,也可以是投毒犯罪的兇器。因此對于人類來說非常簡單的常識積累和場景切換,對于人工智能的發展卻是蜀道之難。
不寧唯是,在構建法律適用大前提的階段,法律解釋是一項極為關鍵的工作,梁慧星將其視為“獲得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規范的作業”[注]梁慧星:《民法解釋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頁。。既然法律是語言符號系統的一部分,其意義蘊藏在規范文本之中,那么則需法律解釋從方法上將規范文本的意義予以恰當地釋放。
對于努力拯救法律客觀性的方法論者來說,法律尚離不開人的經驗總結與實踐智慧,因為法學屬于典型的精神學科,不具有自然科學式的客觀規律,“它既不能完全用數學加以量化,也很難在實驗室里得出規律性的結論。”[注]陳金釗:《哲學解釋學與法律解釋學——〈真理與方法〉對法學的啟示》,《現代法學》,2001年第1期。通常認為的文義解釋、體系解釋與目的解釋等解釋方法,無一不需要解釋者將解釋對象與其前見和解釋環境進行整合。更何況本體論所強調的“讀者中心論”已將民事中的法律解釋切換為法官、原告與被告三方的“游戲”,解釋被重新設定為通過兩個相反過程的說服行為,即法庭辯論階段當事人一方力圖說服法官,裁判階段法官說服當事人一方[注]參見朱慶育:《意思表示解釋理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可以說,作為邏輯三段論的大前提并非是預先存在的、等待法官去查找的白紙黑字規則,而是法官綜合了各種解釋規則以及諸如原則、政策、道德、倫理之類的價值考慮對白紙黑字的規則進行個案解釋而重新產生的規則,我們稱之為“裁判規則”。其中,共性法律所體現的形式正義與個性案件所需要的實質正義在相互沖突中產生張力,需要法官在一般與特殊之間彌合縫隙。此外,法律中的開放性概念總是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更或被注入新的內容,例如“誠實信用”“公序良俗”“公共利益”等,這種變化需要法官在其自由裁量權之內進行法律“續造”。換言之,規范本身沒有概念,改變的只是法官依據當下的生活世界對規范的理解,裁判形成的過程是一個需要法官行走在法律解釋的保守性與創造性之間的活動,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的普勒斯案中判定黑人與白人“分離但平等”,而在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中判決分離就構成不平等,而兩個案件依據的卻竟是同一條憲法規范[注]William Read, Legal Thinki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pp.426-427.。人工智能裁判是根據預設好的算法,根據一個符號得出另一個符號,而個案中所涉及的利益、情感、道德、社會心理及社會觀念無法在人工智能的知識圖譜中精確匹配,“在案件事實曲折、人際關系復雜、摻雜人性和感情因素的場合,如何根據法理、常識以及對細微的洞察作出判斷并拿捏分寸進行妥善處理其實是一件微妙的藝術,不得不訴諸適合法官的自由心證和睿智,即使人工智能嵌入了概率程序、具有深度學習能力也很難作出公正合理、穩當熨帖、讓人心悅誠服的個案判斷。”[注]季衛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司法權之變》,《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因此,也許司法人工智能可以將形式正義的實現運用嫻熟,但對需要法官裁判智慧的實質正義卻仍是望塵莫及。
(三)裁判結論的獲致
第三層面信息的輸出與實現,為法律推理階段。期間法官要反復思考,在法律文本與事實之間進行目光交互流轉,權衡各種因素;在法律與事實之間建立有效的邏輯關系,以最終得出一個妥當合理的結論;在既有法律秩序之內,尋求法律依據,將結論予以正當化與合理化。如果將案件視為輸入,裁判結論視為輸出,那么在案件輸入與判決輸出之間還應存在著一個“加工通道”,而這種加工則是法官對案件的思維運作[注]李安:《裁判形成的思維過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4期。。法官的裁判思維“既包括‘發現’與‘檢測’案件答案的思維,也包括將思維結果予以說明的思維”,Wasserstrom則將此項過程分為“發現”的程序與“正當化”的程序[注]See. Bruce Anderson. The Case for Re-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 Discove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5,pp.336-337.。前者往往受制于法官個體心境、個性、偏見、法律知識、司法經驗及思維定勢的影響,然而后者則以論證的方式將影響“發現”的心理因素控制在正當的范圍之內,同時減少“發現”的任意性與盲目性,由此產生能夠被當事人與公眾接受的最佳結論。裁判的形成也是一個精神的心理歷程,從認知層面看,它需經過主體的頓悟→反思→判斷→決定,正是這一過程無法剝離法官的個體經驗與直覺預判,方顯法律論證通過一系列必要的方法對其進行正當化說明的不可或缺。
無論是弗蘭克基于經驗主義立場認為這僅作為解決問題的“裝羞”門面,是一種策略性選擇,還是阿列克西從規范主義出發將其作為一個法律論證的程序規則,以此來達成司法裁判的證立目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裁判者是從個別的經驗中產生理解、形成判斷并最后作出抉擇的,它是個體從一個過程進入另一個過程的認知歷程,在這一認知歷程中,問題的答案得以發現,相應的決策也得以落實[注]李安:《裁判形成的思維過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4期。。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具有個體認知能力的法官需要處理案件事實、法律知識、直覺預判、個體經驗、地方經驗、時代信息及社會文化等一系列因素,這一方面需要推理計算來保證司法推理的形式正當性,另一方面亦需要通過更為復雜的價值判斷來獲得具有實質合理性的答案。恰是如此,法律從來就無法通過計算而達成一個“唯一正解”,雖然制度層面與實踐層面的裁判必須要給出一個解決方案,但在法哲學層面它卻永遠保持著“可辯駁”的可能性。
也正是如此,法律不是自然科學,它無法用“技術話語”來主宰,更難以模仿自然科學的計算方法去探求一個數字化的、可驗算的真理。作為拉德布魯赫所言的“價值關聯的科學”,司法與“價值無涉的科學”最大的區別便是,裁判者首先應將自己置身于法律評價活動中,采取一種參與者的立場,提出自己對于裁判的正當化見解,這也是眾多法學者所稱的“司法需具有親歷性”的原因所在。
人工智能系統所面對的直接對象不是證據和當事人,而是經過技術人員格式化之后的計算代碼,人工智能首先需要判斷哪些信息、以什么方式可以提交給解決事實爭議的數據處理系統,再將所有與案情判斷有關的信息換算成數字,來表示每一項證據和規則的推論含義,以及需要賦予的重要性,最后再通過某種加權計算公式得出最終的結果。它通過運算的方式完成對知識的生成,以算法來表現法官的思維,由各種字符和運算符號表達將裁判形成過程中具有主體性的內在心理歷程進行了程式化,所指向的結論只能是“唯一正解”,除去這種努力本身已偏離了裁判的真實面目不說,其對于司法最大的誤解之處便是,它以為只要數據足夠充沛、算法足夠強大就可以取代裁判形成過程中的價值判斷,但問題在于,就法律的意義而言,“是”和“應當”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因此,盡管在目前司法人工智能已有眾多諸如消解原理、規則演繹系統、產生式系統、不確定性推理、非單調推理等先進的推理技術和專家系統、機器學習系統、規劃系統高級的運算系統等來求解負責的問題,甚至也可以做到采取循環往復的路徑進行復雜推理,而非僅僅單向度地沿著“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演繹邏輯進行,但是,它仍然無法做到“以某個特定的,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法秩序為基礎及界碑,借以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注][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頁。也即在存在價值選擇的空間中,法官在對已達成共識的雙方理由都進行充分說明之后,對自己所作出的結論仍有充分論證的可能與必要。而這,正是一個裁判被認為是理性的、正當的以及可接受性的必由之路,也是司法過程的實質所在。
結論:人工智能介入司法的慎思與謹行
事實上,問題并未結束。本文所述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諸多“不能”也許只是眼下的技術障礙,但我們永遠無法預測科技的走向與發展,就像AlphaGo與AlphaGo Zero的相繼出現,每一次技術革新都不斷突破人類對技術的想象。不管我們是喜聞樂見于人工智能又一次的出其不意,還是細思極恐后發現人類離滅亡又近了一步,不可否認的是,從技術史來看,人工智能正沿著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軌跡前進。盡管我們目前仍處于弱人工智能時代,并且目前還可以慶幸包羅人類萬象的司法領域畢竟不如圍棋規則那般簡單,人工智能取代法官裁判的路程或許還很遙遠,但技術派卻從未放棄朝著強人工智能的努力,也從未斷定AI“奇點”一定不會到來和超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實現,正如有人已經指出,既然人工智能有替代人類法官的能力,按照“墨菲定律”,它總有可能發生。目前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司法大數據允許人工智能識別法庭的語音記錄,允許人工智能學習案件從立案到判決過程中的全部訴訟材料,實際上就是給了人工智能最初的感官體驗,就像生物的祖先從一個感光細胞開始,終于進化出精密的、可以識別斑斕色彩的眼睛一樣。當人工智能的發展讓人們在各個細分領域變得依賴人工智能,造成人工智能實際上成為最有經驗的那位,從而逐步獲得了人類的信任,就可能得到法官角色[注]李騰:《人工智能的法官職業之路》,載華宇元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院編著:《讓法律人讀懂人工智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40頁。。
然而,這或許并非樂觀。當人工智能被賦予情感、習慣、傳統、常識、經驗、倫理、道德之后,我們曾一切習以為常的情感、習慣、傳統、常識、經驗、倫理、道德可還復存在?當技術專家嘗試將倫理構建進知識圖譜中以使其模擬法官的意志和思維,這種做法本身便面臨著是否違反倫理的質疑。人工智能介入司法的預期是消除法官恣意裁判的“暗箱”以期實現司法公正,但事實上,算法及其算法控制的生產性資源本身就是一個閉環的“暗箱”。一旦在司法決策中獲得話語權,那么公平和正義將交付數據與算法,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其背后的程序員、軟件工程師、數據處理商、信息技術公司權力的介入及其對法官司法決定權的沖擊,這也將無可避免的造就一個技術壟斷和算法獨裁的局面。
紀伯倫曾說:“把手放在善惡交界之處,便可以觸碰上帝的袍服。”作為手握天平和劍的正義化身,法官在司法過程中所進行的明辨善惡的工作本應是上帝的權柄,怎可隨意將之托付他人?為此現代法治設計了一系列制度以使法官職業化、專業化、正規化,例如法官遴選、審判獨立、問責機制、法官職責、職業保障等,而對人工智能的過度期待或者誤解可能導致現代法治的制度設計分崩離析,引起社會結構出現矛盾、混亂乃至失控的事實,以毫無節制的“人工智能+”方式改造審判空間后,這樣的法官定位勢必發生極大的動搖,甚至造成審判系統乃至司法權的全面解構[注]季衛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司法權之變》,《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
所以本文認為,在“智能+”模式下,人工智能在裁判形成過程中最大的意義便是通過信息檢索和其他輔助手段來減少法官機械性勞動的負荷,以提高裁量和數據等處理的質量和效率,也即只能發揮司法裁判中的輔助功能;而對其超越了輔助性范疇的法律預測、司法推理以及司法決策,我們則應持慎思和謹行的態度。
恰恰因為司法的權威不僅來自于同案同判,更來自于法官對他據以形成判斷的法律方法的把握,以及他在裁判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公正可靠、人文情懷、社會責任;來自當事人在其說理之后的服判息訴與案結事了,以及民眾基于此對于法律秩序的信賴服從。而在裁判形成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確定的規則和確定的技術來完成確定的任務,更需要法官以其有限的“智能”和無限的“智慧”,向法律表達無限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