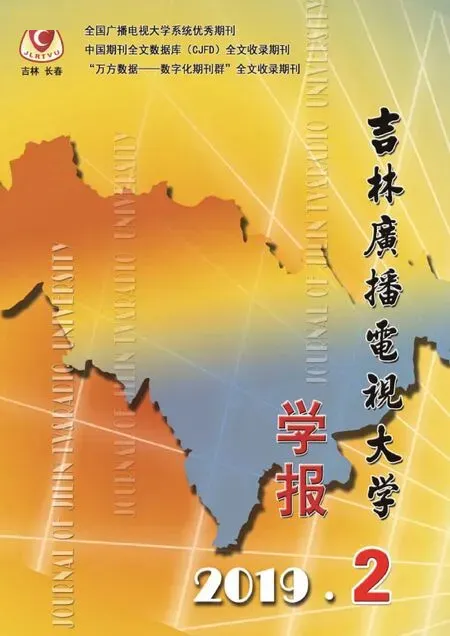關于當代東北地區城市題材繪畫的思考
路 昕
(石家莊鐵道大學四方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一、群體文明的集散地也是個體情感的孤島
現代城市文明的發展中存在的若干問題,牽扯到的不僅僅是環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更為深層次的是由環境變遷和不同人群融合所綜合的人文社會環境的發展問題。因為以上問題的產出均由人的問題所引發,它的核心內涵是人在不同環境下的融合矛盾和不均衡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綜合表現。而這一系列的綜合表現中又會具象化的表現為若干具體矛盾和客觀現象,而這些矛盾和現象為當代藝術創作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創作題材和動機。回歸到城市題材繪畫本身,我認為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解讀,首先從狹義來講,它當然代表著以城市客體本身為題材所創作表現出的關于城市發展,真實環境,地域特征的繪畫,它能夠真實的反映出藝術家的主觀審美視角,為大眾提供新的視覺觀看方式,發現城市新的美或特點等等;而從廣義上來講,城市題材繪畫也可以看作是由反思城市和人類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矛盾、空間、人性變化、地域風貌等各種因素變革的藝術創作。那么它能夠從更加宏觀的視角去關注時代變化之于城市發展的烙印,在變革中人與客觀環境的矛盾、創傷、融合等等,提供出更為豐厚的人文社會思想和更深刻的藝術內涵,這是城市題材創作之于當代藝術創作的最為深刻的價值。藝術家們以圖像和繪畫,構建出了“自然生態”“人文生態”“城市生態”甚至“人性生態”。
誠如莫里斯在人類動物園中提到的“我們不應該把都市居民比作野生動物,而應該把他們比作被關在籠子里的動物……在那里,他們時時都有因為過度緊張而倒斃的危險。”然而城市的構成并不僅限于柏油馬路、電纜、混凝土和玻璃幕墻,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生動的人構成的。但信息時代的快節奏并沒有為每個個體的獨特性價值提供思考的時間和空間,于是他們被貼上標簽,被符號化解構,以便能在信息社會中被快速識別和提取。現代文明的確為我們精心制作了一座座代達羅斯迷樓,并使我們沉浸其中。而此時藝術的價值便在于給予個體重新審視思考自我獨特性價值的機會,給予它應有的尊嚴。
二、獨特地域景觀中的悲劇性價值
東北地區獨特的地域景觀在當下具有豐厚的研究價值。從人文視角觀看,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環境背景下大工業時代的狂飆突進和傳統農業文明的激烈碰撞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發展例證和素材;從客觀環境來看,工業時代遺留下的城市痕跡和變遷更具儀式感和悲劇性。東北地區的豐厚而獨特的原生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更具有一種“大山大水”的特質,更適合于表達一種中國傳統美學中悲天憫人的創作情懷。這不是簡單的個體審美沖動所引發的情感,而是經過特殊地域和人文環境所孕育出的群體性意識,一種情懷。那么這種悲劇性情懷又可以具化成由社會快速變遷所帶來的真實與虛幻的矛盾,表現為個體在大時代背景下的被動與無奈,從而在作品中呈現出的戲劇化的表現,這種戲劇化的內在又隱隱飽含著對于原生環境的懷念與向往和對于當下狀態的迷茫與無助;工業時代遺跡對環境空間的影響在當下常常能給人以一種崇高的悲劇性感受。早在上世紀90年代秦秀杰先生一系列關于反映城市生活的繪畫作品就引起了高度關注。其作品借用了玩世現實主義的戲劇化表現形式,透露出對于個體生存狀態在大時代下的無奈和反思,這種生存狀態可以說表現出了那一時期城市人群生活的真實寫照。而同樣是東北地區表現繪畫的代表性藝術家,崔國泰在畫室里為東北大地的重工業遺骸制作“肖像”,關于老工業遺跡的作品,表現了崇高的悲劇性特征,這是藝術家特殊的生存環境影響下的真實感受,這批龐大的“肖像畫”混合著作者對新舊時代的驚異與哀悼陳丹青先生在相關評論中將其概括為“偉大的殘骸”這種在時代浪潮中的偉大遺跡引發著當下關于生存狀態的共鳴。可以說是地域環境的特性為千篇一律的城市文明景觀賦予了不同的個性,在今天我們把東北地區的地域特性概括為藝術表現中的悲劇性特性,是為了從一個特定視角去觀看日益模糊的城市文明景觀,并試圖去解析說明這種悲劇性特征之于當代的價值。筆者始終固執的認為悲劇性是當代藝術創作所迫切需要的精神和價值來源。過于紛亂的景觀和信息來源使我們太容易被新穎的形式感和獵奇式的圖像化創作所吸引,慢慢的來自于真實的生活感受會被新奇的視覺刺激取代,快速的生活節奏也在壓榨著我們關于藝術創作的思考和耐心。這正是在當下珍視這種獨特地域屬性的價值,它為我們的藝術創作提供了生發的土壤。在繪畫中賦予作品以一種地域性的性格特征,具象化的展現東北地區的城市景觀和人文風貌。
三、后工業時代下的焦慮與信息化社會中主體意識的并行
東北地區的青年藝術家作品會不自覺的表現出一種后工業時代下的思考狀態,的確特殊的地域人文環境在賦予他們創作母題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們更為復雜敏感的感受。面對當前的城市環境和自然景觀,面對他們所存在的客觀環境,他們會思考,敏感的神經會拷問著他們這些景觀的歷史和由來,它們背后的價值,它們之于自我發展的意義。首先,我們能看到在現代工業文明擠壓下隱喻出的類似于荷爾德林的返鄉,這種思想的回歸具有一種精神的指向性,對于自我發展命運的深刻反思,因此,它直指和揭示的是人性在工業文明發展的背后潛存著的被摒棄的危機。東北地區的中青年藝術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城市題材與當代社會文化背景間進行深刻思考和藝術創作的。趙龍無疑是其中的代表,其創作的代表作品多數以城市客觀印象為創作對象,例如《郵寄的風景》系列作品,是以自己長期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哈爾濱為創作本體進行敘述,這種場景的勾勒同時也是自我對于城市記憶感知的勾勒,深刻的反映出社會空間變化給予個人生存經驗的改變和影響。而同樣來自哈爾濱的王巍,在城市題材的選擇和繪畫上則更具有某些古典的審美趣味。《暮光之城》系列作品沒有夾雜過多的個人經驗符號,而是更多的還原出客觀景觀本身的審美表現力。而《捉迷藏》系列作品則更多的以個人視角反映城市變遷過程中的空間痕跡,以其存在和現實的矛盾反思發展與生存問題。其次,我們更為欣喜的看到,近年來青年藝術家在創作中社會意識的不斷生發和強化,他們在通過作品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系,思考自我與社會發展的責任和價值,表達著自己的觀點和聲音,他們用藝術作品解構著社會的種種現象,訴說著自我的文化觀念。如吉林省近年來在青年美展中逐漸嶄露頭角的宮建宇,其一系列聚焦城市共享單車亂象的作品,深刻的反映了藝術家自我對于社會現象的反思和解讀。作品在兼顧傳統繪畫性的同時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反思價值,并不是單純的圖像獵奇式創作或是為凸顯個性語言的機械化作品。同樣來自吉林的青年畫家張彥鵬,近期作品《徑地自在》也一改他在美展中的作品風貌,而是將視角聚焦在城市的邊緣地帶,聚焦在那些我們在城市化發展中不愿看到和刻意忽視的地帶,但他們是真實存在的。
此類題材的創作暗含著創作的敘事主體和圖像轉化過程中的繪畫本體語言探索。如果說圖像的純化會給視覺帶來觀感上極大的刺激和直觀的指向性,那么繪畫語言對于圖像的形式處理則會給予圖像自身更為豐富的象征性和文本空間。它可以借由繪畫關注著過去,并警惕現在和未來若干可能。美國著名新表現繪畫藝術家艾瑞克?費舍爾曾提到“攝影和繪畫都可以某種程度捕捉到瞬間的真實,但照片抓住的真實瞬間是一個薄薄的切片,而繪畫抓住的瞬間是一個復雜得多的時間建構,一個成熟的畫家要能發現和表現那個既包含過去又昭示未來的瞬間。”如安東尼奧·洛佩茲·加西亞和美國的霍默都是表現此類藝術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都是在用繪畫的某種特性通過再現某一時刻的場景來揭示一種永恒的存在,這種存在蘊含著有限生命在無限的空間和時間中所表露出的力量——源自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