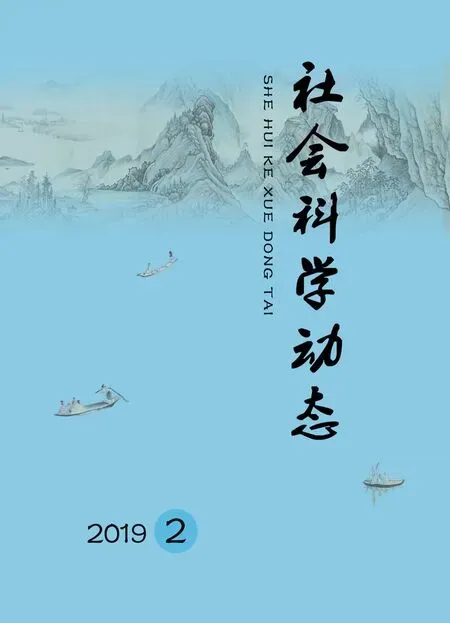粵漢鐵路湖南段建設三題
張衛東
近代以降,鐵路被視為系國運之關鍵,“國家之建設,首重交通,交通之建設,首重鐵路。……各國對于鐵路修筑,無不盡力經營。”①類似的見解,近代以來頗為常見。從這個角度來看,鐵路作為近代交通變革的典型代表,其對一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的社會變遷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對于近代湖南而言,同樣也不例外。粵漢鐵路從最初籌建到最后完成,均與近代湖南社會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林朝杰在文章中說,湖南物產豐饒,然“因交通不便,物產無法輸送,只有停滯一地,經濟不能流通,故此湘省人民生活發生困難。”當粵漢鐵路全線貫通之后,“湘省各地經濟,則已漸成活躍,人民生活程度,已續漸提高,由此可見鐵路交通與政治經濟之關系,粵漢鐵路之完成,既為我國之一大之鐵路交通線,而亦為湖南人之生命線。”②林氏將粵漢鐵路視為“湖南人之生命線”,換句話說,其所反映的是時人視粵漢鐵路為湖南重要的社會變遷動力。關于粵漢鐵路湖南段的建設及其與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的若干問題,筆者曾發表了多篇論文予以論述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但粵漢鐵路與近代湖南社會的關系問題其可論述者可謂千頭萬緒,而學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又頗為薄弱,因此,筆者在此對粵漢鐵路湖南段建設中的三個問題,即粵漢鐵路湖南段的早期勘路問題、民國初年湘路公司的收歸國有以及民國時期鐵路部門對粵漢鐵路湖南段的經濟調查等三個問題略加闡述,敬希方家批評指正。
一、湖南境內粵漢鐵路的早期勘路
鐵路建設的前提是線路走向的勘定。粵漢鐵路大致分為三段:湘鄂段(武昌—株洲)、株韶段(株洲—韶州)和廣韶段(廣州—韶州)。我們主要談湘鄂段的早期勘路情況。
湘鄂段以湖北武昌徐家棚為起點,終點為湖南株洲,全長約415公里。該段除長株段(長沙—株洲)線路已于1909年開工前選定外,武昌至長沙間先后進行過三次勘測。第一次是1898年11月至1899年8月,系合興公司為盡快與清廷簽訂正式工程合同進行草測的;第二次是1906年5月至1907年5月,在贖回路權后,由湘鄂粵三省聘請英國工程師穆三格,按窄軌鐵路標準勘測的;第三次是定線測量,1911年8月開始,1914年測畢,線路走向與合興公司初勘時基本相同。④
鐵路走向遵循一定的原則。那么,晚清民國時期我國國有鐵路的選線遵循怎樣的原則呢?鐵路測量,分三個時期進行,第一是查勘路線時期,第二是擬定路線時期,第三是決定路線時期。“查勘路線,為審定路線初級工作,蓋路線兩端城市,雖經決定,惟路線所經過各地,則可自由采擇,查勘路線者,即根據工程學之經濟原理,預行審定路線,將來所經過各地之舉凡路線之長短、施工之難易、建筑費用之增省、沿線居民生活程度之高下、沿線生產種類及其數量之繁寡、交通運輸情形之通塞、建筑材料之取給收用、土地之當否、路成后若干年交通發達程度之預測,以至路線經過之河流山脈,及一切城市鄉村,是否適合鐵路工程經濟之原理,均須統籌兼顧而闡明之。自表面觀察,查勘路線,似屬輕易,而實際上將來全路交通經濟問題,皆以此定,其大概之標準所關重大,當事者不可輕視而忽之也”。⑤凌鴻勛在總結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建設的經驗與教訓時,對于當時影響鐵道勘路與路線選擇的種種因素發出了深深的感慨,并希望這些因素在今后的鐵路建設中能夠少一些。他說:“一鐵路之線,首尾兩端之選擇,與必須經過之重要城市,每非一純粹鐵路問題,而為一政治或軍事問題,但兩端間或重要城市間,路線之選擇,則純然為一技術之事。路線選擇之良否直接影響于一路之修養與業務之維持,前者猶屬一時一次之事,后者乃屬永久性質,而為一路生存之所系,是以筑路之始,必須慎擇富有建筑與養路之工程司,俾有充分時間,測勘路線。今后吾國筑路之趨向,多系經過山嶺崎嶇工程困難之地,尤須多為比較,以資選擇。茍于開工之始,多費若干時間為路線之研究,必能獲得較好之結果。若只顧于有形的及一時的測勘時間與金錢之多耗,而忽卻無形的及永久的事業之犧牲,寧可謂當?即使在非常時期,為國防急計,不能多所顧慮,但鐵路建設無論如何亦非咄嗟可就之事,徒急于一時之開始,而貽將來無窮之累,甚至欲達其國防上之使命而不可得,寧非至可惜之事?是以鐵路主管,對于路線選擇之重要,宜根本有所審慎,而負責之工程司,于受事之始,亦宜要求其對于測勘路線之必須時間與費用,本其個人之經驗,與慎選之助手,擇得一最適宜之路線而后開工,方得謂忠于所學也。”⑥于治民通過研究也指出,晚清民國時期,國有鐵路的線路走向體現了如下幾個特點:一是“鐵路選線以政治中心為本位”;二是“鐵路選線著眼于利于開采礦藏,并兼顧利于農業和其它工業的開發”;三是“鐵路選線開始注意到利于移民墾荒的問題”;四是“鐵路選線或多或少地考慮到與列強爭利的問題;”五是“鐵路選線以工程易于進行為原則”;六是“鐵路選線還著眼于維護國防,備戰,抗戰”。⑦應該說,這些概括相當全面。
我們知道,清廷發展鐵路事業,其主要著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因此,其鐵路站點和線路的選擇更多的是政治或軍事方面的考慮。同時,由于清廷受到經濟力量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其鐵路建設在選線時也盡量遵循降低工程技術難度或節約經濟的原則,或者“鐵路必取直線,較水路迂折為近”⑧,或者選擇地勢平坦之地⑨,或者繞過施工困難之地⑩,或者靠近水道,以便于建設材料之轉輸?。因此,有學者指出,清末民初在鐵路建設中,鐵路選線基本遵循了“連接重要都市、鞏固軍事戰備、工程難度最小”等原則。?這些原則在粵漢鐵路湖南段的勘測中都有一定的表現。
粵漢鐵路決定取道湖南,勘路工作隨即便提上日程。粵漢鐵路最初勘線的時候,湖南各地風氣還是比較保守的。1898年3月,盛宣懷準備派美國工程師李治于是年春季勘測粵漢鐵路湘境段,但是湖南巡撫陳寶箴反對直接派洋工程師來華勘路。他認為,“勘路猝用洋人,一人倡謠,千人和之,一哄之后,地方正紳必不肯出身任事。始基不慎,事必難為”。?他主張,“必用華員先勘一次,沿途示諭,隨后再用洋工師勘估方穩。”?他的辦法是,最好請詹天佑、鄺景陽兩位中國鐵路工程師來湘主持勘路,如二人不能來,則委派汪喬年從湖北湖南勘路至粵界,“沿途會同州縣,聯絡各地方紳士隨同踏勘標記,并告諭鄉村市鎮,使所過各縣士民皆知此舉系奉旨必行之事。各處紳民俱可入股分利,實于地方有益。并諭知須洋工師再勘一次,即便興工矣!俟勘至粵邊,即會同廣東勘路洋人仍沿此路而下,勘至鄂境。”這樣,雖然最終必然還是要用洋工程師進行定線勘測,但是因為先有汪喬年等先行勘測了一次,各地所謂“正紳”已經周知此事,“又有已經聯絡稟派之紳士,就地隨同保護”,所以“自較穩便”。隨后,陳寶箴提出了自己對于粵漢鐵路湖南段大致走向的建議:“從江夏勘路抵湘,循臨湘、巴陵、湘陰、長(沙)善(化)、醴陵、攸縣、茶陵、安仁、永興或宜章等處勘至粵邊”。勘這條線的原因,陳寶箴說:“此路較由永興經耒陽、衡陽、衡山、湘潭至善化約近百六七十里,又免過兩處大河,無搭橋之費,民情亦較湘(原文如此,疑為渾——筆者注)樸,其必由此路無疑。”?1898年7月9日,陳寶箴再次致電張之洞、盛宣懷對于湘境線路走向提出了修正:“通廣東之路,由長沙改向湘潭、衡州、耒陽、興寧,仍經永興、郴州,抵廣東界”。他在這份電文中,再次重申了“先中后洋”的勘路原則,即先由中國人大致確定線路走向,然后再請洋人進行技術勘測。?應該說,作為湖南巡撫,陳寶箴關于湘路勘線的考慮是比較周全的,正因為如此,盛宣懷對陳的安排也表示贊同。
1898年4月14日,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了《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根據草合同的約定,必須在勘定路線后方能議定正約,因此,勘路問題變得比較緊迫起來。于是,盛宣懷加快了粵漢鐵路的勘路工作。5月4日,盛宣懷電告張之洞,羅國瑞?已由上海啟程赴鄂勘路,可是,這個羅國瑞卻借口身體有恙而遲遲不肯工作,一直拖到7月份,勘路工作始終毫無進展。到了這個時候,中南地區天氣已進入盛夏季節,張之洞、盛宣懷等決定至秋季再行勘路,這樣勘路工作就一直拖到11月份才又啟動。?根據與合興公司的協議,這時合興公司委派工程師柏生士來華進行勘路工作。不幸的是,在此期間維新運動失敗,大力支持鐵路建設的陳寶箴被革職,這多少給粵漢鐵路的勘路工作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在張之洞、盛宣懷的精心安排下,柏生士主持的勘路工作的進展還算比較順利。1898年12月至1899年3月,柏生士等人“經咸寧、蒲圻入湖南臨湘縣界,迤邐前進。統計湖南境內經岳、長、衡、永、郴五屬,廣東境內經韶州、廣州兩府,路長約計二千余里。”?柏氏勘測完畢后,將勘測圖紙及各段里程呈送盛宣懷,盛宣懷又將其抄送張之洞:
柏生士前送一圖,即已咨送者,系武昌至新墻?138邁?,新墻至岳州支路25邁,新墻市至長沙90邁,長沙至易家灣?20邁,易家灣至湘潭9邁,易家灣至衡州107邁,衡州至白石渡?138邁,白石渡至樂昌41邁,樂昌至廣州171邁,廣州至三水31邁。又一圖載武昌至新墻150邁,新墻至長沙90邁,長沙至淥口?45邁,淥口至耒陽130邁,耒陽至永興35邁,永興至郴州40邁,郴州至折嶺?10邁,折嶺至白石渡20邁,白石渡至坪石10邁,坪石至樂昌40邁,樂昌至韶州30邁,韶州至烏石墟20邁,烏石至清遠70邁,清遠至廣州30邁。?
從上述柏生士的初步勘測結果來看,粵漢鐵路在湖南境內大致有兩條走向:(一)武昌—新墻(岳陽)—長沙—易家灣(屬湘潭)—衡州—白石渡—樂昌;(二)武昌—新墻(岳陽)—長沙—淥口(株洲)—耒陽—永興—郴州—折嶺—白石渡—坪石。雖然這兩條線有一些細微的差別,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均沿湘江南下。電文中還提到兩條支路,即新墻至岳州支路(25邁)和易家灣至湘潭支路(9邁),其中的湘潭支路是為了兼顧湘潭的利益。實際上,柏氏還勘測有一條萍鄉支路(66邁),只是在盛宣懷轉發的這份電文中沒有反映出來。?
我們把柏氏所勘測的路線與陳寶箴1898年4月告示中規劃的線路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兩者是不太一樣的。根據前文的敘述,我們知道,陳寶箴規劃的線路是這樣的:“由粵至漢口鐵路,應由湘境宜章、郴州、永興、安仁、茶陵、攸縣、醴陵、長沙、善化、湘陰、巴陵、臨湘等處接入湖北境地。”?這條線路,永興至醴陵間,主要是沿湘東地區穿行,之所以這樣走,對此陳寶箴給出的原因是:“此路較由永興經耒陽、衡陽、衡山、湘潭至善化約近百六七十里,又免過兩處大河,無搭橋之費,民情亦較湘?樸,其必由此路無疑。”?換句話說,一是路線距離短,有利于節約經費;二是免過兩處河流,施工難度降低;三是避免鐵路線路與湘江平行,以保證鐵路開通運營后的經濟效益;四是衡陽、衡山地區民風剽悍,可能施工阻力較大。除了上述四個原因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這樣的走向更接近煤礦產地如醴陵煤礦和萍鄉煤礦等,因為鐵路自身需要大量的煤炭,同時煤炭也是鐵路運輸的主要大宗貨物。“粵漢鐵路在湖南段,原議線路是從郴州過攸縣,經醴陵而至長沙,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請與萍鄉煤礦鐵路相銜接,并遣美國參贊李治,工程師柏生士來萍勘視。自醴陵至萍鄉,即定為粵漢支線,訂約由美國承建。”?這一點凌鴻勛曾指出,鐵路與煤礦關系十分密切,“鐵路要用煤,而且營業上又需要有大量的煤運”,而且煤礦與鐵路路線的選擇具有很大的關系。?
不過,到了該年的7月份,陳寶箴改變了4月份的想法:“通廣東之路,由長沙改向湘潭、衡州、耒陽、興寧,仍經永興、郴州,抵廣東界”。?這條線路設想,與后來柏生士所勘之路線基本吻合。曾任萍鄉縣令的顧家相(1853—1917)在《籌辦萍鄉鐵路公牘》中指出了這種變化:
先是陳右銘中丞撫治湖南創粵漢鐵路之議,欲從粵?東經長沙以達漢口。所定軌道不循湘江沿岸,由郴州迤邐過攸縣歷醴陵而至長沙,并奏明與萍鄉煤礦鐵路銜接。遣美國人柏生士、李治來萍勘視,自醴陵至萍鄉即為粵漢枝路,統歸美國工師承辦。既而粵漢軌道復議改移循湘江直下,不經醴陵,盛公亦遂變前議。?
之所以會出現“粵漢軌道復議改移循湘江直下,不經醴陵”的情況,應該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湘江沿線一向是湖南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區,鐵路線路走向經過經濟發達地區,其經濟效益才能得到保證。二是便于鐵路建設工程中材料的運輸,鐵路沿湘江南下,在鐵路建設過程中能夠走水運,對于建筑材料的運輸具有一定的幫助;同時,湘江自南向北順流而下,而其支流大多與其垂直相交,這些支流同樣也有利于鐵路建設材料運抵建設現場。三是尊重美國工程師的專業意見。因此,粵漢鐵路湖南段線路的走向選擇“循湘江直下”與湘江平行是必然的選擇。
湖廣總督張之洞對于湖南境內粵漢鐵路的走向十分關注,正因為如此,柏氏勘路工作結束后,盛宣懷很快就將路線圖及里程數用電文傳送給他。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三日(1899年2月12日),張之洞委派湖北候補知府、原籍湖南的黃國瑸負責協助柏生士等人勘測湘潭至永興的路線:“由湘潭赴粵程途,本有兩路:東大路,則由湘潭繞東,經醴陵、攸縣、茶陵、安仁以至永興;西大路,則由湘潭南下,沿湘河東岸,經衡山、衡陽、耒陽以至永興。”他要求對這兩條線路要認真勘測,“不厭精詳”:“究竟由湘潭至永興赴粵,東西兩路,以何路較為直捷平坦?施工難易何處相宜?民情物產兩路孰勝?”?務必從中比選出最佳路線,從后來的勘測結果來看,同樣是選擇了與湘江平行的“衡山、衡陽、耒陽以至永興”一線即西大路。
按照約定,線路勘定完畢,合興公司便要與清政府簽訂正式筑路合同。柏生士勘線完畢,合興公司認為草合同400萬英鎊借款不敷使用,要求增加貸款額度。經過談判,1900年7月,雙方簽訂《粵漢鐵路借款續約》即正式借款合同,增加貸款至4000萬美元。由于此時正值庚子之亂時期,1902年7月續約才獲得清廷批準。此后又因合興公司違約,又興起了廢約贖路運動,1905年8月29日與合興公司簽訂贖路合同,同年9月9日又從港英政府借款110萬英鎊“償還”合興公司勒索的675萬美元。
在廢約贖路的過程中,湘省的官、紳、商同時也在努力推進湘路的建設,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矛盾與競爭。多家鐵路公司相繼成立,如,1905年5月,以龍湛霖、王先謙、張祖同等巨紳為首發起成立湖南籌款購地公司;1906年5月,陳文緯、周聲洋、袁樹勛等人也發起成立商辦湖南全省鐵路公司。但張之洞于1907年1月11日,上奏清廷建議由袁樹勛、王先謙、余肇康等湘籍著名紳士出面組織官督紳辦鐵路公司主持湘路建設(以下簡稱湘路公司),而對陳文緯、周聲洋等人組織的商辦鐵路公司則加以排斥。?在張之洞的安排下,1907年3月,以余肇康、張祖同?、席匯湘等人為首,成立了奏辦湖南粵漢鐵路總公司,5月,該公司公布簡明招股章程,此后就是這家官督紳辦的鐵路公司主要負責粵漢鐵路湖南段包括勘路在內的籌建工作。
二、民國初年湘路公司之收歸國有
我們知道,清政府在以湖廣鐵路借款和粵漢鐵路為代表的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所引發的保路風潮中土崩瓦解了,但是粵漢鐵路的建設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清政府垮臺后,1912年5月,北洋軍閥袁世凱主導的北京政府再次宣布“川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政策,而干線鐵路收歸國有,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為了取得列強在資金上的支持,北京政府宣布承認清政府所訂立的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繼續合法有效。與晚清時期相反,此時國內輿論對于干線鐵路國有政策和借款筑路政策的態度發生了極大地改變,即不再籠統地反對借款筑路和干線鐵路國有政策。這是因為,繼清政府而起的北京政府,雖然主要由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所控制,但畢竟革命黨人在政府中也占據了一定的位置,客觀地說,民國初年,全國人民對于這個新生的政權還是抱有相當大的希望的。希望它能夠努力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富強,從而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北京政府的“川粵漢鐵路國有”政策也得到了同盟會黨人的支持。故當時的報紙報道說,粵漢鐵路若“不歸國有,萬無告成之日。湘路公司亦見及此。于是湘路收歸國有之說,即無甚反對”。?1912年5月,湘籍著名革命黨人譚人鳳被袁世凱任命為粵漢鐵路督辦,負責籌辦粵漢鐵路的建設和清還鐵路股款。袁氏北京政府之所以任命譚氏為粵漢鐵路督辦:其一,譚人鳳是著名革命黨人,號召力大;其二,粵漢鐵路湘段距離最長,湘路股款的清退是重中之重,且非常棘手;其三,譚人鳳為湘籍人士,相對而言,工作難度可能會小一點。但譚人鳳最初卻并不愿意擔任這個所謂的“督辦”職務,后經宋教仁做工作,譚氏方答應接受這個任務。?在譚人鳳所結交的朋友之中,他最看重宋教仁的政治才華和政治眼光,在這種情況下,他接受了宋教仁的建議。?
但是,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和籌款建設,其難度在當時的中國各條干線鐵路中可謂首屈一指。因為很明顯,此前曾負責該路籌辦的諸路豪杰如張之洞、盛宣懷、端方以至湘路公司的王先謙、余肇康等人,均堪稱晚清時期中央或地方的風云人物,但他們在籌辦粵漢鐵路的過程中幾乎都未能全身而退:張之洞因湖廣鐵路借款談判耗盡精力而逝,盛宣懷則飽受罵名,端方慘遭殺戮、身首異處,王先謙亦被多方指責,甚至于被清廷斥為“四大劣紳”之一。所以1936年粵漢鐵路全線竣工時,葉公綽撰文回顧粵漢鐵路的歷史時曾指出,粵漢鐵路“不但成本之重,為各路所無,恐資產負債,早已不抵,蓋全路未通以前之三十五年,無日不在虧耗中也”。?同樣,關賡麟也在其文章中說,粵漢鐵路因為遷延時間太長,耗費了巨額的資金,不但借款數額估算嚴重錯誤,而且“盛宣懷之鐵路國有政策,既已一意孤行,不恤輿論,誤謂高壓政策之必能收效矣。民國成立,政府復襲行國有政策,則以為人心所向,必可竟成,恃外債之借入為來源,輕議盡數收買各省商路,負鉅債而不惜,至今無法償還。”后果十分嚴重。?由此看見,籌辦粵漢鐵路的難度非同一般,說它是一塊燙手的山芋一點也不過分。
譚人鳳就任粵漢鐵路督辦后,聘請著名鐵路專家詹天佑為會辦,顏德慶為鄂局總辦,馮梅丞為湘局總辦,設總局于漢口。并重新派人勘測岳州至長沙、衡陽至廣州的線路走向,10月北上,據其自說已“與銀行團議定取款手續,成計劃書”?,準備依靠對外借款清償一切股款。為了實現粵漢鐵路的收歸國有,譚親赴湖南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期能夠在他手里早日完成這條磨難重重的南北交通大動脈。譚人鳳對于他本人擔任粵漢鐵路督辦期間的工作是這樣說的:
聘工界泰斗詹天佑為會辦,委顏德慶為鄂局總辦,馮梅丞為湘局總辦。其余所需各分工程師及材料、機械、電報各處長,皆由詹君推薦,頗慶得人,計自設局以來二三月間,諸事稍以就緒,只待借款提到,即可積極進行。十月間北上與銀行團交涉,妥議而返。即委熊繼貞清算鄂路股款,委常□□?清查舊時購地,委謝吉士測由岳至湘之線,委蘇日新測由衡交粵之線。全路計分四大段,每段于適中之處設一分局。大段之中,復擬分每三十里為一小段。同時招工興筑,以期速成。不意黎元洪、黃克強從此搗亂,一切計劃,遂成泡影。先是黎于予未到鄂之先委一流氓畢□□?為總辦,經予裁撤后,兩次代求改委,予未徇情。十一月,湖北鐵路學生相率求位置,予答以尚未開工,囑少待。該生等乘余往收湘路,大鬧風潮,聯名具稟黎元洪,謂專任私人,屏鄂人不用。黎遂據以達中央,湘路總辦陳佩衡以運動承繼原席拂望,借口股東要求現款,有意把持。經予以大義責之,喚各紳開導,已準備移交矣。適克強返湘,亦主張索現款,另修支路。陳遂假全省士紳名義,電向中央索款,復敢抗延予令矣。袁不悉二事情形,恐積不相能,乃擬調予任長江巡閱使;適克強部屬亦有代其謀此一席者,袁因派人征求克強意見。克強乃命駕問予曰:“路事情形如何?”予曰:“將開工矣。”克強曰:“無款何能開工?”予曰:“已與銀行團交涉辦妥矣。”克強復曰:“聞銀行團不愿支款,鄂人亦多異議,奈何?”予曰:“此無慮,外人重信用,已收我簽押印樣,存驗支付,當不致反復無常。鄂人恃鐵路為生計,急欲謀生,開工后,量能分任事矣。”克強始告予曰:“昨日項城派人來,擬請先生為長江巡閱使,而以余承乏。”余時半嗔半喜,笑應之曰:“我非想作官,其勉就斯職者,欲速成此路而已。數月以來,竭慮殫精,亦自信無忝厥職。今公既肯出負責任,我當組織軍隊征蒙,何屑為巡閱使。”克強去后,隨擬以激烈手段,迫陳移交,以了此行之任務。湘督譚延闿從中斡旋,陳乃備文交出。予即返鄂,準備交卸。二年元日,遂移交克強。先是予之膺斯任也,由袁特任,銀行團借款亦可由予直接支取,與交通部無甚關系。克強由交通部薦任,蒞任后,始知權限位置,皆隸屬于交通部,大不滿意,迭次電爭,未得解決,遂于一月八日以印交秘書看管,脫然而去。?
根據上述譚人鳳的敘述,可以看出,雖然在此之前譚氏并沒有辦理鐵路的經驗,但其工作作風雷厲風行,善于使用鐵路人才,且能夠抵制黎元洪等人的無謂干擾,這自然十分有利于工作的推進。同時,作為湘籍革命家,譚人鳳也有早日完成粵漢鐵路的強烈愿望。不過,也要指出,譚氏對于粵漢鐵路的收歸國有的難度估計不足,過于相信四國銀行團的所謂“重信用”。實際上,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最大的困難是交通部并無大筆的款項用于購買湘鄂粵三省廣大紳民手中的粵漢鐵路股票,雖然北洋政府繼續承認湖廣鐵路借款合同有效,但四國銀行團鑒于中國政局動蕩的緣故,對于投資川粵漢鐵路實則充滿了疑慮。“譚氏迭與銀行團交涉,促其照約交款,而銀行團以前約所訂系漢粵川名義,今僅漢粵用途不合,況前約指定以湘鄂厘金作抵,光復以后,各處厘金,或裁或并實難擔保,不肯交款。”?所以,譚人鳳的所謂與四國銀團借款商議妥當的說法,其實只是他一廂情愿的想法罷了。
但譚人鳳認為,“民國成立,天下為公,國既公有,何況于路”??故而鐵路國有實際上也就是民有,因此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乃大勢所趨,是符合當時中國和湖南的實際情況的。就收歸國有而言,“滿清末造,定鐵路國有政策,風潮一起,遂成革命之導線。今之言路政者,或鑒于前事,而疑國有之說不復可行,此非通論也。處列強競爭時代,鐵路為軍事、實業命脈所系。將欲謀工事之速成、機關之統一,前清之國有政策,實未可厚非。而其所以失敗者,擅借外款,不交院議,紊亂憲章,其罪一;折扣商股,與民爭利,其罪二;人民抗議,遽施格殺,其罪三。積此數因,乃肇大變。由今思之,其主持國有政策是也,而所運用此政策者非也。民國新造,政貴因時。路政一項,以民生主義社會經濟言之,不可不定為國有;以軍事國防言之,尤不可不定為國有。惟施行此政策時,只當謀路政路權之統一。商股為人民財產所關,斷不能損其毫末。且商股所有虧損,并當由國家完全擔負責任。”?他還指出,世界各國以鐵路國有為潮流,“人方日謀集權以進行”,我乃支離破碎,自破壞統一之政策,未免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51]就湖南的情形而言,譚氏指出,湘路公司自1905年開辦之日起,至1911年5月底,共計收入約536萬兩。其中商民股份,僅約151萬兩,余皆米捐、鹽斤加價。而支出則高達563余萬兩。已成之路,不過長沙至株洲105里,其余已購未造者,長株段內30里,株郴段內30里,長沙北門外填基15里。出入相抵,虧欠之銀已達28余萬兩。“試問湘省土瘠民貧地方,財政有限,兼之軍興以來,兵多餉竭,捐款繁苛,公私一空如洗,乃欲于中央與地方行政經費外,括剔社會零剩之脂肪生命,建筑此一千三百七十里空前絕后之大干路,何日興工,何日竣事,何日行車貨運,實不過海樓蜃市,構成理想上之新湖南而已。”[52]可見,譚人鳳認為,粵漢鐵路只有收歸國有,方有建成通車之可能,而粵漢鐵路的建成通車,對于湖南的發展尤屬必要。“五口未通以前,中外通商恃廣州為吐納,行李擔負越五嶺沿湘流而下,故湘潭為大市,宜(章)、郴(州)僻陋之棧房喧呼達旦,生業極盛,上海開通,煙灶生塵矣。”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并“全路開通之后,上海之大市場,必移于漢口”,廣州也會愈加發達,而廣州、漢口商務的發達必然會帶動湖南的發展。[53]應該說,這些認識都相當有見地,對于說服湘路股東支持湘路收歸國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粵漢鐵路如何順利收歸國有?譚人鳳擬定了鐵路股款的贖回辦法:
查三省路股,有由商民籌集者,三省商股及湖南房股是也。有量假官力而籌集者,湖南米鹽等捐及湖北振糶捐是也。處置之法,自難一致,分舉于下:
(一)量假官力籌措之股,仍照清例,換給保利股票,永遠作為地方公積金,充各該省辦理公益實業之用。
(二)商民所集之股,一律換給國家鐵路股票,分紅分利,一仍其舊,并由股票公舉查賬員,監察用途。其從前所有虧耗,無論多寡,悉由政府擔任。蓋股款乃血汗之資,虧耗匪人民之咎,政府既收取路權,自當承認虧耗為路利之擔保。
(三)其已換國家鐵路股票,而欲得現銀,以從事他種營業者,得持赴粵漢鐵路總公所聲明,由政府預籌的款按十成收買,以資利便。蓋投資為個人自由,理無取乎強迫。換票乃普通辦法,事有貴乎通權。格外求全,力圖方便,并非拒絕民股,壟斷獨登也。惟此路股價落至數成,一經政府擔承,即時回復原值,人民方保存之不暇,又何必兌取現銀?且今日需款急迫,受挾外人,吾民方思毀家以紓國難,豈肯傾軋以召危亡?設此專條不過為人民謀便利,必無大宗股票求兌現銀者。儲款二三百萬即足應付,政府其勿以款絀為詞,拂吾民意也。
(四)各省現存款項應一律收回,以便開工時與借款同時提用。路成有余,則以之敷造支線,或展長干路。[54]
按,湘路公司股款的來源大致分為六項:“一為湘民認繳之優先股;一為隨糧帶征之地方租股;一為出境米捐;一為衡、永、寶三府淮鹽溢引之配銷捐;一為本境行銷各省食鹽加價之口捐;一為供差員薪派捐股票。近由諮議局議決者二宗:一為累進租股,系按原有租股層遞加扣;一為房租股,系每年派捐一月房租入股”。盛宣懷還說,在這些股份中,“其正式股捐只有優先股之一百七十二萬元確系商業性質,其余各項派捐或先經奏準或甫議定,雖皆有案牘可稽,實皆涉于懸疑。”[55]事實上,上述股款除商股外,其他股款多有強行攤派性質,“據湖南京官聯名奏稱:該省路股除田租外,尚有米捐、鹽捐、房捐各名目。似此層層剝削,不惟取之富戶,且至擾及貧民”。[56]從譚人鳳的設想來看,他充分考慮到了紳民的利益,這當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這里的關鍵是,收購鐵路的經費從何而來?譚氏的辦法很簡單,收購款項“必出于借款一途”,雖然是借款,但他認為“究不難以該路所得之贏余克期償還”。[57]但我們前面也說了,依照當時的歷史境況來看,粵漢鐵路的借款并不容易達成。1912年11月,湘路公司董事會在給湖南都督譚延闿的電文中說:“同人等查閱譚石屏先生所交交通部致四國銀行代表函,亦于函尾敘明請其見復,現尚未見復信。外交極難,往往有已定條約,因只字片言之不慎,致生絕大之波瀾者”,“該銀行代表又有須候倫敦會議方能解決之語,至今又尚無片紙見復,而謂必無反復,實未敢信。近日在城股東,對于此事,極為注意。有函囑公司堅持須有現銀,方可移交。”[58]由于湘路公司堅持要求交通部收路必須備足現款,譚人鳳乃多次與四國銀行團交涉,要求他們按照與清政府訂立的借款合同繼續付款,但四國銀行團借口中國南北交戰,政局不定,不肯付款。后經路政司長葉恭綽多次交涉,1912年7月11日,四國銀行團“提出辦法四條,致函交通部,請求參酌施行。”[59]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四個條件可以歸納為:一是存款問題、二是管賬問題、三是擔保品問題、四是贖路問題。[60]更具體一點說,四國銀行團要求:將商辦川漢、湘路、粵路收歸國有;粵漢、川漢應同時開工;取消將匯款凈數之半存入交通銀行或中國銀行;所有抵押的厘金收不足時,以各路財產、材料擔保,選派洋人為總會計員、總工程師和管理員,到全路分段管理賬目、材料。達成了這些條件,四國銀行團同意繼續付款。[61]1913年3月1日,交通部復函四國銀行團,基本上全部接受了這些條件。3月3日,四國銀行團復函交通部同意向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第一次付款1200萬銀兩。[62]
雖然譚人鳳的方案力圖照顧到湘路公司股東的利益,并盲目認為,粵漢鐵路一旦由政府收回,其股票價格立刻會恢復原值,同時三省參股的紳商也大多會選擇繼續持有粵漢鐵路的股票,而真正想兌現為現銀的人一定不會很多,政府只要“儲款二三百萬即足應付”。而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湘路公司總理陳文瑋[63]等卻表示,干路國有“我公司并無人反對;借款筑路,公司亦極贊成,惟公司系商務性質,只知求現不賒,否則難以承認”;“應請督辦先備現款,再議交收之法,若徒手空空,侈言國有,此則我輩數人不敢負此重大責任。”[64]1912年11月上旬,湘路公司為此特致電交通部稱:“路歸國有,湘人極表歡迎。公司移交手續,亦早準備。惟現金無著,股東深滋疑慮,應請大部速匯巨款來湘,以便股東自由領還。事關路政,懇速電示。”[65]11月6日,湘路公司又發布公告說:“股東因督辦宣言收回,始欲退現;茍不能即時兌發,股東不放心,同人即不能卸責。比已將譚君所提之議拒絕,一面由同人電致交通部索取現款,一面抱定宗旨,以使股東及人民權利不至損失為主”。[66]
在這種情況下,譚人鳳乃通過湖南都督譚延闿向湘路公司做工作,當雙方大體商議妥當的時候,北京政府又忽然將譚人鳳調任長江巡閱使,由黃興接任粵漢鐵路督辦。如前文所言,黃興并未就任。1913年2月,北京政府交通部任命前兩廣總督岑春煊[67]為川粵漢鐵路督辦,6月18日,岑春煊去職,北洋政府又任命交通次長馮元鼎兼川粵漢鐵路督辦。交通部明確規定,漢粵川鐵路歸交通部直轄,由交通部與四國銀行團接洽借款問題,凡款項的調度以及其他交涉事項,均由交通次長馮元鼎代表交通部處理一切,設立督辦總公所于漢口,統一管理漢粵川各線工程局及其他附設局所。1913年5月間,湘路公司公推陳文瑋、傅定祥為代表與交通部就發還股款以及路事交接事宜反復商議,其中的焦點問題是股款的歸還方式與年限。陳文瑋等向交通部次長兼川粵漢鐵路督辦馮元鼎呈文稱:
粵漢干路收歸國有,乃因前清郵傳部所訂四國借款合同。民國成立,當然繼續有效。因而產出之問題,因之前清郵部所定收路還股成案,亦不能不繼續有效。查前清郵部奏定收回湘境粵漢干路辦法,對于商股發還現款,對于米鹽公股發給期票,曾經明發上諭。嗣因湘籍京官陳請,又特降諭旨,準將租股等與商股一律看待,良以商租房薪各股,皆系商民湊集,各有主名,振興實業,甫在萌芽,非特加愛護,無以恤商情而維信用。若米鹽公股,當初定名曰捐本,含有捐項性質,今由中央發給期票,將全額照本分別定期付換地方,此中利賴,已足無窮,湘省人民,咸知此旨對此久無異議。去年譚督辦奉命到湘,發布宣言書,亦曾申明私股還現之說。后來黃督辦接任路事,又曾宣言保障股東權利。故在湘路歷史上言之,私股還現,公股發給期票,殆已不可變更。此次文瑋等經公司董事會推舉來京,商議收路還股辦法,深知部中困難情形,故與公司董事會往返電商,允將甲項于民國二年度,只還二百萬元,其余民國三四年分攤還清。雖于還股求現之說,未能圓滿貫徹,然款項有著,利息照常,權利既然無損失,困難當能共諒。惟合約內所列甲乙兩項股款,甲項目接收后,即行攤還,至民國四年度還清。乙項目自民國五年度起,方始攤還,至民國十六年度還清,比較原案,乙項恰符前清郵部所定發還米鹽公股辦法。而甲項比諸前郵部所定發還私股辦法,尚有未能適合者。在各股東深知大義,共知鈞部苦難,當亦不忍苛求。若再并區區優先利益而無之,似非體恤商民之道。文瑋等愚見以為,在鈞部雖以甲乙兩項民(“民”當為“名”——筆者注)義分別發還,而在公司支配,仍應根據原案,以甲項還清私股后,方能以乙項攤還公股。庶國家既無反汗之嫌,公司亦免食言之咎。[68]
對于湘路公司的收路還股要求,交通部批文稱,“此事前經迭據代表面商,業已分別性質,載明合約之內,將來本公司支配,自應根據和約辦理。”[69]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湘路公司雖然表示體諒交通部的困難,但從根本上還是要求交通部按照清朝郵傳部所擬定的收路還股方案來進行路權回購。那么,郵傳部當時擬定的方案是什么呢?1911年6月,郵傳部擬定的方案是:“湘路所收五百數十萬兩,有米捐、鹽捐、租股、房股各項四百余萬兩,商股約一百萬兩左右。支款內修路購料約二百余萬兩,據余肇康電稱,洙(株)至長沙一百余里,已經完工開車,碼頭各項,均已齊備。約計其數,耗費無多。擬定將實在商股一百余萬兩,照本發還;其余米捐、鹽捐、租股、房股,除美國贖約經費三百余萬兩外,準即另發國家保利票,長年息六厘,五年后分作十五年攤還,以充本省實業公用”。[70]也就是說,湘路所集500余萬兩股款,商股約100萬兩,米捐、鹽捐、租股、房股等約400余萬兩;商股直接發還現銀,米鹽房租等款除掉合興公司湖南所攤還款外,所剩款項發行國家鐵路股票,年息6厘,5年后分15年本息合計逐年攤還。
根據1913年6月23日交通總長朱啟鈐呈大總統袁世凱文,湘路公司與交通部之間的協商,最初雙方的要求距離比較遠,“公司意在已用之款全數發還現金,而本部財力竭蹶萬分,無從羅掘”,交通部以川路國有分年攤還已有成案,希望湘路公司亦能準此辦理。朱啟鈐指出,“湘人深識遠慮,力顧大局”,湘路公司代表陳文瑋、傅定祥“準情酌理,不為意外之要求”,“深識大體,惟以保全商本擔負債務為請”;交通部則“以國家之款擔任無形之虧累,但求事實有濟,財力可以騰挪,亦未便稍從刻核”。由于雙方推誠布公,彼此交讓,“十余年來紛紜糾葛之路”,最終得以圓滿解決,順利完成了國有化。[71]
1913年6月3日[72],湘路公司在北京與交通部議定了“接收商辦湘路合約”。這份合約一共有20條,一式兩份,附表兩份,交通部與湘路公司各執全件一份。合約中比較重要的內容是第一、三、五、七、八條,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湖南境內原定之粵漢干路路線及三佛(三水——佛山)支路湖南所占七分之三,所有公司已成路線及材料、車輛、廠房、器具,未成鐵路之已建工程、已購地段及本路全線內一切產業權利,一律改歸國有,由部直轄,自由處理一切。所有以前給與該公司之權利,概行取消。
第三條:公司入款,所有商股、房股、租股、薪股,賑糶米、捐、鹽斤、配銷捐一律認為公司資本。
第五條:路歸國有,公司所有資本,應一律發還現款。今將股款分兩種辦法,按照商、房、租、薪股本金額列為甲項,按照米、鹽股本金額列為乙項,分別定期發還。
第七條:甲項資本于民國二年度攤還二百萬元,余數于民國三、四兩年分年攤還,其分年攤還之款,由部先期給與有期證券為憑;自民國二年一月一日起年息六厘(民國二年一月一日以后所交股之日起息),二年度付息四次,三四年度每年度付息二次,已還之本即止息。
第八條:乙項資本自接收后第三年起分十二年每年兩期還清;按照該期還本之數,匯計歷來應付之息,一并給付。息率及計算開始日期與甲項同。[73]
上述合約還有對于甲乙兩項股款的分年攤還表(參見表1、表2)。
表中所列乙項還本付息日期起自1913年7月1日,但同時也說如果交路日期延遲,則還本付息日期亦隨之展遲。事實上,湘路正式收歸國有的日期為1913年10月1日,因此上述乙項還本付息日期也就從該年10月1日算起。1913年10月1日,交通部湘鄂鐵路總局在長沙設立駐湘工程處,同時,湘路公司及其董事會同時撤銷,改設股款清理處,開始正式辦理交接事宜。至1914年2月,交通部主事巢元功、顧梓田報告股款清算完竣,所有甲項股本銀為440萬元,乙項股本銀為473.6萬元。在債款未清算之前,交通部已經代還湘路公司銀元二百七十七萬二千四百四十元二角六分二厘。現負債長平銀六十七萬二千四百兩零七錢九分二厘,英金九萬八千五百二十八鎊十一先令五便士,銀元三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元零三角,以上已還、未還銀元及長平銀、英金等債款合計共約合銀元四百九十五萬九千九百零九元二角四分二厘。所有甲項股款照第七條辦法分八期攤還,每三個月為一期。[76]

表1 湘路收歸國有甲項分年還本付息表[74](單位:元)
在民國初年,湘路的收歸國有并不是孤立的個案,它是北洋軍閥利用鐵路系統向南方擴張勢力的一種手段。當時主管交通的一些政界要人如梁士詒、朱啟鈐、葉公綽、關賡麟等人均為“交通系”的主要角色,他們打著統一鐵路建設與管理的旗號,利用民國初年有利的歷史環境,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將民辦的八條鐵路均收歸國有,而且并沒有花費非常大的代價。同時,商辦鐵路經過多年的實踐,成效微弱,也從側面清楚地證明在當時的中國商(民)辦鐵路尤其像粵漢鐵路這樣的大型干線鐵路是非常困難的,必須集全國之力進行干線鐵路建設,才能真正取得實效,故投資鐵路的商股也愿意在保證自身利益不受損失的情況下,把鐵路建設權交歸國家。張茂鵬在其文章中寫道:“梁士詒一向主張以發展交通事業在經濟方面開發陣地,而統一各鐵路,又為發展交通事業的首要任務。這時,北洋勢力已擴大到南方,沉沒在鐵路建設中的商股感到收益無望,故愿將鐵路權交給交通部。當時任交通部長的朱啟鈐為梁士詒的好友,而任路政司長的葉恭綽更是梁的得力助手,于是梁便以全國鐵路協會會長資格,利用這一時機,與有關方面磋商贖回各路,妥訂章程、合約。”最終實現了大部分鐵路統一建設與管理的愿望。[77]1913年6月3日,交通部與湘路公司訂立合約,12日與蘇路公司訂約,8月與豫路公司訂約,9月與晉路公司訂約,1914年3月與皖路公司訂約,4月與浙路公司訂約,1915年1月與鄂路公司訂約,而川路則早在1912年11月就已經為交通部收歸國有。[78]在兩年多的時間里(1912年11月—1915年1月)就將八條商辦
鐵路收歸國有,確實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也反映了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在民間也具有一定的威信。

表2 湘路收歸國有乙項分年還本付息表[75]
湘路的收歸國有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當時“各省商辦鐵路公司集積了大量資金,受種種條件的限制”,除了少數公司如蘇路、浙路具有一定的實績外,“大都未能發揮資本的效用”。[79]這無疑是對寶貴的民族資本的一種極大的浪費,此時,由國家出面收回鐵路的建設、經營與管理權,對于近代中國鐵路事業的發展應該說是有利的。
三、鐵路部門對粵漢鐵路沿線湖南段的經濟調查
所謂社會經濟調查,就是指“根據交通規劃的需要,對所研究區域的社會經濟狀況作全面的了解,收集各方面的基礎資料。”社會經濟調查可分為綜合社會經濟調查和個別社會經濟調查。鐵路建設屬于個別社會經濟調查,“是指對擬新建或改建的某一交通線路(航線、鐵路或公路)或構造物的社會經濟調查,其目的在于確定客貨運量的大小,決定路線的方向、技術等級和標準,確定施工程序以及論證投資效果等。”[80]這個定義現代化色彩較為濃厚,與民國時期的鐵路沿線經濟調查存在著一些差別,但就其主要意思而言,是差不多的。
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特別是其在1928年形式上統一中國之后,提出了“振興實業”的口號,而鐵路建設被列為重中之重,國民政府鐵道部成立之后,擬定了龐大的鐵路建筑規劃,即所謂“庚關兩款筑路計劃”。鐵道部對于鐵路建設前的經濟調查非常重視,在1930年至1937年間,在各鐵路沿線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調查活動。鐵道部認為,“為培養新貨運起見,尤應設法輔助沿線地方國民經濟之發展,故鐵路沿線經濟調查一事,甚關重要。”[81]這個時期的鐵路沿線經濟調查,由鐵道部或各地鐵路管理局組織,按照鐵道部擬定的“國有鐵路辦理沿線經濟調查指導書”的要求進行,其調查內容包括地理、人口、物產、農業、林業、礦業、工業、商業、交通、社會概況等項目,重點則在沿線主要物產及其運銷等情況,對于與鐵路形成競爭關系的水運和公路運輸也十分關注。調查完畢,要根據調查內容形成調查報告書,并針對所調查的路線的情況提出一定的建議。這次大規模的經濟調查,對于整理路政、發展地方實業以及全面抗戰的準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是發展鐵路運輸的先決條件和重要根據,這就決定了鐵路部門必須對沿線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詳細的調查,粵漢鐵路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5月,其時粵漢鐵路株韶段剛剛實現全線接軌,鐵道部即訓令湘鄂段管理局迅速組織人力進行沿線經濟調查。[82]1937年初,粵漢鐵路管理局指定武漢營業區課員李以介、長沙營業區課員胡世義、衡陽營業區課員姚松年、曲江(韶關)營業區課員蔡惠褀、廣州營業區課員周孟人等,在鐵道部課員江道亨的統一指導下,對各自營業區進行經濟調查。[83]固然,鐵路部門的調查,其著眼點自然是為了發展鐵路客貨運輸,提高鐵路部門的經濟效益,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鐵路作為一種社會聯系廣泛的公共事業,它同時“負有改進國民經濟之重大責任,應盡量設法發展其沿線經濟。”因此,鐵路自身的經營,有賴于沿線各地的經濟狀況,故鐵路欲求其營業之進步與發展,就必須“輔助其沿線國民經濟之發達”,所以,鐵路自身之營業與沿線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一而二二而一之問題,固有相互密切之關系也。”[84]
鐵路部門曾多次對粵漢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進行過調查,我們主要關注對該路湖南段的調查情況。1933年9月底,其時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建設業已正式拉開帷幕,鐵道部組織“株韶段沿線經濟調查隊”(主任一人,隊員二人),沿株韶路及附近各縣進行調查。此次調查,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配合株韶段的工程建設,同時也是為未來粵漢鐵路全線通車后的客貨運營業預做準備。此次調查,原定期限為兩個半月,調查區域原定為湖南省之湘潭縣、衡山縣、衡陽縣、耒陽縣、永興縣、郴縣、宜章縣以及廣東的樂昌縣和曲江縣。上述諸縣,皆為株韶段直接經過之地。但調查隊在調查過程中認識到,鐵路營業范圍,并不能僅僅局限在線路直接經過之地,鐵路途經各城鎮鄰近諸縣也是鐵路營業所輻射的范圍,故鄰近各縣之經濟狀況,也應該一并關注。向鐵道部請示之后,將湖南省醴陵縣、攸縣、安仁縣、資興縣、常寧縣、臨武縣,廣東省仁化縣、始興縣、南雄縣、乳源縣等11縣列入調查范圍,連同原定之9縣,總計20縣。調查時間亦增加兩個半月,連同預定時間兩個半月,總計5個月。本次調查,涉及20縣之人口、地理(位置、面積、山脈、河流等)、陸路交通(公路、驛道)、水道交通、農業、畜牧、林產、地質礦產、工業、商業等事項,調查隊完成的調查報告書除詳列上述調查結果外,尚有總論和結論部分,其內容頗為詳實可靠,實為不可多得之社會經濟調查資料。雖然在調查過程中,調查隊面臨著人手有限、經費短少、時間緊張、交通不便等種種困難,加以時局動蕩,沿路調查過程中時遇匪患,他們能夠在短短5個月完成如此繁重之調查任務,實屬不易。
據調查報告說,此次調查的地域面積約4.7萬平方公里,丘陵多而平原少。全區人口約744萬余人,居民習苦耐勞,湘人尤為儉樸。本區水路交通方面,河流遍布全區,水道交通極為便利,各河水量深淺不一,大約水漲時湘江正流1000噸以下大輪,可自長江通航至湘潭,小輪可上溯至衡陽,民船則可上溯至廣西境內;北江正流,水漲時小輪自廣州可通航至曲江,但無正式航線,民船水漲時,亦可上溯至湘境。然水落時,或不能載貨,或需拉纖,方可勉強通行。調查認為,水路運輸對于將要完成的粵漢鐵路未來之營業影響甚為巨大。在粵漢鐵路株韶段未完成之前,本區貨物之運輸,除少數貴重物品由公路汽車運送外,其余貨物全部走水運。現株韶段正加緊施工,完成可期,而路線南北分別與湘江、北江平行,則將來鐵路水運對于貨物運輸之爭奪,勢所難免。從鐵路的立場來看,湖南富庶之地,多萃于湘西(湘江以西),人口繁密,物產豐富。粵漢鐵路湖南段,沿湘江東岸而行,全線略偏于湘東,故湘西貨物之運輸長沙、岳陽、武漢者,多由所在地乘船直達,或在衡陽或在湘潭轉換大船,可直達漢口。倘改由鐵路運輸,必須先由產地以船運抵湘江東岸,卸于碼頭,運至火車,無車尚須先存貨棧,有了空車,然后裝車北運,其目的地如是長沙、岳陽、武昌,則車運較之船運,不過多一裝卸之煩。倘其目的地為漢口,又須過江一次,則車運較之船運,中途多兩次裝卸。若是客運,雖有不便,尚無太大影響,然在貨運,則不僅貨主要多負擔兩次裝卸費,而且裝卸一次,則貨物有多遭一次損壞或被盜竊的風險,到達之時間,也會因此而延誤。縱使將來實施聯運之辦法,貨主可在漢口提貨,但是上述因中途裝卸而導致的種種風險卻依然存在,即使上述風險所導致的損失貨主能夠獲得一定的補償,那么這種損失事實上被轉移到鐵路部門了。鐵路部門為了避免這種損失,會在運費上設計種種補償辦法,這就必然導致鐵路部門在貨運定價中,加入中途裝卸費與損失賠償等種種費用。正常情況下,鐵路運費已較水運價格為高了,再加上以上種種費用,則兩者運價會相差更大,如此鐵路的競爭力將大受影響。鐵路雖然具有到達較快的優勢,但是如果運輸之貨物如米、煤、鹽等在到達時間上并無特別急迫的要求,而粵漢鐵路沿線之大宗貨物,又恰恰為上述三項,則商人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就是運價之高低了。由此可見,未來粵漢鐵路短途之貨運,如衡陽至武昌間、曲江至廣州間,將會受到水運競爭的嚴重影響。但是未來由武昌至廣州之全程運輸,或由湘運粵,或由粵運湘,由于南嶺橫亙湘粵之間,湘江與北江不能匯通,北江上游之武水雖能通至湖南宜章,然灘多水急,舟行艱難,這時則舍鐵路之外別無他途。雖然水運與粵漢鐵路存在競爭,但亦存在互補。湘江、北江各支流,多與鐵路相交,不啻為鐵路之支線,將來鐵路之貨物,皆須借助這些支流散諸各地。鐵路部門需要認真考慮的是:如何將這些支流運輸的貨物匯聚到鐵路上來運輸,而不是被湘江北江水運奪走。
湘粵交界之處,地勢最為險峻,公路尚未貫通,河流亦南北異趨,交通十分困難,貨物往來,全賴肩挑,循往昔之湘粵大道往來轉運,間或有騾馬駝運,但甚為罕見。各縣間短途販運,則以肩挑為唯一辦法,而旅客之往來,步行之外,惟恃肩輿。公路方面,湘省境內路線頗多,往來尚稱便利,但運費較高,商人尚少利用。湘省公路與粵漢鐵路關系最密切者為湘粵公路,該路由長沙至粵省邊境,與粵漢鐵路平行,業已經完工通車,長約393公里。此線目前為湘粵之交通要道,日后株韶段工程完工,彼此相同的走向,而又相距不遠,除了湘江水運的競爭,與湘粵在運輸上也必然會產生競爭。而公路因運費高企,必然不能支持,因此應該預先籌劃對策,使彼此由相妨化為相輔。粵省公路路線較少,且運費高昂,頗為不便。
全區農產以稻谷為大宗,薯芋雜糧次之。湖南省之湘潭、醴陵、衡山、衡陽、攸縣、安仁等縣,茍非荒歉,皆有米稻輸出,其數量則視收成之豐歉而定。而湖南之耒陽、常寧、永興、資興、郴縣、桂陽、宜章、臨武等地,其稻米產量較少,豐年尚不足自給,荒年則尤須外地輸入。全區多山,故宜于植樹,湖南省之衡山、安仁、攸縣、資興、郴縣、桂陽、宜章等地,林木較多,而湘潭、衡陽等縣,則為各縣木材集散之地。桐油、茶油為湘省大宗土產,輸出較多。該區林木雖多,然樹齡少者居多,加以山農亂伐,故能充鐵路枕木之用者并不多。牲畜以豬雞牛等為多,亦頗有輸出。
礦產方面,全區礦產分布廣泛,種類繁多,儲量豐富。已經開采的主要有:常寧水口山之鉛、鋅及硫磺,攸縣東北鄉之鐵及砒,安仁北鄉之石墨,永興觀音崖之無煙煤,資興、郴縣、宜章間瑤岡仙之鎢,臨武香花嶺之錫,宜章、乳源間狗牙洞之煙煤等,儲量多寡不一,而交通不便,資本缺乏,實為阻礙礦業發展之主要原因,故粵漢鐵路全線接通,對于今后本區礦業之大規模開采與發展尤其重要。工業方面,本區工業殊不發達,新式工業,幾為空白。舊式手工業產品,除醴陵之瓷器、夏布、爆竹,湘潭之紙傘,始興、仁化之土紙等,尚有一定名氣與產量外,其余如土布、鞋襪、藤竹器等,數量較少,且系零星制造,雖在當地社會經濟中占有一定地位,而于將來鐵路之影響則顯然微弱。本區工業之不振,其原因大約為人才難得、資本缺乏、交通不便、需求不多,加之外貨充斥,不但新式工業難以崛起,即原來就有之工業,如瓷器、夏布、土紙、爆竹等,因墨守舊章,亦逐漸衰落,將來之振興,實有賴于粵漢鐵路之完成,而其出品,亦當大力改良方為出路。
本區商業,以衡陽、湘潭為盛,郴縣、醴陵次之。衡陽舊為衡州治府,居湘耒蒸三水合流之處,綰湘南之鎖鑰,水陸沖衢,人物殷豐,其地位實不止商業一端,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皆居重要地位。自長(沙) 衡(陽)、衡(陽) 宜(章)、衡(陽)寶(慶)各公路通車后,商業更顯繁榮,且有超越湘潭之趨勢,其每年之商品營業額已在湘潭之上(參見表3)。湘潭城居湘江西岸,百余噸之輪船終年可與武漢、長沙、岳陽輪船往來,小輪可上溯衡陽、祁陽等地,民船則可直達永州各縣;西循漣水,可入湘西,故過去湘省西南部之貨物,皆在湘潭集散,故其商業地位,除長沙外,首屈一指。近年因衡陽日趨發達,湘南貨物,改集衡陽,而湘西貨物之運銷武漢或由武漢運入湘西者,又多改趨益陽、常德等地,故湘潭之貿易,雖大不如前,然規模尚在,其商業資本額即遠在衡陽之上(參見表3)。其他如郴縣、醴陵、樂昌、仁化、攸縣、衡山等縣,皆具縣治之氣象。湘粵兩省貿易地點,在湖南為郴縣,在廣東為樂昌,尤其是樂昌之坪石鎮,地扼湘粵交通咽喉,粵漢鐵路過其東,且瀕臨武水,在軍事商業方面皆居重要地位,湘米粵鹽為交易之最大宗,鹽尤為湘粵互易之必需品,湘人肩米、谷、雞、鴨或雞蛋之屬,至坪石易鹽而返。

表3 本區主要商業中心商業簡況(1932年)[85]
全區貨物,在輸出方面,以稻、米、木材、煤、各種金屬礦砂、爆竹、茶油、桐油、瓷器、夏布、豬、雞、雞蛋、粗紙為最多,輸入則鹽、棉花、棉紗、綢緞、布匹、煤油、銅、鐵、五金制品、面粉、糖、南貨、顏料、化妝品、書籍、雜貨等為大宗,輸入輸出貨物之轉運地,在北為長沙、漢口,在南為廣州、香港,本區之承轉地,則為衡陽、湘潭、曲江、南雄等地。
綜觀全區經濟狀況,農業已頗為發達,此后當著力于種子改良與推廣銷路方面;礦業方面,尚需有計劃之開發,工業則極度幼稚;林業須提倡培植與保護,乃能取之不竭;商業亦相當發達,將來鐵路公路,相繼完成,交通便利,則商業更易繁榮。本區人口稠密,風氣淳樸,將來粵漢鐵路通車,本區經濟狀況,當會迅速改變。
調查結論認為,粵漢鐵路株韶段正在興工,完工有期,必須根據此次對該路沿線之經濟狀況所做的調查,認真謀劃鐵路客貨運運輸政策。依調查來看,對鐵路運輸影響之最大者,無疑是水運與公路,此外,沿線物產不甚豐饒,礦產多未開發,新式工業幾乎空白,因此,粵漢鐵路通車最初幾年,客貨運收入,與人們的想象恐怕會有很大的距離。不過,可以期待的是,鐵路的運營會變得越來越好,因為隨著鐵路的運營,鐵路沿線之經濟必然會逐漸發展乃至發達。今后粵漢鐵路發展貨運業務,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努力:
其一,湘米運粵。湖南多米,而廣東缺米,粵漢鐵路溝通湘粵,為兩省調劑稻米之盈虛提供了可能。惟湖南稻米,品種稍差,加工技術亦較為落后,故米之口感不為粵人所喜。1933年,湖南稻米豐收,而廣東歉收,于是廣州商會派人赴湘購米三萬擔,首批起運后,即行止辦,其原因即為湘米過粗,廣東人難以適應。今后,湖南省當改進稻種和加工技術,則湘米有可能大批運粵,也會成為粵漢鐵路貨運之大宗。
其二,湘煤銷粵。湖南之煤,已開采者如醴陵、永興等縣,永興之煤,煤質尤佳,然產量不多。廣東之煤礦著名者,僅有一個富國煤礦,產煤有限,每年需從國外輸入煤炭甚多,倘湖南煤礦能大量開采,則由鐵路運粵,不但鐵路能夠增加收入,亦可稍杜外煤之傾銷也。
其三,粵鹽銷湘。廣東之鹽,質量較淮鹽為佳,且價格亦廉,故湘中湘北之淮鹽區,近亦時有粵鹽蹤跡。倘粵鹽能夠在湖南全省銷售,必將取代淮鹽的地位,而粵鹽銷湘必由鐵路,則鐵路與湘省兩受其利益。
其四,湘粵貿易將大增。昔時湖南所需一切日用品,向于滬漢購辦,粵漢鐵路通車后,廣州香港市場亦可向湖南提供大量日用品;湖南各種土貨,昔日亦多銷滬漢,今后可兼銷港粵。從滬漢購辦貨物,或土產輸出滬漢,皆有水道可循,而水道運價遠較鐵路為低。倘在港粵采辦貨物,或土產輸出港粵,則非鐵路不可。為發展鐵路運輸增加收入計,當以低廉之運價使貨物之出入滬漢者,轉而出入港粵也。
其五,湘粵公路,幾與粵漢鐵路平行,鐵路通車后,很多貨物會舍公路而走鐵路。但短途客運,因公路班次多而座位又甚舒適,恐將受公路之激烈競爭,故鐵路預先制定對策,如減低票價,注意改善車上之設備,提高正點率等,或許能吸引部分乘客。
其六,積極與水道運輸配合。水路運輸,實為粵漢鐵路貨運之勁敵。雖然湘江、北江水運便利,但粵漢全程之運輸,似非水道所能競爭。然南北兩端之短途運輸,則水運以其低廉之價格,處處占優。粵漢鐵路處于湘江與北江之東岸,大部分在湘東貧瘠之區,而湘(江)以西富饒物產,水運以其價格低廉、省多次裝卸之勞的優勢,故商家多趨水運。將來鐵路當局之運輸方案,必須處處針對水運,方不致鐵路僅沾水運之剩利。調查隊認為,應實行如下各項,或可稍資補救:(甲)如財力許可,應修建一條支線,聯絡湘西,或提前修筑湘滇公路湖南段,以吸收湘西之貨物。(乙)武昌漢口間造橋梁或鐵路輪渡,渡過長江,使粵漢平漢兩路連接,以省貨物裝卸過江之煩。(丙)武昌廣州修建大碼頭,以便接運粵漢路之貨物。(丁)改善貨物運輸管理,辦理水路貨物聯運辦法。(戊)在湘江和北江西岸城市鎮之間,設立營業所,注重收運貨物,由營業所代運之貨物,渡過湘江或北江時,其駁運與裝卸費,應當免收。(己)貨物之裝卸手續,及運送時間,務求特別迅速,以發揮鐵路之特長。(庚)客貨運價之訂定,務必低廉,對于向由水運之貨物,則訂為特價,雖虧及成本,亦所不惜。(辛)一切裝卸費及各項雜費,能免除即免除,必須收取者,則減至極低價。(壬)應利用回空車輛,對某種貨物運價,予以折扣。上述各項,為調查隊調查后之共同感受,希望后之當事者能認真考慮抉擇。[86]
范廣練,日本鐵路專科畢業,回國后任職粵漢鐵路南段管理局,1937年任粵漢鐵路長沙營業區主任[87],專司沿線經濟調查事務,曾對粵漢沿線各地進行過多次調查。在《湖南醴陵縣屬產煤狀況與粵漢鐵路之關系》的調查報告中,作者認為,煤炭需用甚廣,鐵路需要尤為巨大。如能得適宜廉價之煤,一來鐵路營業支出大為減少,二來運輸收入又可增加,實為兩全其美之事。作者在介紹了醴陵官辦的石門口煤礦和商辦的石成金煤礦的位置、交通、煤質、儲量和產銷情況之后,著重分析了醴陵煤礦與粵漢鐵路的關系。他指出,按照醴陵煤礦儲量約6100萬噸計算,在株韶段通車之后,每年可為粵漢鐵路南段節約燃料費高達42萬元之多,這是其一。其二,粵漢鐵路全線通車后,醴陵煤炭可大量銷往廣州,為粵省工業界提供優良價廉之國產煤,每年可為粵漢鐵路南段管理局增加收入達百萬元以上;同時,湖南煤炭的大量輸入,不但能夠發展醴陵的經濟,還能抵制外洋煤炭在廣東的傾銷,對于提倡國貨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88]
在《粵漢鐵路運輸粵鹽湘米及萍醴煤炭之研究》的調查文章中,范氏指出,粵漢鐵路現已全線接軌,湘粵贛三省人民,因地理相接的緣故,均盼其早日通車,以便三省物產能夠大量快速地調劑盈缺,其中粵鹽湘米及萍醴之煤尤有互濟之必要。廣東缺米,根據統計,1912—1935年間,每年從安南暹羅等地輸入米谷約7961136擔,價值約關銀3500萬兩;而每年輸入的本國米谷卻只有約200萬擔,價值約關銀900萬兩。米谷之外,廣東亦缺煤,據統計,1925—1935年間,平均每年輸入煤炭約750207噸,價值約關銀6632185兩,其中國產煤僅占20%,而洋煤卻占80%。洋煤價格比國產煤高50%,而其銷量卻是國煤的四倍之多,這是因為洋煤的品質較國產煤為高。鹽產方面,廣東每年產鹽余額高達1271000擔,湖南每年需輸入食鹽約2356000擔。因此,就湘粵贛三省經濟而言,湖南多米,每年輸出谷米約703459擔,煤亦儲量豐富,江西萍鄉之煤則尤為著名,則三省米、煤、鹽之產銷供求,正好呈互補互濟之關系。假如粵漢鐵路能夠制定合理的運輸價格,湘粵贛三省政府能夠降低甚至取消諸如米捐、進出口稅等各項費用,則三省各自主要的物產就能夠借助粵漢鐵路實現良性互補之關系,對于三省經濟的發展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89]
1937年3月,其時粵漢鐵路業已全線通車數月,為了發展粵漢鐵路客貨運業務,黃秉鏞奉粵漢鐵路局營業處命令,對該路衡陽區所屬城鎮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調查。本次調查擬對粵漢鐵路衡陽區各站附近城鎮概況、經濟狀況及客貨運情形,進行詳細調查。衡陽區各站附近城市有湘潭、醴陵、衡陽、衡山、耒陽、永興等六個城市,后因時間關系,最終只調查了湘潭、醴陵、衡陽等三縣。雖然調查城鎮有所減少,但對所調查的三個城鎮的各種情況頗為全面詳盡,并針對調查所得,擬定了整頓和發展鐵路客貨運的具體計劃和建議。
本次調查的內容分兩大部分:一是湖南省地理沿革、全省地勢及水系之概況;二是對湘潭、醴陵、衡陽三地的地理、氣候、土地面積、人口、水路交通、郵政、電報、電話、教育、農業、工業、礦業、商業、金融等的全面調查。調查指出,湖南全省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因此湘資沅澧四大水系大抵由西南和南部向東北注入洞庭湖,大江涓水“遍布全省,航行灌溉,無不便利”,水運之發達,“對于本路貨運之競爭,至為劇烈。”
就湖南全省貨運情形來看,湖南全省水系發達,航運極為便利,全省輪船公司除怡和、太古、日清、招商等可通上海、漢口者,其余小輪登記在冊者有89艘,帆船木船等大小船只高達30余萬艘,故“全省貨物80%均由水道運輸。”水運價格便宜,手續簡便。平均由漢口至長沙,或省內各縣之水運價格,大約每擔在3—4角之間。運輸辦法,多由船家直接向商家招攬生意,手續極為簡單便利。遇有回空船只,價格更為低廉。有時甚至還會碰到只收伙食費,而貨物免費代運的。職此之故,“湘省各行商非遇緊急趕市,或冬季水涸,船只不能行駛時,無不樂趨水運。”而且,船家起卸貨物均甚為小心,貨物較少損壞。且店主可以派人監督,對船戶有隨時指揮之權。
公路運輸方面,近年湖南公路進步神速,現在東西南北主要縣份均已通車。同時,正在修筑之公路亦甚多,公路網一成,則湖南全省貨物均可由公路運輸。不過,目前公路運輸價格稍貴,且運量有限,故商人采用公路運輸的尚不多。根據湖南省公路局的統計,1935年全年公路貨運總量為7126248公斤。
粵漢鐵路處水路與公路運輸劇烈競爭之中,且湘省占全路一半以上里程,如不盡快整頓吸收湘省之貨物,則本路營業前景不容樂觀。根據調查,現湖南進口貨品以綢布、呢絨等為大宗,商號多從上海、漢口采辦,由滬至漢每件(約四五百斤)運價約7元;由漢口(小輪運)至長沙或湘潭,每件(約四五百斤)約2.2元。其余洋貨什物,亦多由上海、漢口走水路到湘。湖南之出口貨物,以谷米和桐油為大宗,除谷米特定由火車運粵外,其余運銷省外者,均走水路。湘省之經濟狀況,雖然目前尚不發達,但已有逐漸發展之勢。況且湘省農礦物產豐富,將來發展,不可限量。鐵路宜乘時而起,盡量吸收湘省貨物運輸,以促進本路營業之發展。
本次調查的結論認為,“湘潭為最重要之商區,萬不宜放棄;醴陵瓷器、鞭爆大可發展,物產亦豐,宜助其改進推銷;衡陽時移世易,已失商業之重心,工業亦難發展,宜從緩圖也。”[90]為此,粵漢鐵路應制定如下策略以促進其貨運業務之發展:
(一)修筑湘潭支線,或自辦輪渡接駁,只收一道裝卸費,不另收輪渡費,則湘潭貨物,自可由鐵路運輸。
(二)淥口站從速建筑貨倉,以吸收醴陵、江西貨運。
(三)環繞株洲站附近,廣購地畝,以備將來建筑大規模貨倉;浙贛、湘黔兩路全線通車之后,貨物往南北運輸者,當以此為轉運中心。
(四)建筑衡陽粵漢碼頭,裝卸貨場,以便貨物由該碼頭裝卸。粵漢碼頭原為粵漢鐵路運輸材料而設,惟衡陽貨商因由衡陽站裝卸貨運至對河上岸,每件(約50公斤)連卸費、月臺費、上河費、過江費等合計約需二角九分;若由粵漢碼頭裝卸,每件只需一角二分,是以商人多愿由該站裝卸。惟碼頭對于裝卸貨物,極為不便,該碼頭月臺太短太狹,每次只可靠車四輛,且不能搭板裝卸,以致卸貨時,每將貨物由車上擲下,破壞不堪;又因每次靠車太少,以致貨物不能從速裝卸,而按照站章,延遲起卸者,又須繳延卸費。在此種情形之下,應從速修改月臺建筑裝卸場,以利商人,在貨場未完成以前,為體恤商艱計,貨物到站,確因月臺不能靠車,以致延遲起卸者,準予免收延卸費。
(五)代醴陵瓷商向廣州瓷莊聯絡接洽,開辟新市場,以資繁榮。醴陵瓷器,不下景鎮瓷,較潮州瓷為佳。現廣州銷潮州瓷器甚多,但潮瓷不及醴瓷之佳,價亦不相上下。各窯本有向外開辟新市場之意,唯以固守一隅,無從聯絡。若粵漢鐵路設法代為聯絡,則醴瓷銷路自廣,而粵漢鐵路貨運亦無形中增加矣。[91]
本文作者之所以非常重視湘潭,是因為湘潭原為湘中重心,水運極為便利,為湘省米、藥材之最大交易中心,粵漢鐵路和相關公路的開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交通的便利程度。著眼于吸收湘潭集散之巨量貨物,因此本文作者建議盡快修建湘潭支線。而醴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醴陵本身物產豐富,加之能夠轉運部分贛西之貨物,是以作者亦建議在淥口增建貨倉,囤積貨物,以擴大粵漢鐵路貨物來源。
1937年1、2兩個月,廖仲蘅調查了粵漢鐵路株韶段沿線農產品的產銷情況。這次調查,據其自述,他對湖南的株洲、淥口、衡山、衡陽、郴州和廣東的樂昌、韶關等地,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不敢說把每個隔角都看到了,但至少對于我們所要求得問題,得到了一個初步的解答。”[92]調查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經濟凋敝,欲改變農村的這種狀況,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交通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那么鐵路、公路、水運哪種交通起的作用更大呢?這并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每種交通方式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鐵路經過的農村,究竟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粵漢鐵路全線通車之后,政治上固然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時經過的農村受影響最大的當然要算農產物了。”
廖仲蘅選擇了粵漢鐵路株韶段幾個相對重要的地方進行了調查,它們分別是:湖南的株洲、醴陵的淥口、衡陽、衡山、郴州等,此外還有廣東的樂昌和韶關等地。廖氏主要調查了上述各地的農田面積、農產的種類(主要有稻米、薯芋、雜糧、豆類、湘蓮等)及產量、農產的價格及運銷等有關情況,其重點則在農產的運銷方面,因為這正是鐵路部門需要特別關心的地方。從調查來看,株韶沿線的物產,以稻谷為最大宗,各地自用之外,尚有不少盈余可供輸出;而其他農產如薯芋、小麥、棉花、豆類、湘蓮等項均居于次要地位,各縣自用之外,剩余并不多,因此輸出量相對有限。谷米之輸出,北可至長沙、武昌、漢口等地,南可至韶關、廣州等地;其他農產之輸出,薯芋北可至長沙、漢口等地,小麥下至湖北,上至廣西,豆類可至湘潭、長沙等地,棉花自用者多,外銷較少,苧麻可至長沙,瓜子可至長沙、漢口,乃至上海、廣州等地。由上可見,上述各地農產,除了稻米能夠較多輸出至漢口、上海、廣州等地外,其他農產大多是在湖南省內流通。本區的交通情況,在粵漢鐵路株韶段未完成前,以水運為主,北則依賴湘江,南則憑借北江,依水位之漲落而通航河段亦不同。僅就湘江干支流水運而言,根據1933年的營業報告,湘潭之輪船,客運占六成,貨運占四成,貨運價格一般每擔每百華里約為洋元3角。衡陽之輪船公司,其貨運價目,每百華里,蔴每百斤洋元3角,蓮子每箱洋元6角,豆每袋洋元3角。較之輪船,民船通航河段更多一些,其貨運價格相對輪船要更便宜一些。粵漢鐵路已經全線開通,今后各物產之運銷是否棄水運而趨火車,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大致來看,除南北兩端有水運競爭之外,若貨物全程運輸即由鄂粵互運,以及由湘運粵,或由粵運湘,舍鐵路別無他途。這是因為,南嶺橫亙湘粵之間,湘江與北江不能匯通,故鐵路具有上述優勢。然湘、粵省內短途客貨運,以及湘鄂間客貨運,水運占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對此,鐵路部門必須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爭取。至于湘江、北江各支流,多與粵漢鐵路呈交叉形,鐵路貨物自然可以通過這些支流向各地疏散。然而,如何把這些支流運輸的貨物都匯聚鐵路上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無疑,將來粵漢鐵路車運發達之后,自然能夠擴大鐵路沿線農作物的運銷范圍,“雖不能夠挽救農村整個的厄運,但至少可以減去幾分的嚴重性。”[93]
粵漢鐵路全線開通前后,鐵路部門和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對該路沿線各地的經濟狀況進行了多次調查,撰寫了不少的調查報告,其中部分報告的內容如我們前文所述。根據上述調查內容,人們普遍對粵漢鐵路能夠有效促進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充滿了信心。雖然調查多從鐵路部門的立場出發,但也對各地的經濟建設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例如,1933年9月鐵道部株韶段沿線經濟調查隊認為,株韶段沿線各地應當改良稻米品種及其加工方法,以適應粵省人民對于稻米品質的需求;而黃秉鏞則提出,鐵路部門要主動幫助醴陵的瓷器、爆竹生產商提高他們的產品質量,以擴大其在廣東的銷量。一般來說,“鄰區之生產同,則彼此無互相需要,而貿易不生。”[94]而湘鄂粵三省在貿易上具有良好的互補性,調查均指出,湖南各種物產中,米為最大輸出品,輸出量較多的還有煤、礦砂、桐油、瓷器、茶葉、爆竹等,其他各種農產品、手工業品等輸出量各有不同。同時,粵鹽、糖、煤油、煙草、日用品等各種產品則是湖南需要大量輸入的。粵漢鐵路對于上述各種大宗物產均應制定合適的價格和運輸程序,以爭取盡可能多的貨源。從前湖南所產和所需之產品多從漢口、上海進出,而較少從廣州香港進出,因為南嶺之阻隔,限制了貨品從省(廣州)港(香港)進出的規模,如今粵漢鐵路全線通車,這就為湖南物產的對外輸出和外地產品的輸入開辟了一條新的通道,有利于湖南的對外交流,對于湖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將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各種調查均認為,水運是粵漢鐵路最大的競爭對手,為此鐵路部門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對策,甚至認為哪怕是虧本也要從水運奪取部分貨物運輸。但是,人們也認識到,水運與鐵路雖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也存在著良好合作的可能。湘江、北江各支流多與粵漢鐵路呈正交形,完全可以將其看作是鐵路的支線而加以充分的利用,實現水運與車運的良性循環。一般來說,粵漢鐵路南北兩端確實面臨著水運的激烈競爭,但貨物的全程運輸即鄂粵之互運,湘粵之互運,鐵路運輸實為最佳選擇,水運不能競爭。但是,湘、粵省內的短途運輸,湘鄂間的運輸,水運顯然占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對此,鐵路部門必須認真研究應對。事實上,鐵路與水運乃至公路運輸之間,應盡可能“分工合作,各盡其在經濟地理上的特殊機能,如此交際通,民生遂,富強增進,莫要于是。”[95]
總而言之,對湖南境內粵漢鐵路沿線的經濟調查,對于鐵路部門掌握湖南鐵路沿線地區的經濟狀況,并依據這種經濟狀況制定相應的運輸政策,對于鐵路企業的經濟效益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鐵路是實業之母”,鐵路部門在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對于鐵路沿線城鎮與鄉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將會起到很大的帶動作用。
注釋:
① 知我:《粵漢鐵路完成與中國交通之重要》,《郵協月刊》1937年第5卷第1期。
② 林朝杰:《粵漢鐵路完成與四省特產經濟關系》,《新生路月刊》1937年第4期。
③ 請分別參見拙文《地方利益與粵漢鐵路湖南段之走向》,《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粵漢鐵路株韶段建設三題》,《社會科學動態》2018年第11期;《粵漢鐵路與晚清湖南政治變遷》,《中州學刊》2018年第7期;《粵漢鐵路與近代區域經濟社會變遷》,《河北學刊》2018年第5期;《鐵路社團與民國粵漢鐵路之續建》,《學術研究》2018年第9期;《粵漢鐵路與湘米銷粵》,《貴州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等等。
④ 參見劉統畏主編:《鐵路修建史料(1876—1949)》 (第1集),中國鐵道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頁。
⑤ 《完成粵漢鐵路進行程序》,《廣東建設公報》1928年第3卷第2期。
⑥ 凌鴻勛:《株韶段完工與所得筑路之教訓》,《交大季刊》1936年第22期。
⑦ 于治民:《舊中國鐵路分布及國有鐵路選線原則》,《民國春秋》1993年第1期。
⑧⑨? 參見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 (第2冊),中華書局 1963年版,第438、915、438頁。
⑩ 比如,20世紀30年代,粵漢鐵路株韶段在建設過程中,坪石至樂昌段,若穿過大瑤山,線路最近,但工程極為浩大,最后決定放棄這一線路,改走他線,雖然線路延長11.6公里,但工程難度卻大大降低。參見于治民:《舊中國鐵路分布及國有鐵路選線原則》,《民國春秋》1993年第1期。
? 王輝、劉沖、顏色:《清末民初鐵路建設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經濟學報》2014年第3期。
???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31《長沙陳右帥來電》,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749、749、749頁。
??? 汪叔子、張求會編: 《陳寶箴集》 (下冊),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606、1606、1606頁。
? 羅國瑞(1860—?),字岳生。廣東博羅人。1872年赴美留學,為我國第一批赴美留學幼童之一。肄業于美國倫斯利亞工程專門大學堂。歸國后,曾參加過京漢、粵漢、滇桂等各鐵路勘測工作。歷任江南海關道、署洋務差總管,安南兩廣勘界事宜專管,湖廣大冶鐵路、津浦鐵路南段總局總辦,郵傳部路務議員、交通部技正、技監等職。參見張熊、劉興洲主編:《羅氏源流》,廣東南雄珠璣巷后裔聯誼會、南雄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年刊印,第166頁。
?? 朱從兵:《張之洞與粵漢鐵路——鐵路與近代社會力量的成長》,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9、93頁。
? 今屬湖南省岳陽縣。
? 邁,英文Mile(英里) 音譯。1英里=1.6公里。
? 今屬湖南省湘潭市。
? 今屬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白石渡鎮,白石渡位于湘粵交界處。
? 今屬湖南省株洲市。
? 折嶺是湘粵古道(郴州段)即騾馬古地道勢最高、地形最陡峭的一段,是古今交通要道的一個重要節點。過去的折嶺是一個繁華熱鬧之地,非常具有傳奇色彩,流傳的民間故事很多。湘粵古道連接湖南與廣東兩省,南起廣東省韶關市樂昌市坪石鎮水牛灣,北至湖南省郴州市郴州裕后街。其中湖南境內部分南起宜章縣南關街三星橋,也稱“九十里大道”或“騾馬古道”。這條湘粵古道在上海興起之前一直是嶺南聯系湖南及中原的重要陸路通道。陳寶箴說:“通商以前,兩廣往來商貨,由宜章、湘潭以達漢口,故湖南商務最盛。今則悉從廣東航海,自上海溯江上行。……粵鹽逾嶺行銷,郴、桂地形峻險,小民徒行負販崎嶇山谷之間,以求微利。”參見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 (上冊),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60頁。
? 王爾敏、吳倫霓霞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下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625—626頁。
?《粵漢鐵路借款合同續約》第二款載:“經總工程司測勘,武昌至廣州繞經三水740英里,萍鄉枝路66英里,岳州枝路25英里,湘潭枝路9英里,避車旁路78英里,即共計918英里”。參見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 (第2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12頁。按,《交通史·路政編》所載《美國合興公司粵漢鐵路借款合同》中岳州枝路為35英里。參見國民政府交通部、鐵路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交通史·路政編》(第14冊),國民政府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1935年版,第6頁。多數文獻岳州枝路均記載為25英里,故《交通史·路政編》記載有誤。
? 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 (中冊),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205頁。
? “湘”,原文如此,疑當為“渾”。
? 政協萍鄉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萍鄉文史資料》1984年第2輯,第95頁。
? 沈云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記錄:《凌鴻勛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頁。
? “粵”,原文如此,當為“湘”。
? 顧家相:《籌辦萍鄉鐵路公牘》附刻《萍醴鐵路始末》,曾偉:《〈籌辦萍鄉鐵路公牘〉整理與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03頁。
?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 (第5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3頁。
? 張之洞:《湘路商辦窒礙難行,應定為官督商辦,并舉總理、協理折》 (1907年1月11日),載周正云輯校:《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選編》,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573—579頁。
? 該年12月張祖同死,以魏允恭調補。
?[59][62][65][66][71][73] 宓汝成編: 《中華民國鐵 路史 資料(1912—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06、107—108、17、17、19、20 頁。
?? 譚人鳳:《憶克強先生》,載郭漢民、楊鵬程主編:《湖南辛亥革命史料》 (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1—52頁。
? 譚人鳳:《石牌叟詞》,載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頁。
? 葉公綽:《對于粵漢鐵路完成之感想》,載楊裕芬等編:《粵漢鐵路株韶段通車紀念刊》,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1936年刊行,第7頁。
? 關賡麟:《痛定思痛之粵漢路》,載楊裕芬等編:《粵漢鐵路株韶段通車紀念刊》,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1936年刊行,第14—15頁。
? 羅永紹:《譚石屏先生事略》 (1936年),載郭漢民、楊鵬程主編:《湖南辛亥革命史料》 (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頁。
? 譚人鳳《石牌叟詞》亦言及此事,曰:“委常某某清查舊時購地”,參見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頁。
? 譚人鳳《石牌叟詞》亦言及此事,曰:“委一流氓畢某某為總辦”,參見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頁。
? 陳雨聲:《粵漢鐵路建設史略》,《鐵道半月刊》1936年第9期。
??[51][54] 譚人鳳: 《粵漢路事說帖》, 《民立報》1912年7月8—9日,載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3、61、55—56頁。
[52] 譚人鳳:《致全湘父老兄弟書》,《民立報》1912年7月6、8日,載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頁。關于湘路公司籌集股款之數額,有多種說法,何智能綜合各家說法,認為湘路公司所籌款項的數額如下:1911年6月,為4663128兩(6521857元);1911年9月,為 4913745兩 (7125375元);1913年 9月,為9113880元。當時銀與銀元的比價大致為1∶0.715。參見何智能:《湖南保路運動研究(1904—1911)》,湖南師范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1頁。
[53][58] 譚人鳳:《致全湘父老兄弟書》,《民立報》1912年7月6、8日,載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2頁。
[55]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19《派查湖南湖北路工暨股捐情形折》 (宣統二年九月,1910年10月),載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3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498頁。
[56]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77《寄武昌瑞華帥成都王采帥廣州張堅帥長沙楊俊帥》 (宣統三年五月初四日,即1911年4月31日),載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3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643頁。
[57] 譚人鳳:《致湘路股東書》,《民立報》1912年7月8日,載石芳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頁。
[60]《川粵漢借款又有小爭執》,《申報》1913年3月8日。
[61] 參見武恭忠:《粵漢鐵路修建始末》,載武漢地方志編篡委員會辦公室編:《春蘭秋菊集〈武漢春秋〉二十年文存》,武漢出版社2003年版,第692頁。
[63] 辛亥革命后,湘路公司總理余肇康因病難以任事,湖南都督譚延闿遂委陳文瑋擔任總辦。湘路股東隨即組織湘路促進會,召開全體股東會,推舉陳文瑋為總理,龍璋、文斐為協理。參見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1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 (第二次修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頁。
[64]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通鑒》 (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8頁。
[67] 1913年2月3日,袁世凱任命岑春煊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以代黃興,岑與袁原本是政敵,之所以接受任命,其原因是“蓋鐵路財源既富,督辦可借護路之名寄以軍令;袁以岑繼黃,可緩和國民黨之反感;而岑更思乘機重整軍力,雙方均有所圖謀。岑原計以率往福建之衛隊1000人及將龍濟光部6000人自廣西北調為基本隊伍;不意正調動問,袁即用種種方法,不使此一兵力集中,反使趨于分散,岑始知為袁所玩弄,憤而返滬,而倒袁之意又復加甚。”參見吳相湘:《民國政治人物》,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頁。
[68][69] 《湖南粵漢鐵路公司代表陳文瑋傅定祥呈請交通部根據前清原案辦理文》,《交通叢報》1913年第4期。
[70] 《郵傳部、度支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奏折》 (宣統三年五月,1911年6月),載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 (第3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247頁。
[72] 參見國民政府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交通史·路政編》 (第14冊),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1935年版,第178頁;風崗及門弟子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上),上海書店影印1946年版,第146頁。
[74][75] 參見宓汝成:《中華民國鐵路史資料(1912—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頁。注:本著更為便于觀察起見,此表相對于原表有一定調整。
[76] 參見國民政府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交通史·路政編》 (第10冊),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1935年版,第64頁。
[77] 張茂鵬:《梁士詒》,載楊大辛主編:《北洋政府總統與總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頁。
[78] 風崗及門弟子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上),上海書店影印1946年版,第147頁。
[79] 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下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3頁。
[80] 徐吉謙、陳學武主編、任福田、嚴寶杰主審:《交通工程總論》 (第4版),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36—137頁。
[81][82] 《鐵道部訓令》 (業字第1917號,1936年5月21日),《湘鄂鐵路旬刊》1936年第136期。
[83] 《指定各營業區人員調查沿線經濟情況》,《粵漢月刊》1937年第1卷第1、2期。
[84] 譚沛霖講、高振華記:《鐵路沿線經濟調查之功用及方法》,《經濟學報》1934年第3期。
[85] 國民政府鐵道部:《粵漢鐵路株韶段經濟調查報告書》,鐵道部業務司調查科1934年刊行,“商業”,第K3—K4頁。
[86] 國民政府鐵道部:《粵漢鐵路株韶段經濟調查報告書》,鐵道部業務司調查科1934年刊行。
[87] 參見《粵漢路員工抗敵后援會積極進行各項工作》,《大公報》 (長沙) 1937年8月21日。
[88][89] 范廣練:《湖南醴陵縣屬產煤狀況與粵漢鐵路之關系》,《鐵路雜志》1935年第1卷第2期。
[90][91] 黃秉鏞:《衡陽區所屬城鎮調查報告書》,《粵漢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
[92] 廖仲衡:《粵漢鐵路株韶段沿線之地價問題》,《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03頁。
[93] 廖仲蘅:《株韶段沿線農產物及其運銷概況》,《粵漢月刊》1937年第1卷第3期。
[94][95] 孫宕越:《粵北與贛南湘南之交通與運輸》,《地理學報》1937年第4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