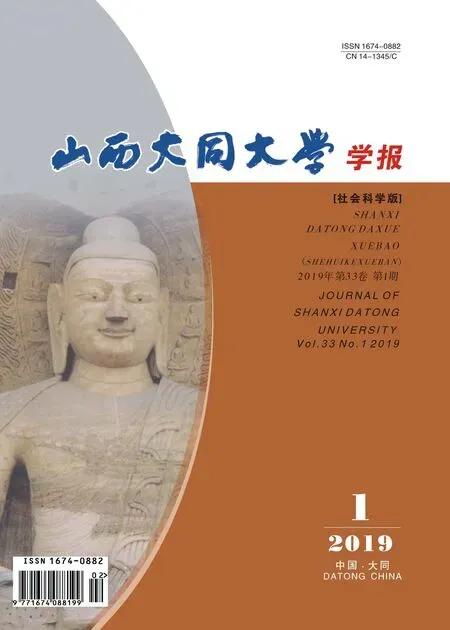秦漢弭災制度淺析
王利霞,王秀玲
(1.大同市博物館,山西 大同037009;2.山西大同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山西 大同037009)
弭災制度的發生、發展及運用是在宗教迷信色彩的外衣下進行的,古人對自然界的變化及其現象缺乏理解和認識,認為災異的發生是各種神靈的警戒及發怒的表現,因此,消弭災禍往往要通過祭祀、祈禱神靈、罪責自己等形式來解決。隨著這一社會意識的不斷發展和歷代統治階層的運作,逐步形成了體系化的消災、弭災制度。然而,單純的弭災救災制度并不能完全起到實際的消災、減災效應。尤其是遇到那些致使農業歉收、經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等嚴重威脅國家統治秩序、社會安寧、經濟發展的重大災異,必須輔之以實際的經濟救災手段,即傳統意義上的賑災、減災制度。
一、弭災制度
弭災即是消弭災禍之意。早在農業起源之時,我國的弭災思想已經形成,當時,人們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缺乏理解與認識,將各種災異的發生歸咎于天威。春秋時著名的思想家子產就曾指出:山川是遭致水旱癘疫等災異之神,日月星辰是遭致風霜雨雪災害之神。[1](P1220)《呂氏春秋》一書中認為如果政令不合時宜,國家動亂,官員腐敗,定會引起自然災害,即所謂的“怪異在變,風雨不適,四時易節,日月星云異態,動植物畸形”等現象。[2](P72)
秦漢時期,受天人感應論的影響,弭災思想盛行。西漢初期學者陸賈就說:惡政產生惡氣,惡氣產生惡災異,蝮蟲(古傳說中的一種毒蛇)等有害物,都是隨氣而生。……于是上天就降臨災變。[3](P15-16)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不僅提出“獨尊儒術”一霸天下的思想,而且糅和儒家、黃老、巫術、方術等思想,使天人感應論更上一層。他認為災是上天對惡政的譴責(災指大災,非常態的災),異是天威的體現(異指小災),因此,君王應節約、省罰、減賦、任賢、遵法等,否則就會有災異降臨。以后歷代統治者繼承了這一思想,并以此作為救災、弭災的理論基礎。
弭災制度具有極強的神秘性,是我國先民與自然界各種災異進行博弈的結果。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災異天譴論”與“陰陽五行災異觀”產生了,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弭災救災系統,秦漢亦如此。主要有帝王自譴祈禱,更改年號、策免三公(宰相),大赦、錄囚等制度。
(一)帝王自譴與祈禱 自秦漢以來,帝王自譴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弭災形式。漢儒及陰陽家認為:每次災異的發生,皆是由帝王過失導致,假若帝王認識到自己的過錯,自然否極泰來。因此,當災異發生以后,帝王通常要反省自己的為政過失。《大戴禮·盛德》指出:疫情、自然災害都與統治者的德行相關,為王者有盛德,則“人民不疾,六畜無疫,五谷不災”,如果天子未能秉承天意,以天道治國家,而導致災異,上天就會降災異于人間,以使君主反省。[4]
帝王自譴通常是要用某些特定意蘊的方式來表現,一般來說主要有下詔書、素服、避正殿等。皇帝通常以此作為與天進行溝通的途徑,來告慰天的警示,回應上天的譴責,懺悔自己未能“身其位,謀其責”,進而以消弭災禍,減輕災異。兩漢時期帝王對災后自責尤為重視,自譴詔計多達30余次。尤其是皇宮或廟宇發生火災以及地震以后,帝王無不以素服、避正殿的方式來自譴回應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如武帝建武六年春,遼東高廟發生火災,未過多時,高園便殿又起大火,皇上為此下詔素服五日。[5](卷6,P159)
祈禱制度作為中國災害史的重要環節,在弭災救災的體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有關祈禱救災的行為在商周以前就出現,以后逐漸流傳下來,成為我國古代社會消災、弭災以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主要方式。
古書中關于祈禱的對象及方式等都有所記載。《左傳》就提到,關于祈禱對象主要有:天帝、龍王以及山川等,一般祭天求雨者被稱之為“雩”,因祭祀時有舞者、有器樂,故又被稱謂“舞雩”。“雩祀”通常有兩種祭祀形式:一是在夏四月,當倉龍、角亢二宿出現時舉行,以求上天普降雨露,物產豐登;二是當旱災降臨后進行的祈雨形式,一般沒有固定的時間,遇旱則雩。[6]其次,對山川的祭祀與祈禱稱之為“望祭”,這種祭祀多在帝王和諸王侯中進行,祭祀的制度及相關禮儀都有嚴格的規定及約束。《禮記·王制》中說:“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也”,[7](篇五)說明只有一國的天子有祭祀天下名山名川的權利,諸侯則只能在其統治區域內舉行望祭。
秦漢時期,對祈禱非常重視,政府專設主管祈禱祭祀的衙門。秦時稱奉常,漢景帝中六年改成太常,其具體職責是掌管禮儀祭祀。太常下設祝官,其職責便是為國家祈禱以消災禍,正如蔡邕《獨斷》卷上云:“大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順風年也。年祝,求永負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策祝,遠罪病也。”[8]由于我國古代旱災較多,祈雨往往會比其他祭祀祈禱顯得更為重要。為了表達祈雨的真誠,除了派遣使者到各地主持祈禱外,皇帝有時會親自祈雨,《后漢書》中記載:建武三年(27年),洛陽遭遇旱災,光武帝親自到洛陽城南郊求雨。[9](卷1上,P2)
祈禱作為我國古代最常用的一種弭災活動形式,不只在上層社會出現,帝王以下的階層即士、農、工、商等,一旦發生災荒,都會進行不同程度的祈禱。但其在意義、規格、形式上都有本質的差別,與帝王相關的祈禱牽涉到的機構要多,規格要大,其意義也更廣泛。雖然祈禱祭祀實質上并不會給救災帶來任何的實際作用,但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科學技術不發達,人們無力應對災害的前提下,對于當時的統治者及人民而言,祈禱祭祀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救災救荒措施。
(二)更改年號、策免三公 前文所述,若災荒發生,通常會被認為與統治者的執政有密切關系,于是帝王便會竭盡全力地“彌補過失”,更改年號便是其中的一種。在漢代之前,紀年沒有固定或特殊的名稱,至漢武帝立“建元”以后,年號的設定遂成定制。表1是作者查閱相關資料整理出來的,與其他朝代相比,漢代“因災改元”的次數較多,尤其是兩漢后期表現的更為突出。

表1漢代“因災改元”表

(據侯外廬《秦漢社會的研究》中“兩漢改元表”統計)
漢代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改元次數,這與當時流行的極具迷信色彩的“災異天譴論”有關。統治集團認為,年號的設置代表了君主的行政意圖,這一君王行為與天道和人事的發展密切相關,是君王承擔消災、減災的一種方式。然而這種沒有實質意義的行為,不僅沒能真正阻止災害的發生或是削弱災異的危害,而且為處理政事帶來了諸多麻煩。因而,自兩漢以后,因災異改變年號的事例逐漸減少,唐高宗有過“咸亨”和“通乾”兩個年號,清太宗有天聰、崇德兩個年號,其他帝王皆使用一個年號。
秦漢時期,尤其是西漢早期,陰陽迷信大行其道,天災的發生皆是統治者不作為的結果,帝王被賦予了處理災異等陰陽之氣的功能,當遇到不愿承擔責任的皇帝,宰相就成為了燮理人間陰陽之氣的主要人物,并通過免職的懲罰以代替皇帝受過。因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10](卷57,P2061-2062)
據史料記載,西漢后期,多位宰相因災被皇帝罷免。《漢書·薛宣傳》記載,薛宣為丞相六年,漢成帝以“朕既不明,變異數見,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以人至相食,盜賊并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5](卷83,P3393)為理由,將其罷免。《漢書·孔光傳》中記載,孔光先為御史大夫,后任丞相,漢哀帝以其“卒無忠言嘉謀……百姓饑饉,而百官群職曠廢……盜賊并起”[5](卷81,P3362)等原因,遂將其罷免。
此后,伴隨著秦漢以后宰相權力機構及政治體制的各種變革,因災策免三公(宰相)制度不斷發生變化,加之,策免三公并沒有減弱或消除災異,因此,魏晉南北朝以后,隨著三公權力微弱,因災策免三公以推卸災異責任的制度逐漸被廢止。
(三)大赦與錄囚制度 當災異爆發后,統治者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心,往往會采取一些取信于民的政策。因此,大赦與錄囚便成了安撫人心的重要舉措。
早在先秦時,統治者以法治國,刑罰嚴酷,名目繁多。當時的有識之士認為,倘若懲罰過重,冤案太多,民間冤氣就加重,從而遭致各種災禍以警示統治者。《管子·王輔》指出,“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11](篇十)的寬政寬刑思想,同時《管子·入國》中記載,因饑荒嚴重,流民以及死傷者人數眾多,于是“弛刑罰,赦有罪。”[11](篇五十四《)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法,陶公派長子賄賂楚王寵臣莊生,莊生見楚王,假托天上的星象顯示有兇兆,要求楚王實行仁政,楚王決定大赦。[10](卷41,P1754)以上可見,先秦時期,大赦儼然成為統治者禳弭災異的手段。
漢代秉承先秦時期的災異之赦,赦免次數增加。“災異之赦幾乎占了整個漢朝赦免總數的三分之一”。[12《]漢書》卷八《宣帝紀》記載,“本始四年(前70年)夏,郡國發生地震,致使山崩民困。于是,皇帝下詔大赦天下”。[5](卷8,P239)漢元帝初元二年(前48年),發生地震,致使民“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憫之……無出租賦、赦天下”。[5](卷9,P281)
不是所有的罪種都可以享有赦免的權力。《后漢書》卷六《順帝紀》載,“陽嘉三年(134年),春夏連旱,寇賊橫行……帝下詔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宜得赦者,皆赦除之”。[9](卷6,P264)即犯有謀反大罪的不在赦免之列。總體而言,秦漢時期的赦免較為寬泛,極易讓罪行嚴重者脫刑,從而為社會不安定埋下隱患。故此后歷代王朝,對大赦都有較為嚴格的規定。
錄囚又稱慮囚,是指對監獄在押犯進行重新審核,查究錯案,以平天怒。西周時期就有省視監獄的制度。《禮記·月令》中就寫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13]西漢建立以后,吸收儒家的慎罰思想,建立錄囚制度,規定:“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9](P3617)東漢繼承了前朝的錄囚政策,且次數更多,其目的也從單純的仁政轉向平衡陰陽二氣。《后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載:“元和二年,大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認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9](卷46,P1550)
以上可知,因災慮囚,雖然于弭災之禍無益,但在因災異之禍使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下,慮囚可清理冤獄,改善獄政,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此外,厭勝、減膳等手段也在當時被當做一種輔助措施運用到國家祈求消災避難的活動中。
在秦漢甚至是以后的歷朝歷代,當災異發生后,統治者皆會或多或少的采取迷信、宗教色彩式的手段以求得救災、消災的成功,所謂“寧使國家多費帑金,斷不可令閭閻一夫失所”,然這些政治性的救災措施皆屬上層統治集團的精神救贖。在巨大災難面前,求助神靈,利用詭異之說難以做出實際的救災、減災成效。
二、弭災制度影響
弭災救荒儀式的舉行對統治者而言,其作用不僅僅是用來禳弭災禍,更能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這也是弭災之所以盛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沒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消災減災制度之前,這種與自然界博弈的消災形式占據重要地位。秦漢以后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消災、減災制度的不斷健全,弭災的作用顯得不甚重要。總體而言,弭災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社會,鼓舞了人心,但其負面影響遠遠勝于它所帶來的積極效果。
(一)延誤救災時機 從上述可知,秦漢統治者舉行的祈弭形式,尤其是盛大的祈禱活動,往往會延誤抗災、救災時機,無法組織災民進行積極的救災活動,使眾多的本該挽回的物質財富因延誤時機而喪失。歷代王朝后期,往往會出現政治秩序混亂、貪官污吏橫行的局面,天災人禍不斷,社會經濟也遭致嚴重破壞。越是社會不安定時,自然災害越多,政府的弭災活動亦多。
我國古代自然災害頻發,尤以旱災居多,因此祭祀、求雨制度為歷朝所盛行。然而祈雨的禮俗、禮儀非常的繁瑣,一般來說祈雨所需時間少則三天多則十天或者更長,同時祈雨還伴隨著宗教的繁瑣細節。因此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愚弄和欺騙了災民,更重要的是它不利于政府組織災民進行積極地抗旱。然而在當時社會認識水平低下,迷信活動盛行的年代里,祈雨卻成為了一種社會行為,得到了社會中大多數人的認同。每遇饑饉、旱災,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下層的貧苦大眾都要進行不同形式、規格的祈禱祭祀儀式。這種行為不僅對災民無益,也同樣玩弄了國家的各級政府官員。所以在全社會都熱衷于祈雨的背景下,很難有人會去組織抗旱、救災工作,因此祈禱儀式不僅沒有給救災帶來實際的社會效應,反而延誤了救災抗災的良好時機,使災害更為嚴重化。
(二)耗費錢財物資 不論是祭祀或是祈禱,其費用一般都較高,這給廣大百姓造成了極大的負擔。據河北省元氏縣出土的東漢三公山石碑記載,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該地連日干旱,縣令命廷掾(縣令的屬吏)帶著酒脯等祭品去祭山求雨,此后不久,天降大雨。于是每逢農忙需雨季節,定時要為祭祀提供貢獻酒脯和圭璧(古代祭祀、朝會用玉器),這似乎變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致使該縣上下不堪重負,縣令不得不請示皇恩,將該山列入祀典,由朝廷出資祭山,以減輕該縣負擔。
地方淫祠也是古代弭災場所的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的存在耗費了當地人民無數的錢財。據《后漢書》記載,會稽地區歷來多有淫祀,常用來做卜筮之用。每逢災異之時,巫祝常借此機斂收錢財,百姓敢怒不敢言,常散盡家財給祠廟以祭慰鬼神,從而致使百姓生活困苦。隨著淫祠不斷增多和斂財手法的增加,其行為嚴重影響到百姓的生產生活,于是,許多有識官員提出搗壞淫祠的建議,并實施了一系列舉措。
(三)赦免錄囚之不足 如前文所述,大赦與錄囚制度雖然不能真正弭除災害,但在某些統治集團的暴政之下,不乏眾多含冤入獄的百姓,大赦或錄囚似乎成為了他們的福音。然而災異之赦,倘若沒有調查犯罪輕重緣由,都將之赦免,無疑會使真正的罪犯漏網,使其輕易逃脫懲罰,難以彰顯社會公正,也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西漢時,有些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災異赦免存在的這些問題,經學家匡衡就提出:每逢大赦之后,奸盜者仍屢見不鮮,屢教不改,有些罪者今日赦后,明日再犯,頻繁入獄,這是因為“殆導之未得其務也”。[5](卷81,P3333)因此,大赦之制又被認為是縱惡的措施,過度的實行大赦,不但會使政治混亂、吏治腐敗,而且嚴重威脅到社會秩序及百姓生活。據史料記載,東漢時,河內有名曰張成者善于用風角占卜,并用此推斷出皇帝要實行大赦,便教唆其子殺人。河南尹李膺下令抓捕了張成之子,恰遇皇帝大興赦免。李膺為民除害、剛正不阿,違令殺了張成的兒子。《后漢書》記載,周紆任勃海太守之職時,每遇赦令后,都閉門不出,遣使臣到各縣盡快處決罪者,而后在公布詔書。這是不少有良知的官員反抗大赦之誤的舉措,然而這僅是杯水車薪,眾多的犯罪者依然在大赦的外衣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總體而言,弭災制度并不能減弱災異的危害,也不能消除災異,相反,各種自然災異的發生、發展不受弭災活動的影響,弭災活動的實行與災異是否消除亦不存在任何關聯。盡管有時弭災活動實行后,災害消除了,但這僅是巧合而已,更多的情況是弭災活動實行后,災害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因此,弭災制度的實行對社會所產生的效應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