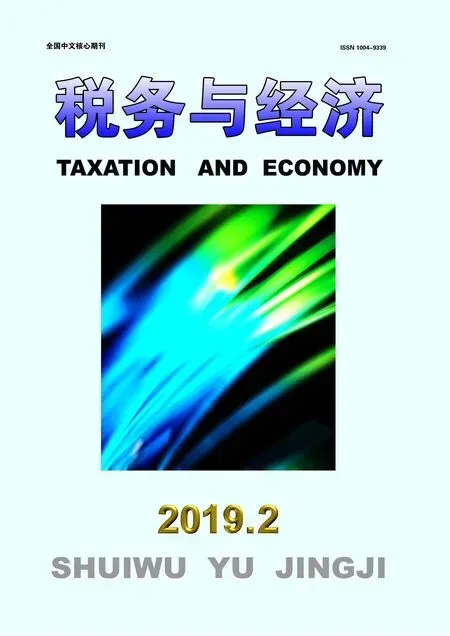農村金融扶貧效果分析
——基于我國26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陳 欽,林秋斌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 財金學院, 福建 福州 350202)
一、引 言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要強化涉農資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農村金融的創新和改革,進一步增強金融資金支持的精準意識和績效觀念。扶貧脫困是實現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按照2010年新確定的貧困標準測算,2010年我國共有16 567萬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17.2%; 2015年底共有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5.7%。金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脫貧致富需要農村金融的支持。所謂金融精準扶貧,是指以金融機構為主體,貧困對象為客體,通過提供適合貧困對象生產生活的特色信貸、保險支持等金融服務產品,滿足其資金需求,以提高他們的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脫貧致富的目的。因此,金融精準扶貧是扶貧工作從“輸血式”向“造血式”轉變的關鍵,在幫助農民脫困致富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為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創建綠色農村等舉措注入核心資本,在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近年來農村金融市場在逐步發展,但改革的關鍵在于供給體系是否優化、扶貧效率是否提高。為此,本文選取2010~2015年的相關指標數據,對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和農民脫貧成效的關系展開研究。通過探討如何精準使用金融支農資金,使之與我國目前經濟水平相匹配,從而實現支農政策的預期效果,可為政府和金融機構服務“三農”、探究金融精準扶貧模式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金融扶貧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早。該理論的研究源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納克斯(1966)曾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指出由于低收入導致的低儲蓄、低購買、低投資等會導致低產出,低產出進一步導致更低收入,如此反復,將陷入惡性循環,必將阻礙一國經濟發展。因此,不發達國家要想走出貧困、發展經濟,就需要注入資金、加大投資、增加國民儲蓄,從而促進資本形成。在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為農戶提供的小額信貸、保險等金融創新服務,有效地緩解了當地的貧困狀況。[1]Patrick (1966)認為在現代經濟持續增長之前金融發展會刺激實體投資創新;隨著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供給推動力會越來越弱,需求追隨現象逐漸呈現。因此,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會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2]Acaravci 等(2009)基于24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人均GDP的實際增長與銀行部門提供的國內信貸是相互作用的,因此金融發展可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可緩解貧困。[3]
自習近平主席提出精準扶貧的政策目標以來,精準扶貧的路徑探索成為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重要課題。農村金融扶貧問題也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相關的文獻研究逐漸增多。關于金融發展該如何支持農民增收,國內眾多學者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對策建議,為政府制定服務“三農”政策提供了參考依據。賈晉和肖建(2017)認為,農村金融發展的創新模式“資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從農村內部解決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有效提高農村家庭收入和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4]王成利(2018)指出,農民收入的提高與金融資源的多少有著極為顯著的正向關系,但是如果農民擁有的社會資源較少,則金融資源對農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效應會大大減弱。[5]
一些學者通過實證方法研究金融支持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分析金融扶貧的成效。申云和彭小兵(2016)基于大樣本農戶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和傾向得分倍差匹配法對減貧效應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產業鏈式融資對農戶的收入提高效果較好,而商業性金融機構融資模式對貧困戶的收入提高效果并不明顯。[6]章貴軍和歐陽敏華(2018)根據江西省貧困村縣的樣本數據,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等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政策性金融扶持有利于農民家庭收入改善,具體的政策性金融扶持項目包括教育發展扶貧、易地搬遷扶貧等。[7]
還有部分學者研究貧困地區的金融扶貧模式,在總結扶貧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洪曉成(2016)認為金融扶貧事業在制度建設上仍然存在問題,因此需要構建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扶貧體系,設立農村金融風險補償機制,完善金融扶貧產權制度以及大力發展農村互聯網金融等。[8]張驍(2018)以青海省貧困地區為研究對象,金融扶貧為切入點,結合恩施州的實際情況,通過探討該地區金融扶貧實踐成效,提出完善金融風險、加強金融體系協調配合和融智扶智等創新金融扶貧的新思路。[9]
現有文獻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基礎。但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在變量選取過程中,大多文獻只選取與金融發展相關的指標作為自變量,而較少使用控制變量。實際上,有很多因素會影響農民收入,因此在實證過程中是否選取以及如何選取合適的控制變量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本文的創新及擬解決的問題有:其一,使用“農業科技投入”這一新的指標作為控制變量,與金融發展指標、農村勞動力轉移指標共同構成技術、資本、勞動三種投入要素,研究這三種要素如何影響農民收入,從而使模型更具全面性和實用性,得出的結論更加符合實際。其二,在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對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和農民脫貧成效的關系展開研究,找出存在的問題并探尋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民脫貧致富的有效路徑。
三、理論模型與方法
(一)變量選取與理論依據
生產函數理論認為,資本、勞動、技術是影響產出的三大投入要素。本文選取的資本要素為農村金融發展的規模與效率,勞動要素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技術要素為農業技術的人力與資金投入,產出指標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以及貧困發生率,以此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
1.因變量。其一,農民收入指標(LnY)。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來衡量。考慮到價格因素的影響,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收入統一調整為2010年的價格水平,以真實反映農民的收入水平和實際購買力。綜合考慮數據的可比性及經濟學意義,對這一變量數據取對數形式。其二,貧困發生率指標(P)。用每年農村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貧困發生率可以反映當前我國農村的整體貧困程度。
2.自變量。其一,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FS)。根據Goldsmith的金融發展理論,金融資產總量占GDP的比值為金融相關率。由于我國農村金融以存貸款業務為主,金融表現方式比較單一,趙洪丹(2011)[10]和張宏彥等(2013)[11]選用農村存貸款之和占農村GDP的比重作為衡量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綜合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農村存貸款之和占同期農村GDP的比值代表這一指標:其數值越大,說明農村金融對服務“三農”發展的貢獻度越大。其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FE)。簡單地說,效率即產出與投入之比;金融發展效率就是貸款與存款的比值,這一指標反映金融機構對資金的配置效率。本文選用農村貸存比率表示農村金融機構對“三農”發展的支持力度:該數值越大,表示農村存款的有效利用率越高。這一指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農村資金的外流程度,其數值越小,說明農村存款用于非農領域的比重越大,即資金外流程度越嚴重。
3.控制變量。其一,農村勞動力轉移指標(LT)。用非農產業的就業人口數與農村勞動力的比重表示。這一指標反映了農村生產發展水平,比重越大表明城鎮化程度越高,農村就業結構也越好。其二,農業技術人員投入指標(AT)與經費投入指標(R&D)。科技投入主要指支持科技活動開展的人力和財力投入。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占總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與R&D經費投入強度反映農業科技投入的狀況。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實證研究的樣本區間為2010~2015年,變量LnY選用的數據來自各省的2016年統計年鑒;變量P選用的數據來自《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2016》;變量AT和R&D選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1~2016);變量FS和FE選用的數據來自《中國金融年鑒》(2011~2016)。由于《中國金融年鑒》沒有統計與北京、上海、天津、重慶、西藏相關的農村金融數據,因此,實證分析基于我國26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構建
在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中,資本、勞動、技術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三種主要因素,其方程式可表示為:
Q=f(K,L,A)
(1)
其中,Q為產出,K、L、A分別為資本、勞動、技術投入變量。基于此方程,本文將因變量即農民人均純收入(LnY)和貧困發生率(P)視為產出;將自變量即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S)與效率(FE)視為資本要素;將控制變量即農村勞動力轉移(LT)視為勞動要素;將農業技術人員占比(AT)與R&D經費投入強度(R&D)視為技術要素。從而,反映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農村減貧關系的生產函數為:
LnY=f(FS,FE,LT,AT,R&D)
(2)
P=f(FS,FE,LT,AT,R&D)
(3)
由于本文收集的是面板數據,因此將選用面板數據模型建立方程:
LnYit=α0i+α1iFSit+α2iFEit+α3iLTit+α4iATit+α5iR&Dit+μit
(4)
Pit=β0i+β1iFSit+β2iFEit+β3iLTit+β4iATit+β5iR&Dit+εit
(5)
其中,i=1,2……26,表示截面數即研究的26個省份;t=2010,2011……2015,表示時間長度即研究的6個年份。LnYit和Pit表示被解釋變量在對應的省份i和年份t的數值;FSit,FEit,LTit,ATit,R&Dit為解釋變量在對應的省份i和年份t的數值;α0i和β0i是常數項,表示不同省份i的影響;α1i,…,α5i和β1i,…,β5i是一系列待估參數,即各要素指標對應的投入產出彈性,表示各個解釋變量對LnY和P的影響程度及方向;μit和εit是對應的省份i和年份t的隨機干擾項。
根據參數類型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分為混合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混合模型是在隨機干擾項滿足古典假定的情況下,對于不同的i和t,模型的常數項和解釋變量的系數均不變,可認為是普通的回歸模型。變截距模型則意味著存在個體或時點效應,因此模型的截距項不同,但解釋變量的系數不變;根據影響方式的不同,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可通過豪斯曼檢驗進行選擇。變系數模型意味著模型結構發生了變化,因此解釋變量的截距項和系數都可能改變。
四、模型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面板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在進行回歸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判斷各變量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以確定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面板單位根檢驗的方法有多種,本文綜合選用LLS、IPS、ADF-Fisher和PP-Fisher共四種檢驗方法,利用Eviews9.0軟件對LnY、P、FS、FE、LT、AT和R&D七個變量數值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 1.檢驗形式表示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后階數;2.*表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3.滯后階數是根據SIC準則確定的。
LLC為面板數據的同根檢驗方法,IPS、ADF-Fisher和PP-Fisher為不同根檢驗方法,不包含截距項的檢驗形式不包含IPS方法。如表2所示,原序列LnY和P均拒絕了四種檢驗方法的原假設,即認為是平穩的;原序列FS、FE和AT也通過了LLC、ADF-Fisher和PP-Fisher的平穩性檢驗。原序列LT未通過IPS的檢驗,但通過了其余三種檢驗;原序列R&D未通過IPS和ADF-Fisher的檢驗,但通過了LLC和PP-Fisher的檢驗。根據單位根檢驗的判斷原則,如果通過了至少兩種方法的平穩性檢驗,則可認為序列是平穩的,因此認為原序列LT和R&D是平穩的。綜上,LnY、P、FS、FE、LT、AT和R&D這七個變量都是平穩的。
(二)面板協整檢驗
由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這些變量原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變量之間很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Kao檢驗方法判斷因變量LnY、P分別與五個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Kao面板協整檢驗結果
Kao檢驗的原假設是不存在協整關系。由檢驗結果可知,LnY與FS、FE、LT、AT、R&D的檢驗P值為0.0260,在5%水平上拒絕原假設;P與FS、FE、LT、AT、R&D的檢驗P值為0.0000,在1%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認為各指標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接下來使用的計量方法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其結果應當是相對有效和精確的。
(三)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的實證分析
由于實證區間為2010~2015年,只有6年的數據,因此不宜使用變系數模型。樣本為26個省份的數據,基本覆蓋了總體的所有單位,定性分析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比較合適,但定量分析還需通過統計檢驗確定使用何種模型。首先使用Eviews9.0軟件分別得到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的不同模型效應的估計結果
注:系數括號中的數值為穩健標準誤;***、**、*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根據表4的計量估計結果,混合模型的可決系數(R2)為51.48%,解釋能力一般。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可決系數(R2)為99.28%和96.90%,擬合優度很高,模型解釋能力較強。同時,三種模型的F統計量顯著,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也大部分顯著,因此本文選取的解釋變量有效且不需要剔除。需通過統計檢驗確定使用何種模型,Chow檢驗方法的原假設是接受混合模型;Hausman檢驗的原假設是接受隨機效應,備擇假設是接受固定效應。本文先利用Chow檢驗方法對樣本截面和時點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拒絕使用混合回歸模型。而后利用Hausman檢驗方法對樣本截面和時點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拒絕原假設,即應當選定的模型為變截距固定效應模型。最終得到該模型的具體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的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
注: ***、**、*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首先,分析金融發展規模(FS)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由表5可知,金融發展規模擴大1%,農民收入提高0.0284%。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國家逐步加強對三農建設的金融支持,多元化的農村金融產品可以為廣大農村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活躍的金融市場有利于滿足農民多元化的融資需求,更有助于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創造更多的產業增加值。值得注意的是,該系數值很小,說明當前農村金融支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
其次,分析金融發展效率(FE)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金融效率每提高1%,農民收入增加0.0448%。隨著農村金融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信貸制度愈加完善,農民更易于獲得信貸資金從事經濟活動,有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村貸款余額為98 040億元,2015年農村貸款余額達到216 055億元,短短五年增長了120.37%,年均增長率達17.12%。金融支農力度的加大,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顯著增長。
再次,分析農村勞動力轉移(LT)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農村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增加會促進農民增收,究其原因,現代化機械的普及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使得多余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其他行業;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農民的就業結構得以改善,促進了其收入的增加。
最后,分析科技投入(AT和R&D)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對于農業科技專業人員比重增加會抑制農民增收的檢驗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從2010~2015年,農業技術人員在全部技術人員中的比重變化并不明顯,因此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尚未發揮出來。分析R&D經費投入強度對農民收入的正效應可知,R&D經費投入強度提高1%,農民收入增加5.5072%。這一變量對農民增收的貢獻最大,說明加大R&D經費投入對于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四)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村減貧關系的實證分析
在計量經濟學中,Tobit回歸模型因其因變量的連續性觀測值受到某種限制,所得的觀測值無法反映總體的實際狀態,又稱為受限因變量模型。由于本文以農村貧困發生率作為因變量,其取值范圍介于0和1之間,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將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和不一致。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建立回歸方程,其左右兩邊的審查值分別設為0和1,模型基本形式為:

(6)


表6 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村減貧的Tobit回歸結果
注: ***、**分別表示在1%、5%的水平上顯著。
如表6所示,除農業技術人員占比(AT)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余變量均在1%或5%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這些因素對緩解農村貧困有比較明顯的作用。
金融發展規模(FS)和效率(FE)與農村貧困發生率負相關,說明金融發展對緩解貧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我國連續多年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支農支出,表現為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和效率的提高。隨著政策的支持和金融支農力度的加大,支農資金從低效率的地區流向高配置的地區,農民收入得到顯著增長,貧困人口也在逐漸減少。
農村勞動力轉移(LT)與農村貧困發生率負相關,說明農民就業結構的改善對緩解貧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LT是反映農村生產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該數值越大說明農村城鎮化程度越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越高,農村就業結構也就越好。隨著農村就業結構的改善,農民收入增加,貧困發生率也就減少了。R&D經費投入強度(R&D)與農村貧困發生率負相關,說明農業科技投入的增加對緩解貧困發揮了積極作用。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農業技術的支持,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有利于幫助農戶增加經營產出,進而擺脫貧困,逐步走向富裕。
五、結 論
本文基于2010~2015年中國26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在單位根檢驗、Kao協整檢驗的基礎上分別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和Tobit回歸模型,研究農村金融支持與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一方面隨著金融發展規模擴大,農民收入顯著增加,貧困發生率隨之顯著減少;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利用效率的提高,農民收入也顯著增加,貧困發生率同樣顯著減少。同時,隨著政策的支持和金融支農力度的加大,支農資金從低效率的地區流向高配置的地區,農民收入得到顯著增長,貧困人口也在逐漸減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金融服務“三農”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就控制變量而言,農民就業結構的改善和R&D經費投入強度提高均積極促進了農民收入增加,其中研發經費的投入對農民增收和減貧的貢獻更為顯著,說明加大科研經費投入,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上述研究為當前精準扶貧戰略深入實施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和參考價值。為了提高精準扶貧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工作:一是進一步發展普惠金融,增加信貸產品,擴大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普及農村金融知識;二是加強金融產品創新,不斷優化金融服務,提高金融發展效率,鼓勵農戶克服不愿或不敢向正規金融機構借貸的心理障礙,引導農戶積極主動尋求商業銀行信貸服務;三是不斷拓展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渠道,打造農村居民增收平臺,將互聯網和非農就業相結合,最大限度使扶貧資源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優化和集成作用;四是加快創新精準扶貧的渠道和手段,全力推進科教興農戰略,強化農村貧困地區農業科技人員的技能培訓,提高農業科研技術人員素質,提高貧困地區農業科技造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