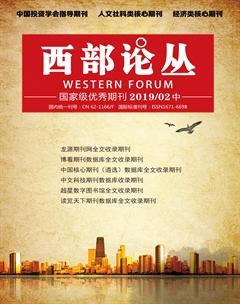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未遂
段雄 邱林明
摘 要:現如今,國際販毒事件頻繁出現,毒品日益泛濫,毒品犯罪行為屢見不鮮,已然成為了威脅社會穩定的毒瘤,加強毒品犯罪的懲治已經刻不容緩。運輸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一種,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我國較晚,尤其是關于其既遂與未遂的界定依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基于此,本研究結合所學專業知識,對運輸毒品罪既、未遂界定標準提出了自己的幾點拙見,僅供參考。
關鍵詞:運輸毒品罪 既遂 未遂
在高額報酬的引誘下,各種犯罪行為頻繁出現,其中運輸毒品的行為尤為猖獗。因運輸毒品罪隱蔽性特征明顯,且較為復雜多樣,關于這一方面的刑事法律法規卻十分抽象,司法審判中關于運輸毒品罪的行為認定較為困難,標準不一。追蹤溯源,關于該罪的未遂與既遂相關界定標準不明確所引起的,案件審判股破產中法律適用問題尤為常見。基于此,對運輸毒品罪的未、既遂界定標準進行統一,有利于更好地打擊運輸毒品的行為,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基本案情
2018年3月11日,嫌疑人田某伙同嫌疑人蹇某駕駛川A*****棕色別克轎車(嫌疑人田某所有)到C市“龍潭寺”附近購買冰毒。由嫌疑人蹇某出資,嫌疑人田某聯系上家“眼鏡”向其購買50克冰毒之后,后又以同樣的方式再次向“眼鏡”購買了50克冰毒以及20顆麻古。隨后二人攜帶購買的毒品駕車從C市上高速公路返回S縣,途徑某高速公路Y縣收費站時自覺異常。于是嫌疑人蹇某便在高速公路出口前攜帶一黃色塑料袋下車步行,嫌疑人田某獨自駕車通過收費站。偵查民警發現嫌疑人蹇某下車后便秘密將其抓捕,在收費站路口將嫌疑人田某抓獲,并從嫌疑人蹇某身上搜出一小袋白色晶體可疑物,從嫌疑人田某身上搜出一小袋白色晶體可疑物及一小袋紅色片劑可疑物。后經嫌疑人田某、蹇某指認,蹇某在抓捕過程中扔在地上的黃色塑料袋內的兩袋白色晶體可疑物就是二人在C市購買的100克冰毒。
二、爭議焦點:運輸毒品能否認定未遂?
第一種觀點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否,應以毒品是否起運為標準,而不是以毒品是否運達目的地來判斷。第二種觀點是只要毒品進入運輸途中,不論在任何階段都是既遂。由于行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起運,則是未遂或則預備。第三種觀點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否,應以是否到達目的地為標準,由于行為人意志力以外的原因沒有到達目的地,屬于未遂,到達目的地的屬于既遂。
筆者認同第三種觀點,毒品是否被運達目的地為犯罪既、未遂的界定。到達目的地后即使由于某種原因而將毒品運回原地或則其他地方也是犯罪既遂。人民法院出版社的刑法典案和刑法配套規定《新釋新解》均認同第二種觀點。
本案二嫌疑人欲將毒品從C市運往S縣,目的地為S縣,途徑Y縣被擋獲,屬于為未遂的情節。通常理解的運輸是一個過程,筆者認為運輸毒品是一個行為犯,行為犯是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的,而不是一起運就可以認定既遂。司法實踐中單純以運輸毒品為目的是很少的,大多伴隨販賣的行為,只是證據無法查實才以運輸毒品定罪[1]。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運輸毒品后如果不能到達目的地,無論你是販賣還是特意幫助他人運輸,都是很難流入下一個環節的,所以其危害性與運輸毒品到達指定目的地是有明顯區別的。本案S縣法院開庭審理后,認定了二被告的未遂情節。
三、運輸毒品罪既未遂的認定
結合相關理論知識,本文作者認為運輸毒品罪屬于行為犯,并不是舉動犯,其理由主要是:刑法第347條款得知,販賣、走私、運輸、制造罪屬于一個同一個罪名,只是并列四個范圍行為,其中任何一個犯罪行為都能夠單獨成罪,也可同其他罪名并列成一個罪。我國現有法律,一般將運輸毒品同販賣、走私毒品并列,并屬于同一個檔次的法定刑,其危害性也一樣。綜上,本文作者認為販賣、走私毒品罪是行為犯,并不是舉動犯。因此,運輸毒品罪也是行為犯,并不是舉動犯,換言之,運輸毒品罪的社會危害性相比于走私、販賣毒品的更重。對于該罪名的立法而言,為了嚴厲打擊這一行為,應將該罪名的既遂標準前移。司法實踐活動中,一些法院以“起運說”作為運輸毒品行為的判定標準。然而,本研究認為行為犯既遂的標準是這一犯罪行為已經完成,運輸毒品罪既遂的標準理應是運輸行為的完成,則是將毒品運輸到目的地。因此,本文作者主張采用“目的說”的判定標準。如果“起運說”作為運輸毒品犯罪行為既遂的標準,那么行為人一旦開始運輸,則既遂,這便是舉動犯,并不存在既遂的說法。在毒品運輸罪中,根據犯罪情節來判定未遂與既遂,全部將其定為既遂,量刑方面則會出現罪行不適應的情況[2]。分析運輸毒品罪的整個犯罪過程,其是行為人先協商運輸目的地及路線,然后接收毒品進行運輸,采取運輸方式將毒品運輸到目的地并交付毒品。行為人將毒品從甲地運輸到乙地,必然是一定距離的運輸,并不用短距離轉移。
若距離較短,例如在同一個城區進行轉移,則不是我們說講到的運輸,而是轉移毒品的過程。剛剛起運毒品同犯罪分子接受到毒品后,運輸到某一個指定的地點的犯罪情節差別較大。起運前被查獲,對于社會危害的較低。毒品運輸到目的地被查獲,其社會危害性較大。如果毒品運輸到目的地,運輸行為完成,毒品被販賣,這一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如果將毒品已然交付給其他犯罪分子,其社會危害性可想而知。所以,行為人準備運輸,但是起運責備查獲的情形同運輸到目的地被查獲的情況,其社會危害性明顯不同。這種不同則是刑法意義上犯罪形態的實質上的去唄,則是未遂與既遂的區分。如果將“起運說”作為既遂的標準,這明顯是沒有認識到毒品運輸的不同階段社會危害性不同,這必然會激勵讓犯罪分子徹底完成毒品運輸行為,這同我國立法的初衷向完全相違背。
四、結語
綜上所述,運輸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重要的罪名,基于我國現行法律,毒品犯罪不管是多少數量,一律嚴格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然而,在處罰這一行為時,應對其犯罪形態(既遂及未遂)進行準確界定,從而公平、公正進行處理。因此,我們可以結合本案例,嚴格區分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未遂,保證司法審判的公平與公正。
參考文獻
[1] 王躍.對運輸毒品案未遂問題的若干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機關黨校學報,2016(04):77-79.
[2] 劉凌梅.運輸毒品罪司法適用爭議問題探討[J].法律適用,2015(07):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