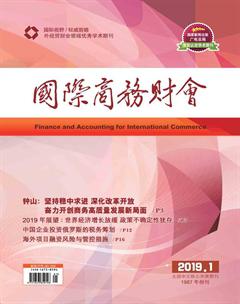金融資源配置與普惠金融
張迎新 李存剛 李焰
【摘要】構建普惠金融體系,建立最優金融結構,實現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發展。本文基于金融結構的視角探討實現金融普惠化的市場化配置機制,研究指出放寬市場準入、政府謹慎介入零售市場和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是實現金融普惠化的市場化路徑。
【關鍵字】資源配置;普惠金融;金融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2.1;F830.2;F015
一、引言
好的金融應該惠及所有具有金融需求的社會群體,以幫助其成長,最終實現共同發展,構建好的社會(羅伯特·希勒,2012)。特別是小微企業、農戶等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地區等也應該享受到應有的金融服務,不應該被排斥。現實并非如此,融資難與融資貴是我國小微企業、農戶和落后地區等面臨的普遍問題,成為其發展的瓶頸。
以小微企業為例,它們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維持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截止到2017年年底,我國小微企業數量占全國企業數量的99%,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吸納就業人口1.5億,解決新增就業和再就業的80%以上,納稅占國家稅收總額的50%以上1。經濟增速回調的新常態下,小微企業的突出貢獻更顯難能可貴。與此極不相稱的是,2017全年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0.74萬億元,僅占企業貸款余額的24.67%。除融資難以外,融資貴也是小微企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委托貸款、民間融資、小額貸款公司,信托租賃和融資租賃等,這些渠道的融資成本都比較高。根據2014年對江蘇常州市41家小微企業的調查2,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的平均年利率為8.3%,高于同期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2.1個百分點;另據遼寧銀監會的一項測算,小微企業銀行融資成本年化利率是12.75%。黃金老(2013)指出,委托貸款的利率大約在10%左右,信托融資和租賃融資的利率大概在10%~14%。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與研究中心與匯付天下共同發布的中國小微企業發展報告2014(簡要版)指出有息民間借款利率平均為18.1%。趙昌文 (2015)對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利率的測算結果為20%~27%。
廣義貨幣量(M2)高位運行的宏觀背景下,貢獻突出的小微企業卻面臨如此融資困局,這種局面長期維持下去,必然會導致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及貧富分化等各種社會問題。這顯然不是好的金融,無助于構建好的社會。問題出在哪里?金融資源配置是理解問題的一把鑰匙。
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動員儲蓄和配置資金。有效的配置應該使稀缺的金融資源流向回報最高的產業或企業,為下期積累更多的儲蓄,同時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也最小。然而,小微企業的貸款回報率遠遠高于上市公司和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是上市公司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2.4倍,信貸資源理應流向小微企業,但現實反其道而行之。不僅僅是小微企業,“三農”領域和落后貧困地區等也都存在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不同程度地受到現有金融體系的排斥,這正是普惠金融所關注的。本文以金融結構為視角考察如何通過市場化配置機制實現金融普惠化。
二、金融資源配置的中國事實
按照林毅夫等(2009、2012)金融資源配置要實現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相適的觀點可以幫助理解中國金融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事實。建國后的經濟發展初期,根據要素的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理論,在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豐裕的條件下,本應該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政府為了實施趕超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所需投資規模大且回收期長,按照林毅夫等(2009、2012)的觀點,大銀行和發達的證券市場才能滿足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金融需求,而當時這樣的金融體系還沒有形成。資本稀缺和儲蓄分散的背景下,政府通過干預措施,如價格控制(利率和匯率限制)、嚴格地準入制度等,提高資本的動員能力,以極低的利率迅速籌集資本。低利率反過來刺激了投資需求,有限的資本供給無法滿足,于是政府通過“信貸配給”解決供求矛盾。這個過程中,政府主導的銀行扮演了以低利率供給資本的職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漸進式轉軌,再加上對金融發展路徑的依賴,我國的金融結構是銀行或者間接融資依然為金融體系的核心,直接融資規模并不大。我國的直接融資占比低于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進一步地,在銀行體系中,大銀行是主體,小銀行微不足道。規模較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了銀行總貸款的很大比例,即大銀行支配了大部分信貸資源。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市場化改革力度的加強,大量的小微企業涌現,日益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角。但是,中國的小微企業獲得貸款的比例遠低于新興經濟體中的其他國家。同時,整個銀行體系中大銀行支配著大多數的信貸資源,而大銀行的主要貸款投向是大中型企業。這說明金融體系對小微企業資金供給不足,對大企業資金供給過度,表現為金融資源的錯配,這種錯配是由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匹配所致,即大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和大量小微企業居于重要地位的經濟結構不相匹配。
依據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相匹配的觀點,小銀行應該成為當前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滿足大量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因為小銀行為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相比大銀行具有比較優勢。
大銀行和小銀行各自的比較優勢在于他們提供金融服務存在系統性差異。首先,對分散風險的要求不同。小銀行資產規模較小,無法提供大額資金,因為要為眾多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才能分散風險。其次,信息處理能力不同。大銀行往往是多重層級組織且具有多重委托代理關系,信息收集者往往不是信貸決策者,對其收集個人品質等軟信息激勵不足,故大銀行的貸款決策更多地依賴公開披露的財務狀況等硬信息,恰恰大企業具有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等硬信息。小銀行組織結構扁平化、簡單化,信息生產者往往是貸款的決策者,有動力獲取小企業的軟信息,且只能依據軟信息為小企業服務,沒有硬信息可用(Pertersen ,2004;Stein ,2002)。因此,從克服信息不對稱能力來講,大銀行具有為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比較優勢,小銀行則有為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比較優勢。最后,成本差異。大銀行給大企業的貸款同樣數額用來給多個小企業貸款成本會加大。
綜上所述,銀行業存在基于規模的專業分工,大銀行應該為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小銀行應該給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這說明大銀行出于經營的經濟性考慮,缺乏為小企業提供服務的經濟上的動力機制。個別大銀行提供小微金融業務僅僅是對政府倡導3的迎合和履行社會責任的考慮。當前的大量小微企業,沒有與之對應的眾多小銀行為其提供金融服務,即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小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普惠金融體系。
三、科學的金融資源配置
林毅夫等(2009、2012)以新結構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將實體經濟的結構特征納入分析框架,基于金融結構和實體經濟結構的匹配性,考察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一個國家在特定發展階段具有特定生產要素稟賦組合,要素稟賦組合決定了要素價格,最終決定了與之相適的行業結構、風險特征和企業規模。由于不同行業的企業風險特征和規模等的差異對金融需求有所不同,而金融體系內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在資金動員與配置、信息處理、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各具優勢。因此,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有特定的金融結構需求,即結構上的供求匹配。當金融結構符合當前的實體產業結構或經濟結構時,金融體系就能高效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支撐,促進經濟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此時的金融結構為最優金融結構,當金融結構偏離最優金融結構時,金融具有消極作用,無助于經濟增長,甚至具有阻礙經濟增長和降低收入等負面影響。
林毅夫等(2009、2012)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相匹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Demirguc-Kunt、Feyan和Levine(2011)運用跨國樣本數據對金融結構偏離最優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發現大的金融結構缺口和較低的經濟產出正相關。Cull & Xu(2011)給出了來自企業層面的證據,在控制了企業和國家基本特征的基礎上,用勞動增長率對銀行業發展程度和股票市場發展程度進行回歸。發現在低收入國家,銀行業的發展及發達的私人信用能夠促進勞動增長率;在高收入國家,股市的發展會促進勞動增長率的提高。
金融結構內生于經濟結構,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最優金融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偏離最優金融結構的金融體系,不是好的金融,無助于構建好的社會。科學的金融資源配置就是實現符合當時經濟結構的最優金融結構。
四、實現普惠金融的市場化配置機制
普惠金融發展的制約因素有金融資源錯配、征信體系不完善、信用風險擴大和監管體制不健全等。其中,金融資源配置錯配是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根本障礙,亟待解決。糾正金融資源錯配的核心是理順其配置的機制,唯有此,才能使金融結構內生于經濟結構的變遷,為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消除機制障礙。金融資源配置的核心機制是市場機制。
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主要是退出金融約束制度,具體地,包括放開準入限制、政府謹慎介入零售市場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等,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強化金融體系的競爭程度,充分競爭的結果是融資成本下降和金融服務的“客戶下沉”,這是金融普惠化的市場化解決路徑。
(一)放開市場準入
放開市場準入限制,可以提升金融機構供給端的競爭程度,以降低融資成本,改善金融服務水平;放開市場準入限制是利率市場化的配套改革措施,如若不然,就沒有足夠的競爭,沒有競爭的情形下,僅僅依靠利率市場化降低融資成本和糾正資源錯配會適得其反;放開準入限制,可以一定程度上使非正規金融正規化,使影子銀行體系萎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且大大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此外,消除對微型金融機構如小額信貸機構的準入限制,可以改善金融結構,提高金融體系為小微企業、農戶等弱勢企業和地區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這是實現金融普惠化的必要條件。
放開市場準入限制的具體措施如下:第一,要放寬各類資本的進入,特別是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加快民營資本進入微型金融領域,鼓勵他們發起或參與中小型銀行、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信貸機構和信用擔保公司等,不折不扣地落實國務院的“新36條”4;第二,要放寬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加入WTO后我國銀行業的改革發展已經具備了外資銀行過度沖擊的能力。此時引入外資金融機構,可以提高競爭程度,還可以引入先進的金融機構經營管理理念和風險管理技術。第三,放寬分支機構的準入。這是金融服務 “下沉” ,為基層,為大眾群體服務的必要舉措。
放開市場準入限制的同時,要加快完善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實現進入與退出的有機統一,建立優勝劣汰的良好機制。完善金融機構破產的相關立法和執法,建立科學合理的存款保險制度。金融機構是否破產僅取決于經營狀況,要切實打破社會上“國家不會讓銀行倒”的錯誤認識,提高金融需求者的風險意識,提高金融機構經營至上、服務至上的宗旨意識。
(二)政府謹慎介入零售市場
政府介入零售市場分為直接介入和間接介入。直接介入零售層是指政府通過國有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在市場的零售層次直接提供金融服務;間接介入零售層是政府通過資金批發使資金流向零售金融機構,由零售機構進一步為特殊群體提供信貸。
政府介入零售市場的初衷是為農村或者偏遠地區得不到正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信貸服務,給予其選擇信貸服務的權利,推動扶貧事業發展和促進經濟增長。但許多證據表明這種方式并不一定能實現預期效果5,CGAP(2006)分析了原因:首先,這種方式容易受到政治的影響,成為政治尋租的工具,最終獲取貸款者往往是政治關聯較強或者非貧困群體;其次,貸款者容易將其作為一種政府的饋贈,償還貸款的意識不高,導致了較低的還款率事實;最后,低利息率不能使金融機構覆蓋其成本,只有政府的持續補貼,這種方式才能可持續。然而,要想實現普惠的初衷,也不是不可能,CGAP(2006)給出了其實現預期目標的苛刻條件。總之,這種方式并不一定是一種高效且可持續的資金配置方式,政府必須謹慎使用。
(三)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直接融資比例太低的結構問題,也有助于解決銀行體系內部大銀行集中為大企業服務,小微企業等被排斥群體得不到信貸資金的結構問題。事實上,上述第一個結構問題解決有助于解決第二個結構問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一是為大企業提供便利的融資平臺,以增加替代渠道,使銀行資金更多流入中小企業等被排斥經濟部門;二是不斷完善創業板、中小企業板和新三板等融資平臺,推進轉板制度,為中等企業或者創新性企業提供融資渠道,同樣有利于銀行信貸資金下沉。三是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提升債券市場規模,同時要打破債券市場的剛性兌付,有利于降低無風險收益率,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上述放開準入限制、政府謹慎介入零售市場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各項措施要統籌安排、協同推進,才能收到良好的改革效果,否則,可能會付出比固步自封更大的代價。
(四)其它配套的改革措施
金融是整個經濟系統的子系統,金融體系內部市場化改革無不與其他經濟問題緊密聯系,故經濟系統內其他經濟改革措施的有效推進有助于金融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取得良好效果。
調整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當務之急。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房地產業和基建,其資金需求規模相當大,銀行體系內的資金難以滿足其融資需求,還需影子銀行體系內的資金來滿足。基建投資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存在預算軟約束,對融資成本不敏感。因此,上述兩大行業對小微企業融資形成了“擠出效應”,致使其融資難且融資貴。另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為了應對危機,政府出臺四萬億的刺激計劃,四萬億的投向大多是工業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如光伏產業、電解鋁、煤炭、有機玻璃、水泥、鋼鐵等諸多產業都存在產能過剩。這些產業的建設期和投資回收期都比較長,致使資金周轉速度較慢,加上投資回報率都偏低,導致資金占用水平較高,留給小微企業的資金所剩無幾。因此,調整產業政策,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但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也是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需要。具體地,要由依賴地產和基建拉動經濟增長,逐步轉變到由科技創新驅動經濟增長;還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具有高產出、低投資的現代服務業;通過“一帶一路”實施,積極消化現有過剩產能,加速資金周轉。
優化政府財稅體制和投融資體制,降低投融資的政府主導和國家壟斷程度,提高社會資本參與公共產品和服務投資的積極性。目的是為了消除城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不合格的融資需求主體,降低預算軟約束或隱性擔保,緩解其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營造公平的融資環境,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可以降低對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和隱性擔保,緩解其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可以提高國有資產的收益水平,降低信貸依賴,降低債務比重和財務風險。一是要從對企業的管理向對價值的管理轉變,促進國有資本的管理、運營和監督分離。二是國有企業要逐漸退出對競爭性產業的控股,轉變為通過參股參與競爭性產業經營,分享收益。三是提高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收益水平。
主要參考文獻:
[1]郭樹清.不改善金融結構中國經濟將沒有出路.國際經濟,2012.
[2]黃金老.壯大實業呼喚低成本融資環境.人民日報,2013年2月4日.
[3]林毅夫,徐立新,寇宏.等.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最新研究進展[J].金融監管研究,2012.
[4]林毅夫,孫希芳,姜燁.經濟發展中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初探[J].經濟研究,2009.
[5]林毅夫,姜燁.經濟結構、銀行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基于分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6.
[6]許成鋼.法律、執法與金融監管——介紹“法律的不完備性”理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1.
[7]楊再平.論我國金融體系的結構問題.管理世界,2002年第4期.
[8]焦謹璞.建設中國普惠金融體系——提供全名享受金融服務的機會和途徑,2009年11月,中國金融出版社.
[9]經濟體制改革論壇:如何根治融資貴難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2015年4月.
[10]趙昌文.從攫取到共容,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
[11]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M].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
[12]Allen F,Gale D.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M]. MIT press,2000.
[13]Beck T,Demirgü -Kunt A,Levine R.Law and finance: why does legal origin matter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 31(4):653-675.
[14]Demirguc-Kunt A,Feyen E,Levine R.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The evolving importance of banks and markets[J].World Bank, mimeo,2011.
[15]Lin,Justin Yifu,Xifang Sun,Ye Jiang.“Toward a Theory of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Mimeo,the World Bank,2011..
[16]Mc Kinnon,R .I.,1973,M 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 c Development,Washi 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7]Petersen M A.Information:Hard and soft[R]. working paper,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04.
[18]Stein J C.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J].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5): 189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