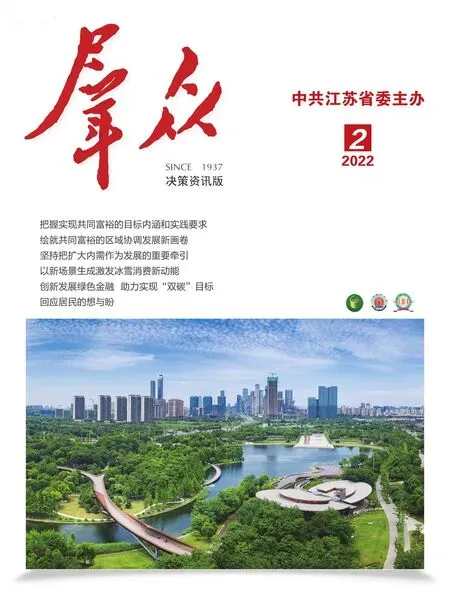重構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何雨
時間與空間共同構成了人類社會活動的二維坐標。相對于抽象的時間,空間是具體的、生動的、實踐的。實踐性構建起了空間與社會的關系,即空間是社會的空間,社會是空間的社會。與自然狀態不同,自人類有意識地利用空間起,空間就具有了社會屬性,成為人類爭奪、占有、使用與改造的對象,因此,空間是社會的空間。一切人類社會活動都必須依托于一定的空間載體,在一定的空間尺度內展開,所以說,社會是空間的社會。作為一種稀缺資源,人類社會的競爭本質上就是對空間區位的競爭,而各種社會問題的源頭也可以直接追溯到空間或區位的競爭上。
不同標準就會有不同的空間形態,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分類標準就是基于所有權關系而形成的空間形態兩分法: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私人空間是為個體私人支配、占有、使用、管理等權限的排他性空間,公共空間則是為公眾集體共同支配、占有、使用與管理的非排他性空間。改革開放40年來,包括《物權法》在內的一系列民法,在推動空間產權歸屬明確化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空間總體屬性的公有性——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城市土地國家所有,天然地限定了私人空間的有限性,也賦予了公共空間的極大彈性,換言之,在私人空間之外,公共空間是一個高度模糊化的地帶。
公共空間歸屬上的模糊性,直接導致了公共空間秩序的模糊性。公地悲劇是經濟學中的著名假說,指的是在沒有外界約束的情況下,個體會無止境地爭奪、占有、使用公共資源,最終導致公共資源崩潰。這一假設不同程度地在我國公共空間的支配、占有、使用與管理等方面上得到了印證。在農村,對集體道路、灌溉溝渠、山坡水塘等公共空間的擠占與侵蝕;在城市,違搭違建、車輛亂停亂放,以及對公共綠地、體育設施等公共空間的破壞等等,都是公地悲劇具體反映。個體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付出的卻是集體利益嚴重受損的代價,對灌溉溝渠的擠占直接影響農田的泄洪與灌溉,占有公共道路停車加劇交通擁擠,搭建違章建筑破壞小區整體環境,等等。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合法的、正當的共識性規則,個體對公共空間的占領往往奉行先占先得、拳頭為王的叢林法則,而這必然導致各種糾紛,成為社會矛盾甚至重大群體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公共空間的各種亂象,源自于作為公共空間的所有者與管理者主體的缺位與失位,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要重新明確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讓公共空間的所有者與管理者重新復位、歸位。這也是邳州在公共空間社會治理創新上的精髓與要義所在。一方面,從產權上對公共空間的歸屬進行清晰化,明確公共空間的邊界與范圍,為公共空間的集體支配、占有、使用與管理等提供法理基礎。另一方面,在堅守私有空間不受侵犯的同時,同樣堅守公共空間不得侵犯的底線。承擔公共空間日常使用與管理的職能部門要全面復位、歸位,切實維護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在此過程中,邳州創新性地賦權、賦能于“95%”的絕大多數群眾,讓他們擁有捍衛公共空間秩序正當的、充分的底氣與依據。從實踐效果看,邳州的努力改變了城鄉公共空間的形象與面貌,改善了黨群關系、官民關系、群眾關系,有效地減少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穩定與和諧。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努力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與積極支持。畢竟,人民群眾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力量來源,也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價值歸屬。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蘇高校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責任編輯: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