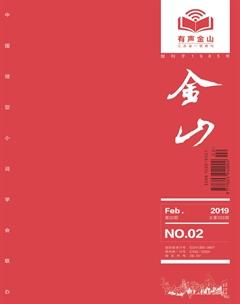父親的戰爭
鐵匠鋪
他沒有成為街面上的小混混,和百萬雄師過大江有關。雄師過了江,就是他居住的小城。小城解放一年后,輟學在家的他重新進了學校并在畢業后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可以這么說,是新政權給了他新生活。
小城解放前是他最為崩潰的一段日子。家里的腳踏車典當了,一套敲打起來熱熱鬧鬧的鑼鼓家伙典當了,典當的原因是一家老小要吃飯,典當的效果是仍然覺得沒吃飽。父母對他說,再沒閑錢了,這學不上了。這是1949年春節期間的事。他點點頭。點頭之前,他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點頭之后就成了輟學青年。先在街頭游蕩,游蕩了一陣,覺得不好意思了,就捧起一塊木板,上面放兩三盒香煙,拆散了論支賣,成了街頭小煙販。有時能賺兩文錢,有時沒生意,就捏一支叼在嘴上解悶。他的白謀職業,沒能拯救家庭的經濟危機,還讓他染上了抽煙的習慣。這個人就是我父親。
小城的軍事地位,在古詩文中顯得很牛,什么兵家必爭,一水橫陳,仿佛得了它就得了天下。其實很不相干。剛剛解放沒幾天,小城中就找不到幾個兵了。大軍過了江,都沒多看小城一眼,就急匆匆地沿著鐵路線向東奔,解放大上海去了。街上多的是布告,各種報告會,講馬克思,講蘇維埃,講新民主主義論,講從猿到人……信息大爆炸,名詞大噴發。青年人天生會被新生事物吸引,他也不會例外。他到新政權辦公的地方探頭探腦,討要入場券,坐在長椅上聽外地口音的干部演講,領取免費發放的宣傳冊。新華書店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小城一解放就有了新華書店。新華書店出售紅色書籍,這些書籍和小米加步槍共同鞏固著新政權對這座城市的占領。袖珍的開本、粗糙的紙張、不純凈的油墨,印著書名和作者。作者是生疏的,書名也不是一看就懂,這個輟學青年和紅色書籍之間明顯存在著溝壑。可是不要緊,正是這種溝壑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他開始購買這種紅色書籍閱讀。令人生疑的是,錢是哪兒弄來的?如今他已去世,沒法問了,但種種跡象表明,解放后,他的日子正在慢慢變好。
小城的政權更迭離不開那場戰爭。戰爭后,城頭上的旗幟變成了紅旗。旗變了,天變了,改朝換代了,這可不啻于一場強臺風啊,但小城好像是處在臺風眼上,風平浪靜地度過了那個非凡的解放時刻。解放軍的運兵船還在江浪中顛簸,這邊舊政權早已灰溜溜地撤走了。小城就是這樣解放的,平淡,無奇,還異常安靜,天空一顆炮彈也沒有落地,更不要說炮彈落地后轟隆一聲巨響把人炸成聾子——見慣了影視上的戰爭,會覺得小城的解放太沒有戲劇沖突。
我也覺得這不像戰爭,太不典型了吧。但這是父親的親歷,那時他十七八歲,感覺敏銳得很,我尊重他的記憶。更何況,他對戰爭并不陌生,經歷了解放戰爭,還經歷過抗日戰爭。日軍快要打到小城時,他正上著小學一年級。
戰火燒來了,往哪兒逃?好像有無數種方案。中國非常大,當時流行逃到大西南,逃到重慶去,那兒是大后方;還可以逃到昆明去,這是聞一多、沈從文的選擇,昆明有西南聯大,他們在那兒當了教授;另一個選擇是四川宜賓一個叫李莊的古鎮,寧靜純樸,梁思成、林徽因就選擇在那兒研究古代建筑;也可以學蕭紅逃往香港,學郁達夫逃往新加坡。等等,等等。輪到祖父頭上,這個問題就簡單了,不用多想,回老家,這是唯一的選擇。
逃難其實是一次特殊旅行,旅行要花錢,逃難也需要銀子做后盾,逃得越遠,花銷越大。漫漫風塵路,要買多少頓早餐、坐多少回毛驢馬車、付多少宿的歇腳客棧錢?遠走高飛式的逃,老百姓是沒法模仿的。祖父想想,要保命,只有逃回老家一條路。掏錢買船票,誰知兩岸間已經斷航,又到京口閘,租下一條運糞船,約好明天,請船主將一家老小順便捎過江去。
說到京口閘,小城人個個都知道。它是古運河上的交通樞紐,是文物遺存,是人聲嘈雜的農貿市場,其實,它還有一個重要身份,即小城糞便的集散中心。糞便這種東西,城市里產得最多,也最不受城市歡迎。哪兒需要呢?農村。過去農村種莊稼,沒有化肥這一說,都用糞肥。于是一種特別的物流系統就應運而生。這個系統的兩頭,一是拖糞車,二是運糞船。清潔工將全城各處的糞便一車車拉到京口閘,倒進一條傾斜的管道,管道的底部正好對準運糞船,一條船裝滿了,撐篙移開,另一條空船又靠上來準備裝貨。是的,糞便在這個系統中已經成為商品,船主花錢買下,販到農村,再轉賣給農民。就這么循環往復,既化解了城市的尷尬,又滿足了農耕的需求。唯一不妙的是,傾倒糞便時,污水橫流,臭氣熏天,那一帶環境不是一般的糟糕。這種情況從民國延續到解放后很多年,直到化肥興起,連農民都瞧不上糞便了,京口閘作為集散中心的漫長歷史才宣告結束。但這已是后話。民國二十六年的那一天,我的祖父急匆匆地趕到京口閘來找船。他想找條干凈些的船,小漁船、小貨船都行,但沒有,全是運糞船。戰爭好像還沒有切斷糞便的物流系統。既然沒得選擇,祖父就跑到運糞船上去打探,誰知一問嚇一跳,客輪停運后,運糞船竟也緊俏起來,這一條已有人交了定金,下一條、再下一條同樣落實了客源,慌亂地繼續詢問,總算找到一條,也不討價還價,船主說多少就是多少,還千恩萬謝的。父親哪里坐過這種船,臭哄哄的,躲也沒處躲,船一晃蕩,艙里的糞便也跟著搖,撞得船殼嘭嘭響,這時候船上最臭。坐船過江的經過,父親統統忘記了,他只記住這個細節:臭!小小孩童,懂得什么戰爭,懂得什么戰爭的野蠻與血腥,他只是憑著自己的嗅覺,將侵略戰爭和一種丑惡無比的氣味牢牢拴在了一起,刻骨銘心,終生沒忘。
輾轉回到老家,有門親戚將一間舊草房借給他們暫住。父親的依稀記憶是:一片曠野上,只有這間孤零零的小房子,周圍沒有任何人家。最可怕的是天黑之后,整夜都能聽到野狼長嚎,關上門,堵上窗,躲在被子里也害怕得要命。夜夜如此,擔驚受怕,再加上其他種種生活上的不便,熬過了一個月,祖父痛下決心,還是回家吧。
僅僅隔了一個月,小城已經成了淪陷區。小城淪陷那幾年,正好對應父親的小學階段。父親的小學軌跡是殘缺不全的。逃難前他是小學生,逃難回來他就找不到學校可上了。城內的各所學校,有的炸毀了,有的解散了,有的成了占領軍的養馬場,有的學校今天還在敲鐘上課,明天校門口就貼出告示說“奉旨”關門。這是父親經歷的第一次輟學,整整有一年時間。之后,父親開始上私塾,這家上了幾個月,又轉投另一家,連續三年,輾轉了好幾家。那些隱藏在崎嶇街巷和昏暗屋內的私塾,叫什么堂號,先生的尊姓,父親一個也沒記住。小城淪陷的第五年,父親才找到一所正規小學上四年級。
淪陷區的日常生活,父親的印象并不深刻。依稀記得的是進出城門要搜身,不帶良民證會挨打,還說鬼子兵時常出城去掃蕩,殺了人就將頭顱掛在城門上,但馬上又會補充,說并未親見。這么看來,這場侵略戰爭對這個孩子的傷害似乎輕微得很。父親和侵略者之間的距離,可以說很近,僅隔了一堵薄薄的磚墻,日本兵巡邏的皮靴聲聲聲入耳,但也可以說很遠,他忙他的大事情,我過我的小日子,彼此相處還算平安無事。日子如果始終這樣,也算是這個孩子的福氣了——可惜這畢竟是假象、是幻覺、是夢想,而夢總歸要破。起因是家中養的一條哈巴狗,叫“哈哈”。這個狗名要給滿分,因為那是個特別缺少笑聲又特別需要笑聲的年代。不論誰喊哈哈,哈哈都會站住,用那張小丑臉盯住你看。這一天,哈哈在家門口遇到兩個日本兵,不知是哪個環節上出了錯,日本兵生氣了,端著刺刀槍追哈哈,哈哈跑回家,日本兵也沖進家門,哈哈剛剛躲到床底下,就看到日本兵的四條腿堵在了床前。日本兵彎下腰,用刺刀往床下捅,沒捅幾下,狗不叫了,一只狗遇到兩條狼,完敗。日本兵將哈哈挑在槍刺上,出門,上路,一個在前,一個在后,繼續他們中斷了的巡邏任務。追殺哈哈的全過程,兩個日本兵沒講一句話,但全家人嚇得直哆嗦。父親之前從沒看過掃蕩和屠殺,這一下看到了,而且是零距離接觸,刺刀尖就在自己家里閃著寒光,床前還有哈哈的血污。所幸日本兵沒有拿人開刀。但細一想,在侵略者眼中,人并不比狗更有尊嚴,人和狗都可能成為他們的軍事目標,這一次,恰巧選中的是一條名為哈哈的哈巴狗,若是選中了人,你往哪兒逃,還不是一樣躲在床下待斃?從此,這家人再也不養狗,也不養貓。
小城光復,不當亡國奴了,但這家人的生活并未見好。上到高一,父親又輟學了。祖父說沒錢了,父親說不上了。父親一點情緒也沒鬧,甚至還有一種和祖父不謀而合的得意。
小城解放前夕,舊政權早已撤走。老百姓是不在撤走之列的,撤走的是舊衙門的大小官吏和他們的家眷。父親有一個要好的中學同學,家長在舊軍隊里當官,父親說,他也搞不懂那是個校官還是將官。他去過這個同學的家。他家窗戶上裝的玻璃,從外面看不到家里,可是在家里卻能清楚地看到窗外。那時我才上小學,他很神秘地給我講這個同學家的事,我最好奇的就是這塊玻璃,仿佛在聽神話。解放前夕,這個同學跟隨家長撤往臺灣,從此杏無音訊。在解放后的歷次運動中,父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動機,每次都會交待這個“社會關系”。我不知道父親會在材料中如何提及他和這個“關系”的關系,也許有檢舉,也許有揭發,也許有合理的想象補充和上綱上線的批判,而那塊神奇的窗玻璃一定是每份交待中必有的生動情節。有條件閱讀父親這些材料的人,會不會也對這塊玻璃感興趣?具有這種功能的玻璃叫單向透視玻璃,也叫單面鏡,現在一點不稀奇了,可若時光倒退到七十年前,這種單面鏡,有幾個人知道,又有幾個人用過?父親的這個同學住在一條巷子里。這條小巷至今猶在,似乎沒什么品質好的深宅大院,尋常巷陌中,究竟是何種人出于何種目的要在家中安裝這種玻璃,不由地讓人想入非非。
小城剛解放,父親就想投身革命。有一次是部隊文工團招考,他參加了考試卻被淘汰了,原因很可笑,他連什么叫人民民主專政也不知道。后來,他考上了師范學校。從此以后,父親就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讀書,當老師,退休,最后得了一場病。父親想病好,和病斗,但病不配合,反而斗倒了他。“打敗”“打勝”都是戰爭用語,父親親歷過戰爭,熟悉這些詞匯。可是,他的親歷其實只是旁觀,他沒打過真仗,更沒打過硬仗,偶爾遇到一次,一打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