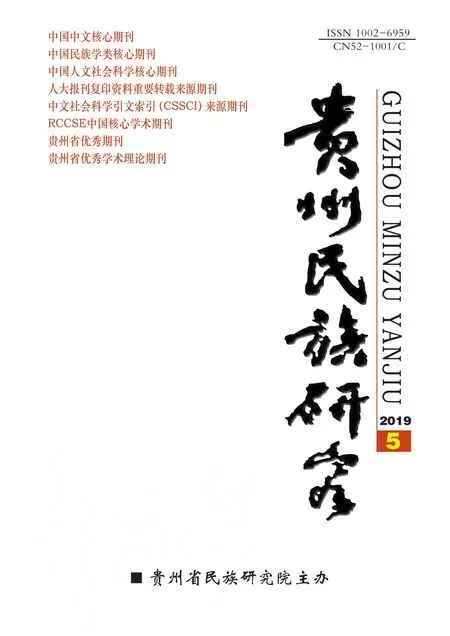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提出與保護
李德嘉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2)
我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協同發展的統一國家,古代的王朝往往通過“書同文”的文化政策語言文字的通行,進而實現社會、經濟、文化的一體化。近代以來,伴隨民族國家概念的興起,“中華民族”逐漸成為我國各民族的共識,在“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之下,近代學人提出了邊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國家通用語言教育的平衡問題,進而指出必須在推行“國語”的同時,保留邊疆固有民族語言文字的特色和習慣,使民族語言文字和國家通行語言“互相溝通、互相光輝”[1]。新中國成立以來,保護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已經成為政策制定的基本共識。堅持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的原則,提倡各民族之間相互學習語言,是我國長期關于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基本認識。“中華民族”本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產物,“多元一體”是費孝通先生對中國民族發展特點所作的總結,也基本反映了中國民族語言傳承發展的基本趨勢。“多元一體”也基本反映了中國民族語言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即中華民族的語言譜系是由中國各民族語言長期交流,共同發展所形成的,在堅持規范使用國家通行語言的同時,在少數民族地區保護發展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發展成為中國的基本語言政策[2]。
然而,在現代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出現了弱勢語言在不同程度上的退化和瀕危現象,在此基礎上,各國都提出了相應的語言保護政策。有學者指出,語言保護必須處理好民族語言與通行語言、語言的共性和個性等關系[3]。在依法治國的宏觀戰略下,以法律手段尊重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權利成為語言保護的重中之重。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了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發展和使用自由和風俗習慣自由,是語言權利的憲法規范基礎。語言的學習和教育,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區推行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教育是民族語言文字保護的重要基礎,因此,保護民族語言文字受教育的權利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所提出的民族語言教育權是指民族自治地區公民所享有的接受民族語言教育機會的權利,屬于民族語言文字權的派生性權利。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提出,不僅具有法律和政策依據,而且具有保護的緊迫性和重要意義。本文旨在通過提出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概念,突出民族語文教育權利的重要價值,并嘗試探討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基本內容和規范原則。
一、提出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民族語言文字權利屬于人權范疇,是族群或個人選擇一種或多種語言作為私人或公共領域交流工具的權利,這項權利不因語言使用范圍的廣狹、族群人數的多寡而有所區別[4]。一般認為,語言權利的權能可以概括為:學習權、使用權、傳播權和接受權。語言權利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語言群體,如訴訟法中所規定的公民有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其具體落實的權利主體往往體現為訴訟關系中的個人[5]。而就某一民族的語言文字權利而言,其主體則往往是某一語言群體。語言權利其實不限于少數民族,多數語言群體和少數語言群體均享有語言權利,但多數語言因為語言使用群體廣泛,存在使用習慣上的強大優勢,需要提出保護的往往是少數語言群體的語言權利,多數表現為少數民族的民族語言文字權。一般而言,民族語言文字權的義務主體往往是國家、政府機關或社會團體。也就是說,民族語言文字權的實現往往需要國家或政府機關從政策層面予以支持,并以國家的力量予以保障。換言之,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義務主體是國家,國家通過政府教育部門和公共教育組織積極履行組織民族語言文字教育、傳播的義務,除國家的積極義務之外,社會、組織和個人也負有尊重民族語言權利的義務。
民族語言文字權利具有積極與消極雙重面向。第一重面向是消極意義上的語言權利,是指少數人所具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國家不得否認或歧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第27條中規定了少數族裔有保留自己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權利。該公約因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而具有法律約束力。但該公約對于語言權利的定義主要是一種消極權利,即要求國家和政府不得歧視、不得干預,但并未賦予國家和政府推動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的積極義務。《公約》中的非歧視規定對于少數群體的語言權利明顯不足,因此,必須具有積極意義上的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第二重面向的權利則要求賦予國家積極推動權利保護的義務。1992年聯合國《在民族或種族、宗教和語言上屬于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第一條中就明確賦予締約國保護少數民族的存在發展及其語言、文化、宗教方面的民族特征的積極義務,并且以賦予締約國積極義務的方式在第四條第三款中要求締約國采取措施確保少數人有充分機會學習母語或在教學中使用母語。
民族語言文字權利所具有的積極面向主要依靠國家促進語言文字的教育來實現,也是民族語言文字權利得到有力保障的重要條件,因此,需要將此積極意義上的語言文字權利抽象為民族語言教育權,以突出國家對民族語言的教育、傳播所承擔的義務。
二、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基本內涵與法律保障
(一)基本內涵
民族語言教育權是指民族自治地區公民所享有的接受民族語言教育機會的權利。民族語言教育權可以分解為兩個維度的內容:一是接受民族語言的語文教育,二是接受以民族語言為媒介的公共教育。國家公共教育中的民族語言教育和使用民族語言的教育是民族語言權利保護的重要方式,只有將本民族語言成為教育媒介,公民可以使用民族語言接受各類文化、科學、藝術教育,才能保證民族語言不至于瀕危或成為使用程度極低的“文化遺產”。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權利主體是個體而非集體。過去有觀點認為,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民族語言文字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即將民族作為權利主體加以整體保護。事實上,民族是一抽象概念,既非法律上的實體,也非擬制的權利義務主體,難以作為權利主體存在。故而,長期以來《憲法》中的民族語言文字權多是一種原則性規定,在實際的立法和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出現民族自治地區“一刀切”現象,政策往往在強化通行語言和弱化通行語言之間搖擺,將民族語言的發展、使用擺在了國家通行語言的對立面。事實上,只有將民族語言教育權定義為個體權利,法律所保障的是個人接受民族語言教育的機會,法律要求國家為民族自治地區的公民提供選擇接受優良民族語言教育的機會。既然是權利,而非義務,也就賦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選擇語言教育的自由。
其次,民族語言教育權的義務主體主要是國家,國家需在公共教育體系中設置民族語言的語文教育和以民族語言為教育媒介的知識教育,為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提供接受民族語言教育的機會。除國家所承擔的積極義務外,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也負有不得干涉、歧視民族語言教育的義務,不得干涉他人自愿接受民族語言教育的權利。
最后,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內容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享有自主選擇語言教育的權利,也具有要求國家提供良好語言教育機會的權利。作為國家應該提供良好的民族語言教育機會,通過民族語言教育促進語言文化發展,實現民族語言文字的保護。但作為權利主體而言,個人則有選擇接受何種語言教育的自由。當然,語言權利不僅具有消極自由的內容,更具有積極自由的意義,個人也具有向國家主張要求接受良好民族語言教育的權利。
(二)法律保障
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法律保障措施:第一,賦予自治機關在教育使用語言上的自治權。自治機關可以根據國家的教育法律、方針政策,根據本民族自治地區的實際情況,決定在公共教育中的什么程度、什么范圍內使用民族語言。《民族區域自治法》第36條規定了民族自治機關在教育用語上的決定權。第二,保障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和少數民族語言授課。《民族區域自治法》第37條第3款和第4款規定了民族學校中間使用民族語言授課和采納少數民族課本,同時賦予各級政府扶持少數民族文字教材編譯出版的義務。第37條同時明確要求推廣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實際上是在落實民族語言教育權和推行普通話之間尋找平衡的位置。第三,堅持“民漢兼通”的民族語言教育政策,實現民族語言和國家通行語言的雙語教學,秉持“民族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交融進行”的民族語文教學觀念。
三、民族語言教育權的規范原則
(一)平衡國家通行語言教育與民族語言教育
語言不僅具有交流工具的功能,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通行的語言起到了促進民族融合,形成共同的文明記憶的文化溝通作用,是國家統一、民族共融的文化基礎。因此,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往往會推廣使用國家通行語言,以期實現民族和地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國制定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一方面以法律形式規范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使用;另一方面,保證了在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傳播和發展。就民族語言教育權的規范而言,首先應該平衡國家通行語言教育和民族語言教育,既不能厚此薄彼,忽視國家通行語言教育,也不能忽視民族語言教育,導致民族語言的傳承失序。
平衡國家通行語言教育和民族語言教育關系,需要國家對語言政策采取最小干預的立場,既不能為保護民族語言而在民族自治地方強推民族語言教育,也不能為促進民族交流著力于國家通行語言教育而自然忽視處于弱勢的民族語言教育。國家以中立姿態,在民族自治地方同時提供國家通行語言教育和民族語言教育,為公民提供選擇良好民族語言教育的機會。國家通行語言的地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在經濟交往、文化發展中往往處于優勢地位。民族語言只要有良好的教育傳承,有寬松的發展環境,也自然在民族自治地方處于重要的文化交流地位。國家的民族語言保護義務主要是為少數語言族群提供語言選擇機會,保護瀕危語言的傳承,不宜矯枉過正,忽視國家通行語言的重要價值。
(二)突出雙語教學在民族語言教育中的意義
在教學中運用民、漢雙語模式是保障民族語言自由使用和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促進民族語言發展的重要措施。生活是語言發展的源動力,如果一門語言難以適應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則勢必成為“活化石”。因此,民族語言教育中的重要環節是雙語教學,使學生能夠運用民族語言學習各科科學文化知識。少數民族語言使用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權利的真正落實,需要雙語教學實現民族語言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真正運用,有助于實現社會整合[6]。同時,雙語教學的培養目標是“民漢兼通”,在促進民族語言傳承保護的同時,兼顧國家通行語言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目前,雙語教學的開展存在發展不足的問題,其中原因有三:一是當地人對雙語教學存在認知錯誤,要么認為民族語言無用,要么不愿意學習通行語言,認為會被“同化”;二是雙語教學缺乏優良的師資和教材,師資和教材建設無法適應社會需求;三是雙語發展不平衡,雙語教學實施過程中,有重漢語輕民族語的普遍傾向,導致學生雙語發展不平衡[7]。
破解當下雙語教學中的問題,需要在民族語言教育法規政策中傾向扶持雙語教學建設發展。一是鼓勵培養雙語教學的優秀師資,選拔兼通民族語言和漢語的人才擔任雙語教學的師資;二是鼓勵編寫、出版優秀的雙語教材,組織力量翻譯、編撰優秀的民族語言教材。
(三)促進民族融合,維護國家統一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維護民族繁榮發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語言的融合交流在促進民族融合、國家統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國家統一雖然離不開通行語言的支持,但也并不意味著國家統一必然采取語言同化政策。語言生活的多樣性有助于推動多元文化的發展,也有助于促進民族的融合交流。因此,語言的多樣性對于統一多民族的國家而言同樣重要。但從另一角度而言,語言權利的發展和傳播不得有破壞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不正當目的,保護民族語言的教育、發展和傳播也并非意在阻礙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前述聯合國《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第8條第4款明確規定宣言中所提出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違背聯合國宗旨與原則的活動,特別是國家主權的平等、領土完整。宣言在序言中表明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旨在促進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四、結語
當下民族語言文字的保護與發展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在新時代民族團結發展的語境中提出民族語言教育權不僅具有法律依據而且有現實的意義。明確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基本內涵和規范原則對于解決民族語言發展中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民族語言教育權的提出也呼喚在法律層面明確民族語言教育權的內涵與規范。需要指出的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的發展體現了“多元一體”的特點。民族語言權利保護也需要堅持“多元一體”思路,民族語言教育權實質是要求國家在推行通行語言的同時,在民族自治地區提供優質的民族語言教育機會。綜上所述,在學理和法律上提出民族語言教育權有助于推動新時代和諧民族關系的構建,語言是民族融合交流的媒介,多樣化的語言生活環境有助于實現民族間的交流交融,做到語言文化方面的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實現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