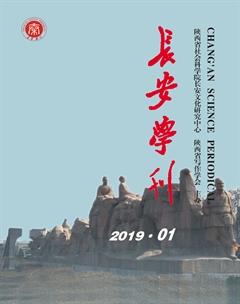淺析沈從文的《邊城》
龍曉靈
摘要:《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在這里他建構了“希臘小廟”來供奉“人性”,建立了一個美麗寧靜,平淡質樸,如詩如畫的湘西,它與世隔絕,在那里時間是靜止的,空間是被定格的,這個世界遠離歷史的長河,遠離現實世界與時代。本文旨從時間敘事、空間敘事敘述看沈從文在《邊城》如何構建一個極度凈化、理想化的“湘西”,以及在時空敘事中他如何“在想象中(這應該算是‘未來)用理想之光燭照湘西人生歷史圖景,再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1]
關鍵詞:邊城:時間敘事:空間敘事:“水”意象
文章編號: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 043 - 03
沈從文曾說:“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緒下寫成這個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寫她的意義。”這“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這個故事填補我過去生命中一點點哀樂的原因。”[2]作者要展現“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也是作者的心靈棲息地,與作者現實中現代化的世界相異。作者關注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并把《邊城》給“在那個社會里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3]作者關注人性原始、自然、健康的美,并在歷史的時空中保持人性之“常”,以此重造國民性,使國家和民族強盛起來。
一、《邊城》時間敘事
中國與西方在敘事時間上存在著差異。中國以“年月日”——以大觀小的敘事時間,在以年為單位的時間劃分體系中,季節、月、節氣、節日、日期、時辰是基本刻度,其中又以季節、節日、時辰為小說敘事最重要的時間點。古老的中國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它遵循的是天氣與自然作物成熟的時間規律。西方以“日月年”——以小觀大的敘事時間。工業革命的變革,資本主義的發展,機器為主要的生產工具,這都與以農業為主生產方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人們是按小時制來獲取勞動報酬。因此,西方以日為單位的時間劃分體系中,確立二十四小時、六十分、六十秒精準的時間,小說敘事主要為逐日敘事和精準的鐘點化敘事。
時間具有兩種形式:客觀時間和主觀時間。首先,客觀時間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改變,無論物質是在空間的運動過程中,還是在空間循環變化的先后邏輯關系和變化過程中。《邊城》以節日敘事為主要時間。邊城“最熱鬧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過年”。文中以端午作為小說的敘事時間,文章共二十一章,除去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插敘的手法描寫兩年前的兩個端午節,其余章節描寫“今年”的端午節。作者以節日、清晨、黃昏、夜晚等時間,呈現一種循環式的時間發展而非現代性不可逆轉的線性時間,增強文化性,淡化歷史性。沈從文以這種“無時間意識”的時間觀,構建一個原始化、自然化的理想的湘西,這是不僅意識上還是文化上都對現代文明的抵抗。
其次,心理時間是個體對客觀事物延續性和順序性的反映,個體主觀對時間的感知。文中描寫了祖孫二人意識的心理時間:一是爺爺的心理變化,主要是圍繞翠翠的婚事。祖父愁喜交加,把翠翠給一個人“是不是適宜于照料翠翠?……翠翠是不是愿意。”[3]但是當祖父知道唱歌是二老不是大老時,由“快樂”到“莞爾而笑”,心中明白翠翠喜歡的是二老。天保的死,二老怪罪于老船夫,此時老船夫不安、憂愁。二是翠翠的心理變化,翠翠端午節這天在順順家看龍舟的羞怯與不自在,面對儺送時“臉還發著燒不便作聲”。兩年前的端午是“甜而美”對翠翠來說。“為了不能忘記那件事,上年一個端午又同祖父到城邊河街去看了半天船,”[3]之后儺送要做渡船時“翠翠大吃一驚,同小獸物見到獵人一樣,回頭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3]描寫出翠翠歡喜、留戀、害羞和慌亂的心理變化。作者采用回憶式描寫和現實描寫呈現人物的心理變化,從而增強故事性、情節性。同時也強調了人物心理變化都最終消逝在時間里,歸于平淡,“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長長的白日下醫治好了。”[3]客觀時間的籠統性與心理時間的變化性,展現了湘西世界中人生形式的一種“常”態——在一個獨立于歷史和時代之外的“湘西”,這里人事之間的變化,沒有時代和歷史的干擾和侵蝕,是一種“原始”、“自然”的變化,終會在生活中消逝歸于“常”態。這“或許就和兩千年前屈原所見的完全一樣。”[4]
二、《邊城》空間敘事
二十世紀空間敘事受到關注,它是后結構主義經典敘事學提倡跨學科研究的方式之一。空間和時間分別為物質運動的持續性和物質存在的延展性,它們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與基本屬性。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文中說“時間維度只是敘事的表征,空間維度作為敘事維度的前提,本來就是敘事表征所內涵的維度,是使時間維度成為可能的維度”。[5]時間延展的重要性在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中可以體現出來,中國的傳統小說主要以線性時間為主,以此處理故事并形成情節來推動敘事的發展。而在近現代都市敘事中,空間敘事中空間的轉換會使時間產生停滯的敘事錯覺,空間的并置使時間產生疊合效應,空間敘事使小說的空間感增強,而時間明顯縮短以及淡化。空間敘事分為地理、心理和文學這三個空間。首先,地理空間又是客觀空間,即故事發生的地點。沈從文《邊城》以“茶峒”為大空間背景,以河街與碧溪蛆空間和祖孫與順順家庭空間這兩組為小空間背景,其中河街與碧溪蛆空間是物理空間上的并置,祖孫與順順家庭空間是抽象空間上的并置。碧溪蛆和河街這兩地理空間是湘西一部分,是故事事件的發生地,在這不僅敘述凄美動人的愛情,也呈現出山美、水美、人美的湘西風貌。《邊城》的前三章描寫了湘西蔥郁清澈的山水、水邊的白塔和河床等自然風景,以及描寫邊城中的賽龍舟、抓鴨子、唱山歌等風俗民情,呈現出邊城世界未受現代文明浸透的自然原始的生活面貌與獨特的文化品格。其次,心理空間與客觀空間不同,前者更加抽象和復雜,也是對地理空間的體驗和感受,而呈現出人物的心理變化和狀態。《邊城》中人物的心理空間呈現一種純真善良、樂觀灑脫、勇敢堅韌的形態。沈從文描寫翠翠如“小獸物”一樣乖巧、天真和活潑,“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3]同時還敘述翠翠在渡船上面對陌生人的注意的舉動“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3]的純真善良。儺送告訴天保要渡船不要碾坊的樂觀灑脫:天保不會唱歌,但是仍與二老約定唱歌,當知道翠翠喜歡儺送時,選擇下船出走的樂觀灑脫。端午節上的賽龍舟、搶鴨子,表現了邊城人的勇敢堅韌,通過人物的心理空間展現“湘西”人性的純凈化和理想化。沈從文通過地理空間和心理空間的敘述,描寫出一個淳厚質樸、寧靜明亮“湘西”,在這里呈現人性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與現實中浸透著現代文明的湘西是相異的。作者筆下的“湘西”具有雙重意義的空間,即物理空間和文學空間。文學上的“湘西”是自然明凈,喧鬧又寧靜。如碧溪蛆渡口的明凈和寧靜,河街碼頭的明亮和喧鬧,都呈現一種自然、淳樸的生活;這里“一切總永遠那么靜寂,所有人民每個日子皆在這種單純寂寞里過去。”[3]這樣的“湘西”存在于作者心中、存在于作者筆下的文學的敘事空間,是作者向往的“心靈世界”。沈從文在《邊城》中采用空間的并置和轉化,增強空間感,淡化時間和情節,以此構建一個如詩如畫的“湘西”。
三、《邊城》時空交點:“水”的意象敘事功能和象征意義
時間和空間在小說里是二者不可缺一的。“小說的空間形式必須建立在時間邏輯的基礎上,這樣才能建立起敘事的秩序:只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創造性結合,才是寫出偉大小說的條件,才是未來小說發展的康莊大道。”[5]沈從文從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建構一個極度凈化、理想化的“邊城”世界,它不存在歷史和時代中,是一個獨立存在的世外桃源。“邊城”里寧靜清明的自然環境,碧溪蛆渡口拉渡祖孫、端午節時河街的人們賽龍舟和搶鴨子,翠翠與儺送天保的愛情故事都與水有關。沈從文曾表明水對于他的重要性:“我感情流動而不凝滯,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于我有極大的關系。”[7]他用“水”來呈現自己追求的“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水”對于作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
“水”的敘事功能。“水意象是進入《邊城》深層結構的第一把鑰匙”[7],《邊城》發生的故事,都與水有關,文中明線是翠翠與老船夫和船總順順與兒子,暗線則是“水”。水“充當了一條隱形線索連結起故事始末。……串聯著邊城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7]故事情節的發展都與“水”有關,如翠翠和爺爺靠水謀生,翠翠與儺送因水而愛,天保溺水而死,儺送順水而下并不知歸期,祖父死于暴風雨之夜,翠翠獨守河邊拉渡等等。“水”展現了一個喧鬧又寧靜且如詩如畫的邊城,小河“正因為處處有奇跡,自然的大膽處與精巧處,無一處不使人神往傾心。”[3]《邊城》寫到茶峒依山的“城墻如一條長蛇,緣山爬去。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余地設碼頭,灣泊小小篷船。……貫串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著陸,一半在水,因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設有吊腳樓。”[3]“水”為邊城人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質用品,同時也塑造了邊城人的精神面貌。這里的人們依水相伴,依水謀生,他們平和、勇敢、堅韌、善良、誠實等等。如描寫漲水時人們面對“隨同山水從上流浮沉而來的有房子、牛、羊、大樹”“不拘救人救物,卻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3]作者以“水”敘寫邊城故事,以水構建“邊城”,同時也以“水”構建人性。
“水”象征意義。“水”是中國文化中一種常見并意蘊豐富的意象。在《邊城》中“水”的意象內涵不僅豐富而且的得到了升華。“水”在文學上被賦予情感化,它孕育著湘西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者表層上以水的清澈明凈、平緩寧靜描述邊城的寧靜、安詳,贊美邊城人與事的美好,而深層上詩化了邊城的自然景觀并反襯出邊城中人們的淳樸與純真,從而表現了邊城世界蘊含的品格與情操。沈從文筆下的“水”具有象征性,用“水”建構一個理想的世界和追求一種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端午節不僅是一個以水為主的節日,也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與的節日,以此圍繞水來呈現邊城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水的平和寧靜和動蕩不安,這都賦予湘西人一種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水的平和寧靜呈現出邊城人純真、質樸、包容及善良等等,如在碧溪蛆渡口拉渡的老船夫“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于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里活下去。”[3]。水的動蕩不安呈現了人勇敢、拼搏、堅韌、進取及從容等等。如端午節的賽龍舟和搶鴨子表現邊城人的精神。這種充滿活力、野性、自由的人性,來源于原始的自然。作者追求的不是現代西方文明中異化的人性和漢族封建文明三綱五常束縛人性,而是一種原始、自然、健康的“人性”。“在對‘水的愛戀中,沅水流域的風土人物升華為沈從文的理想與寄托,被賦予了由‘水所表征的至真至純的人性和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邊城也因之而呈現出理想社會圖式——一景觀明麗凈美、百姓質樸純粹、社會安定有序,一幅人性伊甸園的和美畫卷。”[7]
四、結語
從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看,沈從文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構建一個理想化的“湘西”,并呈現一種人生形式,即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健康性的人性。這表現了作者在面對現代文明的沖擊時的無奈與悲涼,以及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愁。從道德視角,呈現理想化的人性,是“為湘西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觀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來走向。”[1]《邊城》構建理想化的社會圖式是一種烏托邦,存在于沈從文的文學的時空敘事中,成為他抵抗現代文明沖擊的心靈家園。
參考文獻:
[1]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 - 1997.上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2]轉引凌宇.沈從文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 ,02
[3]沈從文.邊城[M].卓雅選編、攝影長沙:岳麓書社,2009
[4]轉引閆曉昀.《邊城》時空維度與敘事意圖[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1(06)
[5]龍迪勇.空間敘事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序2
[6]龍迪勇,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J].思想戰線,2005( 06)
[7]閆曉昀.論《邊城》的意象選擇及其敘事功能[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7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