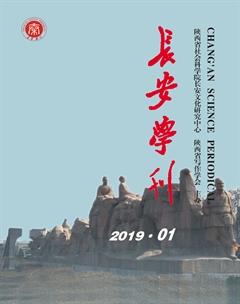凝視下的女性自我意識探究
范光華
摘要: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通過構建一個以“陳府”為代表的封建男權社會空間,表現了對女性生存境遇的人文關懷。電影本身就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鏡像反映,導演在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往往帶入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在《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影片中,無論是主人公頌蓮還是影片中的其他角色,都處在不斷的被凝視當中,作為男權社會中的女性,在被觀看、被凝視的過程中,究竟是堅守自我,還是喪失了本心?本文試做探究。
關鍵詞:凝視;女性;自我意識
文章編號:978 -7 - 80736 - 771 -0(2019)01 - 087 - 03
“凝視”原本是一個哲學概念,而后才進入心理學及視覺文化等領域,拉康將“凝視”概括為“我們通過觀看的方式與物構成聯系,隨著表征的排列,總有某個東西在滑落,在穿越,被傳送,從一個舞臺到另一個舞臺,并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困其中,這就是凝視。”[1]在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中,勞拉·穆爾維在其《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所提出的凝視理論認為電影鏡頭代表的是男性凝視的目光。女性主義將凝視理論引入精神分析理論當中,在“看與被看”中重新確認女性的主體性。凝視意味著“權利”,意味著被凝視的一方被降格為“物”的層次,也就是主體將“欲望”與“想象”投射到女性的身體當中。在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就中通過構建一個以“陳府”為代表的封建男權社會空間,探討了女性的自我主體性問題,影片中將女性視作被凝視的一方,與凝視的主體之間進行互動,以女性為切入點透析了深刻的社會問題,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作用。本文將從“凝視”的角度出發,分析《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影片中的女性在男權背景之下的自我意識問題。
一、凝視的對象——女性身體
依據拉康的觀點,女性的生理結構在整個男權社會中是以一種缺乏或被閹割的形態下進入語言和文化系統的,因為男性掌握著閹割之權,所以女性的存在就象征著父權的壓抑和威脅,而電影本身就是維護男權意識形態的文化表現,因而女性就成為了塑造男性的“客體”,變成了男性的依附品,也就是說男性在凝視女性時塑造自身的主體性,獲得滿足感,繼而使被凝視的女性成為了低一等的存在。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作為封建男權家長制代表的陳老爺就是凝視的主體,他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娶了四房姨太,將女性視為自己的所有物,如收藏家一般,這四方姨太都各自擁有不同的身份,體現了陳府中女性身份的多元性。大太太名叫毓如,是陳老爺明媒正娶的千金小姐,又生育了大少爺飛浦,頌蓮初見她時自語道“她該有一百歲了吧”,作為陳老爺的發妻自然是年老色衰也不受寵愛,大姨太的身份象征著封建社會嫁娶之禮中的門當戶對,是陳老爺身份的象征,而其后的幾位姨太就不再受身份的拘束了。而姨太名叫卓云,她既沒有大姨太顯赫的身份,又沒有光鮮亮麗的姿容,她秉承著“母憑子貴”這一信條于暗地里迫害三姨太,自己費盡心思卻只生了女兒,是典型的笑里藏刀。三姨太梅珊是戲子出身,擁有姣好的面容,她敢愛敢恨、敢作敢為,具有反叛精神和追求自由的勇氣,也是府中唯一一個敢對陳老爺說“老娘不愿意”的女人,但也似乎是這種潑辣如同烈火一般的性子使她深得陳老爺的寵愛。而四姨太,也就是影片的女主人公頌蓮,她是一名學生,雖然大學只讀了一年,卻代表著接受過新文化、新教育的新女性。四房姨太代表當時社會中女性身份的多元性,陳府就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而作為陳府大家長的陳老爺就是這些姨太們的主人,享有至高的地位和權利,甚至能決定這些女人的生死。
影片中當凝視主體——陳老爺在審視自己的姨太時往往帶有一種權威性,這是由于整個封建社會以男性為尊的傳統文化所影響的,此外這種凝視還帶有一種隱秘的性暗示,即影片中最常出現的“捶腳”,每當陳老爺決定今晚去哪位姨太院中休息時,都會提前有婆子為姨太捶腳,腳在陳老爺看來對于一個女人尤為重要,他說“女人的腳最要緊,腳調理順了就什么都順了,也就更會伺候男人了”,表面上看“捶腳”是老爺出于對姨太們身體健康考慮的一種福利,但這種福利只有被“點燈”的姨太才有,而且“捶腳”的重點在于“更會伺候男人了”,其中暗含的寓意不言而喻。實際上,“腳”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對于女性有更深層的含義,與“腳”相關聯的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裹腳”行為。自商朝時就傳有妲己裹腳一說,一直到北宋以前典籍中均有記載關于古代女子裹腳的行為,但彼時還沒有跟女性的身份地位有牽連,直至北宋時裹腳之風盛行,人們崇尚小腳,即“三寸金蓮”,這實際上是宋明理學重建傳統禮教秩序禁錮女性的行為,是男性話語權力下女性美的畸形塑造。三從四德、節烈等封建禮教倫常壓迫女性使之成為身份地位卑于男性的存在,更是男性把玩的對象,清代方絢的《香蓮品藻》中甚至將女子的小腳分為“五式九品”,品論其優劣,這種對于“小腳”的把玩實則體現了封建男權思想的呈現和低級的審美趣味,于是使“小腳”成為了一種隱喻的性暗示。在影片中“腳”的地位如此特殊,聯系封建時代女性傳統的“裹腳”行為,其中的性含義不言而喻。“腳”作為女性身體的一部分,在影片中以一種獨特的文化含義表現出來,用以彰顯凝視者的主體性和權威性,使得被凝視的女性被物化,以滿足凝視者的癖好,而這四房姨太所代表的時代中不同身份的女性,被凝視者收藏,如同所有物一般的心態也是其主體性的彰顯。
二、凝視中的隱喻建構
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導演會通過各種隱喻的暗示進行對社會現實的一種鏡像呈現,觀眾在凝視的過程中了解導演的意圖,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導演的創作產生共鳴,從中獲取自身需要的,選擇自身想要了解的東西。在《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影片中張藝謀導演就運用各種元素進行暗示,無論是鏡頭、臺詞、場景,還是色彩等等,都在不斷向觀眾傳達各種信息。如陳府是整個影片中最主要的場景,也是整個故事發生的地點,陳府作為一個符號、一個標志,亦名“陳腐”,帶有張藝謀導演一貫的隱喻風格,暗示著整個封建社會的腐朽與落后。影片中的陳府一眼望去漆黑又幽深,厚重老舊的院墻給人以壓迫沉重之感,而進入陳府的影壁上古老的文字如一個個符咒一般,將整個院子封印起來,顯得氣氣沉沉,特別是陳老爺的四房姨太,每個姨太所居住的院落都是劃分成一個四四方方的狹小空間,而這四房姨太守在自己的院落中就好似“人”在“口”中,組合成一個“囚字”,這些無法選擇自己的女人就好似被陳老爺所豢養的囚犯一般,在這個陳舊破敗的環境里不得自由。
又如陳府中的管家介紹自己所說的“我叫陳百順”,百順就是百依百順,意思是在這個陳府中所有人都得對陳老爺百依百順,這就是府中生存的規矩,一旦違背了這個規定就會有凄慘的下場,這也暗示封建家長制的權威不容侵犯,是一種極其腐朽的體現,是整個陳腐的封建制度的一種鏡像呈現。陳老爺是這個陳府里的統治者,在影片中他從未露過正臉,通常都是以一種模糊的的形象出現。在陳府中他自比于帝王,妻妾和丫鬟都會為了得到他的寵幸而爭風吃醋,更甚于陳老爺每次傍晚歸家,各房姨太都得候在各自的院前“聽招呼”,以便由陳老爺決定今晚點誰的燈,以“點燈”的形式彰顯自己對女性的恩寵和至高無上的掌控,在陳老爺面前這些女人們就像是玩物一般揮之即來、揮之則去,全然以老爺一人的喜怒決定命運。陳老爺雖然以模糊的形象示人,但其在陳府中的影響無處不在,這就象征著整個封建文化的影響之大,在無形之間禁錮著人性,決定著人的命運和生死,是整個封建社會深遠影響的一種表現。
三、女性自我意識的缺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身份地位并不高,甚至僅是被當做男性傳宗接代的工具,在這種封建男權社會的背景下,女性并沒有話語權,其存在是為了彰顯男性的權威,這種不平等自古有之,古時社會以“三從四德”為道德規范和社會準則來約束已婚女子的言行,更是將“三綱五常”視為天理成為約束人們的桎梏,其中的“夫為妻綱”更是將女性變成了男性的附屬品,男權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縱然是在文明開化、提倡女權的今天,仍然有壓迫女性的地區和事件存在。在這樣的歷史淵源之下,蘇童把對封建思想中一夫多妻制的不滿發泄到了《妻妾成群》這部小說中,而張藝謀又將其以影視化的呈現方式拍攝成電影,以女性為塑造對象是張藝謀的一貫風格,如他自己所說:“寫女性面對壓力,更能說明社會問題,因為女性承受的東西更多一點。從全人類的社會分工來看,男人做一件事可能會容易一些,而女人要做一件事就很難。”[2]這就是張藝謀作為一個導演的人文關}不。
起初頌蓮并無心于妻妾之間的暗流涌動,未經世事的她也未能看清二姨太卓云偽善的面目,也不理解府里“點燈”和“捶腳”的規矩意味著什么。后來當頌蓮開始慢慢意識到“點燈”和“捶腳”的好處時,意味著她開始受到了性本能的驅使,本能欲望驅使頌蓮去討好陳老爺,以便得到“捶腳”的權利并加入到了妻妾之間的明爭暗斗中并做出了“假孕爭寵”這種與其文化女性身份截然相反的做法。隨著府里的生活越久,頌蓮的內心也慢慢被蠶食,隨著她衣飾顏色的逐漸加深,暗示她變得和這府里的人一樣開始依附于陳老爺,彼時的她意識到自己只有獲得老爺的寵愛才能在府里活下去。但是當假孕事發后頌蓮被封燈,她記恨告密的雁兒,揭發了雁兒私藏燈籠、私點燈籠的行為并罰她跪在院中的雪地里,最后導致了雁兒的死亡。此外,頌蓮在一次醉酒后說出了三姨太梅珊和高醫生的私情,導致了梅珊被陳老爺處死。可以說,雁兒的死是由頌蓮直接造成的,而梅珊的死也是間接由頌蓮所造成的,在陳府里生活久了的頌蓮失去了自我變成了一個殺人兇手,她做了太多的荒唐事。陳府就是封建的社會的象征,暗示了封建社會蠶食壓迫人性,更是使女性受到了迫害。
“人跟鬼就差一口氣,人就是鬼,鬼就是人”,這是頌蓮失寵后在樓頂和三姨太梅珊說的話,這既是頌蓮的心里話,也是導演所要表達的:在這個代表著封建舊社會的陳府中人和鬼都沒有差別,這是府里每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時代所造就的悲劇。頌蓮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原本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但縱使她接受了新文化,卻沒有被新思想所改造,骨子里仍然是一個帶有封建思想的舊女性,而她的悲劇性就在于她自我價值喪失、自我意識模糊,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應具備的獨立的人格。“人的自我覺醒”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封建時代背景下人的自我被壓抑、個性被束縛,特別是封建男權下的女性更是喪失自我,甚至是意識不到自我,所以追求自我的覺醒才顯得尤為重要。
《大紅燈籠高高掛》揭示了在男權主義社會中女性的被動與無奈,在這種封建制度之下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才能求得生存,就好比頌蓮嫁人前依附于父親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當家庭出現變故以后嫁了人又依附于陳老爺,這種對女性的極不平等是時代和社會的悲劇,最后只有當影片中的頌蓮瘋了才能說出這個社會的丑陋和真相。而影片最后陳府又迎來了第五位姨太,又是一年的夏天,似乎預示著又是一輪悲劇即將上演,就如同大太太初見頌蓮時說的“罪過,罪過”。影片中出現過“夏”、“秋”、“冬”三季,唯獨沒有出現過“春”,是因為導演說過這些女人的生命中沒有春天。影片的表達彰顯了導演的態度和意圖,張藝謀導演將特定歷史背景之下女性的悲慘命運進行細致的描繪,更是借助頌蓮之口對壓迫人性的現實表達不滿,具有深刻的人文內涵和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1][法]拉康.凝視的大對體[M].選自吳瓊主編.視覺文化的奇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m版社,2005(25)
[2]孫翠玉.“女性范例”:“消費社會”意識形態的女性規訓——布希亞思想的女權主義探微[J].北方論從.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