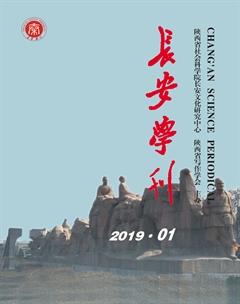試析沈宋貶謫詩歌的故鄉情結
陸丹
摘要:沈宋作為初唐時期貶謫文人的典性代表,其詩作表現出濃厚的故鄉情結,本文意在解析沈宋從現實家園的瓦解到理想家園的構建之心路歷程,探析其故鄉情結的深刻內涵和文化意蘊。
關鍵詞:貶謫 沈宋 家園情結
文章編號: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114 - 02
“故鄉情結”作為文學的母題,古已有之,是受宗法觀念與儒家思想影響,文人形成的精神歸屬和情感歸屬。這一情結蘊含著古代文人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經歷,以及建立在地緣與血緣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的鄉戀之情。沈宋生活在貶謫制度日趨嚴酷的唐代,“故鄉情結”成為沈宋的貶謫與詩歌的主線,貫穿他們貶謫命運的始終。
一、沈宋故鄉情結產生的原因一現實家園的瓦解
(一)貶謫之悲一政治理想的破滅
沈宋南貶之故在《舊唐書》上有所記載“坐臟配流領表”(《舊唐書》卷一九〇)。“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舊唐書》卷一九〇)從記載的文獻資料看來,此二人皆被貶謫至蠻荒之地即嶺南。唐代嶺南地遠,環境惡劣各方面都極為落后,成為流貶罪臣的重鎮之一,因此,有著“四罪地…瘴癘地…蠻荒““文身國”等稱謂。可謂是“凡人蠻荒之地者,多為貶謫、淪落之人”。由此,“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宋之問《度大庾嶺》)是貶謫詩人對故園的深情回望,蘊含著的萬般眷戀之情。又如宋之問《早發韶州》“故園長在目,魂去不須招。”
(二)異域之殤——對異域的畏懼、不適
沈宋跨越時空情境,置身異域卻難以適應由此滋生故園之思。自然環境惡劣,“瘧瘴因茲苦,窮愁益復迷。”(沈儉期在《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炎蒸連曉夕,瘴癘滿冬秋。”(沈儉期《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游》)沈儉期《入鬼門關》詩云:“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面對瘴癘之地,沈宋“畏南”“畏途”“盼歸”心理亦不足為奇,如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儉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所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沈宋除了對瘴氣的書寫之外,亦有對毒物以及險境的書寫如“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宋之問《入瀧州江》)“馳波如電騰,激石似雷落。”(沈侄期《自樂昌溯流至白石嶺下行人州》)或是對異域奇山險水真實書寫,或是采用夸張地手法,將嶺南妖魔化以抒發內心的憤懣,對于中原文人而言,異質的嶺南即為異域之殤。
文化氛圍亦如此,有別于帝京的飲食習慣、方言俚語等的隔閡勢必會產生疏離感和陌生感。沈宋南貶謫居異域自然與異域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氛圍格格不入,自稱“犧惶客”“投荒客”“巖棲客”,此外,詩作常采用比對的手法,贊揚故鄉,貶低異鄉。“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沈侄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表現出對昔日故鄉的深切眷戀,如“始安繁華舊風俗,帳飲傾城沸江曲”(宋之問《桂州三月三日》)表現根深蒂固的故鄉情結,對異鄉的情感終究沒有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如“魑魅天邊國,窮愁海上城”(宋之問《發藤州》)“代業京華里,遠投魑魅鄉”(宋之問《桂州三月三》)“魑魅(鄉)”的稱謂,對異域充斥著鄙夷和不屑,缺乏認同感。
(三)生命之嘆——對生命短暫的憂懼
貶謫之悲與異域之殤的交匯致使沈宋的生命觀導向悲情的基調,丹心江北死,白發嶺南生。”(宋之問《發藤州》)詩作中融入詩人對生命體征的感悟和體認,“丹心”與“白發”,反差劇烈的比對中折射出詩人所經歷的現實周遭,生發理想家園的破滅而生命飄忽易逝之感。回歸成了詩人最后的訴求和期盼如“歸心不可見,白發重相催”。宋之問《登粵王臺》,“鬢發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宋之問《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別”與“離”的現實周遭使詩人陷入無盡愁思中,從而引申對人生短暫易逝感喟“自從別京洛,頹鬢與衰顏。”(沈儉期《入鬼門關》),“別離頻破月,容鬢驟催年。”(沈儉期《度安海人龍編》)悲嘆生命之短暫的詩篇不勝枚舉。望越心初切,思秦鬢已斑。宋之問《登北固山》除了衰老,還有疾病的侵襲:“夜則忍饑臥,朝則抱病走。”(沈儉期《初達罐州》)沈宋的詩作不乏表現對生命的憂患。
二沈宋“故鄉情結”的表現
(一)對政治理想渴望
貶,即貶謫,《說文》:“貶,損也。”“謫,罰也。”遭受貶謫便成為逐臣的身份,這是政治理想挫敗,仕途失意的表征,亦意味著悲情的命運的降臨。由此觀之,貶謫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封建專制下的權力爭奪都帶有血腥的味道,“流落蠻荒”被定義為政治失意亦或是人生的失敗也罷,最終將會導向不可抗拒的生命悲劇。另一方面,深受儒家的人世意識熏陶的詩人即便身處逆境,仍舊胸懷家國之志,忠君報國的思想未曾動搖,“放逐還國都”沈宋就是很好的說明:“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沈儉期《初達驩州》)從貶謫詩人對“赦書”“洛陽酒”的期盼可見,詩人對理想家園的渴望,忠君戀闕的情懷厚重而綿長,“兩地江山萬余里,何時重謁圣明君。”(沈儉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拋除兩地之遙,表現一心盼歸的回歸意識。
此外,在表達對政治理想等家國意識的詩作中,常常將屈賈作為詠懷的對象,同為貶謫文人,皆懷有家國之思,生命之共感亦相通,更能引發共鳴。“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宋之問《登粵王臺》“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宋之問《度大庾嶺》。
(二)對至親摯友的懷戀
貶謫意味著“別”與“離”,告別生活在這片故土上的建立關于地緣血緣的親友,“兄弟遠淪居,妻子成異域。”(宋之問《早發大庾嶺》)“死生離骨肉,榮辱間朋游。(沈儉期《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攜。”宋之問《發端州初入西江》沈儉期《度安海入龍編》《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亦表現出對親友的眷戀和不舍。
此外,懷戀親友的情感在節日來臨之時,尤為強烈。宋之問《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貶謫道中恰逢寒食節,內心的孤寂、慘怛充斥每一個思歸之人,詩人臨江眺望,渴望再看看昔日的鄉友、至親,想到自己逐臣的身份欲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實屬不易。逢佳節,倍思親。又如沈儉期的《嶺表逢寒食》:“嶺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沈儉期的《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宋之問《寒食江州滿塘驛》等諸篇,皆是表達在時空轉化對比中,故鄉之思。
三、理想家園的構建一實現精神返鄉
現實家園的缺失使詩人被迫踏上歷險至遠之路,沈宋的詩歌中不乏“南”、“北”,的對舉,南北異質的空間意識意在說明鄉路之遙,,動輒萬里、千萬里。欲歸無望的詩人作為政治失意者,以政治“囚徒”的身份謫居蠻煙瘴雨的嶺南,唯有從詩歌創作和佛蘊禪思尋找生命的慰藉和寄托。
(一)托諸文字成就文學之不朽
屈賈為早期貶謫文人的典型代表,完美詮釋了文人貶滴,常形諸歌吟。貶滴的重壓下,文人內心極具苦悶的愁緒,個體生命無所皈依,欲歸無望苦悶等將沈宋推向絕望的深淵。欲擺脫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途徑以尋得精神慰藉與心理補償,唯有寄情創作。沈宋的艱難的境遇使其掀起了情感的波瀾,“發憤抒情”成了他們消解悲情的途徑。
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提到“詩窮后工”非詩能窮人,而是詩人在遭仕途失意,歷經磨難的境遇下,發而為詩,將滿腔的憂憤寄寓于詩歌并將獨特的生命體驗融于其中。沈宋亦如此“之問再被竄謫,途徑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①明代郝玉麟《廣東通志》:“唐詩之興,始自杜審言與沈宋倡為律師,而沈言之孫甫稱大家……至于咸通以后,其衰極矣。一代名家,始終寓跡,多在五嶺三江間,他幫所無也。”②沈宋的的貶謫詩歌在情感內容、創作水平上有著顯著的提高,迸發出強有力的力量,為人稱道。
(二)超越苦難的佛禪觀照
唐代“三教合流”的社會風氣下,沈宋貶謫前與佛禪有一定淵源,據文獻記載,二人長安生活中有著僧人往來以及誦讀佛經佛典之經歷,沈宋南貶之行親近佛禪便不足為奇了“影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宋之問《游韶州廣界寺》)。
“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參”(沈儉期《九真山凈居寺謁無礙上人》)值得一提的是佛禪與山水的融合便成為貶謫詩人消釋憂慮的途徑。如宋之問《宿清遠峽山寺》詩云:“香岫懸金剎,飛泉屆石門。空山唯習靜,中夜寂無喧。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寥寥隔塵市,何異武陵源。”③
此詩體現禪宗追求寂靜之境,展現寥寥空宇中遠離喧囂的圖景,亦是詩人空靈心境的真實寫照。這其間的佛教意蘊,正如禪宗所倡導的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空靈山水之境亦是消釋心中郁結的圣地,置身異域奇山秀水中,洗滌塵念,從中獲得解脫。貶謫之殤在佛韻禪思的觀照下,起著消釋之效。“山空聞斗象,江靜見游犀。”(沈儉期《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山空”“空山”亦是空靈禪境“彌覺靜者安”的深刻體悟以及“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宋之問《游韶州廣界寺》)隨緣自適的審美襟懷。
四、結語
沈宋的家園情結蘊含復雜而又矛盾的情感,現實家園的瓦解到理想家園的追尋,轉向文章事業與佛蘊禪思以消釋貶謫之殤,實現精神返鄉,這是對早期貶謫文人屈原以自殺的方式來抵抗悲劇命運的超越。因此,貫穿沈宋的貶謫生涯的故鄉情結具有超越性。
注釋:
①《舊唐書·宋之問傳》,
②(清)郝玉麟:《廣東通志》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唐]沈儉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理校注;《沈儉期宋之問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年版卷二第83頁
參考文獻:
[1][唐]沈儉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瑾校注;《沈儉期宋之問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
[2]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